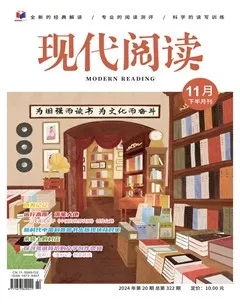探寻荒诞背后的文学创作逻辑
2024-10-30李小军







《促织》和《变形记》是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必修下册第六单元的两篇联读课文。该单元属于新课标规定的“文学阅读与写作”任务群,是高中阶段第一次集中开展关于小说这一体裁的学习任务。其单元人文主题侧重“观察与批判”,要求“领会作家对社会现实和人生世相的深刻洞察,拓宽视野,体会其对旧世界、丑恶事物的批判意识;学会观察社会生活,思考人生问题,增强对社会的认识;提升审美情趣和审美品位。”
从单元篇目的编排来看,两篇小说归属一课,是基于两篇小说在内容上都写了人化为虫的故事,体现了作家在“变形”中对社会的深刻思考与批判。在学习这两篇课文时,我们务必要深入到文学虚构的边界和创作逻辑的层面,只有理解了“变形”这种看似荒诞的表达背后的深层逻辑,进而把握荒诞类文学作品的创作规律,才能真正提升阅读素养。对于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表达形式多么荒诞,其背后定有一套内在逻辑支撑,而正是这种内在逻辑的存在,让荒诞更真切地逼近真实,甚至超越现实。
基于课标和教材的要求,根据创意读写的原则,我们开启了这趟探寻之旅。本文设计了三组探究活动,通过文本细读、梳理探究来逐步走进作者的创作理念深处。
荒诞背后的第一层逻辑:生活逻辑
探究活动:《促织》中的成名之子“魂化促织”时是九岁,请问可不可以是三岁或者十九岁,为什么?
当代作家毕飞宇在评价《促织》时说:“《促织》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吏’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虽未免有过誉之嫌,但《促织》情节逻辑之谨严、细节刻画之生动,从“成名子九岁”就可以窥见一斑。所以我们从这个人物的年龄设置开始进入文本,目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领会作者于创作中对生活逻辑的遵循。如果是三岁,成名之子也许会因为好奇,犯“窃发盆”这样的错误,但是三岁的孩子还没有形成强烈的畏惧心理,在母亲的斥责“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后,绝不会因为害怕而投井自杀。退一步说,即使他投井自杀,对于一个三岁的孩子来说,概不会出于愧怍而想到要魂化促织,拯救家庭,帮助家庭实现逆袭。如果是十九岁呢?已经成年的成名之子,根本不会犯“窃发盆”的错误,而是会和父亲一样到处寻觅促织,帮助家庭脱困。
因此,蒲松龄将主人公的年龄设置为九岁,正是基于九岁孩童的真实心理特点:第一,有好奇心,所以才会“窃发盆”窥探促织;第二,有畏惧心,所以才会因为惧怕父亲的责备,投井而死;第三,有愧怍心,所以才会通过魂化促织来帮助家庭。这真是太精妙了!正是这样的细节处理,让这个荒诞的故事具有了生活真实感,让我们置身故事中,与作品中的人物一起悲哭喜乐。
另外,从情节发展的角度来看,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说:“故事是关于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一个个事件的叙述。情节强调的是事件之间要有因果关系。一个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这是故事。国王死了,然后王后因哀伤而死。这则是情节。”
我们从“成名子九岁”出发,来梳理《促织》的情节因果线:
可见,“成名子九岁”就是这个故事内在逻辑的发动机,推动了整个故事如一列火车向前奔驰而去,让整个故事真实可信,环环相扣,逻辑严谨,产生了持久的艺术魅力。这就是荒诞背后的第一层文学创作逻辑:生活逻辑,指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虚构要符合现实生活中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不是胡编滥造。正如毕飞宇所说:“在小说里头,即使你选择了传奇,它和日常的常识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不顾常识,一味追求传奇,小说的味道就会大受影响。”
而这样的生活逻辑在《变形记》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变形记》中,在格里高尔变形前后一家人的态度变化,格里高尔的心理活动、与家人的语言交流等,都是具体的生活细节,体现了作品中的生活逻辑。但如果小说仅仅只有生活逻辑,那就不能称其为小说,而有可能成为通讯报道了。《变形记》除了生活逻辑之外,还有另外一层逻辑:让故事成为故事,让“大甲虫”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艺术形象。
荒诞背后的第二层逻辑:艺术逻辑
探究活动:格里高尔为什么要变成大甲虫,而不是其他小动物(如狗、猫、猪……)?根据文中内容,分别概括格里高尔与大甲虫的相同点。
首先,格里高尔为什么不能变成小猫或小狗?学生们通过交流讨论,发现大甲虫和猫狗在文学欣赏上的区别:猫狗是身形可爱,招人喜欢的;猫狗是行动敏捷,来去自如的;猫狗是有家养价值的,而大甲虫全然不具备这些特点。
其次,大甲虫与格里高尔的生存状态是相匹配的。学生讨论明确了大甲虫的形象特点与格里高尔生存状态之间的相通性,归纳如下:
由此说明,作者在构思让格里高尔变成什么时,充分遵循了这一艺术形象的内在逻辑,格里高尔不能成为猫、狗、猪,因为这些动物的艺术特征不能反映出格里高尔的生存处境,所以格里高尔只能成为“大甲虫”,只有甲虫才能深刻地反映格里高尔在社会和家庭重压下得不到片刻喘息的生存状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让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甲虫属于有翅目生物,应该是“会飞”的,可是《变形记》中的大甲虫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硬壳下面有翅膀,当然也不能通过“飞走”来解决问题,这就是作者艺术匠心所在。这构成荒诞背后的第二层逻辑:艺术逻辑,即小说家的任何创造必须符合艺术想象、艺术隐喻、艺术形象、情节运行等内在规律。
有了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的支撑,一个荒诞故事就能够让读者接受,并且读者能够在艺术家营造的荒诞世界中读出生活的真实、生命的现状、社会的侧面。但是伟大的作家远远不满足于此,他们要用荒诞的方式表达比真实更深刻的东西,于是我们继续探究其第三层逻辑。
荒诞背后的第三层逻辑:思想逻辑
探究活动:为什么《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了“大”甲虫,而《促织》中的成名之子是变成了“小”促织,一“大”一“小”分别有着怎样的寓意?
试想,能否让“促织”变成“大促织”,而让“甲虫”变成“小甲虫”?这显然是不行的。那么作者的用意是什么?这就要联系作家各自的思想、风格以及所处的社会背景等来理解,走进作家的思想世界。
“大”与“小”在此处显然不是简单的昆虫外形的展示,而是作家思想表达的需要。卡夫卡通过甲虫之“大”,使作品凸显出十分荒诞而不可思议的基调,讽刺了资本主义社会对底层个人“个体性”与自我意识的扭曲与异化。是残酷的社会生活让格里高尔异化成了一只甲虫,丧失了劳动力,被家人厌弃而孤独死去,反映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制度下世人奉行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泯灭人性,让人沦为了工具,意识不到自我的存在,最终被社会倾轧变形,走向毁灭的社会现实。《变形记》的格里高尔与《促织》中成名之子的文学形象具有高度相似性。蒲松龄通过描写成名一家“以征蠹贫,以儿化促织富”的辛酸沉浮,深刻揭示了17世纪末为政者贪婪凶残、横征暴敛的罪恶,讽刺了明末清初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朽。促织之“小”,正是苛政之下普通百姓受尽欺凌迫害、生命泯于尘埃的悲惨现实的深刻展现,寄托了蒲松龄对社会现实的洞察批判与对底层群众的深切同情。
《促织》与《变形记》中人的“异化”,体现了蒲松龄、卡夫卡超脱自身时代的、对人文精神的清醒认知。这就是两位作者思想的伟大之处,也是我们探讨的荒诞背后的第三层逻辑:思想逻辑,即作者在创作过程中,通过文字所传达的深层次的对现实世界的哲理性认知。每一个伟大的作家都是将自己的思想逻辑性地融入到故事架构和角色塑造中。思想逻辑使作者不仅仅关注故事的表面情节,更着眼于通过故事来探讨社会的复杂议题,并尝试给出自己的理解和解答。
通过这样的创意联读,我们把握了鉴赏荒诞类型艺术作品的一种思维路径和阅读方法,那就是无论多么荒诞的故事,其背后都必须要有生活逻辑、艺术逻辑、思想逻辑的支撑,这样的荒诞才能以艺术的方式更加逼近“真实”,才能成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艺术比现实更加真实。正如毕飞宇所讲:“文学需要想象,想象需要勇气,想象无论多么遥远,也有边界。无边的是作家所要面对的问题和源源不断的现实。”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