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人之窝》与“晚期风格”写作
2024-10-27范科苑
摘要:陆文夫199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人之窝》,无疑是其晚年文学反思与文学探索的一项重要成果。学界涉及陆文夫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向来注目于《美食家》《小巷深处》等在当时引起轰动的小说或经典文本,有关《人之窝》的反响至今寥寥。这部长篇小说被湮没在时间长河中,尚未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足够了解与认同。本文围绕《人之窝》文本内外的诸种因素,从作品本身、外界批评、作家主体角度切入,对当代文学史上被遮蔽、被遗忘的这部长篇小说进行再挖掘,试图打开重新理解“晚年”陆文夫的思路及意义空间。
关键词:陆文夫;《人之窝》;文学批评;晚期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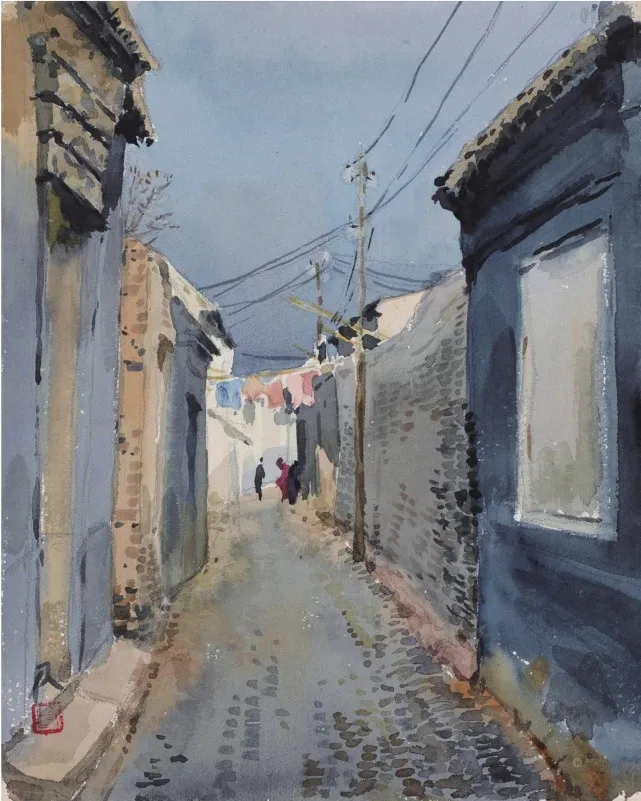
作为当代文坛中“小巷文学”的开拓者,陆文夫素以中短篇小说饮誉文坛,以《献身》《小贩世家》《围墙》《清高》四度捧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以《美食家》斩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95年,长篇小说《人之窝》付梓问世,最初刊于《小说界》,同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作为陆文夫毕生发表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①,《人之窝》在其创作生涯中的独特性地位自然毋庸置疑。这也是他晚年的苦心孤诣之作,67岁完成的毕生最后一部小说作品。对于这部呕心沥血多年的鸿篇,陆文夫在完成时如释重负:“这部长篇小说我早就想写了,可谓酝酿已久。”[1]《人之窝》通过人与住房的关系联结起解放前后的两个时代,映照出深广的历史内涵和社会内容,可谓角度新颖、涵义幽微。然而,隔着近30年回望,《人之窝》在文坛上反响平平,并未泛起太大水花。在陆文夫的作品中,从影响力来看,凝结日常饮食之道的《美食家》,一经发表即产生轰动效应,被视为代表其创作实绩的标志性文本,价值得到充分肯定:“《美食家》是陆文夫创作道路上的一块丰碑,是陆文夫迄今所达到的最高成绩。”[2]“《美食家》是可以传下去的。”[3]在陆文夫的其他作品中,《小巷深处》是在社会上知名度甚高的成名作,《小贩世家》作为新时期颇负盛名的短篇小说广受好评,《围墙》由于当时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公开推荐,引起全国舆论关注。而《人之窝》,看起来不温不火,“似乎反响也不够强烈”[4],“并没有太大影响”[5]。为何这部小说湮没无闻,被忽视的真正症结何在?它在相关评论和阐释中的命运如何,与作家创作道路存在怎样的关系?本文试图围绕《人之窝》文本内外的诸种因素,探讨上述一系列问题。
一、文本内部:从《人之窝》本身说起
如果对陆文夫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纵的总览,可以发现,1986年以后,由于有着专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规划,他明显放缓了写作节奏,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除发表《清高》《故事法》《享福》寥寥三个中短篇小说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小说问世。1995年5月,《人之窝》这部“十年磨一剑”之作终于完稿。或许是从中短篇小说领域转向长篇小说写作的缘故,在结构上,陆文夫选择以多个短篇拼接缀连的章节形式来铺陈叙事。小说通篇以苏州“许家大院”为叙事舞台,上部以20世纪40年代末为始,在时代暗涌下的生活皱褶内,演绎一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命运。许家后裔许达伟为了实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民主思想,主动共享出自家大院请青年学子同住,企图组织一个平等的“小社会”,对“大社会”作出精神意义上的逃离。然而“房子可避风雨,却也是罪恶的渊薮”[6],当“我”和同窗好友唱着青春之歌住进大院时,也被动地卷入房子的保与夺之下街坊邻里间的暗斗明争,“抢房”风潮致使本就气数将尽的大院四分五裂。解放前夕青年们为求避祸,被迫撤离这个“窝”而风云流散。下部的历史时空定位在“文革”初期,以“我”重返故地——许家大院的所见所感为伏线,小说叙事属意强化“文革”中“小巷”内的派别纠纷,创新性地展现了各色人等在政治斗争中对房产的占有权和支配权所导致的暗箱争夺。投机者诸如万青田、吴子宽之流对大院的觊觎,女佣胡妈、胖阿嫂的拱火,汪永富为抢房而进行的“窝里斗”等,融喜剧、悲剧、闹剧色彩于一体。小说收尾在插队落户的时代大潮中,大院内多数人都被勒令离城下乡,再次在政治风暴中辗转流离。
就内容与风格而言,《人之窝》保持着陆文夫式的“糖醋现实主义”、幽默感、苏州味、凝练含蓄的固有特质。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巷凡人”的写作观念,对民间社会和世俗本相的深度介入,在这一长篇中仍有强劲体现。仅就叙事层面而言,小说整个叙述视点就是作为寄居者的“我”对时代风云中许家大院的审视性叙述。“我”站在时代更迭的轴心,见证了大院中以争夺房产为主的人际纠葛,串联起各色房客的遭际和前远巷半个世纪的历史变迁。经由第一人称介入式叙述,人物内视角与叙述人外视角交替出现。类似的叙事模式,可追溯至陆文夫1983年发表的《美食家》,同样以寄居有产者之家的“我”(高小庭)的视角介入,追踪朱自冶几十年的饮食消费史,由此发出深刻的时代追问,达成历史反思意味。而就人物塑造而言,许达伟与落难小妾柳梅的爱情,又颇有早期作品《小巷深处》中张俊和徐文霞的影子,知识分子与寡妇、妓女克服身份阶层差异、告别旧日阴影走向新生的模式,隐含了对政治文化空间之外纯粹爱情的共性叙事。由此,可以说《人之窝》在文本演绎上,与先前的创作风格构成了显豁的承袭关系。作家凝集和调用已有的写作经验和叙事资源,在写作意志上表现出强大的自我复制性,这就使得《人之窝》成为确切意义上的集大成之作。
在与以往文本保持呼应的同时,《人之窝》也另辟苍穹,呈现出了有别于之前创作的新质。当人们依旧沉浸于“小巷文学”近乎类型化的风格特征时,事实上,陆文夫已经以相当自觉的“探求”企图,将视野放到了更广阔的空间。《人之窝》以大宅院、大家族为叙事场域,在个人史、家族史、民族史三者的交汇点上承载宏阔信息,这是陆文夫之前的小说中几乎不曾涉及的。社会历史、政治迷局、代际纠葛、人性欲望,全部杂糅进一方大院内加以呈现。小说在时代政治意指的框架内,以批判眼光审视市民文化特征的弊端和弱点,同时对人情之美、纯粹情感等日常生活的正面价值给予肯定,保留了些许开放的弹性。
对于《人之窝》,陆文夫这样为自己的创作定位:“我写小说欢喜开宗明义,欢喜把话说在前头。《人之窝》也是如此,一开头就把‘创作动机’坦陈于读者的面前。”[7]小说是这样起笔的:“有一点无可置疑,我们高贵的祖先是没有房子的,他们或是盘在树上,或是钻进洞里,倒也省力。不过,上树或钻洞总是不大舒服,也非长久之计……于是,亿万年间人类为了房子便进行着惊心动魄、无声无息的世界大战。”[8]这显然亦庄亦谐,以一种幽默诙谐的笔调渲染出暗讽之味。不仅开头“开宗明义”,《人之窝》在标题命名上,也直截了当,具有极明晰的叙事指向。“窝”(居所、房屋)是一己容身之处,是人生存的必要空间。陆文夫小说以物象命题较多,典型如《围墙》《门铃》《井》《圈套》,皆捕捉生活中某种特定物象形态,作为阐释整部作品寓意的切口,寄寓不同层面的深刻含义。而《人之窝》中的“窝”——“许家大院”,显然也带有某种整体性的象征意味。陆文夫不仅依托大院局势披露扭曲畸变的丑陋世态,尤为切要处在于,借“住房”之主题,对民间生存本相中包藏的理想、欲望、争斗,进行了寓言式探讨。事实上,在《人之窝》发表后时隔不久,他又写了一篇题为《安居》的随笔,透过“作家和房子的关系”,反思空间条件对写作主体的生产所构成的潜在影响:“我年轻时对住房的大小好坏几乎是没有注意……及至生儿育女,业余创作,才知道这居房的大小好坏可是个厉害的东西!”[9]关于“人之窝”的民生问题,陆文夫又获得了新层面的切身实感。
1996年,在“第三届上海市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奖”评选中,《人之窝》名列长篇组三等奖。在获得评奖制度确认与推崇的同时,这部长篇小说的不足之处也一望而知,正如评委在评语中所述:“为小人物立传。小说围绕一幢房子展开,比较真切、深入地表现了某些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从历史纵断面上开掘一点,将其辐射到社会各个角落,见出艺术功力。结构匀称,文笔精致,时有点睛之笔。整个作品显得比较成熟。有的人物形象较为扁平化,议论过多。”[10]“有的人物较为平面,议论过多”这样的微辞,直指小说人物塑造存在脸谱化、概念化的弊病。从整体而言,《人之窝》还有诸多由此而生的瑕疵与遗憾,它对小巷凡人叙事的重归、对民间栖居问题的开掘,呈现出了“有限度”的超越意义。
二、文坛回响:批评的浮光掠影与文学史上的无名
在文本本身之外,一部文学作品必须依托文学批评、文学史、意识形态等外在要素的发掘和推动,才能最终进入经典的行列,进而赢得更多读者。“实际上经典化产生在一个eb5c410c7a8eec8ac4adc6a254ac38c86591085f04d32e925bd53b1aec9e5b2d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政治等等。”[11]批评家如何看待《人之窝》,作出何种经验性的审美阐释和判断,对《人之窝》的学术价值、流传价值都可能有出乎寻常的重要影响。那么《人之窝》在文学批评场域中究竟处于怎样的状态?
在《人之窝》发表后的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涌现出10篇即时性的评论文章。批评家们各施拳脚,针对这部长篇小说的选材、风格手法、艺术蜕变、作品意义,留下了诸多有价值的观照和解读,指出了《人之窝》的两个主要特色:
一是“小巷凡人”叙事格局及其背后蕴涵的民间立场。夏一鸣1995年写就的《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和民间社会——兼评长篇小说〈人之窝〉》,立足于地域文化视角,认为陆文夫“把苏州文化的背景移植到居住文化上来”,以温和的笔调描写“抢房”风潮,显示出浓郁的民间宽容精神,作者把笔墨移情到小人物身上,所塑造的许达伟这一苏州落魄子弟,和朱自冶、徐丽莎、林南生属于同一形象类型——“在社会上永远是一群长不大的‘婴孩’”[12]。张德林同样将“为普通人、小人物‘立传’”视为理解《人之窝》内在意蕴的切口,察觉到小说幽默风格中审美感情的倾向性[13]。王鸿卿、刘刚在对《人之窝》的评析中,关注作家写作的精神意涵,探讨文本如何将诸多社会内容纳入“平民历史”中加以具体化呈现[14]。
二是“探求人性”的主题和沉郁厚重的历史叙事。相关批评文章如吴海的《审美视点:对人性深度的探寻与开掘——陆文夫长篇小说〈人之窝〉散论》,将《人之窝》与《美食家》《小巷深处》指认为“人性探索‘三部曲’”,强调陆文夫的美学视野始终没有脱离对人性本质、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审思,“把人性要求置于社会变迁之中”[15]。郑祥安以细读的方式进入小说文本,从视角和人物的角度,推敲作家如何于“小”中见出丰富,投射人生探求、历史思考的深意[16]。戴翊的短文《质朴真切的〈人之窝〉》同样围绕“作家对历史和人生的真知”[17],省察小说内里所承载的政治历史的分量。
此外,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还有其他四篇评论:范小青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瞩目于作品“浓郁的浪漫”“崇高的理想”之中“举重若轻的大手笔”[18]。60年代初就追踪陆文夫创作的评论家曾文渊,在《〈人之窝〉与精品意识》中,注意到陆文夫创作少产多思的特质,指出《人之窝》仍有抱憾之处:“大约是期望过高所致,主要是觉得后半部特别是结尾部分匆促了些”[19],对小说再版时适当续写和增补给予期许。张德祥《一部不掺水的小说——陆文夫的〈人之窝〉读识》、明照《审美象征的风景:读陆文夫长篇小说〈人之窝〉》分别对小说情节推演[20]、“窝”所具备的美学象征意涵[21]进行较为细致的爬梳与辨析。
上述10篇90年代后半期的批评和阐释文章,为《人之窝》留下一个历史研究的短镜头。可以发现,在这并不长的批评队伍里,例如夏一鸣、张德林、郑祥安、曾文渊、戴翊,都与上海关系紧密,他们或为上海杂志社、文学期刊编辑,或为上海著名文艺评论家,积极介入文学生产,参与文学创作的评价。正如陆文夫《起步在上海》中所言:“我开始走上文坛是走到上海去的。”[22]由于这种和上海文艺界、出版界的终身联系和密切来往,当地评论家们追踪他的新作动态并先后撰文评述,关注程度自不待言。遗憾的是,从上述为数不多的10篇时评来看,这些文章大多给人留下随感的印象,留下的只是小范围内对这一长篇小说的框架式看法,并不证明评论家已在之前的学术积累上,对作家作品完成了进一步的深化讨论。由于时间距离太短,也难以沉淀出带有总结性质的成果来,这些评论仅能算是浮光掠影的介绍或评析。
关于《人之窝》的评论,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出现评论热潮之后,21世纪以来,很长时间内没有新的评论。同时,翻阅近20年间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可以发现一个现象:文学史在论述陆文夫及其创作时,往往采用五六十年代加80年代的方法,相关评述基本出现在两处,一处是“十七年文学”,《小巷深处》位列“百花文学”中一朵独树一帜的小花;另一处是80年代,《美食家》被视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小贩世家》等参与对世俗生活情态与地域风情的共同呈现,被纳入“归来者”的历史反思、“文化”韵味写作。而晚期作品《人之窝》,在文学史中“榜上无名”,或仅略附一句。如此一种情形,再次证实陆文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所决定的。而晚年长篇《人之窝》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尚未得到学术共同体的足够了解与认同。此外,倘若再联系起上述10篇时评文章来看,文学史本身也是建立在此前批评活动的基础之上的,“历史现场的文学批评所筛选的文本,成为文学史叙述首先要关注的对象”[23],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陆文夫的文坛影响力与80年代中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先锋”和“寻根”文学之后,他的创作活力逐渐削弱,影响力日渐式微,围绕他的研究也随之开始退潮,学界关于《人之窝》的反响至今寥寥。从外部要素来说,历史现场文学批评的浮光掠影或缺失,也导致《人之窝》被文学史深沉地“遗忘”了。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作品发表的时机也不能忽视。事实上,《人之窝》出版的1995年,这在当代文学史上毋庸置疑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实力派作家竞献长篇新作,长篇小说潮声盈耳、数量激增,从不同路径上显示出对个人、现实、历史的深度介入。“1995年的小说,似乎主要在长篇……阅读的期待在长篇,创作者的追求也在长篇。”②在“长篇热”创作态势之中,《长恨歌》《丰乳肥臀》《家族》《许三观卖血记》《苍天在上》等优秀小说如蜂拥般涌现。文学史在对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竞写潮进行整体性评价时,往往首先着重关注那些推崇技术、语言和叙述前卫性的新潮长篇小说,其次关注具有现实精神与社会效应的主旋律长篇小说,抑或关注影视化的长篇历史小说对中国历史的敞开及重写。在这样的视野中,《人之窝》因受艺术高度、选材角度或各种因素的限制,被其他小说的强光所遮蔽,甚至处于被忽略和边缘化的位置,成为一座沉没于当代文学史深处的矿址。
三、《人之窝》与作家“晚期风格”写作
《人之窝》完稿于1995年,这一年陆文夫67岁。从作家整个创作生涯来看,《人之窝》被研究者公认为是晚年陆文夫的着力之作,是他文学事业的夕阳晚景,且这一长篇小说创作未能尽如人意——王尧以《人之窝》为界,划分出“创作后期”,指出“晚年陆文夫是有些落寞的”[24];陈辽称自己“认真阅读了这部长篇小说,认为《人之窝》写得不算成功”,“人所共知,陆文夫从1986年起,虽然也写过《清高》等较好作品,但在小说创作上再也没有实现对1978—1985年间优秀作品的超越”[25],他还注意到,《人之窝》在一些文学奖项的评奖结果上并不圆满,1999年,陆文夫将《人之窝》申报了“茅盾文学奖”,最终未被评上;王燕论及一种现象:“有不少评论家认为,《人之窝》不是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无法匹敌同时代捭阖纵横的长篇历史小说,其自身艺术功力也没能达到《美食家》的辉煌。”[26]这些研究都关注到陆文夫“晚年”写作的特殊之处,作家的个性心理与文学选择背后蕴含着颇值得解析的一系列问题。
由“晚年”“后期”“晚境”等语词,可以使人联想到“晚期风格”这一概念。萨义德纵观近现代西方文学和音乐家的晚年创作,对一种生命进入老境的观念与风格——“晚期风格”作出阐发。他提问说:“艺术家们在其事业的晚期阶段会获得作为年龄之结果的独特的感知特质和形式吗?我们在某些晚期作品里会遇到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27]萨义德对“晚期风格”的论述比较复杂,“晚期风格”或意味着一种新的和解与静穆精神,成就圆融的智慧,或潜藏着不安宁的张力和批判性,呈现出深刻的冲突。那么,从作家个体角度看,《人之窝》究竟是“老手颓唐”还是“衰年变法”?不论是面临“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或是“不妥协、艰难和无法化解之矛盾”,是否有隐伏的自我指认或变化线索?从更广阔的视野看,这一晚年的尝试对他的意义何在?这些问题都需要解答。
讨论陆文夫的晚期风格之变及其意义,身体与年岁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进入20世纪90年代,陆文夫已逾花甲之年。面对衰老的肉体,加之多年肺病的缠绕,他在写作上的精力每况愈下,显得力不从心,“写《人之窝》最后几个章节时,整个人是趴在电脑键盘上的,一只胳膊支撑着身子,一只手敲打键盘”[28]。《人之窝》发表后,陆文夫的小说创作也就永久性地终止了,“年逾七旬,疾病缠身,精力不济,老骥伏枥,主要是休息,能写则写点儿,不能写就做一点儿写作之外、力所能及的事。”[29]他无疑知道或深信,自己已经步入自然意义上的“晚年”。
也许是“年岁”的缘故,从心态的角度看,作家也产生出诸多到了一定的“年岁”才有的感悟。参照陆文夫晚年的文字,不难体味到其中的心境和况味——晚年的他已经看清、看轻一些东西了。在《人之窝》完稿前后的1993年至1998年,陆文夫针对彼时的个人经历、文坛现象,创作出一批随笔或生活散文,其中有忧虑也有劝勉:《清高与名利》谈到那种出于个人自约的清高;《文学史也者》显示出他在晚年对文学史规律的认识,较为超然地面对文坛上的生前身后名;《静观自得》视“静观”和“自得”为写作者观察这个世界的要领;《有限》洞彻了人一生之力的“有限”:“人的生命有限,死期即谓之曰大限。”“人的学识有限,毕其一生之力也只能对某些方面懂那么一点儿。”[30]这些都是陆文夫对文坛众生包括自己身为“作家”的观察,寄寓着老者特有的沉稳思虑。晚年的陆文夫焕发出一种柔韧有力的成熟性与和解精神,“愈来愈显示了他内在阴柔、渴望美、与现实和生活妥协的高调适立场”[31],举重若轻,洞若观火。
不论是“清高”“静观自得”,还是关于“文学史”与人之“有限”,借着散文随笔疏泄情感、回归思考,这些叙述中分明带有“却顾所来径”的意味。事实上,回顾陆文夫的创作履历可知,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小巷深处》初入文坛,到60年代初因《葛师傅》等“工厂系列”而再获关注,再到80年代《美食家》抵达艺术高峰、名噪一时,在走过十来年的文学荣耀后,来到90年代,他进入生命意义上的晚年、文学事业上的晚期,所面临的显然是影响力的日渐式微和个人创作困厄的浮现。身为一个感知极为敏锐的作家,陆文夫也很快意识到了这种落差和转变,这一点,在费振钟同他的闲谈中体现得最为直接:
“我觉得,你1986年后,也就是《井》以后,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已经为数甚少,当然,你主要在准备写长篇小说《人之窝》。这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但给读者的感觉,你开始退到另外一些新锐作家的后面。而你的淡出文坛,因为有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作为铺垫,显得比较自然。或者可以这样说,你明白你的写作处境,明白90年代将会对你的写作产生新的要求和新的考验,因此你很明智地选择了自己的位置,主动淡出,站在旁观的立场,冷眼打量文坛的朝云暮雨,花开花落。
“我只是想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你说得对,我是主动淡出。‘淡出’以后,才能够有时间总结自己,反观自己。”[32]
“主动淡出”,实际上是对于自身处境的自觉意识,是晚年陆文夫的一种自我指认。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在20世纪90年代抱持一种沉默寂静的立场。曾在20世纪80年代风头无两的作家,在风云变幻、新人辈出的时代新环境里,收敛锋芒走向“退场”,并在沉静中“总结自己”,显示出一个写作者进入沉思的状态。在这一时期,陆文夫的生命经验、文化反思、审美理想逐步走向一种从容不迫的境界,进入“人情练达即文章”的老境。在《人之窝》的写作中,明显结合作家个人半世人生的世事历练和沉淀。陆文夫综合地调动毕生对历史的洞察理解,在社会变动及“文革”背景下,对抢房风潮作了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观照,不论是对于历史的认识,或是对于人、人性的认识,都提供一种不能一语道尽的复杂性,流溢出此前创作中未曾表现的气息——如果说《特别法庭》《唐巧娣翻身》《围墙》指向“新时期”意识形态下对政治官僚和教育问题的反思,《小贩世家》《美食家》《井》的表达内蕴逐渐向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演化,《毕业了》《清高》蕴含的是挥之不去的日常生活怀旧意味,那么到了《人之窝》,则是从思想意义上综合的灵魂审视和哲学观照,激荡出形而上的魅力。“窝”之内外,杂糅了房子的封闭性和开放性、社会的物质欲和精神欲、芸芸众生的迷失和救赎。陆文夫洞悉历史的创伤性结构,以“窝”为题,纾解着时代重压下个体何以找寻栖身之所的问题,而对风雨涤荡的一代应如何置放理想,则流露出无奈和彷徨。他在《人之窝》的结尾借许达伟之口极富寓意地说:“铺路,作铺路的石头,让沉重的历史的车轮从我们身上碾过去。”[33]这颇有一种老者在饱阅人生后的喟叹之感,使作品内核充满隐喻的历史张力。
进入某一特定场域,以时代氛围的可感标识勾勒小说人物脸谱,思考社会现象,这似乎构成陆文夫创作的一种恒定结构模式。事实上,《人之窝》正体现了他重拾惯常思路并加以延续和生发的自觉。然而,或许是在长年创作中养成的谨慎心理,抑或“文革”余惊尚在的反映,《人之窝》一面体现着反思历史的心理渴求,一面又将历史进行微观化处理,政治的欲望与争斗被简化为对房产的攫取,使叙事者稍显挥洒不开。在塑造以许达伟为首的知识分子群体时,陆文夫以“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情怀在他们身上植入新生与希望,却又似乎未能厘清他们在“文革”中更复杂的身份位置,因此大部分人只是“作铺路的石头”,被动地应对奸刁之徒的欺压。直至小说结尾,大院住户再次在政治潮汐中辗转流离,陷入悲剧性的轮回,而许达伟们也依旧前路漫漫,不知所往。这样开放式的收尾似言犹未尽,实则透露出作家内在的矛盾仍有增无减。浓郁的民间宽容精神,使陆文夫在此阶段所意识到的社会和历史问题,都有着一种点到为止的含蓄。《人之窝》因此也不可能在20世纪90年代日渐复杂的新阶段中,进一步丰满“文革”甚至更早时期历史的文学建构,抑或作为启示录回应新的历史阶段的文学、文化命题,提供新的思考资源。这些局限性本身,也证明陆文夫在写作困境中“未完成”的找寻。时代之“变”、个人的“欲变”与“不变”相互纠缠,终致《人之窝》成为他创作后期甚至一生文学事业的夕阳晚照。
四、结 语
作为陆文夫毕生发表的唯一一部长篇、最后一部小说作品,《人之窝》无疑是陆文夫晚年文学反思与文学探索的一项重要成果,尽管创作未能尽如人意。陆文夫已往生多年,也留下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作品,《美食家》《小巷深处》在被时间过滤后仍然可圈可点。然而,文学史在遴选、突出强调某些重要文本时,必然会舍弃、遮蔽另外一些事件和角色,“否则,其撰写的未经筛选的文学史是不能被称为文学史的,那只是资料的堆砌而已”[34]。随着时间的洗汰,《人之窝》将会或已然暗淡,但研究是没有任何边界可以约束的,在作家个案研究中,除了关注具有文学史经典化元素的文本之外,也不能遗漏掉已被置放在“文学史正典”之外的其他作品及现象。唯此,方能完整而准确地对作家文学创作的个性、成就及局限进行整体性评估,而非将作家与其成名作、代表作终生捆绑在一起诠释,作出片断式的定论。因此,对《人之窝》的再挖掘、对“晚年”陆文夫的重新理解,也牵连出文学研究如何精细观察和解剖作家个案的严肃命题。对作家作品的专论,正是在文学史主体扎实系统的研究基础之上,另建一份文学档案,将被遮蔽、被遗忘的作品现象归入其中,以补正、充实单一化、片面化的解读方式,去掉覆盖在作家或作品身上的似是而非的印象。或许这就是重评《人之窝》与“晚年”陆文夫的意义所在。
注释:
①《人之窝》是陆文夫一生中发表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但不是他创作的唯一长篇。“《人之窝》是我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前写过一个长篇小说,抄家时被抄掉了”。参见袁晓庆、汤泓:《小巷深处访大家——陆文夫访谈录》,《绿洲》1998第6期。
②此为郜元宝在给陈思和的信中,谈到的关于1995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些看法。参见陈思和:《关于长篇小说的历史意义》,《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董宁文.写自己经历过的事——访陆文夫[M]//人缘与书缘.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63.
[2]陈骏涛.重要的是对于生活的见解——陆文夫创作管窥之一[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3]李凖.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吗[N].文艺报试刊号,1985-4-20.
[4]何镇邦.望云斋说之四:文学道路上的“探求者”[J].芳草,2012(4).
[5][26]王燕.双重视角下的自在写作:陆文夫的文学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79,274.
[6][8][33]陆文夫.人之窝[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475,3,496.
[7]陆文夫.开宗明义[M]//陆文夫文集(第5卷).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353.
[9]陆文夫.安居[M]//陆文夫文集(第4卷).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36.
[10]大奖办公室,编.上海第三届(1994—1995)第四届(1996—1997)“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获奖作品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187.
[11][加拿大]斯蒂文·托托西.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马瑞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44.
[12]夏一鸣.陆文夫笔下的苏州和民间社会——兼评长篇小说《人之窝》[J].当代文坛,1995(6).
[13]张德林.为普通人、小人物“立传”──评陆文夫长篇小说《人之窝》[J].当代作家评论,1996(2).
[14]王鸿卿,刘刚.栖居与平民历史——评长篇小说《人之窝》[J].中国图书评论,1996(6).
[15]吴海.审美视点:对人性深度的探寻与开掘——陆文夫长篇小说《人之窝》散论[J].江西社会科学,1997(12).
[16]郑祥安.独特的视角 独特的人物——评陆文夫的长篇新作《人之窝》[J].社会科学,1996(7).
[17]戴翊.质朴真切的《人之窝》[N].人民日报, 1995-11-14.
[18]范小青.安得广厦千万间[J].当代作家评论,1996(2).
[19]曾文渊.《人之窝》与精品意识[J].书屋,1996(6).
[20]张德祥.一部不掺水的小说——陆文夫的《人之窝》读识[J].小说选刊,1996(5).
[21]明照.审美象征的风景:读陆文夫长篇小说《人之窝》[N].文艺报,1995(24).
[22]陆文夫.起步在上海[M]//陆文夫文集(第5卷).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330.
[23]方岩.批评史如何生产文学史——以“新时期文学十年”会议和期刊专栏为例[J].文艺争鸣,2019(6).
[24]王尧.重读陆文夫兼论80年代文学相关问题[J].南方文坛,2017(4).
[25]陈辽.我所认识的陆文夫[M]//江苏省作家协会,编.永远的陆文夫.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121.
[26][27][美]爱德华·萨义德.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M].阎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4.
[28]范小青.陆文夫二三事[M]//何镇邦,李广鼐,编.名家侧影(第2辑).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23.
[29]陆文夫.姑苏之恋[M]//陆文夫文集(第4卷).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270.
[30]陆文夫.有限[M]//陆文夫文集(第5卷).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06:336.
[31]黄文倩.在巨流中摆渡:“探求者”的文学道路与创作困境——一个台湾研究者的视野、思考与再解读[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1:254.
[32]费振钟.我要想一想——与陆文夫闲谈[J].北京文学,2001(10).
[34]丁帆.关于百年文学史入史标准的思考[J].文艺研究,2011(8).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