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荒唐的世界
2024-10-27王火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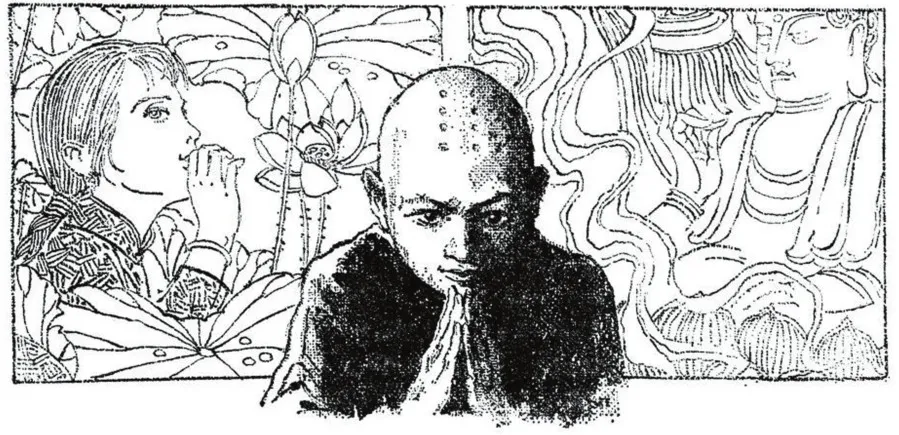
前 言
《受戒》是汪曾祺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以一种幽默的笔触写出了一个看似荒唐,细想之下却又无比真实的故事。步入社会,经过生活的磨砺后,才能真正读懂《受戒》的内核,看似是在写生活,其实是在描绘人文社会的结构。就像《西游记》,初看时那就是一部神怪小说,仔细看那是在描绘芸芸众生,当终于明白了那其实是在描绘中国社会内在的运行机理时,就已经对社会对人情世故有了深刻的理解。
《受戒》就是这样一部有着传统韵味的小说,在看似荒唐的情节背后,隐藏着的是一个再真实不过的现代社会。当你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就已经是芸芸众生的一员了。笔者深知自己水平有限,剖析这种经典之作未免有些贻笑大方,权当诸位茶余饭后消遣之作。
一、初看时,是个笑话
《受戒》很吸引人的地方是幽默风趣的表达方式,让人只看个开头就欲罢不能,很想一口气就读完全文。这呈现出一个作家的功底,一部文学作品的好坏,最简单的检验方式就是看读者是否愿意读下去。
当然,《受戒》之所以被称为汪曾祺先生的代表作之一,除了写作的方式很吸引人之外,还在于该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交代一些基础的环境信息和人物信息。这看上去很反常,因为一般的写作方式是一边推进情节一边交代人物和环境,这样小说的前半部分才不会显得过于臃肿。
汪曾祺先生在其他小说里,也喜欢用很大的篇幅去交代这些基础信息,而且交代的方式很像是听一位老先生在讲故事,并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但故事就是很好听。
认真回想一下的话,现在这样的作家已经很少了,似乎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国内作家的写作手法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没有了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感觉。当然这可能跟年龄也有关系,汪曾祺老先生出生于1920年,之后的人生几乎经历了中国最动荡又最有希望的年代。
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他重新开始创作的时候,已经是1979年,当时他已经59岁,放到现在都准备退休了。这个年龄段的作家肯定有了足够的定力,足够的技巧,再加上他的经历,形成了一种较为独特的写作风格。
所谓的“独特”是相较于现在而言,在跟鲁迅先生同时期的那代作家里,也有类似的风格,但似乎在那个动荡的时代结束后,这样的风格就越来越少见。放到现在来说,汪曾祺先生的风格是比较独特的,而且他的小说没有新文学运动的作家们那么强烈的批判性。
《受戒》里用大量篇幅交代基础信息的设计,之所以不会令人觉得臃肿和累赘,大概是因为表达方式比较幽默风趣。笔者第一次读《受戒》的时候,还在校园上学,当时感觉很有意思并印象深刻的缘由,就在于《受戒》足够风趣。
比如小说中关于和尚的描述:“他(明海)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1]
这个描述就很有意思,尤其是把“婊子”跟“和尚”放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在我们的文化里,婊子是不被主流价值观所认可的一种职业,但和尚却不同,他们给人的印象是:坐在幽静的大殿里,面对神色安然的佛祖塑像,盘着腿,敲木鱼,朗诵经文,似乎超脱于俗世。
之前的劁猪、织席子等等,那都是铺垫,就为了引出“婊子”和“和尚”。这个巨大的反差,迅速把“高高在上”的和尚,拉到了世俗的尘埃里,还形成了一个十分幽默的桥段。
最初在读完《受戒》后,笔者还希望模仿这种写作手法,但每次尝试都感觉不伦不类,完全没有这种洒脱。到很多年之后才发现,有些东西不是想模仿就能模仿得来,它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人生经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定的天赋。
很多涉及神韵的东西都需要天赋,所谓的“神韵”像是画龙点睛,这一笔稍微有点儿歪就丧失了其“神韵”。之所以说需要天赋,是因为这种神韵大概率需要写作时的某种感觉来促成,这像是《庄子·天道》中所说的:“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在创作具备“神韵”的文学作品时的感觉,很难用具体的语言表达出来。
就好像《庄子·天道》中提到的人物轮扁,在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车轮后,终于感受到了制作车轮的奥妙。这种感受就需要天赋,很多人做了一辈子车轮都没有开窍的那一瞬间。写小说跟做车轮的开窍条件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或者同一个职业,不同人对于开窍的感触都不太一样。
当然有这些思考,那都是后话了,笔者在最初读到《受戒》时,就感觉这是一部有着幽默色彩的小说,当时就觉得好玩,感觉汪曾祺先生是在讲一个很有意思的笑话。另外就是有鲁迅先生《社戏》的感觉,看到小和尚明子(即明海)跟农家女小英子日常生活中的桥段,就感觉像是在回忆童年中令人魂牵梦萦的点点滴滴。
比如明子和小英子在玩“正经人”的“铜蜻蜓”时的表现,所谓的“正经人”是经常到“荸荠庵”打牌的两位牌友。“荸荠庵”就是明子出家的地方,看了《受戒》笔者才了解到,原来“庵”并不只是指“尼姑庵”,大者为庙,小者为庵,庵里也能住和尚。
经常到“荸荠庵”打牌的“正经人”,一个是收鸭毛的,一个是打兔子兼偷鸡的,“铜蜻蜓”是偷鸡的必备工具,或者说作案工具也可以。汪曾祺把他们称为“正经人”,这又是一个令人会心一笑的地方。
明子和英子在玩“铜蜻蜓”的时候,一时之间在庵里找不到“实验对象”,于是英子便带着明子去自己家,用她家的黑母鸡做实验。在很久之后他们回忆起来,这些捣蛋经历一定是在童年中最有趣的记忆。
起初,笔者觉得《受戒》跟王朔的小说类型差不多,也是到了很多年后才发现,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受戒》所表达的内核,更偏向于描绘社会的运作逻辑。
二、这是一个无比荒诞的世界
如果稍微有点儿社会经历的人去读《受戒》的话,就能感受到这篇小说当中从内到外的荒唐感。在小说的一开始,介绍了主人公明海以及他的年龄后,字里行间就开始透着一股荒唐感:“这个地方的名字有点儿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人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儿,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庵本来是住尼姑的。‘和尚庙’‘尼姑庵’嘛。可是荸荠庵里住的是和尚。”[2]
这些描述初看没什么,但认真阅读的话又觉得有点儿古怪,这个地名从理论上来说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一解释就不一样了。首先从描述上来看,庵赵庄根本不像是一个“庄”,就像是一个阡陌纵横的村落,但它叫“庄”。还有就是“庵”里住着和尚,前文中也有解释“大者为庙,小者为庵,庵里也能住和尚”,从理论上而言,这一点确实没什么不妥的地方,不过跟大多数人的常识有偏差,令人觉得反常。
细想的话,这应该是在作心理铺垫,这个地名就很反常,那么在后面出现更反常的描述时也就让读者有“心理准备”了。果然,后面很快就“语出惊人”:“他(指明海)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3]
之后就列举了前文中提到的那些劁猪、织席子等等职业,让读者很快就明白过来,在明海的家乡,“当和尚”是一种职业!跟织席子、箍桶没什么区别。这个时候第一轮荒唐感来了,和尚竟然是一种职业?
宗教光环和文化环境赋予了和尚一定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让大家对他们有一定的刻板印象,总觉得出家人是不杀生、不爱财、不好色、不贪嘴的修行人。可是汪曾祺先生却将人们对出家人的这些印象逐一打破,随着《受戒》小说内容的继续展开,开始介绍荸荠庵,以及住在这里的和尚。首先是老和尚普照,一开始的描述还中规中矩,“一花一世界”“一声不响地坐着”,好像还有点儿高僧的样子,但在最后却说:“他是吃斋的,过年时除外。”[4]
这是一个很有喜感的描述,本来那句“他是吃斋的”,依旧没什么问题,可是后面那句“过年时除外”,突然来了个转折,让人啼笑皆非的同时,也忍不住怀疑起这老和尚对佛祖信仰是否虔诚?
另外三个和尚分别是仁山、仁海、仁渡,随着对他们的介绍,第二轮荒唐感扑面而来。首先“仁(人)山仁(人)海”的谐音就有点儿不正经,再单独说这三个和尚,仁山是荸荠庵的主持,但大家都不叫他主持,也不叫他方丈,而是叫他“当家的”,他每天所做的也是算账、理财的事务。
仁海则更有意思了,他有老婆,而且他们在庵里的生活,跟正常的两口子过日子没什么区别。唯一不同的是,仁海的老婆很有分寸,为了不影响仁海的事业,白天不怎么出门。仁渡则像是现今的“夜店歌手”,不光人长得帅,还有许多绝活儿,比如很会打牌,比如杂技表演,比如很会唱小曲。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可是细想一下,他是个和尚啊,会这么多绝技,还有那么多相好,这真的好吗?
当介绍完这些人物后,已经能明显感受到字里行间那股荒唐感,荸荠庵叫庵也就算了,这些和尚的品行也都有问题啊,太没有“职业素养”了!最终,在几个和尚杀猪的桥段中,荒唐感达到了顶峰:“他们(指和尚们)吃肉不瞒人。过年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一切都和在家里一样,开水、木桶、尖刀。捆猪的时候,猪也是没命地叫。跟在家里不同的是多了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遍‘往生咒’,并且总是老师叔(普照)念……三师父仁渡一刀子下去,鲜红的猪血就带着很多沫子喷出来。”[5]
试想一下,在大殿当中,在神态安详的佛像面前,几个和尚在杀猪!这怎么想都觉得是对佛祖的亵渎。但一上来就说“他们吃肉不瞒人”,可见庵赵庄里的人们,对和尚们的行径早已经司空见惯,没有谁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所以他们才“不瞒人”。这就很荒唐,他们哪怕是在院子里杀呢?在佛像面前干这样的勾当,未免有些过分了。
而且杀猪时的往生咒听起来就很敷衍,毕竟那是由“过年的时候吃肉”的普照老和尚来念的,让人不禁质疑,念不念的有什么区别吗?另外就是三师父仁渡那“一刀子”,不得不说仁渡和尚真的是多才多艺,连杀猪都会。
《受戒》的情节推进到这里,会让人不禁感叹,这真是一群荒唐的和尚啊!
一群荒唐的和尚住在一个荒唐的庵里,庵所在的地名都很荒唐!
更荒唐的是,他们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存在着,没有人质疑和尚吃肉,没有人质疑和尚收账,没有人质疑和尚娶老婆,没有人质疑和尚杀生。最终会发现,其实是没人跟和尚们较真,或者说这就是底层社会的状态:对于大多数事情没人较真。
这样的状态就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很多我们认为有规矩、有秩序的事情,其实是没什么规则可言的。就算突然了解了一些内幕,比如外乡人听说荸荠庵的和尚杀生吃肉,也不会有人跟和尚们较真。仔细想一想,现在寺庙里的和尚,大多数都跟荸荠庵的和尚们差不多,没有多少真正的修行人。
从很久之前开始,寺庙就是像景区一样的营生了,只是人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缘由,不愿意往这个方向想而已。比如人们觉得自己拜佛时十分虔诚,佛祖也一定十分灵验,那么侍奉佛祖的和尚们也一定是虔诚的,否则对不起自己的虔诚,对不起佛祖的灵验。就算和尚们不够虔诚,但自己礼佛的心态是虔诚的,于是和尚们吃肉、杀生、娶老婆就都不重要了。
这更像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欺骗,或者为了达成自己心中某种目的,所以视而不见。可是人们在潜意识里早已经有了定论,因为在读到荸荠庵的和尚们的行径时,相信大多数人并不会觉得惊讶。
看吧,没人跟他们较真!
到这里,会让人觉得《受戒》似乎是在批判这些和尚们的行径,但继续深读的话又会发现,汪曾祺并没有作任何批判的意思,最多就是调侃了一下。比如描写仁山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屋里摆的是一张账桌,桌子上放的是账簿和算盘。账簿共有三本。一本是经账,一本是租账,一本是债账。和尚要做法事,做法事要收钱,——要不,当和尚干什么?”[6]
这个描述只说到“账簿和算盘”,却没有说仁山贪财。如果要说明仁山贪财的话,不需要直说,只需要有一两句描述,比如加一句仁山打算盘或者翻账本的描写,这个人物立即就变得贪财阴鸷起来。在后文中说到荸荠庵有几十亩庙产的时候,仁山甚至会变成一个地主的形象。
《受戒》中仁山给人的感觉没有那么阴鸷,反而是一个尽量帮助外甥、打牌总是输的形象。这就像是个“又菜又爱玩”的中年大叔,让人讨厌不起来。能给人这样的感觉,完全是因为汪曾祺先生一开始就不打算把和尚们写成贪财好色的人物,所以在字里行间都没有关于仁山贪财的描写。
特别是最后那句反问“要不,当和尚干什么?”问得理直气壮!这绝对是赋予了仁山这个人物内在神韵的一笔。这个和尚可能跟人们想象中的和尚不大一样,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真实的、有着七情六欲的人!
那么汪曾祺先生写《受戒》的目的如果不是批判,详细地描述这些荒唐的和尚们干什么?
这才是《受戒》的内核,这部小说本身不是在写和尚,而是在写生活。
三、荒诞,但真实
如果普照、仁山等四个人不是和尚,而是四个搭伙讨生活的普通人,而荸荠庵也不是庵,而是这四个人共同经营的事业,情况立即就不一样了。普照是他们事业的领路人,或者说是他们这家公司的元老,经验丰富,沉着老成。仁山则是这家小公司目前的总经理,仁海和仁渡都是公司的员工,仁海稳重干练,仁渡业务能力强。仁海的老婆是职工家属,明海是新来的实习生。
有毛病吗?
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这似乎才是《受戒》这篇小说的精髓,也是笔者读到的第三个层次的意思。在笔者看来,这是《受戒》之所以经典的重要原因,这篇小说的三个层次几乎满足了所有读者的需求。第一个层次,这篇小说像是个很好玩的笑话,这满足了以读书为娱乐的人们的需求;第二个层次,这篇小说在描写荒诞的寺庙生活,满足了有着批判眼光的人们的需求;第三个层次,这篇小说在描写一切的一切重归生活,满足了有丰富阅历的人,或者像笔者一样,从事写作事业,带着学习大师的心态阅读的人们的需求。
一般而言,经典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不同群体能读到不同的东西。这是《受戒》比较独特的地方,看上去像是在漫无目的地闲聊,其实写着写着又重归生活,而且是十分真实的生活。
和尚们吃斋念佛,传经布道,这是人们想象中的修行者,但不一定每个和尚都是这样。和尚首先是人,只要是人就有自己的生活,从这个角度出发,和尚们吃肉、打牌、娶老婆、做法事的时候收钱,也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这就是普通人生活的写照,只要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不做修行人都没关系,没人跟他们较真。
这样说可能听上去很没有公德,但这就是生活,因为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已经精疲力尽,没人有精力会去计较和尚吃不吃肉的问题。这也是底层社会一直以来的现状,只要不是利益相关,一般大家都不会管自身利益之外的事情。在大多数时候这并不冷漠,而是做人太累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荸荠庵里的和尚们搭伙过日子,在最初的时候也一定是为了生计,很可能是没办法成家,才只好出家。这依旧是社会百态的真实写照,朱元璋为了生计也做过和尚,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性:世间百态皆可为生计!和尚、道士的宗教信仰也不例外。
很多高高在上的人曾经批判过这一点,但笔者却认为,这是中国人的智慧。有了生计才会有闲情逸致去谈宗教,去谈伦理道德,没有生计一切皆是虚妄。所谓“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没有经历过绝望的人生,就不要去批评以“做和尚”为生的人。他们在庵内吃肉就吃肉,打牌就打牌,只要没有影响到他人,没有在庵外有恶劣的行迹,都是可以谅解的。
《受戒》所表达的社会性在如今的文学作品中也不多见,它没有批判,只有描述,也不是在抒发个人的情感,或者发牢骚,就是把底层社会的一幕幕生活状态摆在读者面前;而且对社会性的描述,是那种社会运作状态的描述,《受戒》没有觉得这样的状态是病态的,是应该被抵制的,而是告诉大家社会的运作逻辑就是这样的。
这是笔者在前言中会提到《西游记》的原因,这部名著读着读着就会读到人情世故,就会读到中国上层社会的运作方式。吴承恩是见过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人,所以他把上层社会的运作逻辑,隐藏在了《西游记》里面。《受戒》也有这样的内核,它在深层次中所描绘的,就是中国底层社会的运作逻辑。
至于小说名为什么叫做《受戒》?而不是破戒?可能是因为没有受戒的话,就不会有破戒吧?如果说《受戒》只是在描绘生活,描绘社会的运作逻辑的话,那么这部小说也不会成为经典。它还作了升华,明子和英子的爱情部分,就是让小说得以升华的部分!
这是一段十分干净的爱情,两个人青梅竹马,早就暗生情愫。就算他们最后划船进入芦苇荡,也不影响这段感情的纯净。
英子是一个很聪明的姑娘,在她姐姐为自己准备嫁妆,请明海来画花样的时候,英子就喜欢上了明海。原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因为明海能画很多花样,而且惟妙惟肖,于是“大娘(英子的母亲)看着也喜欢,搂住明海的和尚头:
“‘你真聪明!你给我当一个干儿子吧!’
“小英子捺住他的肩膀,说:
“‘快叫!快叫!’”[7]
在笔者看来,英子十分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如果明海做了英子母亲的干儿子,英子以后便很容易有理由去找明海了。果不其然,因为姐姐要赶嫁妆,田间零碎的活儿英子就全包了。她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找明海帮忙。
为什么找明海?因为他是英子母亲的干儿子,帮干娘家里干点活儿,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个时候就显现出英子的“高瞻远瞩”了,一来二去,他们的感情当然就越来越好。
明海也很聪明,不然他也不会有机会成为善因寺的“储备方丈”(沙弥尾),到这里,其实明海也是个有故事的和尚了。就像仁渡很会唱小曲,有很多相好一样,明海和尚很会画花样,十里八乡的姑娘都请他帮忙画花。
对于明海和英子的情愫,汪曾祺先生一直处理得很隐晦,这都是为了情节上最后的爆发。在《受戒》的最后一部分,明海到善因寺受戒,在善因寺待了几天后,英子划船来接他。两个人在船上讨论起善因寺的方丈,一开始还像是在聊八卦一样,聊着老方丈的小情人,但当英子得知明海未来可能要做方丈的时候,谈话的氛围立即就不一样了:“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了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8]
前文中对英子和明海的所有描写,都为了让这句“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更有冲击力。情节推进到这里,所有读者就已经知道,明海绝对会答应,后面的情节都理所当然了。而英子说这话也并没有给人不够矜持的感觉,汪曾祺先生在这里处理得非常巧妙,英子先是让明海不要当方丈,又让他不要当沙弥尾。因为方丈不像是普通和尚那样随意,方丈不能娶老婆,只能养情人,显然这并不是英子想要的。
如果对这一段的描写稍微多了点儿,或者稍微少了点儿,味道就都不一样了,这又是“神韵”,也是模仿不来的东西。有了前面的两个问题,那么当英子说出“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的时候,读者会祝福他们,而不觉得这是在诱惑刚受戒的明海破戒。
这段唯美的爱情让《受戒》得到了升华,毕竟每个人都在生活中煎熬,谁不希望有这么一份美好爱情呢?它在《受戒》里面就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典雅,芬芳。可惜,明海是个刚刚完成了受戒的和尚,这段爱情又是冲突的,不恰当的,这时候再次把读者送到了煎熬的生活当中。
《受戒》所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荒诞的世界,但它又真实无比,因为这个世界本质就是荒诞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荒诞的事情,世界在一个个荒诞的叠加中持续地运作下去,直到永远。但也不用灰心,也许在下一个路口,就能遇到“明海”或者“英子”那样唯美的佳人。
参考文献:
[1][2][3][4][6][7][8]汪曾祺.汪曾祺小说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4:1,1,1,5,6,13,21.
[5]汪曾祺.汪曾祺小说集[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4(2020.10重印):10.(引用的片段中出现过两次的“家里”一词,原文中是“家人”,为了避免发生误读,笔者改为“家里”)
责任编辑 饶丹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