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星空与半棵树》对城乡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2024-10-27章以畋
摘要:陈彦在《星空与半棵树》中通过新时代农民与返乡知识分子的在乡选择对城乡问题作出了新的思考与回答。小说主人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由以往的“离乡”进城寻找生计路径,转变成为更好的“返乡”所以离乡,主动充当乡村振兴参与者的“在乡”路径,主人公道路改变的背后是陈彦对城市形象与乡村新功能的全面把握。当生活在现代化都市中的人的意义感与归属感无法得到确证,乡村开始承担“心灵”之乡的角色,召唤游子的回归。
关键词:城乡问题;陈彦;《星空与半棵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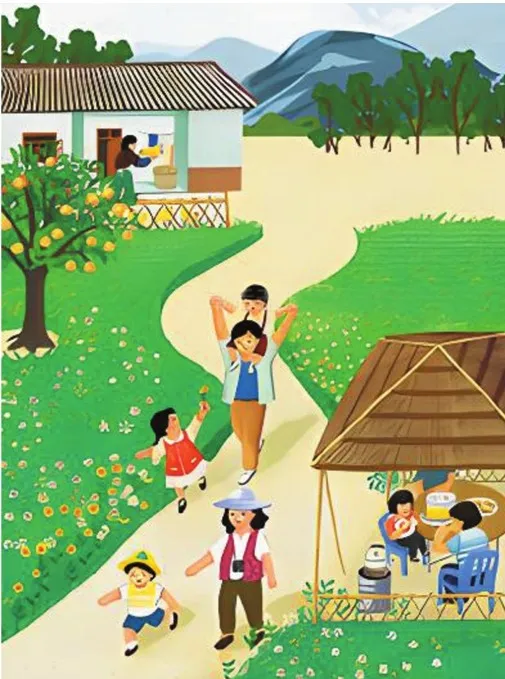
村庄是中国乡土小说生发的源头,也是作家成长的精神原乡。作家之于乡土的眷恋感与归属感,最直接的表现即这一群体对文学村庄的精神皈依。新时代以来,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乡村进入剧烈的社会转型期。现代乡村的剧变向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提出新的要求,以新视野、新思想与新方法表现新的中国故事成为“新乡土写作”的基本美学原则,也成为新时代“新乡土小说”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近40年的城乡交往叙事以具象化、日常化、现实化的农民命运书写,拓宽了“乡土文学”的审美视域。[1]
陈彦从《西京故事》《装台》开始,持续对新时代城乡巨变中的农民问题给予深切关注,始终注视着时代中小人物的命运,于时代洪流中为小人物立传,是其不变的创作初心。在新作《星空与半棵树》中,他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小说中的平民意识及底层关怀,但在尝试回答城乡问题时,陈彦第一次将寻找答案的目光由城市转移到乡村,乡村成为其主要叙事背景。在这部作品中,主人公由以往离开家乡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人,变成对家乡建设的主动参与者,新时代的新农民形象跃然于纸上。当城市不再充当农民心中想象的乌托邦,乡村于农民心中呈现出待建设振兴的形象,乡村的新功能被发掘,新时代农民何去何从、乡村振兴如何进行的问题在小说中得到探索与回答。
一、对城市生活“祛魅”
在《星空与半棵树》中,陈彦选择将北斗村作为与城市相比对的空间,即城市隐喻“他乡”而北斗村暗示“故乡”。因此,作为寄寓作者怀旧思绪的本体,北斗村的人文自然被赋予了暖色调。小说从离乡进城乡下人的个人经验出发,对城市生活进行了祛魅与还原。将进城的乡下人对城市的态度分为不同的两个维度,以温如风为代表的乡下人对城市的认知打破以往惯例,呈现出不卑不亢的姿态,而安北斗的前妻杨艳梅、孙铁锤则延续进城乡下人固有的对城市生活的羡慕、崇拜心理。陈彦根据这两类人对城市生活的不同看法,为其安排了不同结局。
小说塑造了一个典型的新农民形象温如风,他离乡是为了借助政府权力惩罚家乡地头蛇,以保护自己在村庄中抬头挺胸生活的合法性,由于拒绝了北斗村“地头蛇”孙铁锤的权力规训而受到其欺辱,温家成了北斗村中的边缘户。温如风选择由村到乡镇,再到省城、京城不断上访,期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改善自己家庭在北斗村中的生存环境。在一路上访的过程中,温如风第一次离开了自己从小生长的北斗村,通过温如风的视角,陈彦展示了城市的多种特质,城市热闹精致,但也冷漠疏离,城市只能作为温如风上访的暂时停留空间,无法让其获得归属感。在温如风看来,城市带来的不仅是热闹,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空虚,在城市上访的过程中,他看见了人们的隔阂、冷漠,在上访迟迟得不到结果的时候,家乡就成为温如风情绪的寄托,他渴望早日上访成功回到家乡,渴望家乡缓慢的生活、原始而融洽的人际关系和宁静的田园乡土。在一定程度上,乡愁乡思是其城市生活的衍生情感,家乡与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相关联,凝结着他幸福的梦与安稳的归处。
进城的孙铁锤则与温如风对城市的看法形成巨大差异,孙铁锤觉得城市的一切充满诱惑和吸引力,于是急于将自己包装成老板,抹去自己农村人的气质以融入城市生活。奢靡的享乐使其欲望不断膨胀,为了获得更多钱财他开始聚众赌博、谋财害命、欺男霸女……面对家乡铁路建设的发展机遇,孙铁锤利用自己的资源在村中建立公司开山炸石,除了温如风,村民纷纷选择加入其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孙铁锤公司盲目实行的“开山炸石”爆破,让北斗村中六个无辜村民不幸殒命,他所办的赌场更让许多人家破人亡,但孙铁锤的怪胎式发达,让整个村的男女老少为了眼前利益唯他马首是瞻。纵观整部小说,孙铁锤是陈彦笔下唯一的“扁平人物”,他贪婪好色,无恶不作且毫不悔改,陈彦为他安排的结局以及对他的批判态度,警醒着读者对城市生活作出正确判断,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问题进行反思。
安北斗前妻杨艳梅的人物形象呈现出双重矛盾特点。第一重矛盾是生活表面与内里的矛盾。进入城市后,杨艳梅感受着两种生活。一种是表面的生活,衣食住行光鲜靓丽令人艳羡;另一种是内里的生活,富足外表粉饰着家庭破碎与精神孤独,这是祛魅和还原后的城市生活。第二重是精神与物质的矛盾,杨艳梅的两任丈夫安北斗与储有良分别隐喻着乡土生活与城市想象。与安北斗在一起,可能要一直待在封闭的北斗镇,通过储有良,却能追逐省城的繁华喧嚣,她在精神与物质的选择中徘徊,最终选择了储有良。再婚后却发现储有良的政治野心像填不满的黑洞,“他似乎有无尽的电话要打,不是让人组织给他投什么票,就是让人引见他去见什么人。”[2]人心欲望的窟窿永远填不满,她无法与储有良产生精神交流,城市是个功能性较强、生态性不足的地方,“她多少次梦见与安北斗在阳冠山上望星空的日子,可肉体又绝对回不到那个世界去了,尽管在精神上不断回溯反观。”她的形象深化了传统乡土小说对城市生活的表层书写,享乐主义与实用主义得到反思,城市的生活不仅仅是穿着高跟鞋跳舞、咖啡屋、时髦衣服与名牌化妆品,还有人生起落跌宕后的平淡寂寞与繁华喧嚣背后的煎熬。
通过温如风、孙铁锤与杨艳梅的对比,读者可以看到乡下人在面对城市诱惑时所作出的不同选择以及人物各自面临的问题,陈彦笔下对城市生活的探索从其精致富足的表面到人性异化、精神孤独的深层,一方面以现代性的眼光看到了现代城市生活的复杂面貌,不再以笔下人物的向城之路当作乡下人对现代文明追求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在情感上表现出对乡村自然环境与传统邻里交往方式的眷念。还原后的城市生活不再令人疯狂地迷恋,因为建设中的家乡呼唤着游子的注视。
二、为乡村功能“赋魅”
时间在《星空与半棵树》中被隐去,城市与乡村作为互相联系的空间清晰浮现,乡村的新功能被发现,陈彦赋予北斗村一份特殊意义:走向振兴的乡村不应只局限于城市人偶尔消遣寻乐的游逛之处,更可以成为为整个城市人群潜在的身心症候提供疗愈与灵魂喘息的精神出口。这不但为乡村振兴中的经济建设提供思路,更对乡村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文化生态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在《星空与半棵树》中,村庄内部的环境污染问题、土地抛荒问题、乡村伦理解构问题,显然给北斗村的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的协调造成了多重悖论。当北斗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获得经济复苏、环境改善、社群伦理关系修复后,其自然风景与人文风景的和谐复归成为必然的结果。
陈彦将北斗村精神文化生态建设的希望寄托于重新发掘乡贤文化,刻画了一个丰满的乡贤形象草泽明。中国的乡土小说一直占据文学史的重要位置,乡贤文化从晚清到今天从未断裂,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不同的改变,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乡贤文化的支持。作品中乡贤文化叙事始终凝聚着作家对历史进程中乡村传统文化与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这样的乡贤叙事,不仅仅是历史与现实的叙事反映,同时也是以叙事方式参与到中国乡村精英与乡贤文化的建构中,以此分担历史道路选择中的迷思与焦虑。”[3]新时代乡土问题与时代面貌正发生转变,这需要作家及时发现并调整自己的创作方针。在小说中,民办教师草泽明出现,这是一个平日如古代隐士般住在远离北斗村的一个草屋之中的人物,却会在北斗村人心浮躁、价值失落之际去京城“上访”,只为推倒村霸孙铁锤立在村中酷似其爷孙仨人的佛像。草泽明认为,孙铁锤明明作恶多端却想让自己流芳于世,这雕像是对公平正义、道德人伦的败坏。由闭门不出到主动上访以守护乡村的公序良俗,其前后转变体现出一个乡间知识分子天然的使命和担当。借草泽明之转变,陈彦再次表明了自己写作的底层关怀——形而上的事情固然伟大,但形而下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珍重。陈彦正是通过这些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小人物悲惨的命运遭际,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民众精神,体现出这些平凡人物大雄藏内、至柔显外的高尚品质。他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感染着读者,将读者的感情无间隙地带入陈彦的文学世界之中。[4]也只有建立在真实生活之上的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感,才是坚实有力的。
风景书写一直是乡土文学的重要构成,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时期作家曾凭借启蒙理性的批判目光“发现”了乡村,以废名和沈从文为代表的“京派”作家又以诗意的呈现取代文化批判,建构乡村风景的另一重书写维度。然而,在“被发现”“被审视”或“被诗化”的过程中,乡村风景始终是现代作家剖析社会与人性,表达个人情感的中介,是一种背景式的存在。与之相较,新时代的乡土文学显然更加注重乡村风景的独立价值,并有意识地将之作为重塑乡土文化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出坚定的文化自信。[5]陈彦对乡村建设的思考则围绕北斗镇10多年间来来往往的三任镇长南归雁、蓝一方和牛栏山在北斗镇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政策展开。南归雁在任时,选择发展旅游业,搞“点亮工程”,又请省上的民俗专家设计了“万人社火大巡游”,让本就贫困的北斗镇财政赤字更加严重。南归雁被调走之后,新上任的镇长蓝一方又开始考虑“新的经济增长点”,于是让全镇乡民不惜“毁产”也要种甘蔗酿酒,做决策时,没有考虑乡民各家酿酒手艺的参差,也没有提前考虑甘蔗酒的受众与销路问题,这种盲目激进的做法迅速暴露弊端,酒酿成后乡民家家存着三五千斤的酒却严重滞销。北斗镇的发展过程忽视了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没有考虑到北斗村自身的优势,使得村民之间人心涣散、只以各自利益为出发点,乡土伦理逐渐瓦解,整个村庄的价值认同开始从仁义礼智信向功利时效性转型,然而急功近利是一切生命的成长瓶颈,社会发展尤其如此,北斗镇的经济建设陷入困境。
北斗镇的振兴路径最终指向了自然文化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发现自然的力量,发挥乡村的独特功能,即通过保护乡村生态,让乡村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风景成为抚慰人们内心的天然疗愈师,通过乡村独特的个性发展生态旅游,为生活在城市的人们被物质的压力和拥挤的交通所裹挟而感到身心俱疲时提供休憩之所。北斗镇建设路径的最终转向由南归雁的改变体现,南归雁在经历数十年的实践,回永安县担任县委书记时,认真调整方针,选择了研究北斗村泥石流综合治理、修复开山炸石的生态环境并解决河流小溪枯水断流问题,最后从安北斗对星空的痴迷与其建立天文望远台的建议中,发现了北斗镇发展应重视“星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此为全书极为重要的一笔,乃是种种矛盾种种问题多个层面复杂交织之后最具观念和现实意涵的重要选择,不仅具有总括全书的复杂寓意,亦是足以开出指涉现实且深具实践意义的重要一维。其所依托之‘自然’观念,庶几近乎儒家所论之‘整全生机观’,即不再将人自外于自然,以‘人力征服’自然而获得发展,而是将人重新归入‘自然’之宏阔背景中一并考虑。”[6]
三、“此心安处是吾乡”
温如风的上访作为本书的表面线索,北斗村的建设发展则作为本书的隐形线索,但陈彦在全篇着墨最多的人物却是安北斗,这一新时代的乡村知识分子形象汇聚着陈彦对知识分子理想品质的具体想象,通过安北斗,陈彦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知识分子为什么返乡?
随着我国现代化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离乡学习的青年数量一直增长,这些具备更高文化水平并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最终不能都留在城市中,城市的容量是有限的,乡村建设同样需要一部分知识分子回到家乡,然而在“知识分子返乡”这一问题上社会层面的公共认同尚未被建立起来。安北斗以大学生身份回到家乡受到许多人质疑,人们觉得:念了一回大学,最后还是要回到乡村。似乎读完大学从城市回到乡镇,就会被父老乡亲钉在成功的“耻辱柱”上。这一看法背后浓缩着新时期返乡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安北斗的形象作为这一时期返乡大学生的缩影,反映着整个时代的精神困顿。
陈彦在小说中尝试从精神信仰层面建立知识分子的返乡认同。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动物视角——猫头鹰,它充当了小说中预言家与作者代言人的身份,在北斗镇的斗转星移中默默观察,见证着人类悲欢离合的生命历程,成为深化小说主题的阐释点,安北斗则是全篇唯一被猫头鹰选中的人,是整个叙述过程中的主人公。“代表着浪漫主义、理想主义化身的安北斗,是真正主宰小说光明走向的主角,他是隐藏在整个叙述主体背后的那个牵线人。”[7]
安北斗的在乡选择体现出个体对于独立意识的追求,安北斗常以家乡的星空为参照思考现实琐事和人生进退荣辱,他拒绝领导将他调往城市,安心于在乡镇基层单位处理细碎繁琐的工作,脚踏实地地解决家乡发展中的问题,也会为了天文学知识和夜观星空废寝忘食。北斗镇的镇长来了又换,有高升的也有被贬的,安北斗却一直被安排从事看上去窝囊有余但前途不足的“劝访”工作,面对丈母娘和妻子对他始终待在北斗镇的不满与怨怼,他依然选择认真处理工作琐事,不卑不亢守在从小生长的土地上,他相信只要“不屈从于任何欲望纠缠撕裂,就活得游刃有余、自由奔放”[8]。在《星空与半棵树》中,读者能够感受到安北斗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独立思考的能力、丰富的精神世界和高尚的价值追求。当今世界,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上升,与之相对的是宗教、信仰消退,当上帝消失,世界缺少能够指导利用技术发现并使之为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目的服务的道德力量,所以有可能产生人们几乎难以想象的后果。上帝消失的背后实际是人的情感、价值的失落,当人的劳动的价值被量化、成为理性主义的工具,人最终成为机器一般的人。[9]小说中“星空”的隐喻和安北斗这一具体知识分子形象的存在,正是陈彦呼唤信仰与精神价值在个人人生中存在的意义,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有安北斗这样怀抱信仰、独立思考的人,人文主义才不会失落,于是就有了新时代的乡土小说在私人以及公共层面建立知识分子“返乡”认同的可能性。返乡知识青年原本就与乡土世界血脉相连,他们的逆向流动,不仅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空间的联通、交叠,更意味着乡土世界的新变化需要从根本上借助自身内部的力量。由是观之,农村新人的逆向流动便具有了明确的象征意义,新农村建设的在地性由此得以彰显。
结 语
陈彦笔下的乡土形象,在有意摒弃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思想史以西方现代性为价值标准衡量城乡的范式后,城市的价值体系不再作为走向现代的必然,农村也不再被贴上愚昧、落后、前现代的标签,乡村的新功能被发现并以责任与情怀诉说着对游子的召唤,呈现出主动参与建设和改变的历史姿态。《星空与半棵树》与时俱进,对正在发生的山乡巨变、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新现实进行审美书写,在这个意义上,《星空与半棵树》体现出陈彦对新乡土中国叙事的有效尝试,小说中的众多人物的离乡都是为了最终更好地回到家乡——无论是为了有尊严地在家乡生活或是为了更好地建设家乡。弃乡进城现象不再是城乡二元问题的必然产物,陈彦以乡村建设为背景平衡调节了长久以来乡村人口在陌生的“他乡”与回不去的故乡间的矛盾,以丰富深厚的人文眼光思考并尝试回答着城乡碰撞的时代性问题。当古典的乡土文学的家园品质正在遭受城市化的巨大考验时,文学化的新乡土叙事正在试图与市场中国的行程同向同行,产生出警示和价值引领作用。
参考文献:
[1]张继红.论新文学传统流变中的“乡土文学”与“新乡土小说”[J].当代文坛,2021(1).
[2][8]陈彦.星空与半棵树[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640,690.
[3]白现军.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贤文化传承与创新[J].北京社会科学,2021(12).
[4]韩伟.人间·人心·人生:陈彦《装台》的三个面相[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
[5]朱佳宁.“回得去的故乡”何以可能?——新时代乡土文学初探[J].创作评谭,2022(6).
[6]杨辉.天何言哉:《星空与半棵树》中的自然和人[J].南方文坛,2023(5).
[7]丁帆.星空下的黑暗与光明——陈彦《星空与半棵树》读札[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4).
[9]吕西安·戈德曼.隐蔽的上帝[M].蔡鸿滨,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42.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