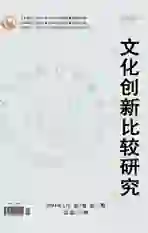从“文献”到“实物”:近代中国文物保护困境与图书馆的因应
2024-10-18张治军
摘要:近代中国,由于西方列强的掠夺、官方在文物保护领域的职能缺位、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及地方博物馆建设的滞后,使得众多古籍和古器物流散海外,形成文物保护的现实困境。在此情境中,图书馆团体深刻反思自身肩负的文化使命,积极因应文物流失的局面。在政府的支持下,各级公立图书馆不仅继承了古代藏书楼的传统,不断开展古代典籍版本的征集、保存和出版工作,而且自觉担负古代器物保存和展示的新使命,实现了由保护古代“文献”向保护古代“实物”的深化,扩充了图书馆的文物保护功能,保存和拯救了一大批珍贵文物。图书馆作为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积极推动了近代文物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图书馆;博物馆;藏书楼;文物保护;近代中国;文化使命
中图分类号:G269.2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8(c)-0064-05
From "Documents" to "Objects": the Library's Response to the Dilemma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in Modern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China, due to the plunder of Western powers, the government's neglect of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the lack of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the la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museums, many ancient books and artifacts were lost overseas, resulting in a realistic dilemma of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In this context, library organizations deeply reflected on their cultural mission and actively responded to the situ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being lost.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government, public libraries at all level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ancient libraries by continuously conducting the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but also consciously assumed a new mission of preserving and displaying ancient artifacts, deepening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documents" to the protection of ancient "objects", expanding the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function of libraries, and saving and preserving a large number of precious cultural relics. As an important force in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libraries active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Key words: The library; The museum; The ancient librar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Modern China; Cultural mission
文物在中国近代一般被称为“古物”,古籍与古器物均归属古物之类。近代中国图书馆继承了古代藏书楼的保藏传统,致力于古代典籍的征集和出版。然而,这一时期西方列强的掠夺、官方在文物保护领域的无力、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及地方博物馆建设的滞后,使得众多古籍和古器物流散海外,形成文物保护的现实困境。在这一情景中,图书馆团体深刻意识到自身肩负的文化使命,自觉承担起非纸质文物的征集、保存和展示工作,实现了由保护“文献”向保护“实物”的扩展,深度参与了近代文物保护事业,成为近代文物保护的重要力量。
1 旧传统与图书馆新使命
中国古代官方和士大夫皆重藏书,“购募”经典之举由来已久。在官方看来,先贤经典可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纲纪,弘道德”,无论是公开还是收藏均有助于国家治理,“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1]。官僚阶层和一般士大夫更将书籍视作近乎完美之物,既可陶冶情操,又可指导实践,无论何人皆可“求无不获”[2],因而民间搜罗典籍蔚然成风,更有甚者,“所藏之富,与秘阁等”[3]。基于古代公私藏书楼的传统,许多珍贵典籍得以流传至清末,成为近代中国诸多知名图书馆的“立馆之基”。
一般而言,近代中国图书馆前身为古代公私藏书楼。较著者如浙江省立图书馆,自称“承文澜阁之旧业,继藏书楼之成规”[4]。正是在传统的影响下,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推广创办图书馆将保“旧”与进“新”并重,主张“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5]。各省督抚秉承这一宗旨,也多以“保国粹”和“惠士林”为由申请创办图书馆。
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公共属性更加凸显,特别是在开民智以救国的社会思潮中,图书馆更加重视社会教育功能,极力主张“吾辈执掌近代知识之宝库,典守先民之遗藏者,丁兹时会,尤应以知识之明灯,出有众于幽暗”[6]。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渐加深与反思传统的现实情境中,官方努力宣传“对于吾国原有之文献加以整理,从而发扬固有之文化”[7]。图书馆界同时意识到“吾邦之国粹,寄托所在,非图即书”[8],进一步认识到传统典籍在近代的文化价值,社会对图书馆的期许转向保存文献和阐扬文化,认为“图书馆不仅负有保存文化之责而已,且负有发扬其所保存之文化而光大之使命”[9]。具体而言,就是“要将过去的前人的文化绍介之于今人、后人,使再经一度的溶化,一则使其不致停滞,一则使其有所发扬,永久递进”[10]。
一方面,近代中国图书馆基于藏书楼的传统,将征集和保管古代典籍视为自身的一项重要职责,如浙江省立图书馆主张“努力于网罗散佚、征存文献之工作”,希望可以“引起本省人士珍视地方文物之观念,而益深爱乡爱国之思”[11]。另一方面,在现代图书馆观念的影响下,古籍的保存实以公开阅览和发扬文化为旨归,“欲保存古籍,舍一扫旧式藏书之故策,从事于公有活用,其道莫由”[12]。这成为图书馆在近代的新使命,也成为其参与近代文物保护的内在动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藏书楼的观念中,图书馆保存的“国粹”一般指“先哲遗著即古代名著”[13],很少将其延伸至纸质文献之外,近代图书馆文物保护对象的扩充主要受到外在现实的刺激和影响。
2 近代中国文物保护的现实困境
中国历代存世的古物数量大、种类多。这不仅由于古代诸多“法象制器”因制作精美而“造诣精微,垂则万世”[14],还得益于自古就有的收藏传统,官方则“自周以降,历代文物,皆藏内府”[15],而“民间知识分子的7BqWuvspvpYFxsgbYUbxFQ==搜藏风气,尤为广被,而曲尽制度”,因此“其搜集、陈列、供人观赏、陶冶性情,变换气质,久为古代社会所重”。然而,由于古代重视“秘藏”,公开范围极其有限,无论是藏书还是金石器物均可因天灾和兵燹而损毁,古物流失在所难免。
在近代,大量珍贵古物更多地面临盗掘和外流的危机,古籍器物在这一时期屡遭劫难。一方面,相比战争掠夺的侵略性和野蛮性,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边疆地区相继开展所谓游历和探险活动,发现古代遗迹的同时,趁机掠夺大量器物、典籍,在学术外衣之下更具迷惑性;另一方面,国内盗墓和私掘活动猖獗,有些地方“盗掘新旧坑穴,触目皆是”[16],大量古代墓葬被破坏,国内古董商因之在各地搜罗古物售予外国买家,众多出土器物和私家珍藏不断流落海外。当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是文明古国,古物古籍为数最多,关系文化极为重大,可惜国人不知爱护,以致流出海外者,不知凡几,如山东海源阁藏书之散佚,国粹有沦亡之忧,且外人要求到我国内地考查者很多,珍藏古物,被其运去者亦复不少,故亟应设法防止[17]。
由此可知,当时古籍古器物均面临流失海外的厄运,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官方已经认识到古物外流对于传承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巨大破坏。然而由于当时文物保护机构的弱势、文物保护法规的缺失以及政局的动荡,社会无法有效阻止古物的外流,更是加重了这一悲剧。而另一层面也反映出,在古物流失的刺激下,国人的文物主权意识开始觉醒,外国人将中国古物私运海外的情形不断受到国内社会各界的质疑和反对[18]。
在维护文物主权和文物追索的过程中,国内古物专业保存机构的缺失,成为文物保护面临的另一个困境。中国历代古物皆藏于类似“内府”等机构,被视为近代博物馆的历史渊源。清末以来“西人考古西陲,于是敦煌的遗书、流沙的坠简,相继以出,捆载而去,三代两汉之物,流传海外,不负见于中土,国人研究本国文物的,反有材料缺乏之应”[19]。在此种情境中,博物馆的职责首在“保文物以存国性”[20],保存古物成为推动博物馆创办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这一时期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和田野考古活动的开展,更加明晰了博物馆作为古物保存机构的正当性。1926—1927年,李济在发掘山西西阴村遗址时,约定在中外合作考古发掘之后“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博物馆,或暂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管”[21]。安阳殷墟发掘之时,傅斯年等也持同样主张,“本院特派员在各地发掘古物,将来如何陈列,亦仅限于首都及本地博物馆”[22],均可说明各级公立博物馆保存古物的使命。与此同时,现代博物馆观念又具有公共服务的属性,所藏古物“与图书馆同样的为一般民众而开放”,旨在发挥教育民众的作用。
然而,与文物保护面临的紧张局面相比,这一时期博物馆在规模和数量上均相对滞后。一般言之,1905年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则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博物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博物馆数量“岁有增加”。根据中国博物馆协会的统计,1936年具有一定规模的各级各类博物馆数量有80座[23],是为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高潮。尽管曾昭燏等回顾这段历史时,对中国博物馆取得的初步发展感到欣慰,而事实上囿于社会动荡不安、政府支持不力、专业人才缺乏、各地文物保有量不同等因素,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步履维艰。国立博物馆建设方面,故宫博物院承自清代皇室收藏最具规模,而国立中央博物院长期处于筹备阶段。省立博物馆建设方面,除了河南博物馆和浙江西湖博物馆,其他各省博物馆建设相对滞后,始终未能实现各省拥有一座独立的省级博物馆机构。因此,更多的博物馆学人认为“近年来我国文化上的建设,图书馆方面规模粗有可观;而于博物馆方面之建设,至今尚在萌芽”,这种不平衡使得“教育不易普遍,即民族文化亦蒙莫大损失”。由于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其无法独立承担保存和展示古物的职责。
近代中国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备,使得古物流失情况严重,古物保护实际上处于一种“失序”的状态[24]。再加之博物馆发展的滞后和职能的缺失,使得古物保护,尤其是非纸质古物的保护陷入困境,以此造成在没有建立博物馆的地方,古物的征集、保存及展示需要另择他处,客观上需要其他机构或者团体承担保护古物的使命。
3 图书馆从“文献”到“实物”的自觉
基于藏书楼的传统,近代图书馆以保存古代典籍为使命。而面对近代古籍流失造成的恶果,特别是“国内图书馆所不可得者,而外国图书馆则有之;国内图书馆所罕见仅有者,而外国图书馆则尽有之”,使得图书馆团体深感“对本国国粹,且不能自保,宁不可耻?”古籍外流之耻激发了图书馆保存“国粹”的使命感,将保护古籍、保护传统文化同爱国爱乡联系起来,从而坚定地承担起保护古籍的职责,努力征集和保管古代典籍。在1927年,图书馆界人士李小缘提出不同级别的图书馆应该承担相应的保存文化的职责,特别是国立图书馆应该重点承担保存和发挥创造的职能,如“收回流落东西洋之敦煌遗书、永乐大典,禁止古版书出洋”,而省立及公共图书馆也应该注重“搜集本省一切文献”[25],均表明了博物馆团体的迫切需求。
此外,面对近代古器物流失的严峻局面及博物馆职能缺位的现实,图书馆界也在理论上反思自身能否保存古代器物的问题:
博物院与图书馆皆有保存地方文献之责,但所谓文献者非仅图书印刷之件而已,如铜铁、建筑之类皆是。故在有博物院地方皆当属于博物院,而以图书等附陈其中,俾得聚于一处。若仅有图书馆,则实物方面之文献,究应由图书馆保管与否,实一问题[26]。
此种言论主要参考欧美博物馆与图书馆发展的历程,提出了图书馆能否保管“实物”的问题。虽未明确表示图书馆可以保存古代器物,但提出无论收藏与否,图书馆都应注意古代实物,并对其进行详细记录,以备研究者参考,并未否认图书馆保护古代“实物”的必要性。
反观现实层面,近代中国图书馆与博物馆由于旧有收藏的传统和公共服务的属性,使二者共同肩负着保存国粹的职责。社会人士也大都能认识到博物馆与图书馆在保存和发扬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认为博物馆“同为文化之一,应与图书馆一并举办”[27]。图书馆学人也认为博物馆“能发扬文化、启迪民智、保存文献,影响于国家社会之隆盛,则于图书馆事业有同样之功用”[28]。博物馆学人更是有此认知,认为图书馆与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犹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
正是基于同样的保存文化与社会教育的功能,近代中国博物馆事业与图书馆事业几乎同时起步,而后者呈现一种全面发展的趋势。清末新政时期,各省督抚争相创办省级图书馆,形成了一场公共图书馆运动,而不是同博物馆一样零星建立。民国时期,在国民政府和各省政府的支持下,国立、省立、县立等各级各类图书馆相继建立,人员配备、建筑规模、藏书种类及专业化程度等均取得长足进步。1935年,根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统计,全国各省份和主要城市中,各级各类公私立图书馆总数达4 032座[29],图书馆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几乎每县、市政府所在地均设有公立或私立图书馆”[30]。图书馆在数量和规模上的发展水平均领先同一时期的博物馆,以致近代图书馆学人也意识到“我国博物馆为数无几,其规模宏大而管理得法者,更寥若晨星”[31]。
古物流失与博物馆职能缺位的困境激发了图书馆学人的使命意识。他们不仅以保存古代典籍为己任,而且在纸质文献之外,致力于保存古代器物。早在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召开第三次年会时,图书馆教育组裘开明等即提出“各省公立图书馆得附设古物陈列所案”,认为“各地因无博物院,所有古器古物类多散失,或遭私人损弃,或流入外人之手,诚可痛惜”,因此主张“借现有图书馆另辟一间为博物陈列所,所费不大,举办甚易”[32]。这一建议由于时局动荡并未很好施行。1927年,李小缘再次提出图书馆在保存先哲遗著之外,省立图书馆应“附设省立博物院,搜集本省古物、碑帖、遗迹等物件”。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召开第一次年会之时,袁同礼又提交“谓各大图书馆搜集金氏拓片遇必要时得设立金石部以资保存案”,中央大学区立苏州图书馆还提交“图书馆内添设历史博物部案”[33]。均可见图书馆团体对古代器物保护的高度关注。20世纪30年代,中华图书馆协会按照这些提案,号召各地图书馆重视“国故之保存”[34]。在此影响下,国立和许多省级公立图书馆承担了保存古物的职责,如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及山东、山西、安徽、湖北、湖南等省立图书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最初的设想中,省级以下的公共图书馆应该偏重普通图书,但实际上为数不少的县立图书馆也承担了搜集地方古物的职能。如江苏省铜山县立图书馆起初纯具图书保管与借阅职能,后拟改建增设古物陈列所,以便“保存藉征文献”[35]。
同样,面对文物保护的困境,官方也希望保护古物“以免流入异域而保国粹”[36],通过权衡图书馆全面发展的现实及博物馆与图书馆在职能方面的相似性,主张“古物中之有国宝价值者,若为官物,则设国立与地方官立之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及古物保存处所等”[37],将图书馆视为承担古物保护的合法机构。特别是图书馆的数量和分布范围远超美术馆等机构,使其在更大程度上承担了保存古代器物的职责。1928年,江西省政府出台《江西省征集图书文献条例》,将“各地金石”纳入征集范围,明确“凡征集之图书文献,均由江西省立图书馆保管之”[38]。江西省立图书馆在考察江浙、上海等地的图书馆之后,进一步认识到保存古物的职责,计划筹备“古物征存所”或“金石陈列室”,提出“遵照条例所征集之文献特品或就全部特办古物征存所或就一部附设金石陈列室,此亦图书馆职责所在,而他者早有筹议及之者也”[39]。在安徽省,“近年遇有古物出土,省府率皆令发该馆(安徽省立图书馆)保管”[40]。这都充分说明了地方政府对图书馆保护古物工作的支持。
无论是图书馆学人的使命自觉,还是地方政府的赋权,都是对这一时期文物保护困境的主动因应。在传统与现实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图书馆的文物保护实现了由“文献”向“实物”的深化,填补了博物馆职能的空缺。省立图书馆如安徽图书馆以“迄今尚无博物馆之设立”为由,提出“本馆为启迪民智、发扬文化起见,对于有关历史文化之各种实物资料,日事搜罗”[41]。县立图书馆如海盐图书馆针对流落荒野的地方古物,认为“在地方博物馆未成立以前,图书馆亦应从事搜罗,以资保存”[42]。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现代博物馆的专业性质,图书馆的因应具有一种过渡的性质,难以完全取代博物馆的地位。除山东省立图书馆等少数图书馆自创立之初即附设金石陈列所等机构收藏古物外,其他多数图书馆仅是在文物保护困境的影响下承担了古代器物的保护责任。图书馆团体实际上对二者的职能区分有着较清晰的认知。李小缘在提出省立图书馆附设博物院保存古物的同时,也提出“俟办理得法,即当扩充成为独立行政机关”。因此,在民国时期浙江已经成立省立西湖博物馆的情况下,省立图书馆认为“本省有省立西湖博物馆,凡古物金石原在该馆历史文化部征集之列”,而图书馆的金石收藏只是“以人事之因缘,间亦有承外界之赠遗者”[43]。足可见在已经成立博物馆的地方,除捐赠等特殊情况外,图书馆已经不再主动承担纸质文献之外的古物征集和保存工作。
4 结束语
近代中国古物外流的现实及古物保护的困境,激发了图书馆学人保存国粹的民族主义意识,促使其在保存古代典籍之外,自觉担负起保护古代器物的使命,实现了由保护“文献”向保护“实物”的深化,形成了图书馆参与近代中国文物保护的特殊面貌,也成为20世纪30年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尽管图书馆承担博物馆的功能并非近代中国独有,外国亦有类似现象,但是共同现象背后因应的是不同的现实情境。抗战之前,山东、安徽等省立图书馆及诸多县立图书馆积极征集、收购、保管流散古物,成为推动近代中国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此外,各级图书馆还注重辟室陈列和举办展览会,向社会展示所购藏的古物,积极开展社会教育,发扬传统文化,进一步深化了文物保护职能。
参考文献
[1] 魏征,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903.
[2] 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M]//苏轼文集(第十一卷).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59.
[3] 孙猛.郡斋读书志校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7.
[4] 浙江省立图书馆.发刊旨趣[J].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932(1):1.
[5] 李希泌,张淑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Z].北京:中华书局,1996:123.
[6] 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宣言[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3(1):1.
[7] 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国民党中央文化事业计划纲要[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28.
[8] 佚名.太原图书馆协会成立经过[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6):14.
[9] 喻友信.图书馆员应有之真精神[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4(2):6.
[10]林宗礼.图书馆的新倾向[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3(3):5.
[11]佚名.本馆三十周年纪念会纪[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3(6): 24.
[12]严文郁.美国图书馆概况[J].图书馆学季刊,1931(3/4): 321.
[13]蒋镜寰.图书馆之使命及其实施[M].苏州:中央大学区立苏州图书馆,1929:9.
[14]包遵彭.中国博物馆史[M].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4:2.
[15]曾昭燏,李济.博物馆[M].上海:正中书局,1947:4.
[16]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要求从重惩处盗掘古墓窃取文物罪犯的呈(1935年2月)[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638.
[17]佚名.全国图书馆设施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1(5):26.
[18]李建.近代中国文物主权意识的兴起[J].东岳论丛,2005(4):27-31.
[19]陈端志.博物馆学通论[M].上海:上海市博物馆,1936:8.
[20]国立历史博物馆.发刊辞[J].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1926(1):1.
[21]李济.西阴村的史前遗存[M].北平:清华学校研究院,1927:1.
[22]傅斯年.本所发掘殷墟之经过[M]//安阳殷墟报告(第二期),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389.
[23]中国博物馆协会.中国博物馆一览[M].北平:中国博物馆协会,1936.
[24]徐玲.博物馆与近现代中国文物保护[J].中国博物馆,2019(1):57-58.
[25]李小缘.全国图书馆计划书[J].图书馆学季刊,1927(2):210.
[26]镜.书评·博物院图书馆与地方文献[J].图书馆学季刊,1929(3):461-462.
[27]培.青岛文化建设:图书馆博物院地点接近公园[N].天津益世报,1932-04-22(7).
[28]佚名.新书介绍·博物馆学通论[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7(4):47.
[29]程焕文,等.中国图书馆史·近代图书馆卷[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71-79.
[30]史全生,等.中华民国文化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739.
[31]佚名.新书介绍·博物馆概论[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7(4):47.
[32]中华教育改进社.新教育·第三届年会报告号[M].上海: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622.
[33]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纪事[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8(2): 7.
[34]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致全国各图书馆书[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29(1/2):2.
[35]佚名.铜山县立图书馆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5(2):46.
[36]王世杰.教育部长王世杰致行政院呈(1934年6月7日)[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789.
[37]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古物之范围及种类草案说明书[M]//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文化(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636.
[38]江西省教育厅.江西征集图书文献条例[M]//江西省政府教育厅暂行教育法规汇编.南昌:江西省教育厅,1928:104.
[39]江西省立图书馆.考察江浙图书馆报告[M]//江西省立图书馆馆务汇刊.南昌:江西省立图书馆,1929:19.
[40]佚名.安徽省立图书馆二十二周年纪念[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5(1):6.
[41]佚名.一年来之安徽省立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6(1):10-11.
[42]佚名.海盐县立图书馆新讯[J].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4(2):6.
[43]佚名.浙省图书馆对于浙江文献之搜集与整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1936(6):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