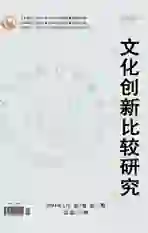中华文化对赛珍珠文学创作的影响
2024-10-18左月平孙莹
摘要:赛珍珠童年时期生活在中国并受中华文化熏陶,这对其创作观念的形成、题材内容的选择和作品的叙述手法均有深刻影响。赛珍珠从私塾教育与仆人口述等渠道习得中华文化,无论是儒家文化还是民间文化,都在赛珍珠作品中体现出其中华文化的涵养效果。赛珍珠汲取这些文化精华并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话语转化,将文化习得经历转化为文学创作经验,使得自己从故事讲述者转化为小说创作者,成为体裁形式意义的探索者。她因中华文化习得而对中国底层社会生活有了深入体验,从而以“格物致知”进行中国乡土题材文学创作活动。
关键词:赛珍珠;中华文化;习得经历;儒家文化;民俗文化;文学创作经验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8(c)-0011-05
A Study on Pearl Buck's Chinese Culture Acquisition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Creation Experience
Abstract: Pearl Buck lived in China during her childhood and was influenced by Chinese culture,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her creative concepts, the choice of subject matter and the narrative techniques of her works. Pearl Buck learned Chinese culture from private school education and servants' oral narration. Whether it is Confucian culture as a "great tradition" or folk culture as a "small tradition", both reflect the cultivation effect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Pearl Buck's works. Pearl Buck absorbed these cultural essences and transformed them into discourse in literary creation. The cultural learning experience was transformed into literary creation experience, which also enabled Pearl Buck to transform from a storyteller to a novelist and an explorer of the meaning of genre form. Because of her learning of Chinese culture, she had an in-depth experience of the life of the lower class society in China, and thus carried out her literary creation activities on Chinese rural themes with "investigating things to gain knowledge".
Key words: Pearl S. Buck; Chinese culture; Learning experience; Confucian culture; Folk culture; Literary creation experience
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年)3个月大时便随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从此开始了长达近40年的在华生活,主要生活在江苏的镇江、南京和安徽的宿州等地,度过了人生中至关重要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自幼在天然汉语社会语境中的成长经历为其系统习得中华文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来赛珍珠因中国题材小说创作,尤其是《大地》三部曲、《母亲》等作品获得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的作品主要聚焦中国乡村,展现了细节化的中华文化元素,这与她童年习得的中华文化知识影响是分不开的。她不止一次表达对中国及中国人民的深切情感,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肯定,表明中华文化对她的影响是多面且深刻的,是中华文化决定了她在写作上的成就[1]。赛珍珠习得中华文化的途径大体可分为家庭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两方面,接受的文化内容主要包括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代表的哲学文化和口述故事为主的民间文化。这不仅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素材,奠定了其人物原型和创作技法基础,也影响着她的体裁选择和创作宗旨。
1 在中华传统文化习得中明晰文学创作导向
一种文化对浸润其中的人的观点和实践有着极大的制约作用。私塾教育是旧时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主要途径,也是童年赛珍珠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渠道。中国文化浸润让她在具体情境下加深了对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解,直至将其内化为滋养自身的文化修养,进而成为其作品社会内涵的来源。
1.1 在私塾教育中熟知儒家文化传统
赛珍珠10岁时师从家庭教师孔先生,接受以儒家思想和行为规范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系统洗礼。“仁”学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等这些赛珍珠从小学到的中国哲学观念,后来均细节化地体现在她的中国题材作品创作中,筑造着她的创作观。她的中国小说注重秩序、和谐,推崇以忠孝仁义等伦理精神为内蕴的儒家文化,诠释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学传统。她曾表示:“从孩提时期起,孔子就影响我的思想,我的行为,我的个性。孔子是我的参考系。”[2]在一对一的家塾教育中,孔先生除了给赛珍珠讲解《四书》《五经》等典籍,也教她一些中国历史、风情民俗知识,指导她进行古文阅读和写作,深化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认知。孔先生还时常联系实际,表达自己对儒学的看法,讲解孔夫子的道德观和对当代的启示[3],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对儒家传统思想的接受。
林语堂说:“孔子将为家庭制度提供的哲学基础视为一切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基础,强调作为人类一切关系基础的夫妻关系、儿辈对父母的孝顺,强调祭祖坟、敬祖宗等宗庙祭祀。”[4]赛珍珠非常赞同这种强调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的家庭基本关系,对中国传统家庭中心地位的推崇在她的诸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如《大地》讲述的是王家三代人的家族史,《龙子》《群芳亭》等也都是以传统大家庭的聚合开始,中间穿插着包办婚姻、自由恋爱等新旧冲突,最后以家庭的分化为结尾。赛珍珠在小说中将“父为子纲”这种复杂的孝道传统置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刻画阐释,如王龙夫妇悉心照顾父亲,在父亲去世之后按照当地习俗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中国儒教的三纲中还有“夫为妻纲”,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伦理约束下,中国妇女的地位和独立性较低。从小生活在此种文化环境下的赛珍珠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在作品《大地》《母亲》《庭院里的女人》中塑造了“阿兰”“母亲”“吴太太”等一批恪守儒教妇女德行的中国女性形象。“母亲”在丈夫离家出走后,对瞎眼婆婆不离不弃,尽心侍奉。《结发妻》中的妻子“深明内则,受过良好的庭训”[5],有着孝顺老人、依顺丈夫等为妇之道,但终因满足不了留洋归来的丈夫对新女性的要求,惨遭抛弃后以自杀的方式维持尊严。透过这些角色,赛珍珠一方面表达了对中国妇女勤奋、贤惠、为家庭牺牲等传统美德的赞赏,另一方面出于对中国旧式妇女命运的关注和思考,客观揭示并同情她们在旧社会男权压抑下的艰难处境。这体现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本意识,即孔子所说的“仁”的现实意义,也是现代文学的“启蒙主义”。
1.2 以文学承袭儒者的“士君子”精神
受孔先生的教导,赛珍珠形成了影响其一生的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情怀和“爱人”之心。孔子提出“君子忧道不忧贫”,“士”理应承担起对“道”的传播和弘扬,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6]。赛珍珠自小目睹广大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阶层受欺凌、受剥削的种种不幸,为其坚韧、勤劳、善良的品质所震撼。由此,她认为“正是这些善良、坚强的农民,形成了中国的核心”[7],怀着“士君子”般关注黎民百姓疾苦的人本精神,以悲悯关爱之情塑造了一批典型的中国农民角色。《大地》中的王龙是中国传统农民的代表,他有着勤劳节俭、善良宽容、安土重迁等美德,同时也有着安贫畏命、愚昧落后、贪图享乐等狭隘意识。赛珍珠没有刻意丑化或美化中国农民,只是力求真实地表现这一群体的生活,探讨现代文明冲击下中国农民的出路,这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士人历来对现实的关注不谋而合。赛珍珠的早期作品对天灾人祸之于平民的影响总是格外敏感,哀民生多艰,也启迪读者思考如何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儒学命题。她秉持着作家细致体察社会民生的深重使命感和责任感,昭示着对中国“士君子”精神的承袭。
赛珍珠为儒家所倡导的士人精神及世界理想所折服,自觉地在文学创作中探索解决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渠道。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和而不同”的处事方式、“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容态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合相生理念等都是构成她中西文化和合思想不可或缺的精神给养[8]。面对中西文化碰撞,她站在文化多元立场寻求不同文化的共性,探索沟通的纽带,如在《东风·西风》中以异族通婚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方式。小说的结尾,桂兰哥嫂爱情的产儿的诞生象征着东西两个世界的融合。她希望不同世界的人能怀有宽阔胸襟和博爱精神进行异质文化的平等沟通,中西文化共存共荣,这显然是一种儒者文化心态。类似的思想在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四海之内皆兄弟》中也得到了彰显,这既是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接受,也是她尝试沟通中西方文化的特殊用意。她后来说道:“我从小就懂得应该把地球上的各个民族……都看成一个大家庭内不同的成员,这种观念是孔先生最早灌输给我的。”可见,对“天下一家”思想的认同和推崇,为赛珍珠日后成为一名世界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除了关注中国的妇女和农民,赛珍珠还关注近代中国年轻的海归知识分子,刻画了一群胸怀天下、有着救国抱负的中国知识分子。《同胞》中的詹姆斯是一位对中国有着强烈认同、满腔赤诚、立志回国为民服务的华裔留学生。面对现实和理想的冲突,经过一番挣扎和理性思考,他决定回到农村,探索一条扎根农村农民、服务大众的实践之路,完成报效祖国的历史使命。这个人物突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知易行难”的窠臼,具有探索性。詹姆斯所走的路,实际上是赛珍珠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归派”应该走的路[9]。这些描述和思忖既源于她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也是其承袭和践行从孔先生那里习得的传统儒者的救世情怀和中国古典哲学价值观所倡导的“士志于道”的精神基质的实践。赛珍珠说自己“不能忘记孔先生和他教给我的儒教伦理和一些高贵的思想”。“在孔先生绅士、贵族式的培养下,我形成了我的个人品味。”可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赛珍珠打上了生命成长的底色。
2 在“听中国好故事”中努力探索小说艺术
赛珍珠最早是从仆人们讲述的各式民间故事中接受中国文化滋养的,经此了解中国民间文学传统。保姆王妈讲的精妙绝伦的民俗故事、厨师讲的古典小说历史故事、说书艺人讲的和戏班子演的故事,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进而萌发了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讲故事”的形式进行小说创作的理想。这些仆人在赛珍珠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有原型基础。
2.1 在保姆讲述的民间故事中体验民俗文化
民间故事表现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是儿童了解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仆人们所讲述的故事为赛珍珠后期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资源,也使她无形中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学知识与故事叙述手法。中国传统的叙事方式并不强调完整的结构和高超的技巧,也不太注重故事情节的因果关系和上下文的连贯性,如同支离破碎的生活本性。赛珍珠认为,“生活中并没有仔细安排好和组织好的情节,没有主要情节和次要情节之分……我们不知他们的结局,正如我们不知自己的结局”[10]。她的代表作《大地》明显贯彻了这一创作精神。书中,尽管主人公乐天知命,但他们的命运却由不得自身,经常受战争、灾荒等外部冲击,这也和赛珍珠小时候听到的故事中的人物情节相似。
个体在童年时期可以通过民间故事进行文化习得和道德养成。赛珍珠小时候在中国的生活主要由王妈照顾,王妈也是讲故事的主体,经常给赛珍珠讲抑强除暴、劫富济贫的民间故事,有时候也讲一些神话故事或者自己的家族史。在跌宕起伏、妙趣横生的故事情节中,中国人淳朴善良、勤劳聪慧等优秀品德和朴实的民俗风情给予了赛珍珠美好的情感熏陶。后来她据此回忆,“乳母所讲的故事,给我的印象很深……使我爱中国,理解中国,并且使我相信中国民众和我们的血族相同”[11]。这让她对中国小说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兴趣,并不断深化对中国小说的研究。她在诺贝尔文学奖的主题演讲中说道:“我最早的小说知识,关于怎样叙述故事和怎样写故事,都是在中国学到的。”[12]可见,和谐的主仆关系为赛珍珠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这也是江南民间文化对其文学思维的直接影响。
讲故事是用语言描述事件内容及其人物联系,实际上是民间的文学形式,是简化的小说。赛珍珠本人对于故事与小说的关系也有专门的论述,“中国的著作中很早就开始包含故事素材。除开说书人和巡回演出的艺人,多少世纪以来,也一直有写下来的故事”[13]。虽然小说在概念上比故事更具内涵,但小说一般包括人物、情节、环境三要素,实际包含了故事基本结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大多以民间传说、故事为原材料加工形成,赛珍珠认为中国白话小说富有民俗精神。她在《中国小说》中作了具体阐释,“中国小说就是从这种故事并充满了几千年的民俗精神中发展起来的”,民俗精神就是中国的本质精神,也是鲁迅《中国小说史》中的认知延续。除了王妈,家庭厨师也经常给赛珍珠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的原型历史故事,其中精巧的故事设计、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逐渐让她领略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
中国保姆不仅是赛珍珠生活的关怀者,也是其中国文化的启蒙老师,用精彩的故事为她构筑了温暖的童年天堂。底层人民是俗语、谚语等民间文学知识的积累者,也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虽然仆人们大多数目不识丁,却善良聪慧,在赛珍珠看来平凡而伟大,“这些人是她了解中国世界的第一扇窗户。在她那些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中,很多故事都是从这扇窗中看到的”[14]。儿时与仆人打成一片的独特生活经历对赛珍珠的创作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后来她以智慧善良的仆人为原型,刻画了“王龙”“阿兰”“母亲”等真实自然的人物,挖掘出她从小在中国仆人身上体会到的深刻而温暖的人性。当然,赛珍珠对其缺点描写也毫不避讳,力求还原他们的真实生活,结合人物身份和社会时代背景的局限,反而使角色更具魅力。
2.2 从“说书人”到“小说家”的身份转化
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记忆很大一部分是以口述的通俗方式代代相传的,深刻影响着底层人民的日常口头交流方式。“口口相传的经验是所有讲故事者都从中汲取灵思的源泉”,在说书口述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小说植根于普通民众生活,这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决定了中国小说只有关注市井人生,才有生命力。早期赛珍珠接受中国传统文学熏陶几乎都是通过“非书面的”展现市井百态风貌的口述故事,正是民间文学的通俗性逐步塑造了她的平民创作观,使她很早就下定决心为普通老百姓“代言”。她甚至认为自己就是一名说书艺人,最终通过艺术锤炼成为小说家。
本雅明指出小说家与说书人的区别:“长篇小说与讲故事的区别在于它对书本的依赖……那可以口口相传的东西,与构成小说基本内容的材料在性质上判然有别。……小说与这类文体的差异在于,它既不来自口语也不参与其中。这使小说与讲故事尤其不同。讲故事的人取材于自己亲历或听说到的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转化为听故事人的经验。小说家则闭门独处,小说诞生于离群索居的个人。”[15]讲故事者所讲的故事多掺杂着个人或身边人的经历,将听来的经验与自身的经验相融合,通过艺术的创造性转化成为听者的经验,在古代这就是“说书人”。可见,“经历”与“经验”之间的转换关系是决定“故事”与“小说”区别的关键,而赛珍珠正是通过表述民间,进而实现通俗文学在城乡之间的现代性转换。故事是过往事情的话语形态,听故事的人能从先辈积累的经验中汲取智慧,而小说则多关注现世,激发读者对自身命运和现实的思考。赛珍珠不仅在作品中告诉别人自己的经历,也告诉别人自己的中国生活经验,给世人以教诲,从优秀的“说书人”逐渐转化为出色的“小说家”。她的作品语言十分口语化,不仅融合了从小听闻的各种民间故事、所见的各式中国乡村风貌中的他者经验,也渗入了她自己的童年经历及所思所感。在谈到《大地》的创作时她表示:“故事是久熟于心的,因为它直接来自我生活中种种耳闻目睹的事情,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正是为自己到今天仍热爱和景仰的中国农民和普通百姓而积郁的愤慨,驱使我写下了这个故事。”她继承了中国古典文学和口述文化关照平民生活的写作宗旨,对中国人民的熟知和同情驱使其以说书人的视角客观叙述故事,这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对其深厚的平民化影响。
除了创作观念和内容深受中国民间文学口述文化影响,赛珍珠的创作手法也以中国古典小说为参照系。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小说缺乏形式,赛珍珠却认为中国的古典小说不仅有“无形中的有形”的独特体裁形式,而且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具有优越性”,“真实地展现了创作出这种小说的人们的生活”[16],做到了艺术和生活的水乳交融。巴赫金认为,“伟大的艺术家应该学会用体裁的眼光看现实”[17],看穿并激活体裁的现实性和社会内涵,因为每一种体裁形式都是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手段,投射着作家对生活的思考和理解。赛珍珠以这种生活观所反映的朴素唯物主义视野,通过生活模仿实现小说结构的完整,体现了对中国古典小说形式的跨文化转化。
中国小说离不开民间口头创作,其特点之一是许多故事情节常常来自民间文学。民间故事在发展过程中融汇许多史籍、书面文学成分,为形成小说形式奠定基础。从小听闻中国民间通俗故事的赛珍珠深谙这种叙事模式,将中国古典文学小说的说书传统发扬光大。她借鉴民间艺人及说书人的创作方法,利用长期接触中国百姓社会生活的扎实经验,将自己的想象融入创作,写出了富有中国民俗精神的史诗性作品——《大地》,成功印证了这一创作手法。正如姚君伟所说,传统的和自然的叙述模式适合于一个讲故事的艺人,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赛珍珠实现了儿时的理想[18]。这种手法表现了集体的客观记忆,只不过是以作家个体的主观记忆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3 结束语
在中国日常生活与民间风俗的长期浸润中,赛珍珠完成了生活启蒙并触摸到中国民俗本质,结合她所受到的中国传统哲学濡染,最终成为承袭儒者精神、致力于为平民讲故事的中国题材小说家。无论是社会活动,还是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赛珍珠都坚定地站在中国普罗大众的立场上。通过早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丰厚经验积累以及对民俗的民间性、群体性等根本特征的把握,赛珍珠运用说书人讲故事的手法对此进行创造性转化,呈现出一个真切、立体的中国。她的文学创作不仅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还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通过她的作品,许多西方读者得以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增进了对中华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为推动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做出了重要贡献。综上所述,中华文化对赛珍珠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层次的,不仅为赛珍珠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感来源,还塑造了她独特的文化视角和思考方式,使她成为连接中西文化的桥梁和使者。
参考文献
[1] 朱希祥.全球化语境中的赛珍珠研究[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47-52.
[2] BUCK P S. China: Past and Present[M]. 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72.
[3] 裴伟,周小英,张正欣.寻绎赛珍珠的中国故乡[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4] LIN Y.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J].Journal of Nervous & Mental Disease,1937.
[5] 赛珍珠.结发妻[M].常吟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6]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 保罗·多伊尔.赛珍珠[M].张晓胜,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
[8] 叶旭军.赛珍珠中西文化和合思想探究[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62-67.
[9] 郭英剑.抒写海归派知识分子的发轫之作: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同胞》[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59-65.
[10]彼得·康.赛珍珠传[M].刘海平,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11]赛珍珠.我的中国世界[M].尚营林,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
[12]BUCK P S.The Chinese Novel: Nobe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Swedish Academy at Stockholm, December 12, 1938[M].New York:The John Day Company,1939.
[13]赛珍珠,张丹丽,姚君伟.中国早期小说源流[J].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20-27.
[14]叶兆言.走近赛珍珠[J].大家,1997,20(2):4-37.
[15]瓦尔特·本雅明.讲故事的人[M].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6]朱刚.无形中的有形:赛珍珠论中国小说的形式[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6-40.
[1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M].白春仁,顾亚铃,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18]姚君伟.论中国小说对赛珍珠小说观形成的决定性作用[J].中国比较文学,1995(1):8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