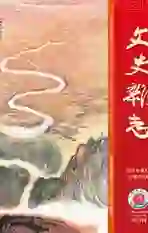宋代“白衣会”考述
2024-10-13屈斌
摘 要:“白衣会”的仪式活动以“僧仪”为基础,融合了更多传统的地方集体性活动。在宋代,“白衣会”的数量显著增加,但各组织仍保持分散和独立的结构,并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间存在横向联系。类“白衣会”组织主要活跃于政治、经济腹地区域,如北宋时期京师腹地的京东、京西、河北地区,南宋时期江南腹地的浙江、江西、湖南等地。这类结社组织在宋代历史上并不罕见,它们反映了社会变革和人们对权力与身份的回应与探索。
关键词:白衣会;在家佛教徒;秘密结社;仪式
“白衣会”是宋代的一种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它最初可能与天文现象或者死者祭祀活动有关,在宋代可能融合了多种地方信仰、宗教观念和道德准则,形成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由于其隐秘性和非正统性,历史上对“白衣会”的了解主要依靠一些零散的官方记载,很难找到完整和详细的记录。尽管如此,这并不能否认研究它们的重要历史和社会意义。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反映了宋代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人们对权力、身份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回应与探索。通过深入研究这些组织的性质、组织结构、仪式活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可以揭示宋代社会权力关系的微妙之处,进一步理解当时社会的多样性和权力的复杂性。
一、“白衣”的多重释义
“白衣”一词的语义大致可归结为两种:白色衣服及其引申义;某种天象预言。身份象征和认同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和文化共同建构的过程。不同时间、地域和群体的文化背景可能赋予“白衣”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宗教中,白色常常象征着纯洁、虔诚和清净,因此穿着白衣可能是对这些宗教意义的体现和表达。在宋代,摩尼教、弥勒教和佛教都与白衣有一定的联系。然而,对于白衣作为身份象征的接受和认同是多样化的,这取决于特定的背景和文化环境。需要考虑不同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以全面理解“白衣”作为身份象征的意义。
在宋代以前,摩尼教教徒的服装是以白色为特征的。如《佛祖统纪》载云:“(大历三年)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大历六年)回纥请于荆、扬、洪、越等州置大云光明寺,其徒白衣白冠。”[1]同样,弥勒教徒的装束也以白衣为主。唐玄宗开元三年(公元715年)颁行的《禁断妖讹等敕》就记载到:“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2]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亦考证称:“白衣为弥勒教之服色,起原当在元魏之世。而白衣天子亦为弥勒教之谣谶”,而历史上此时期之弥勒教又与摩尼教纠缠不清。[3]由于两教服饰皆尚白,因而过去不少研究宋代民间秘密宗教的学者一见到“白衣”字样,便将其归结到摩尼教或弥勒教的范畴,这无疑是值得商榷的。根据目前的研究,尚未发现将摩尼教或弥勒教徒单独称呼为“白衣”的记载。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白衣”更多地是指代这些教徒的服饰特征,而非特定的宗教称谓。
蒋绍愚认为“白衣”指俗人,是从“黑衣”指僧人相因生义而来的,“黑”与“白”是一对表颜色反义词,“黑”既可指僧,“白”也就受其影响。佛教徒通常穿黑色衣服,所以俗人被称为“白衣”。[4]在家佛教信徒也属“白衣”。如“虽为白衣,奉持沙门。至贤之行,居家为行”[5];“唯大目连,为白衣居士说法,不当如仁者所说”[6]。此中“白衣”指在家佛教信徒,而非特指白色衣服。
“白衣”一词也常被引申为没有功名或官职的士人。如“(胡)瑗以经术教授吴中,范仲淹前知苏州,荐瑗知音,白衣召对崇政殿,与逸俱命”[7]。这里的“白衣”指没有官职的士人。此外,为官府当差的小吏也常被称为“白衣”,如“白衣给官府趋走贱人,若今诸司亭长掌固之属”[8];“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卫则不然”[9]。
“白衣会”较早见于《史记·天官书》:“昴曰髦头,胡星也,为白衣会。”[10]后来随着占卜、占星术的发展,“白衣会”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象征意义。宋代的天文志书中也经常提到“白衣会”这一天象预言。《宋史·天文志》载称:“木与土合为内乱,饥;与水合为变谋而更事;与火合为饥,为旱;与金合为白衣之会,合斗,国有内乱,野有破军,为水。”[11]这是说,木星与土星相合,国家将有内乱出现,五谷饥穰,百姓食不饱腹;木星与水星会合,将有阴谋政变的事情发生;木星与火星会合预示着旱灾出现;木星与金星会合则为“白衣会”。显而易见,“白衣会”作为天象预言,常与内乱、饥荒、政变以及旱灾相提并论,表明它是王朝统治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灾祸或危机。[12]天文志书中的天象预言在当时被广泛应用,被认为能够揭示出天地间的神秘变化和人间的命运。“白衣会”作为一种预言,常常与社会动态紧密相连。人们相信通过观察天象的变化,可以预测到社会的变迁和可能发生的灾祸。这种天象预言对于统治者和人民来说,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也可能引发对“白衣会”等组织的关注和警惕。此外,“白衣会”也预言着与统治集团相连的人物的死亡。公卿大臣白衣而会,则是皇室遇丧的礼俗。有时遇有天灾异象,公卿也白衣白帽而朝。[13]
上述观点基本提到了“白衣会”性质的各种可能,那么宋代“白衣会”究竟属于何种性质的宗教组织?它具体的仪式活动有哪些?它们为何在宋代广泛兴起?为何又受到朝廷的严厉禁止?为何宋代的统治者特别纠结于这一问题?屡禁不止的背后是否表明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
二、宋代“白衣会”的性质及仪式
仅就史料情况而言,有关“白衣会”的记载并不多。不过,恰是从这些零星的记载中,我们发现这些规模并不大的“白衣会”竟活跃于整个宋代历史的舞台。这种现象是极为少见的,毕竟它们只是民间自发的分散的秘密结社团体而已,并不具备宗教的传承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确实需要更加关注“白衣会”的性质和仪式活动,以解释其长期存在的原因,更好地理解其在宋代社会中的角色和影响。
早在太祖朝,民间已经出现了“白衣会”的活动。《长编》卷八“乾德五年四月戊子条”载:“禁民赛神,为竞渡戏及作祭青天白衣会,吏谨捕之。”[14]“祭青天白衣会”显然是一种特定的宗教仪式。《三教应劫总观通书》述称:
世界上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者是燃灯古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度道人道姑,是三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度僧人僧尼,是五叶金莲为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15]
三教应劫即三佛应劫,苍天、青天、黄天为三大劫期,青天应劫救世之佛是释迦佛。结合这些信息,或可推断“白衣会”是一个在家佛教信徒的秘密结社组织。他们可能以祭拜青天、融入在家佛教信仰为主要活动。史料中提到的“赛神”和“竞渡”等,它们在民间常常作为一种宗教仪式或庆典活动进行。这些活动与白衣会的“祭青天”有关联,可能是“白衣会”成员在特定时刻和场合进行的一种仪式性活动,通过竞技方式表达对神灵的敬意和虔诚。这些活动不仅与在家佛教信仰有关,也可能融入了当地的传统信仰和民俗习俗。它们共同构成“白衣会”的宗教和社会实践,反映了当时民间宗教的多样性和宗教活动的丰富性。
宋仁宗时期,以“白衣会”为名号的结社活动开始频繁出现。宝元二年(1039年)四月,有官员奏称:“府界民间讹言有寇兵大至,老幼皆奔走入城郭。又乡民多为白衣会以惑众。请立赏募告者。”[16]《宋史·荣諲传》载:
太康民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号“白衣会”,县捕数十人送府。尹贾黯疑为妖,请杀其为首者而流其余,諲持不从,各具议上之。中书是諲议,但流其首而杖余人。[17]
如上可见,这一时期,“白衣会”已经被当作一个正式的组织,并且引起了官方的怀疑和追捕。然而,由于它被怀疑涉及“妖教”,导致官方的打击和限制。尹贾黯对“白衣会”表示怀疑,并认为他们可能与妖邪有关。他建议杀掉首领并流放其他成员,但荣諲持不同意见。最终,中书有关部门决定流放首领并杖罚数人以了结此案。根据这段史料的描述,可以得出一些关于白衣会的情况。首先,白衣会被描述为“事浮屠法”,而“浮屠”一词通常指代佛教。尽管摩尼徒“妄称佛教,诳惑黎元”,但史料中始终未见称之为“浮屠法”的记载。因此,可以初步推断白衣会是一个在家佛教徒的秘密结社组织。其次,史料提到有数十人被捕并送到官府,这表明白衣会当时的规模并不大。记载中还提到了“为首者”,这意味着白衣会内部可能存在会首或领导者。第三,史料中提到“白衣会”的成员会相聚进行祈福禳灾的仪式。事实上,“祈禳”也是宋代一些官员判定佛教徒的相关佛事活动是否属于“白衣会”的重要依据。《折狱龟鉴》记载了同时期蔡州的一起“依浮屠法相聚”事件,处理结果与太康县不同,据称:
吴育参政知蔡州时,京师喧言有妖人数千在州界,诏遣中使名捕者十人至,则请以巡检兵趋确山索之。育谓曰:“使者欲得妖人还报耶?请留勿往,此乡民依浮屠法相聚耳。可走一介,召之立至。今以兵往,人心惊疑。奈何?”中使以为然。召之果至,械送阙下,皆以无罪得释,而告者遂伏辜。此又矜谨之大者也。夫太康所捕有罪,而蔡州所送无罪,何也?事浮屠法相聚祈禳,名“白衣会”,法所禁也;依浮屠法相聚,无祈禳事,非“白衣会”,法所不禁也。苟非矜谨如此,岂能不滥如此哉?[18]
这个案例显示了当时处理类似事件时的一种差异化态度。对于太康县的案件来说,涉案人员是“白衣会”成员且有违禁的祈禳活动,因此被定罪。而对于蔡州的案件来说,人们仅仅是依照佛教法相相聚,并无违禁的祈禳活动,因此没有定罪。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在宋代,在家佛教徒之间的组织活动是相当频繁的,并且官方对这些活动持较为宽容的态度。这进一步突显了当时佛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普及程度,以及在家佛教信徒对于组织活动的需求和参与的意愿。
北宋中晚期以后,民间各种秘密宗教组织盛行,已经很难对它们作进一步区分。不同的组织之间可能在教义、活动方式和组织结构上存在相似之处,给统治者带来了困扰。朝廷采取了军事行动平定这些组织活动,并通过立法禁止它们的存在。然而,这些组织不断变换名称,改变活动形式,以继续传播其教义。南宋时期的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呈现出多样性和变化性。《宋会要辑稿》记载:
(绍兴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枢密院言:“宣和间,温、台村民多学妖法,号吃菜事魔。鼓惑众听,劫持州县。朝廷遣兵荡平之后,专立法禁,非不严切。访闻日近又有奸滑改易名称,结集社会,或名白衣礼佛会,及假天兵,号迎神会,千百成群,夜聚晓散,传习妖教。”[19]
这段史料描述了南宋高宗时期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盛行情况。尽管朝廷采取了措施进行镇压,但这些组织仍然能够通过改变形式和方式来继续存在和传播。根据这段史料的记载,官府认为这些组织与“吃菜事魔”有密切关系。这表明统治者将这些组织视为一体,认为它们是同一类别的宗教组织或者宗教现象。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教义、活动方式或组织结构上存在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以秘密的方式组织起来,进行夜间聚会和传授妖法的活动。这种相似性让官府难以对它们进行准确的区分,因此将它们归为一类,并将对它们的镇压视为一项整体任务。至于“吃菜事魔”的性质,日本学者竺沙雅章曾作如此阐释:
(此前的不少学者)一见记载中有“吃菜事魔”的字样,就一概视作明教,即摩尼教的资料。但是,资料的记录者对于诸秘密宗教的识别究竟明确到何等程度,尚属疑问。况且,当局取缔邪教,并不管它是否为摩尼教,而只在乎所有不可靠的宗教社团,因此在上呈的报告中并未对这些社团逐一严格区分。有鉴于此,即使记载中称为“吃菜事魔”,也不能一律断定它们是摩尼教。[20]
说得具体一点,“吃菜事魔”是当时各种民间异端宗教或团体的总称,摩尼教和“白衣礼佛会”都只是其中的一种。这里的“白衣”代指在家佛教信徒的可能性更大些。“白衣礼佛会”很可能是由在家佛教信徒组成的秘密团体,他们以白衣为标志,秘密地举行仪式和礼佛活动。他们的宗教实践可能结合了传统的土著信仰,其中“假天兵”和“迎神会”等元素可能源自当地的传统信仰。然而,由于白衣会的活动主要发生在夜间,也确实存在一些违法乱纪的情况,因此统治者对他们的活动持有负面看法。这也足见南宋时期民间宗教的多样性和官方限制异端宗教活动所形成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民间宗教的多样性反映了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追求和多元化的宗教需求;另一方面,官方对异端宗教的限制则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统治权威。
除了那些被官府认为与“吃菜事魔”有关的组织外,南宋时也存在一些遵纪守法的“白衣会”。它们可能更加注重佛教的修行、礼仪和道德规范,以及与当地民俗习俗的结合,以与被指责为学习妖法或进行不法活动的组织有所区别。这些遵纪守法的“白衣会”可能是以相对正统的佛教信仰为基础,秘密地组织起来进行诵经、忏悔和其他宗教仪式。它们可能以小组为单位,遵循严格的规章制度,并将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夜间,以避免引起官府的注意和干预。这些组织可能由有道德威望和经验的人领导,并吸引一定数量的信徒参与。不同地区的“白衣会”可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传统,以适应当地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环境。《夷坚志》描述了南宋时期鄱阳地区举行“白衣会”的情况:
鄱阳少年稍有慧性者,好相结诵经持忏,作僧家事业,率十人为一社,遇人家吉凶福愿,则偕往建道场,斋戒梵呗,鸣铙击鼓。起初夜,尽四更乃散,一切如僧仪,各务精诚,又无捐匄施与之费,虽非同社,而投书邀请者亦赴之。一邦之内,实繁有徒,多着皂衫,乃名为白衣会。[21]
从材料来看,此“白衣会”当为在家佛教徒结社组织。其由年轻人组成,每十人为一社。这表明白衣会是一个以小团体为单位的组织形式,旨在让年轻人相互结合,共同从事佛教修行和僧侣事业。仪式活动上,“白衣会”成员在遇到人家的吉凶福愿时,一同前往建立道场,进行斋戒、梵呗、鸣铙和击鼓等仪式活动。他们的活动于入夜后进行,直到UrTlpSO42KmTjP+jK+Lig7RhRQUXJb8Xg+kPjPkWOOo=四更天才散去。这些活动与僧侣的仪式相似,显示了白衣会成员对佛教信仰的认同和实践。“白衣会”的成员对仪式非常认真,精诚备至。同时,会社成员没有捐献或收取费用。这表明他们的参与是基于信仰和共同利益,而不涉及金钱交易。这一时期,“白衣会”的规模极大,以至于“一邦之内,实繁有徒”。这显示了白衣会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社会认可度。
这一时期,“白衣会”的发展再度引起统治者的不安,导致理宗颁布禁令来限制其活动。禁令中规定:“(宝祐五年正月)丙午,禁奸民作白衣会,监司、郡县官等失觉察者坐罪。”[22]这说明“白衣会”的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以至朝廷对其感到担忧,并采取限制措施。禁令的颁布可能有几个原因:首先,“白衣会”作为一个规模较大的秘密结社组织,其会员数量众多,活动范围广泛,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和不稳定因素。其次,“白衣会”以在家佛教信徒为主体,参与与佛教相关的仪式活动。在统治者眼中,佛教是一种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宗教力量,可能会对其统治地位和社会控制产生影响。再者,南宋时期,民间涌现了众多秘密宗教组织。朝廷对这些宗教组织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态度,对“白衣会”也会一视同仁。这一禁令的颁布也反映出当时朝廷加重了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和控制力度。
通过对以上史料的整理与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白衣会”的性质确实可以被认定为在家佛教信徒的秘密结社团体。在家佛教信徒在宋代的社会中占据一定比例,而“白衣会”作为他们的组织形式,为他们提供了共同参与仪式和交流的平台。第二,“白衣会”在发展过程中的规模逐渐增大,从北宋到南宋,“白衣会”成员数量显著增加,从数十人发展为“一邦之内,实繁有徒”。然而,各个组织之间仍然保持分散和独立的结构,这种分散性可能是为了避免被官府察觉和打击,从而使“白衣会”能够在禁令下继续存在。第三,“白衣会”的仪式活动不仅保持了佛教传统,还融入了当地的民俗仪式。这种结合使得“白衣会”能够更好地与民众建立联系,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同。第四,“白衣会”主要活跃于江南经济腹地区域。相对于宋代的核心城市,这些地区更为开放和包容,社会秩序较为松散,对于“白衣会”这样的秘密结社活动容忍度较高,从而使其能够在这些地方相对自由地发展和存在。
事实上,类似“白衣会”这样的组织在宋代并不罕见。北宋时期,京畿腹地已有各类民间秘密结社组织的活动。如张方平曾奏称:
臣闻京畿、京东西、河北民间传习妖教寝盛,比曾上言,乞加防禁。盖愚俗传习,初无恶意,渐为诱惑,因入于邪。州县官司因循,不切觉举,至于法寺议断,又亦例从宽典。以故愚民公然传习僧徒谶戒、里俗经社之类,自州县坊市,至于军营,外及乡村,无不向风而靡,所由来者渐矣。[23]
这段文献记录了京畿、京东西、河北地区民间传习妖教的情况。尽管最初传习无恶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受到邪教的引诱和影响。地方官府对此问题未能采取切实措施,宗教管理机构也以宽典处置,导致普通百姓公然传习邪教徒的预言戒律和淫祀乱经等,以致从城市到乡村,以为风尚。南宋时期,民间鱼龙混杂的所谓“食菜事魔”的“白莲菜”结社活动在江南是比较活跃的。[24]这类组织通常是基于宗教、信仰或社会团体而形成的秘密结社,旨在满足成员的精神需求、追求共同的目标或维护自身利益。这类组织往往具有独立性和自治性以及煽动性,进而威胁到王朝统治和国家统一。当它们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朝廷对其的打压乃至镇压则是难免的。
三、“白衣会”与宋代政治及经济腹地
除“白衣会”外,“吃菜事魔”“白莲教”等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民间秘密宗教被广泛认为兴起于宋代。这些组织的兴起不仅是社会变革的产物,也是人们对权力和身份的回应与探索,是对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一种自发性反应。通过秘密结社的方式,他们寻求集体行动,以维护自身利益、追求更好的社会地位和保护自身权益。这些组织为社会底层群体提供了一种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反映了他们对权力和社会秩序的不满和追求公平正义的愿望。
宋代是一个充满变革和转型的时期,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政治格局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唐以前,中国社会主要由世家大族控制,门阀氏族在地方上拥有广泛的权力和影响。随着唐朝的衰落和宋朝的兴起,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开始发生。一方面,唐朝的衰落导致了中央政权的削弱和分裂,使地方官员和地方豪强有机会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政治局势的不稳定促使地方精英寻求更大的自治和控制,以确保自身的利益和地方的稳定。另一方面,商业活动的繁荣带动了市镇的发展,市镇逐渐成为了经济交流和社会互动的中心。这使得地方人群逐渐从农业生产者转变为商业资本家和市民。他们通过经济活动成功积累了财富和社会地位,并希望通过掌握地方权力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此外,社会流动性的增加也为地方权力的重新分配创造了条件。唐朝以前,社会地位主要由出身和家族背景决定,世家大族对地方资源和权力的控制相对稳固。唐朝的动荡和社会变革使得个人能力和经济实力逐渐成为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这促使地方人群积极争取自身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从而通过形成秘密结社组织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愿景。
在宋代,类似“白衣会”的结社组织大都活跃于政治、经济核心城市的腹地区域,北宋时期主要分布于京东、京西、河北地区。这些地区都与开封相邻,与京师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政治腹地,它们承担着重要的行政和军事职能。中央机构、京畿驻军等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的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都相对复杂,社会动荡和政治变革也更为显著。类似“白衣会”的秘密结社组织活跃于这些地区,反映了当时政治腹地的社会变革和人们对权力的回应与探索。这些组织也可能是民众在动荡时期寻求安全感和形成凝聚力的形式之一。
南宋时期,类“白衣会”结社组织的活动重点转移到浙江、江西、湖南等经济腹地区域。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和商业发展为秘密宗教的兴起提供了土壤。第一,商业的兴起带动了地方就业机会的增加,吸引更多周边人口涌入,使得周边地区成为这些新兴市镇的物资供应地,造就了一种新的“中心—腹地”格局。第二,周边乃至更远地区外来人口的涌入,可能带来新的思维方式或价值观念,当然也包括宗教。就腹地而言,面对中心市镇的繁荣,心理的落差感以及对于财富的占有欲也在不断冲击他们固有的价值观念,这也为新的宗教的进入奠定思想基础。第三,从心理机制层面,流动也使得外出人口的不安全感、不确定感和孤独感增加。他们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会主动或被动寻求建立一种包容差异感的信任机制,于是,带有新的诉求的宗教出现成为必然。
佛教的社会化和平民化趋势、社会变革、文化传播和地方特色等因素共同促进类似“白衣会”这样的组织的形成和构建。在宋代,佛教逐渐从精英阶层扩展到普通民众。这种佛教的社会化和平民化趋势为“白衣会”提供了生成的土壤和基础。相对僧团,在家信徒更容易与普通民众建立联系,更能满足后者日常生活包括信仰的需求。在家佛教信徒注重修行和道德实践,而“白衣会”作为在家佛教信徒的秘密结社组织,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共同实践和深化信仰的平台。它不仅满足个人信仰需要,还增进了社会互动和集体认同。宋代大量出现的佛经翻译、佛教经典注释等,促进了佛教思想的传播和接受。普通民众通过阅读和听经等方式接触到佛教思想,形成一定的宗教知识和理解。这为他们加入“白衣会”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参与动力。另外,“白衣会”的形成和构建也与地方社会的特殊性和文化习俗密切相关。不同地区和社群可能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和仪式传统,“白衣会”往往因地制宜,融合了当地的民间信仰和习俗。这种地方性的特色使“白衣会”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和文化,增加了他们对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注释:
[1](宋)志磐撰、释道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卷四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962页。
[2](宋)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一十三,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88页。
[3]唐长孺:《白衣天子试释》,《燕京学报》1948年第35期,第227—238页。
[4]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5页。
[5][6](后秦)僧肇等撰《注维摩诘经》卷二,线装书局2016年版,第51页,第72页。
[7](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四十,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503页。
[8](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宋超等标点《汉书》卷七十二《龚舍传》,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89页。
[9](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079页。
[10](汉)司马迁著,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05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卷五十二《天文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74—1075页。
[12]王凤、张世超:《“白衣”溯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3期。
[13]林剑鸣、吴永琪主编《秦汉文化史大辞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1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乾德五年四月戊子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15]《三教应劫总观通书》,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3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5页。
[16]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卷三百三十九《宋绶一》,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21页。
[17](元)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三十三《荣諲传》,第10707—10708页。
[18](宋)郑克编撰,杨奉琨校释《折狱龟鉴校释》卷七,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30页。
[19]马泓波点校《宋会要辑稿·刑法》卷二,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3页。
[20]〔日〕竺沙雅章:《关于吃菜事魔》,载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7卷(思想宗教),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1—362页。
[21](宋)洪迈撰,何卓点校《夷坚志·三志壬卷第六·蒋二白衣社》,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12页。
[22](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十四《理宗本纪四》,第859页。
[23](宋)张方平著、郑涵点校《张方平集》卷二十一《论京东西河北百姓传习妖教事》,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24]黄公元编《杭州净土文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本文系河北省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9世纪以来冀东南地区的国家、市场与秘密社会”(HB19LS008)研究成果
作者:中山大学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