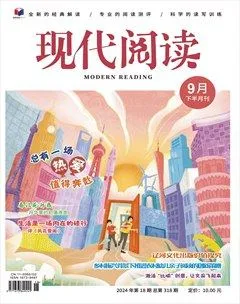《流浪的星星》看见疼痛:不再流浪
2024-10-09袁筱一
长篇小说《流浪的星星》是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2008年,勒克莱齐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已出版五十余部作品,包括小说、散文、童话等。
流浪,人的一种生存境遇
《流浪的星星》是一部关于流浪的小说:流浪之前的幸福时光,流浪,逃亡,永远找不到家的悲剧。如果我们相信神话模式的毒咒,人也许注定要流浪,而一旦走出家门,就永远也回不去了。
流浪如是成为人的一种生存境遇。具体到小说里,流浪的背景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才结束时的背景中,从主题上说,这里有一个用理性和逻辑解决不了的悖论:犹太人二战中惨遭屠戮,失去家园,然而,当他们终于得到所谓正义的垂顾,出发往自己的家园走去之时,又有另一批人不得不面临流浪的命运。
为什么在这个世界,就连上帝的选择也是如此“非此即彼”呢?
事实上,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青年时期在冷战氛围中度过的勒克莱齐奥深谙这个问题背后的历史。《流浪的星星》虽然从二战开始,却不仅止于二战。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犹太人与周围阿拉伯邻国的斗争达到高潮,中东局势变得越来越混乱和复杂。当然,勒克莱齐奥的高妙之处,在于他并不直接书写,从而避免了直接回答的尴尬。
流浪前的美好家园
1943年夏天,法国尼斯后方的一个小村庄成了意大利人管辖下的犹太人聚居区。艾斯苔尔,小说的女主人公就是从此时开始慢慢明白过来,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总是在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与他者存在的不同:宁静而美丽的生活被打破了,接下来便是恐惧、耻辱、逃亡和父亲的离去。还有逃亡中如梦一般的爱情和爱人的离去。
小说的开头一直在我的记忆里,美得如同我们在梦想没有破灭的时候所能够感受到的那样一种叮叮咚咚的欢愉:
而水就这样从四面八方流淌下来,一路奏着叮叮咚咚的音乐,潺潺流转。每次她忆起这片场景,她总是想笑,因为那是一种轻柔而略略有些异样的声音,宛如轻抚。
从我们的生存境遇而言,在我们没有被逐出家门之前,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有家的孩子。然而家在哪里呢?家和爱情一样,无论幸福或凄美,都只能作为记忆里的美丽而存在,仿佛勒克莱齐奥笔下这一段可以调动起所有感官的春天。
春天转瞬即过。冰雪融化之后,小说直接进入夏天,强烈的色彩扑面而来,用小说里的话就是“那样一种盈溢了全身,简直——叫人有点害怕的幸福”。而这样的幸福后面所掩藏的事实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眼看着他们的假期以死亡而告终”。而且,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夏天,就像是大洪水到来之前的美丽田园:
太阳灼燃着草地,连河里的石头都要烧着了,群山在深蓝色天空的映衬下,显得那么遥远。艾斯苔尔经常到河边去,到山谷的深处,两条激流交会的地方。在那里,山谷变得十分宽阔。环抱着山谷的群山于是更加遥远。清晨,空气依旧还平整、清凉,天碧蓝碧蓝的,然后到了下午,云聚集在北面和东面,垛在山峰的上方,卷起令人晕眩的漩涡。光影在河流清波的上空轻轻摇晃着。所有的一切都在轻颤,转过头来,水声,还有蝈蝈的叫声,一切都在轻颤不已。
人生以出走为根本前提
我们看到,小说大部分是以艾斯苔尔的视角展开的,没有那么多哲学的思考和关于战争、生命、死亡的直接追问,一切都只是一个即将丢失生活、家园、真理的少女的无辜。在《流浪的星星》里,人物和叙述者成了这个世界里的一粒尘土,在我们看不见的力量的驱使下四处飘摇。他们的视野是局限的,只是被逐出家园的这一路。尽管如此,作为存在的根本境遇而言,这局限的视野却已经相当完整。
文字的力量就在于,它可以描述一种模式,这种模式我称之为命——文字意义的宿命和其他意义的宿命有很大的不同——它规定了我们的人生永远也挣脱不了的一些边界和方向。于是你在看到好的文字的时候,一定会情不自禁地问,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呢?于是归根到底,有了罗兰·巴特的那句话:不是文本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文本。
艾斯苔尔,父亲眼里的“小星星”,在这个村庄度过了她最后一个幸福的夏天。虽然一切已经有所改变,可是动荡之前的美好总是或多或少会掩盖暗流汹涌的本质。在这幅暂时静止的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最传统的描述:费恩先生和他的钢琴所遭受的命运;美丽的,有着一头红发,与意大利宪兵队长私通的拉歇尔;温和、善良,偷偷帮助犹太人逃出法国的父亲;和父亲在一起工作的马里奥;和艾斯苔尔一起疯,对包括爱情在内等即将来到的一切似懂非懂的小伙伴;什么话也不说,深爱着自己的家的美丽母亲。
在战争的笼罩下,哪怕是这幅看似静止的画面上,日子的节奏也变得紧张起来,所有的矛盾都会凸现在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层面里。仿佛因为有恨,我们才更需要爱,而因为爱,恨会不断产生,不断激化。
德国人逼近,父亲离去——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艾斯苔尔终于要开始流浪的旅程。放在存在境遇里,我们会明白,无论有没有灾难,有没有战争,大写的历史是否投下或怎样投下它的阴影,我们总有一天会明白,家园并不存在,人生是以出走为根本前提的。
奔向“光明之城”的流浪之路
家园并不存在,这是怎样让人痛苦的领悟呢。艾斯苔尔开始流浪,她周围的人和她一样,踏上了流浪之路。流浪注定是人类的悲剧命运,原因在于:当我们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意识到家园并不存在的时候,我们总会一厢情愿地认为,在世界的某个地方,仍然还有“家”这样的地方在等待我们的归去。为此,我们踏上流浪的旅程。艾斯苔尔的流浪,一直是以那个“光明之城”耶路撒冷的存在为前提的。仿佛所有的苦难和眼泪,都会随着抵达光明之城而烟消云散:
我简直不能够想象,一个像云一样的城市,有大教堂,还有清真寺的大钟(我父亲说那里有很多清真寺),周围都是起伏的丘陵,种满了橘树和橄榄树,一座奇迹一般的城市,在沙漠上方漂移,一座没有平庸、没有肮脏、没有危险的城市。一座时间只被用来祈祷和梦想的城市。
因为有光明之城的诱惑,流浪会显得那么美丽。而且流浪在勒克莱齐奥的笔下显得尤为美丽。在流浪的路上,除了对光明之城的憧憬,还有对原有家园的回忆。艾斯苔尔想父亲,她想着父亲就在山里的某个地方:
在那高高的地方,他可以看见她。他不能下来,因为时刻还没有到,但是他看着她。艾斯苔尔可以感觉到他凝视她的目光,那么温和,可又是那么有力,像轻抚,像微风,和树间的风混在了一起,和卵石滩上水流的轻颤混在一起,甚至和乌鸦的叫声混在一起。
这是天堂里的目光,从上而下的,悲怜的目光。
勒克莱齐奥在《流浪的星星》里的慈悲在于,他没有借艾斯苔尔的眼睛和嘴亲述死亡。他也没有直接从艾斯苔尔的眼睛里看到光明之城并不存在的绝望。因此,流浪的这一路,风景尽管残酷,在回忆和未来的轻烟的笼罩下,一切却只是忧伤而平静的。
故事之外的相遇
在我们迷途的过程中,爱情即使在最美好的时刻也只能是一种力量,和宗教、大海、词语一样的神秘力量。它不是能够挽救我们于水火之中的避难所,它不代表光明,它和这个世界一样脆弱,抵挡不了死亡的来临。《流浪的星星》里,我们可以看到,爱情是自然发生的,没有先在的关于爱情的概念,没有刻意的规定,只是自然而然的接近、交缠和不能分离。在流浪的途中,艾斯苔尔与牧羊人雅克相爱,对于她来说,这爱情能让她继续流浪下去。
艾斯苔尔和雅克有了孩子,在战争的危险还没有完全离去的时候。而雅克也没有能实现他的梦想:学医,带着自己的妻子、孩子去加拿大,他甚至还没能看到自己的孩子就已经死了。肉体的流浪暂时告一段落,知道自己仍然结束不了流浪的艾斯苔尔已经没了眼泪。所有在那个不复重来的夏天里迸发出的强烈感情和色彩,经历了漫长的疲惫,经历了向往、等待和绝望之后,终于渐渐隐去,成为要找寻“疼痛痕迹”的平静。
从艾莲娜到艾斯苔尔——艾莲娜是艾斯苔尔的本名,而她出发去流浪之后,就真正成了父亲嘴里一直叫着的艾斯苔尔:小星星——这个流浪的故事只完成了一大半。
就在艾斯苔尔即将达到圣地时,她遇到了萘玛。这是故事之外的相遇,艾斯苔尔到达圣地,到达想象中的光明之城时,萘玛却是在出发去往难民营的途中。小说自然地转到第二条线上,萘玛的故事。
在难民营里,绝望是更底层的,是没有生存条件的绝望,饥饿,干渴,还有鼠疫。最底层的生活要求很容易将人的精神消减为零。人们只晓得等联合国的运粮车,所有的记忆和憧憬都让步给了眼下对于生存的基本要求:
在人们的眼里,开始出现一缕轻烟,一片云,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漠然。再也没有仇恨,没有愤怒,再也没有眼泪,没有欲望,没有焦灼。
为了生存,萘玛和萨迪跑了,这个故事没有结尾,只是在没有尽头的路上,萨迪指着雾后的群山说:“我们大概永远都到不了阿尔穆基了,永远看不到神灵的宫殿。也许神灵也已经离开了。”
也许,我们永远也回不到自己的家园了。
流浪与隐喻
故事始终只是勒克莱齐奥小说中的一个部分,一种形式。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小说从不交代战争的背景,以及悲剧的具体由来和发展。作为人物,没有正义与非正义,没有好与坏,对与错——早在写《战争》时,勒克莱齐奥就已经明白,战争从来不是个人的对错。
就是这样不曾交代任何背景的情节,在小说行至后半部时,也越来越有淡化的倾向。如果说,尼斯后方的小村庄还构成了一个人物事件交错纵横的世界,有爱,有恨,有强烈的色彩,有无奈和茫然,奴尚难民营却就只剩下了一缕轻烟。
同样,作为当代小说的最大特点之一,《流浪的星星》也毫无顾忌地突破了情节的线性结构,具体而言,就是打破时空,打破单线和唯一。小说的两条主线,一条是艾斯苔尔,一条是萘玛。这两条线唯一的交会之处是在艾斯苔尔抵达传说中的圣地,而萘玛被迫离开,踏上流浪征途的时候。这是一次于故事发展没有任何意义的相逢,却开启了小说的另一条主线。除了主题性作用以外,在结构上,它成为小说两个声部的连接点。也就是说,萘玛其实是艾斯苔尔的另一段生命。
如果说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办法同时拥有两种命途,小说里的人物却可以有,这是文字世界突破现实世界种种限制的一种方式。就好像在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中,雅罗米尔可以拥有另一种并行不悖的生命体验——克萨维尔。
要想将作品的主题嵌入读者的生命里,这样的文字总需要有一种隐喻的力量。隐喻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激活你表层的经验和感觉,却并不成为牢笼,把你框定在内容的牢笼里。在经验里,你找到了联系和想象。
而如果我们相信勒克莱齐奥的隐喻,《流浪的星星》里,在事隔40年以后,艾斯苔尔重新找回了泪水,她终于得以远离。泪水是我们看见了疼痛的证明吗?我不知道,不过,在艾斯苔尔将父亲的骨灰撒入草坡的时候,或许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她可以不再流浪。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文学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