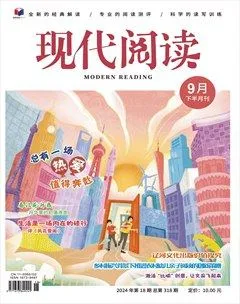春江花月夜
2024-10-09鲍鹏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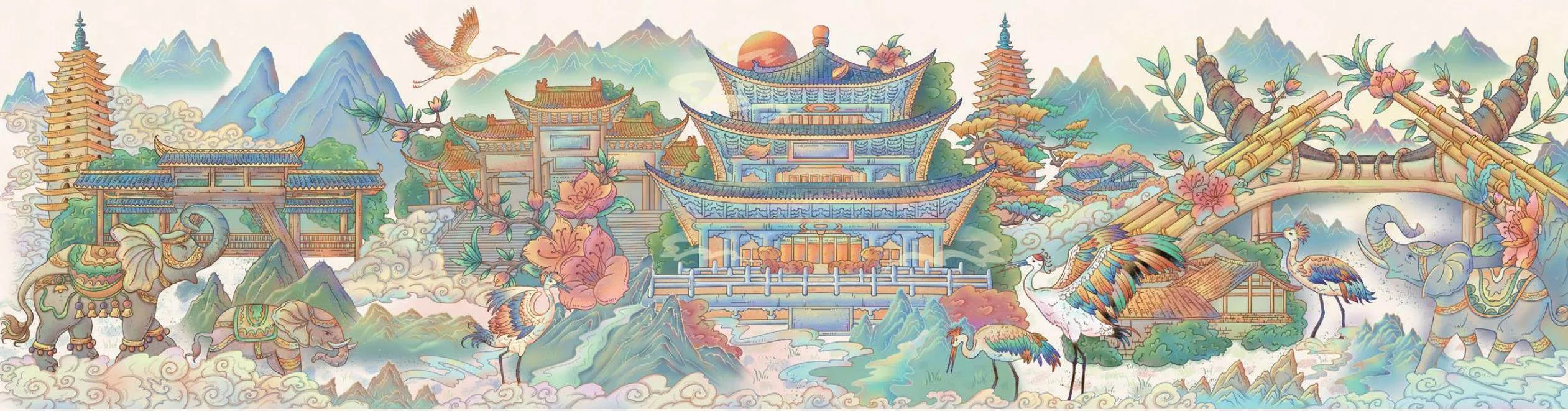
艺术作品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常常连作家本人也不能把握,他的笔往往不自觉地反映了某些本质。
正如曹雪芹无意中揭示了封建末世的没落命运一样,《春江花月夜》也在有意无意之中唱出了迎接封建盛世的赞歌。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诞生之时并没有“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声势。相反,在唐初至明初这一漫长的时间里,她倒像是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绝代佳人。作为一首乐府诗,她幸因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而得以留传后世,随着覆盖她的历史尘埃逐步褪去,她的光彩愈来愈明丽,终于升腾为一轮皎然独照的明月。明高棅在《唐诗品汇》中还把她列入“旁流”,至清末王闿运就称之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闻一多先生更称之为“顶峰上的顶峰,诗中的诗”。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样一个阔大神秘的景象吧——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潮涨海平,洪波浩荡,横无际涯。在这样一个浩渺神奇的境界之中,月亮从浩浩荡荡的大海里水淋淋地诞生了!我们顿时想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宏伟,但同时又感到惶惶不安,躁躁欲动,感受到这境界的扑朔迷离的神秘,历史好像又回到了神话的时代。诗人一开始就以强大的气势唤醒了人们沉睡的思考,紧接着,椽笔一横,把人们刚惊醒的注意力从垂直的方向——深、高的方向,引向平行的方向——远、宽的方向:
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随着月下春江的滟滟之波,人们想象着千里之外,万里之遥的月明之夜;想象着同在这千里万里的月光下的人们。隋炀帝的“流波将月去”或可是本句的导源,但是张若虚这里没有了冷漠不关己的“去”,而加上了热切关注的“随”和“何处”,这就表现了一种企图,一种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高空引向人的世界的企图。下文诗人的视线又从江流、月照转到流霜、白沙,我们的视线经过几次周折,终于回到了眼前切身的亲切的境界:
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
前面大笔挥扫,横空万里,此处却轻吟低唱,曼语缠绵。水绕芳甸,月照花林,空似流霜,汀如迷沙……多么温柔妩媚,情意绵绵啊!神的宇宙和人的现实像一对迷醉了的恋人,静谧而又热烈地偎依在一起了……低首之际,猛一仰天,我们不禁又大吃一惊:
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
江天一色,因月明愈见其迷茫;孤月一轮,因江阔更显其伶仃。它们并没有因为对方而消释了自己,渺然不可分,而是在对立之中更确切,更实在,更理想。这是多么阔大而凄清的意境,澄洁而惆怅的情绪啊。这轮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月亮,作为人化的自然现象,跃上高空,大梦初醒般地冷峻而深刻地注视着人生的悲欢离合,悔恨检讨着历史,思考着人生的真谛,历史开始清醒了,开始疑惑和探问了: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
这是一连串多么令人于神秘之中产生恐怖和震动的问题啊!从屈原《天问》的“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到张若虚的思考;再接下去是李白和苏轼的把酒相问,宇宙规律一直是中国诗人们探索的对象。如果说屈原《天问》显示出先秦理性精神在南方的萌芽;李白的问月是盛唐人睥睨一切凌驾宇宙的气概的表现;苏轼的问月又表露了对人生缺憾认命似的深深的痛悼的话,那么,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问月则是从魏晋南北朝之乱到隋的短命覆亡之后,初唐人走向封建盛世的先声。他从孤月独照,过渡到江月照人。人出现了!人,这个渺小的生灵,在宇宙笼盖的清辉下,影影绰绰而又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历史的焦距终于对准了人,这是多么巨大的历史跨度!
诗人不经意写来的“皎皎空中孤月轮”和“江月何年初照人”两句,这种人生价值的发现,却是历史经过了多少艰难才走完的历程!六朝人的人生观强调现时的享受,否定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责任,因而也否定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托名之作《杨朱》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表现。历史的气息启动了诗人的情思,他从广漠的宇宙中看到了人类的孤独;从自然的永恒中看到了人生的短暂。《春江花月夜》正深刻地表现了这种执着者的迷茫和深刻者的孤独,作者不由疲倦地喟叹一句:“但见长江送流水”。人的智慧能达到之领域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其现实性却是有限的。每一个时代的人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寿命的局限,只能切身地完成本时代的任务,人生中总要用一些失去的东西来偿付得到的东西。张若虚的时代已不是六朝玄思的时代,他属于实干的时代,不能因为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的东西。因此,他理智地把自己和自己这个时代铸为历史阶梯上的一个新的石级。
如果说汉末《古诗十九首》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由于不能控制住对永恒历史的迷茫,从而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产生了怀疑的话,那么,《春江花月夜》则正是由于理智地控制住了面对广漠宇宙而产生的虚无主义的思想苗头,才使他获得了面对现实的信念。张若虚从儒家的经世哲学出发,指出了单个人作为人类组成部分的价值和责任,从而把个人有机地组织进历史的链条和网络中,把个人融入了整个社会,才使诗篇充满着温存和希冀,充满着创造历史的信心和勇气。而把人们博大精深的智慧引向对人类自身幸福的探求,这才是时代的要求,是历史应有的转折。
白云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明月楼。
在诗人那里,天道和人道是和谐的;哲学和人学是一致的。他把对天道的探索转成对世俗人生的关注;把哲学的玄思引进伦理的责任——在深刻而紧张地思索着宇宙的奥妙时,他并不曾忘却人生的苦难和呼求。一片悠悠而去的白云,竟引出他无限的联想,并由这种联想生出无限的同情。白云自去,浦上愁人,在这明月高悬的夜晚,多少人扁舟天涯,又有多少人离恨高楼?旷夫怨女,都在他温暖的心胸中挂念着:
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
白云已逝,游子不归;帘子易卷,月华难收,捣衣砧上,拂去还来。一边是固执的月亮,一边是无可奈何的愁人。如果说开首的“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月”还是神秘的神,“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月”又过于冷峻和渺然的话,那么,这时,她正是亲切而又有点可恼的人!月亮也从高空走向世俗人间,和人们的思想感情完全融合了!
至此,月亮改换了三次位置,经历了两段巨大的历程:它从六朝宫廷的醉生梦死中跳上了冷峻而清醒的高空,经过了一连串的深刻的反省思考和探索,终于摈弃了神的诱惑,认识到人生最深刻的意义和责任,带着人的亲切走向人间,去抚慰人间那些痛苦,激发人间的向往。“孤月”是离开脂粉的必经之路,但这里的月是温柔的,是纯净的感情和澄洁的思想的表露。这位思妇意识到了月之可亲可信,她深情地说: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她的爱情是纯洁的,月华也是纯洁的,让纯洁的爱情随着纯洁的月光流照着对方吧!但这不过是少妇天真的幻想,她自己也知道这是幻想:
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
鸿雁自去,而月光并未随之去;鱼龙潜跃,亦不过纹圆之波,波静则月华亦敛。逐月流照,已是失望,而现实却还真实存在着: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可怜”者,犹情人也。春(或寓为青春年华)已过半而情人不归,这怎能不日思夜梦呢?
一个平凡的少妇所代表和象征的人世间的痛苦和向往,正是诗人对宇宙、历史、现实进行思考和探索的出发点和归宿。现在,诗人为他的智慧和勇气找到了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但是面对着荒芜的现实,他仍有不尽的迷茫:
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
江水流春欲尽,而一夜的好月也西斜了。终于在西天的海上,雾蒙蒙地不见了——从“海上明月共潮生”到“斜月沉沉藏海雾”,思考、思恋、幻想、痛苦,终于是“碣石潇湘无限路”。作者写月是为了写人,月“生”正是为了月“沉”,它自始至终都是具体的,又是象征的,从开始的宇宙美的象征,到中间的宇宙本质的象征,再到最后一层对人间苦难怜悯的象征,它是美,是真,是善。康德说,使我们震惊的,是我们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使我们震撼的,就是他所呈现的那一特定夜晚的星空和他心中的道德善。
到了这时,诗人广博而深刻的思想汇成了一条月下春江,带着他淡淡的花香般的忧郁的情怀,粼粼而下,浇灌、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这确实是“诗中之诗,顶峰上的顶峰”!在缠绵悱恻的温柔中隐藏着深刻冷峻的思考,包蕴着不可抑制的勇力;在忧愁伤怀的喟叹中有着激人奋起的呐喊,在温情的月夜下呼唤着时代的曙色。这正是这首诗的内在精神和魅力,也是她的价值所在。
是的,我们的诗人是多情的,是人道的,他还不忍心就这么结束了,在碣石潇湘的无限路上给人以无限悠远的怅望。因而他接着写道:
不知乘月几人归,
乘月有归人,这是多么伟大的乐观!历史学会了同情,历史也就要进步了。但是,诗人又是矛盾的,他在“乘月”前加“不知”表疑问,在“归”前加“几人”表其少。这种矛盾正是那个时代的矛盾:历史虽然已经开到了拓荒的前缘,但面对的旷野却正是一片荒芜。诗人惆怅,却并不绝望、颓废,透露出调和矛盾的愿望。这种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在六朝的宫廷诗中同样是找不到的。迷惘而不失执着,软弱却依然倔强,这也是一个时代前进的条件。
落月摇情满江树。
全诗由紧张而舒缓,由开阔雄伟而缠绵温柔。宇宙、历史、现实的紧张思考,到这里化成了一片温情,躁动不安的思想和感受得到了安抚和平静。
“什么时代产生了诗人?那是在经历了大灾难和大忧患以后,当困乏的人民开始喘息的时候”(狄德罗《论戏剧艺术》)。张若虚生逢其时,他正处在自汉末黄巾至隋末这几百年的大乱过后的喘息苏生的时刻。时代玉成了他,他也报答了时代。他以他的《春江花月夜》出色地喊出了时代的呼声,出色地表现了时代的憧憬。
如果李白、杜甫可以代表盛唐;那么,张若虚可以毫无愧色地代表初唐。他的《春江花月夜》在当时是一种预言,是一种信号,一种盛世降临前的信号;在以后,直至现在、将来、永远、是一轮明月,是一轮照耀万古的明月!
(来源:商务印书馆《中国人的心灵:三千年理智与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