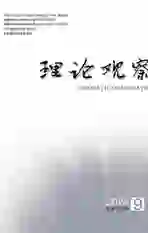论《论语今读》中的个体与群体
2024-09-29刘欣
摘 要:《论语今读》中的个体表现在对个体情感、个性、价值、命运的重视,同时重视个体间的关系;《论语今读》中的群体大致等同于家庭、宗族、国家、文化的制度规定。李泽厚认为,儒学阐发个体思辨理论,提供群体实践法则。个体与群体指向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内圣外王、仁与礼、教与政等概念。宗教性私德与个体情感、信仰、气质相关,社会性公德指道德规范、社会秩序等,私德与公德交融互渗,构成儒学的全面图景。李泽厚强调并重个体与群体,维护社会文化长久发展。他用《论语今读》构建“第四期儒学”,阐发自身理论。
关键词:《论语今读》;李泽厚;儒学;个体与群体
中图分类号:B8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9 — 0067 — 04
李泽厚重视儒学,将儒学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称为历史性积淀。《论语今读》通过《论语》的义理解读拓宽了儒学的核心思想,古为今用,促进其现代转化并提升其文化价值。李泽厚用“六经注我”的方式使其《论语》解读更具个性,也为自身哲学、美学理论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本文试图为《论语今读》中的个体与群体概念搭建架构,并在厘清其相互关系中进一步探究李泽厚视域下的儒学。
一、个体之“悦”与群体之“乐”
《论语今读》中的个体首先体现在对个体心理与人性情感的重视。李泽厚注重儒学中的情感因素,认为儒学培育人性情感,塑造“人性心理”,即“人化的情感”。这种情感是真实的、关乎此世的,对个体的日常生活有直接的积极作用。李泽厚划分审美形态为“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美学四讲》),此三“悦”也皆由个体心理生发。相比强调理性与道德规范,李泽厚对感性与情的重视更加顺应自然人性,尊重个人感受以及情感积淀中的个体人生意义。另外,《论语今读》中的个体体现于对个性、个人价值的关注。李泽厚认为,人们学习儒学的目的为变化气质并建立个性,探索个人主体性。普通人应当遵照儒学在“诗”“礼”“乐”中树立人格、启迪性情、完善人性的引导。他提出“情本体”,指导人们在真实的情感和情感的真实中获取艺术美与天人合一的体验,人们由此能身心健康、发展充分并自由决定命运。他认为,内心思想和外在行为如一,才能塑造健康的人性。他所提出的“人的自然化”范畴便指个体通过实现身体力量,回归自然,吻合宇宙节律获得天人交会的快乐。最后,《论语今读》中的个体体现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李泽厚解读儒学命运观,认为个体的命运是偶然的,但要有“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信念并在实践中做出努力,由此“知命”“立命”(《论语今读》),面对偶然的命运尽力做出正确选择,在有限中把握无限。“不患人之不己知”(《论语·学而》),个体命运首先存在于自我认知中,并体现于个体生存、价值与尊严。李泽厚认为儒学强调人的勤奋与韧性,以收获深沉人生。人应当“尽伦”“尽人事”“不怨天不尤人”(《论语今读》),培养责任感,实现人格成熟,把握个人命运。
中国自古是人伦社会,个体生命体验与人际紧密相连,个体修养根源于又超出人际情感。因此,对个体的强调离不开对个体间关系的关注。《论语·学而》篇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李泽厚认为“学而时习之”带来的“悦”关乎个体实践,“有朋自远方来”的“乐”则指主体间的1bf1969740af06e4f4ea3b31c6ca413a关系情感。《论语》中有君子“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孟子》中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孟子》)等说法。李泽厚认为把人的生存意义放置于此生的世间关系中是儒学与其他哲学的区分点,亲友关系既紧密关乎个体情感,又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关系与“主体间性”(《论语今读》)便是个体向群体的连接方式。重情感即重对方与双方关系,认为里仁为美,构建充满人间的情与爱的现实世界。[1]240-242在传统文化中,亲情、友情等人间情感和理性的社会关系是一体的。人是社会性动物,个体独立又紧密联系于群体、社会。《论语今读》解儒学既强调个体之“悦”,又重视群体之“乐”。
《论语今读》中的群体包含了家庭、宗族、国家、民族、阶级、宗教、文化等的规定、义务等。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写道,“儒学的观念、范畴远不是只供个体思辨的理论,而主要是供群体实践的法则。”[2]38“群体实践”一重普遍性,即提供社会各阶层能够运用维护社会和谐运转的普遍范式,其主体包括构成精英文化中的统治阶级与构成民俗文化的平民百姓;二重实践性,重视人们外在行为的体现、历练与实际社会政治功用,这明确表现了儒学的“实用理性”思维。儒学观点首先由个体思维在遵从感性中生发,逐渐经由时间与实践检验积淀、规律、规范至群体法则。李泽厚认为《论语今读》成书目的为解构并重建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传统,解构儒学的半宗教、半哲学特性,以及内圣外王、宗教性道德与社会性道德等含义,个体与群体指向也明显体现在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概念中。道德行为虽时常和个体的利益、快乐相悖,但宗教性私德能在个人的内心感受与坚守中得以体现,引导人们在敬畏中修习、完善自身。它在向理性客观规律靠近的同时,保留了人们心中神秘性冥冥中主宰的宗教性的部分。社会性公德是外在道德、政治的规范、秩序等。宗教性私德通常与塑造个体情感、信仰、气质相关,社会性公德则有关社会公平、正义、合理。如笔者认为,《论语今读》中的“礼”有多层含义,一指礼教,它是自古以来的行为准则、生活规范,是经长期检验的宗教性道德;二指礼制,它与仪式、制度等维护外在体制的公德概念紧密相关、具有长期性;二者共同构成了具有人文特性的“礼”。儒学在思想上较为宽容、兼容、灵活,但严格要求行为符合礼制规定,通过对“伦常道德”的规定与日常践行,使相对法规与绝对律令融为一体。宗教性私德具有自觉性、历史性,社会公德具有强制性、时代性。[3]74-76相对于从“让”角度劝导个体符合礼制,群体更偏向从“义”的角度,以外在强制力量治理群体行为。“内圣”(《论语今读》)与个体真实直接的体现相关,其主体便为微观个体,“外王”(《论语今读》)主体则为自王侯将相至平民百姓的宏观群体。群体之“乐”由先秦诸子百家延续至今的中华两千年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特性、积淀所保证。由荀子、董仲舒等人所发展的讲礼制事功、春秋大义,引道德、阴阳,体制分权,文官制度等保证中央集权国家统一的,注重历史与经验的社会政治思想;与颜回、曾参、宋明理学所延续传承的与人内心情感尊崇相关的道德形而上学两条线索是儒家的命脉,它们构成了完整的儒学。[4]72儒学第一条脉络主要汲取法家智慧,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中“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等思想;第二条线索吸收道家精髓,二者构成“儒法互用”与“儒道互补”的图景,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中华文化的心魂。
二、个体与群体之交融互渗
李泽厚强调个体与群体的一体性。首先,他认为“温情脉脉”的宗教性私德对公德具有范导作用,维系个体独立和人格尊严是构建社会性公德的重要资源。他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由个体感受出发,可被引申至人际、社会并成为社会性公德的基础。另外,“仁”“义”“礼”“孝”“信”等《论语》中多经讨论的范畴,它们引导的同一行为中往往包含了范导个体与群体的双重意义,从而具有个体与群体两层内涵。如儒学对“孝”的重视与推行建立在亲人彼此间感情与依赖共生的自然基础上,在对“孝”的践行加以理论指引与行为范导后,逐步将其促成社会伦理规范、道德律令及天理所在、宇宙规律;即由私德出发,构建公德。同时,公德对私德有规范作用,个体道德来自群体伦理;公德的良好维护为私德实现提供了良好环境,公德的共同遵守保证了私德的健康状态。私德顺应个体情感,但李泽厚认为应当将其加以节制和理性化;“温柔敦厚”(《礼记·经解》)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整个社会的有序温情。情绪、欲望被理性所规律、均衡,情理结合,以收获“合乎情理”“合情合理”的效果。宗教性私德为个体追求心灵完善的“绝对律令”,它是自由意志与本体所在,社会性公德则具有宽容精神,它不干预个体选择并保障个体权利,对个体价值选择保持中性立场;公德还具有共同准则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构成共同的时代、民族内容,促成个体维护公共道德的自觉。儒学从一开始便重视推广“教育”“教化”并精进其理念与方法,重视教化以助人伦,使公德与私德交融互渗,个体思辨与群体实践并向发展,维护大小传统,即精英文化与传统文化并行,统治阶级与平民百姓上行下效的稳定社会结构。儒学强调政教合一,“教”即宗教性私德,“政”即社会性公德,“教”讲究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柔性方法。由此可见,私德主要起范导性作用,公德起建构性作用。只有将个体与群体、宗教性私德与社会性公德之间搭建起符合人性的阶梯,才有可能实现儒家的文化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地国亲师”等说法,都是在此基础上探索出的合理伦理实践结构。虽强调道德、公德,但其建立基础并非为压抑与泯灭个体,而是在共同社会遵循的前提下探索人的自我与主体,个体与群体和谐浑融,不至偏颇也避免局限,才能达到儒学的“中庸”要求,维护制度与文化健康长久发展。李泽厚曾援引鲁迅的走的人多了才有了路一语,说明“人”既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群体,也是实在的个体。他认为实践中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将两者分立而视,避免以一方思路遮盖另一方。如从政凭借的是才干实力,而非“内圣”涵养,依靠个体的道德修养也难以真正维护社会正义等。
由此可见,《论语今读》中的个体与群体关系是两方并重,和谐平衡的。个体与群体相互指向,相辅相成。这在李泽厚对“内圣外王”“情本体”“主体间性”“人道之本”等范畴的论述中都能得到体现,这也体现了儒学的“中庸”之道与其奥义。李泽厚认为儒学并重“仁”与“礼”,儒学的“人道之本”外在为“礼”(人文),内在为“仁”(人性)。“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论语集注》),他认为“仁”的本义和爱紧密相关,爱首先生发于最真实基础的人性,既是原始的动物性反应,也是文化社会中普遍的行为。[5]10“仁”直接关乎情感与精神,所以能够在顺应人性中“引情入理”,建构和谐的心理结构,由此产生“治心”的效用,长此以往便塑造了民族性。同时,仁中有智,他认为“仁”具有公德效应。“礼”对感情有规范与塑造作用,同时能分化等级秩序,将各种人伦情感转化为理性的社会关系。他重视心理,认为人的心理也是文化积淀而来,若“仁”更多偏向保护心灵自由,“礼”则更多地维护了文化历史。由此可见,儒家的“人道之本”于内是自然人性,于外是社会行为。儒学并重个体心理与群体表现,融跨宏观与微观,重和谐,能通过对情感的重视柔性凝聚社会秩序,使“民德归厚”,并且使“人道之本”经上行下效得到推行与固化。比如慎终追远的习俗建立在个体对于亲人的感情,以及自巫史文化以来人们对祖先的尊敬基础之上。《论语今读》一书虽将个体与群体分开论述,但对双方施加了同等的关注,使得个体内心与社会取得了客观与和谐的平衡。《论语今读》对《论语》的重建体现在构建文化心理结构,达到或恢复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心理认同,使人获得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上,其旨归更加充满了对“人”这一具有个体与群体双重意义的关注。由此,李泽厚力图使人达到内在心理与外在行为合一,塑造真正的人性尊严。
三、个体与群体于李泽厚美学观的体现
《论语今读》是李泽厚建立“第四期儒学”的有效成果,他从自己的理论角度出发,为儒学搭建了更加完整的框架,由个人推演至家庭与社会,运用“情本体”“度”“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乐感文化”等重要范畴对儒学做出独特解读。同时,李泽厚反驳了过往《论语》解读或社会文化中过度强调儒学之群体性、权威性而忽视个体与情感、宗教性私德的一面,如新儒家的部分理论。综合个体相关内容在《论语今读》中较高的出现频率和较多的篇幅,以及对“仁”“情”等偏向个体概念的重视,相较群体,李泽厚更加重视个体。这一点符合了传统人道主义以及美学偏向感性学、人性心理的属性。面对“仁”“礼”始终难以融为一体的历史经验,他提出 “仁”“礼”分途的说法,分别探讨人的内心遵循与外在礼教,将不同构建作用到不同方面,从而真正维护个体独立与心灵自由。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反复通过提及其弟子所记载的孔子之行为、言语,说明孔子作为个体有缺点、情绪,会犯错的普通一面,展现其细微处的个体实践并表现其个体生命的生趣与尊严。比如孔子作为常人有言行不一致之处、与弟子朋友相处较为活泼,颇具个性活力,并不像后世塑造的那样刻板。
另外,本文认同李泽厚注释《论语》不是为了论述其本义,而在借孔子所言说明自己看法的观点,即使用了《六经》注我式的释读方式。[6]首先,《论语今读》解读的“情本体”重要概念体现了对“人”这一具有个体与群体双重意义的普遍关注。“情本体”与李泽厚对人性心理结构、人的主体性、人生观等剖析息息相关。它由充满感性的自然人性、情感表达生发,同时它对人性的重视是引情入理的情感塑建,即建设理性化的情感,这一点在“人化的情感”与“内在自然的人化”的情理结构中得以体现。人性心理为情与理的结合,它们是经由文化积淀后的深层心理结构;情理合一,可以恢复真正活泼、具体的人间情趣“情本体”,通由“悦神悦志”(《美学三书》)直达崇高。其次,李泽厚在美学研究后期重视巫史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由于自原始巫术以来人对自然神秘和天地敬畏的自然情感,相较于理,“天”能够更直接地与人的情感发生联系,“天心”“天理”的本体是情感。[7]79因此,巫史文化能够不断以历史形式流传在人心中,连接着宗教性私德;由巫史文化逐渐演化来的礼也成了中华文明的重要形式,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会性公德。经由巫史文化长久影响形成的心理积淀使得中华民族更能接受融合道于伦常日用的习惯。巫史文化既强调了个体,又强调了神秘主义的群体性质,在顺应“人”与“天”的亲密与信赖、个体对命运与天道的尊崇基础上,经由神秘性发挥群体意义上的宗教、历史作用,由此强化、扩充、塑造了礼制与文化规定及其权威。再次,“度”意味着“适宜”“合宜”,它强调恰当与分寸感;“度”即中庸,是中国辩证法的重点。《论语今读》中个体与群体、公德与私德、情与理等二分平衡的概念便体现了这一“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日常哲学。强调“度”有助于融合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矛盾,在个人心理与社会积极作用的统一中乐观面对生老病死,关注今生今世的外在行为、社会效应并对此持乐观心态,也符合李泽厚对于儒家“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传统中一个世界(人生)的宇宙观等内容的解读。最后,李泽厚强调儒学的“实用理性”特点并予以运用,以最贴合人们日常与实际生活的、具有工具性意义的行为指南为切口勾连个体与群体,并上升至理论与思维高度。这与他一直以来的“吃饭哲学”研究特点一致,穿衣吃饭为第一要务,由此不离实际,贴合民生。他始终关注人的实践、生存与发展,这与他从“前实践美学”经由“实践美学”至“人类学本体论美学”的研究路径相符。以《论语今读》为基础,他在晚年进一步关注并投身于伦理学研究。
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多以古之现象反观今日,关注当下社会现象,如知识分子地位处境与价值立场,学术环境等。他以中国的“现代性”为参照探索推进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良性机制,在宏观与微观双重角度重视了“人”,具有人文情怀。他完成了对儒学文化精神的全面解读,做到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相一致。他强调个性追求,个体的终极关怀,体现了实践论哲学、美学对人与人的目的的关注。李泽厚以佛教、基督教、西方哲学等观点与儒学原典进行碰撞,以对《论语》的注、疏、解与随性而发的形式展示了学术文本对传统文化转化性的创造的有力探索,以及充分汲取经典资源,构建、充沛自身学说,并始终立足于构建社会、文化,做出将理论应用于社会实际的大勇努力。
〔参 考 文 献〕
[1][2][3][4][5][7]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6]李健胜.李泽厚对《论语》的文本定位与思想阐释——以《论语今读》为中心[J].西北师大学报,2011(06):26-31.
〔责任编辑:侯庆海,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