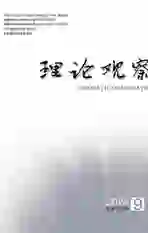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研究
2024-09-29郭万敏
摘 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极具时代价值。在数字阅读偏好的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已形成一定规模。本文在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重要价值的基础上,把握其发展趋势和厘清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之策。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策略
中图分类号:G2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9 — 0142 — 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极具时代价值,这令其成为数字化阅读推广的重要内容,并在技术赋能下朝着数字化阅读推广方向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但仍存在问题,针对问题提出解决之策正是本文的主旨。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的重要价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优秀精髓,是中华民族自春秋战国至明清时代几千年来的劳动实践创造积淀的,在新时代仍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结晶。[1]其所蕴涵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2]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积淀,表征着中华民族鲜明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先辈留给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在数字阅读给读者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与改变的当下[3],通过数字化阅读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的重要价值。
(一)实现文化整合和文化传承
在我国当前主位文化的构建中,数字化阅读推广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前结构”(“前识”)[4]的当代叙事转换,可发挥其文化解析辨异和协调统一功能,在与主位文化价值取向融合过程中,实现主位文化的文化整合和文化传承。
通过数字化阅读推广,可在阅读主体心理上形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巩固与叠加,在思维领域留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记忆“前识”。此“前识”便构成了阅读主体对其他文化潜在的解析辨异能力,在现实的文化碰撞中,解析“他者”文化,进行“优劣”、“好坏”、“先进与落后”及文化地位的辨异,在解析与辨异过程中旨在突出主位文化及其价值观,使文化的整体实现取精华、弃糟粕的系统优化,并自觉抵制劣、坏、落后和腐朽文化,防被其侵蚀和准确把握各文化在主位文化中的位置。譬如“吃苦耐劳”优秀传统文化“前识”对当下存在的“享乐主义”腐朽文化在“体化实践”时所体现出来的解析辨异和自觉抵制与抛弃。
要被主位文化所整合,除了上述的解析辨异功能外,还需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主位文化的协调统一。在数字化阅读推广中,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在形式、内容和价值的当代转化后,使阅读主体对“我们之所以是我们”等问题予以情感化回答,令“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5]等精神内核成为阅读群体引以为自豪的共同记忆,并在与主位文化的价值融合中构筑起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成为主位文化的强大支撑,实现与主位文化的协调融合。协调融合的目的是走向统一,统一源自“合法性”。就如伽达默尔所认为的“历史认识是从此在的前结构得到其合法性的”那样,那些在几千年的劳动实践中形成的“大同”、“小康”、“幸福”等文化记忆便成为当前主位文化中的诸如“全面小康”、“共同富裕”、“中国梦”等价值取向合法性的历史文化依据,为主位文化提供了合法性辩护,实现文化价值取向的融合统一。
文化整合的目标之一是实现文化传承。文化传承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根本,中华民族历经千年而不绝的根本正是中华文化的代代接续传递。受多元文化思潮影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代际递减加速,且面临被阻断和歪曲的风险。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的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烙印着我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轨迹,蕴涵着人们对“仁爱思想”、“民本价值”、“诚信道德”、“正义行为准则”、“和合处世之道”和“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承载着恒定向上的价值观,展示着我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和家国情怀。通过数字化阅读推广,在推广主体、内容与阅读主体交流互动的信息、知识和情感交流中,完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史缩写和完成内容、精神与价值的当代转化的经历和提炼,在阅读主体心理上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忆的共识建构,使阅读主体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掌握其内核与精髓,“体化实践”其价值理念,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人们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进而形成文化认同,实现文化传承。
(二)促进国家认同
共有的文化背景在公民国家认同建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习总书记也强调“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民族的基因”,其所蕴涵的哲学思想、价值观念和科学智慧正是中华民族形塑“我者”、区别“他者”和抵御“文化虚无”的精神标识和增强民族成员的团结感的国家认同基础。根据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可借助象征符号离开它的承载主体存续[6],且通过一定方式便可传播开来,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从中获取国家认同意义阈值。然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国家认同的“意义阈值”正面临传承代际递减和在文化虚无主义冲击及数字阅读娱乐化、功利化中不断式微。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可唤起、重构、强化和刻写人们的文化集体记忆、情感、价值和意识,令其在文化记忆复归中确认自我的国家身份。[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阅读主体那里的记忆重构本就是以促进国家认同为目标归旨,这是我们国家根据现时代价值理念,有意识地选择和进行记忆重构的结果。在数字化阅读推广中体现为遵循从“真实历史”到“效果历史”的“以史释‘此在’”的诠释逻辑;在话语建构上体现为从“传统文化”到“优秀传统文化”再到“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的转变。如此,在数字化阅读推广中就会将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历史情节、符号、精神、情感、价值等赋予时代价值的“效果历史”后,借助于数字媒介载体呈现于阅读主体面前,以符号展示、话语沟通、场域复归等途径唤醒阅读主体的文化集体记忆,帮助其确立“我之我在”的身份定位,在价值引导、情感共鸣中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忆的情感皈依,在“体化实践”中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集体记忆内化为个体记忆、外化为实际行动,进而转化为国家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感,形成国家认同。譬如在CCTV-1推出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以国家领导人讲典故的方式赋予优秀传统文化历史本体所诠释的先辈们对“小康”、“大同”的追求,在赋予其新时代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效果历史”后,可令阅读主体认识到“共同富裕”是国人一直以来的理想追求,如此就可形成向心力、凝聚力,以此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忆裁决和意识驯化展现过程,同程潜在规训阅读主体政治文化价值观,并建构起对国家的认同。
(三)助力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多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指导意见,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关法规政策予以落实,并大力度实施以资金扶持打造传统文化IP的方式发展传统文化产业。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1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46%,其中传统文化产业占比有明显的增长幅度,正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随着支持力度的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步伐加快,各相关主体纷纷借助技术赋能,贯彻落实数字化新兴产业发展战略理念,推动文化向数字文化升级,涌现出大量的“数字+传统文化”的产业与服务。特别是在一些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较多的地方,地方政府已组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作为吸引人的一项品牌创新和文旅融合的典范[8] 。譬如河南、山东等地依托数字技术,创建起虚拟现实文化景区、数字文化博物馆、数字文化纪念空间等新业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阅读推广品牌创新上,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从中吸取养分,提炼体现民族精神气质的文化内涵。如《新神榜:杨戬》《大鱼海棠》等动画电影,以“封神宇宙”与“生死轮回”的东方哲学观,令传统文化IP电影再度进入大众视野,引发持久的市场热度和经济价值。
一些地方推出“传统文化IP+数字化+旅游”战略,以“一机游”、“码上读”、“一秒入画”等沉浸式交互体验、数智导览新型文化旅游服务等提升了中华优秀文化旅游产品质量,增强了大众的体验性和趣味性。让阅读主体在传统文化数字体验馆感受“时光带不走的乡愁”,玩一场传统文化剧本杀,体验一下古人所经历的种种田园风光、诗情画意和惊心动魄[9];“一秒入”“清明上河图”、“金陵图”,看尽汴京人民的生活状况,领略金陵城市风貌,“感受民族的悠久历史”;在各种“神话网游”中尽情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实现其经济价值,助力国家的经济发展。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的发展趋势和存在问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的发展趋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令各推广主体纷纷将其作为阅读推广工作的重要内容。实践中,数字信息时代阅读主体数字化阅读倾向愈加明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朝着数字化方向发展,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化阅读推广联盟正在加速发展。自我国《公共图书馆法》(2017年)明确规定公共图书馆要把“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职责任务后,各地图书馆便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作为一项重要服务内容,在探索中形成了图书馆阅读推广联盟。随着政府、社会、个人加入及网络传媒、数字出版机构、数字技术服务中心和第三方数字阅读平台等新生传播力量的加入,各新旧推广主体纷纷本着创新合作理念和依托技术赋能,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触发点,推动阅读推广主体朝着跨界联动方向演进,数字阅读推广联盟正加速发展。实践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常以“主题内容”等形式置于各数字阅读联盟推广工作范围内,譬如“吉林数字阅读联盟”、“网络书香·阅见美好”APP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近年来也兴起了专题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阅读推广联盟,涌现出诸如“国风”、“古书之美”等数字阅读APP。
随着数字化阅读推广进程的加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主体也正加速朝着跨界数字阅读推广联盟方向发展。比如各地依托图书馆,联合学校、文化传媒、出版社、社会机构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传统经典数字阅读资源扫码读”、“春节特别阅读”等阅读推广活动。事实上,数字化阅读主体的跨界联动本就是数字化阅读时代乃至未来元宇宙阅读时代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未来将会呈现出由政府部门、公共图书馆、学校、家庭、领域专家、科研机构、科技公司等,构建起跨界多元主体的数字阅读推广联盟。联盟成员在阅读推广中发挥各自的功能,实现包括内容创新、形式创新、精神提炼、价值引导和提供技术支持、推广渠道、推广载体、推广策略等在内的功能模块,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的规模化和内容体系化。
第二,阅读内容数字化形态朝立体化方向发展。数字化阅读推广定然要面临完成阅读内容呈现形态的由传统向数字转化的浩大工程。当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内容的数字化转化主要方式是对原有文本镜像化、数字产品化、数字化处理再造,或直接数字原生化生成[10]。数字化后的呈现形态主要包括电子图书、有声读物、数字绘画、网络动漫、网络游戏、影视、短视频、数字音乐和数据库等。同一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又常以样态叠加形式呈现,这在近几年各出版社以“国学经典”为主题,推出融“文、图、视、声”于一体的一系列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读物中得到较好的体现。以数字信息时代为契机,现正逐步形成了以数字图书为主,数字融媒体和数字文创衍生产品为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立体化呈现形态。譬如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美术馆等联合举办的“客中月光照家山——北京画院藏齐白石精品展”(展地为湖南美术馆)就是在数字技术赋能下,实现包括“序章”、“礼遇白石”和“万竹山居”、“五出五归”、“一花一世界”、“白石画屋”、“白石花园”五篇剧情的场景复原,打造了一场时光回溯,带阅读主体走了一程齐白石走过的人生之路。
第三,复合式数字推广渠道构建正在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渠道主要有单渠道、多渠道、复合渠道三种类型。在具体的阅读推广中,借鉴于营销理论,推广主体会依据推广环境、推广内容及阅读主体的不同而选择最佳的渠道类型。其中复合式数字推广渠道能灵活地将渠道并行、渠道承接、渠道派生等多种渠道融合路径进行整合配置,能实现更具丰富、创新、多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11]和提高阅读内容的传播速率、转发率、分享率和覆盖率而被越来越多的推广主体所选择。这样,同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就会以不同的形态或以相同的形态在各大网站、社交媒体、阅读APP、公众号、官方媒体等不同的数字阅读推广渠道上传播。比如“中华经典主题阅读推广”就是典型的复合式数字阅读推广。该主题以电子语音书、动画、解读视频、诵读视频等形式广泛在各数字阅读推广渠道上传播。随着智能化新型阅读终端的发展,数字阅读场景将不断拓展,推广主体也在紧紧抓住这一契机加快与新兴社交平台的合作运营,正在实现多层面、立体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复合渠道式的推广,以获取更多的阅读市场。
第四,元宇宙阅读模式初现。元宇宙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的互动沉浸呈现形式正悄然兴起。早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宇宙阅读模式多以数字阅读体验馆的形式出现,而5G阅读、智能阅读、VR/AR阅读等单一或组合式的元宇宙阅读模式已初具规模。从第十一届到十四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展示的产品中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宇宙阅读已得到进一步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咪咕数字传媒探索的“全时在线”、“全息交互”模式,“挑灯工作室”创新的互动沉浸式体验,都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其传播的重要内容,并致力于打造更多如“剧本杀”、“影视类”、“互动剧本”类的有强社交属性的互动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内容,现已有如《墙头马上》这样推广昆曲的推广品牌。
随着“元宇宙博览会”、“元宇宙论坛”、“元宇宙数字出版”、“元宇宙文化峰会”等相继出现,“元宇宙+”概念“热”起来了,“优秀传统文化+元宇宙”也在领域内“大热”,各阅读推广体借此联合打造出《清明上河图》《金陵图》《挥扇仕女图》等“博物馆数字化+元宇宙”的阅读推广模式,其中《清明上河图》运用业界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动作捕捉技术、沉浸式多感官交互技术等打造了一个沉浸式文化体验场馆,并融合了元宇宙MVS概念、VR虚拟现实、AR增强现实、人屏互动、沉浸式展厅、全息投影、数字孪生、人工智能AI、NFT、国潮文创、文学艺术和研学教育等内容。《金陵图》通过Unity引擎实时渲染技术,实现阅读主体可创建自己的角色,“一秒入画”亲身感受金陵盛世的无限风华,体验第一人称视角的画中漫游,在“生意盎然”的金陵城里当一回“宋朝人”。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存在的问题
自1997年“榕树下”网站上线至今,我国数字阅读兴起已有二十多年。早期兴起的网络文学融合了国学经典、诗歌、节气、刺绣、曲艺、茶艺、中医、制瓷、园艺、服饰、饮食等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以各种方式重构组合、活化创新,通过数字化阅读渠道推出一批优秀作品,后期出现了直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元素的专题数字化阅读推广。不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从传统转向数字化终是处于探索初期,还存在一定问题,主要体现为:
第一,推广主体联动不足和技术人才“紧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阅读推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发挥各推广主体所长,持续联动合作方可完成。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及主体间联动合作意识不强等原因,使得现有的推广主体联动合作多被限定在同质、同单位里,大范围的跨界、跨区域联动合作有,但较少,尚未形成多元主体良性互动的合作式推广格局,这大大削弱了阅读推广力量,推广的持续性不足,规模化、体系化的阅读推广主体联动尚未形成。
“技术赋能”是数字化阅读推广的核心命题之一,故需多样化的技术人才参与其中。在一定程度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具有公益性,经济效益相对不高,这就较难令网络传媒、数字技术服务中心等推广主体主动去技术赋能优秀文化阅读推广。图书馆、政府、学校等作为阅读推广主力,一方面,常因岗位设置、管理、技术开发资金不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技术人才引进不足,较难形成技术合作团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转化较难有突破;另一方面,受知识产权、版权、技术专利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体制内有限的技术人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阅读推广中所发挥的功能相当有限。可见,技术人才并不紧缺,只是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导致体制内技术人才紧缺,体制外技术人才不能有效整合,而显得优秀传统文化数字阅读推广“人才紧缺”。
第二,数字阅读内容供给和品牌创新不足。在激烈竞争的数字化阅读市场环境里,各推广主体多以供给阅读主体所喜爱的内容抢夺市场,那些知识性的内容较少去挖掘开发和供给,即使是在特定仪式操演的类如“春节”推出了专题式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但新颖度、吸引力仍不足,常表现为一种知识宣教而被阅读主体所舍弃。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多、数量大,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专业性,实现大范围数字化整合也是困难重重。譬如因人力、财力不足,整合意识薄弱及面临跨部门、跨地区协调配合等问题,使得相当多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未能实现数字化整合;受经济利益的影响,一些阅读推广主体倾向于蹭热点,频现同一主题的低水平重复性的数字化产品;受专业水平的影响,在内容、精神创新上存在明显不足,频现较多“有形无魂”、“无形无魂”的庸俗化数字化产品;受数字化阅读娱乐化、流量为王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平台甚至出现歪曲、恶搞优秀传统文化的情况;数字化阅读开发在顶层设计上没有长远系统的规划,内容供给尚未形成体系化和规模化。如此种种导致在数字阅读空间里,优秀传统文化供给偏少、质量偏低,不能满足阅读主体的阅读需求。
品牌创新上,一些推广主体虽一再提出诸如“传统文化+技术”、“让传统文化活起来”等品牌创新理念,也推出了“中华传统经典动漫”(“大闹天宫”)、“优秀传统文化+元宇宙”(“清明上河图”)、“品牌优秀传统文化有声读物”(《甲骨文》)等品牌。但是,受技术主义思维的影响,在运作中过于注重科技元素的堆砌和强调推广形式的新颖。此做法在推广初期确实能吸引阅读主体,但由于对品牌化运作重视度不够,致使创建品牌的质量偏低、持续性不足,未形成品牌集群效应。如此,即使通过各种“技术花式”吸引了阅读主体,也常会因此不足无法满足阅读主体对阅读的高质量诉求而失去阅读市场,阅读生命周期相对较短。
第三,技术赋能给阅读主体带来“信息茧房”困境。技术的发展引发信息传播媒介领域的全方位变革,全社会已然进入融屏时代。在融屏里,每个数字阅读主体都被“数字化”,都有自己的“数据空间”,通过大数据算法机制的介入,可准确掌握阅读主体在阅读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偏好。每当推广主体在数据库里透过屏幕选取阅读主体阅读、浏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据基点时,都会在完成信息过滤后将常被阅读,或高频次阅读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优化后,在常用或高频次使用的推广媒介中再投放。如此经过推广者与阅读者间的不断“输出—反馈”的循环,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内容通过媒介渠道更加精准地传播出去,由此带来靶向性更强和可实现内容二次到多次传播概率,令阅读推广更具有持续性。但此算法推荐也会借助“回音室效应”和“过滤气泡”,将阅读主体困在“信息茧房”,形成思想圈禁,致其观念固化、认知单一化、信息窄化和圈层化,一定程度上阻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内容传播的路径,阅读主体也将沉溺在自己的“回音室”、“气泡”打造的信息“茧房”中“狂欢”而不能触及“房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的策略
与传统阅读推广一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策略的核心问题仍是实现阅读需求与供给的高适配以“抢得”更多的阅读主体。应于此,基于上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发展趋势,针对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如下策略。
(一)政府主导成立数字阅读推广联盟合力“发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具有价值规训的特殊意义,政府作为推广主力应发挥主导功能,做好顶层设计、整体规划,通过一揽子的政策形成组合效应,支持各地都能成立多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阅读推广联盟。此可促进区域乃至全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布局的延伸和渗透,改善资源分散、割裂等问题;可打破版权壁垒,实现数字产品共享、技术共享、服务共享、平台共享;能有效提高传播效率,促进数字阅读推广向村镇“下沉”,实现链条末端渗透化,实现推广的广覆盖。
图书馆具有体系成熟、布点广泛、资源集中、专业化程度高、组织管理经验丰富、阅读推广环境好的优势,是数字阅读推广的核心力量。建议先由国家通过立项方式扶植一批由各地方政府支持,地方图书馆牵头的,联合学校、社会机构、公益组织、数字阅读推广平台等推广主体构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联盟”,并要求通过联盟运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在联盟内形成结构性功能。功能主要包括提供保障与协调各方工作,具体承担和操作阅读推广活动的实践,协助完成推广活动等。
(二)加快数字资源建设的提质扩容和加大品牌创新力度
数字资源建设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的前提。通过推广主体(联盟)协同发力,自建或整合不同渠道的数字资源,加快数字资源建设的提质扩容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所要强调的是当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建设的提质扩容应依托数字阅读推广联盟形成地域乃至全域“一盘棋”格局。即在建库的选题和整体规划时要注重内容的继续性、关联性和各地资源库间的联动性;加强标准规范建设,以确保资源在服务与使用中具有可操作性和持续性。
为了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数字化阅读推广的传播率、覆盖率,数字资源建设还应体现多样化和体系化。即资源库建设应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可在有限条件下一味求“大”和“全”,要近期计划结合长远规划,令数字化阅读推广在多样化的基础上朝着体系化方向发展,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传承和契合当下的现实需求指向,同时要关照阅读主体需求性大的内容,将其收录进库,形成专题型的数字资源库。类如中国传统文化民俗篇、经典篇、神话篇、医药篇等专题有声读物。
当然,真正能实现阅读持续性的是品牌创新。数字化阅读主体的阅读需求具有即时性和呈碎片化的特征,这使得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资源的权威性难以完全知晓,且在社交媒体里,这些资源有被娱乐化的现象,降低了阅读主体对其的信任度。这要充分发挥域内权威专家的优势和技术领域人才所长,挖掘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呈现载体、创新推广渠道,打造高质量数字化阅读推广品牌,同时在品牌中整合进阅读主体认为有趣、有价值内容,以吸引和留住阅读者,甚至将其引导为优秀传统文化阅读的忠实“粉丝”和阅读传播推进的“中间链”。如此,在品牌定位的基础上铺开多元立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活动,又在活动中不断完善强化品牌影响力,增强数字化阅读推广持续性。
(三)技术赋能阅读供给与需求高适配延长阅读生命周期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数字化阅读推广中,阅读主体同推广主体及推广内容之间遵循“需求N(浏览B—兴趣I)-搜索S-注意力A-吸引A-行动A-分享S-实践P”[“N(BI)SAAASP”]的关联过程。基于“自由”和“权利”的理念,阅读主体可自由选择阅读内容和决定参与到阅读哪个阶段。因此,阅读供给与需求的适配越高,就越能吸引到更多的阅读者,阅读生命周期就越长,反之就越少、越短。这就要求推广主体在阅读周期的每个阶段都要尽可能地掌握阅读主体的阅读需求及在阅读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并帮其解决。“用户画像”技术的介入可实现此诉求。
“用户画像”(User Profile,又译为人物角色)是基于民族志数据进行用户原型分析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1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中对“用户画像”是基于数据融合技术,根据阅读主体的“网络数据”,通过关联规则算法,抽象出阅读主体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中的行为特征,聚焦分析其在阅读各阶段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需求及会遇到的问题,进行标签化处理,据此为其供给所需内容和解决阅读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时形成一个标签化“全景”导航服务,为差异化阅读群体提供专业和人文性的阅读服务,并在常态推广和仪式化操演中引导阅读主体走向持续阅读、深度阅读。
特别要强调的是,这种“用户画像”必须是即时性和同程性的。譬如通过即时性的“用户画像”可准确把握阅读主体实时“行”的动向,适时引导,形成良好的互动分享实践图景,延长阅读生命周期,这在动漫《大鱼海棠》展播推广活动中表现突出。《大鱼海棠》从精神、人物名、音乐、服饰、建筑、色彩等无不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同时融合了包括诸如镜子、玻璃鱼缸等现代元素,传达出“天规在上,永不可违”(遵循大自然的运行规律)的精神。该片在各大院线上映后,从中央电视台至地方电视台及各大网络平台等都相继予以展播。随着片尾曲《大鱼》的广泛传唱,形成多次“热搜”,后在文化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又发起了多次线上讨论,网友们都纷纷表示被影片中的中国美所吸引,被主人公的责任担当精神所征服。
(四)技术赋能消解“信息茧房”负效应打破阅读信息孤岛
“信息茧房”问题是数字化阅读推广中常见问题,导致的主要原因是算法法则倾向于阅读主体兴趣的同质信息推送,最后导致信息固化。如此,消解“信息茧房”的策略应是打造一个具有较好流通性的“信息蜂房”来确保阅读主体对整个优秀传统文化阅读环境的认知的真实、客观、全面和准确。[13]
这里的“信息蜂房”,是指旨在拓宽阅读主体(接收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信息的接收渠道,使其接触多元阅读推广信息,从而构建起阅读推广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真实客观的阅读推广信息系统。其原理是通过优化算法参考数、优化服务平台、提升媒介素养及实现人机协同过滤[14]等技术,减少重复推送同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信息,增加异质信息发布,同时削弱群体极化;增加人工编辑进行把关,平衡“信息蜂房”中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的流通量和增加信息间在“蜂房”“碰面”的可能性;优化信息分发模式,形成丰富多元的信息组织获取组合,将搜索、关注、算法、熟人、陌生人联结起来,避免信息“偏食”;增加阅读主体接触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信息的渠道,突破媒介壁垒,打破信息孤岛,让目标用户能有效接触“房外”信息,并根据自我的兴趣和需求选择阅读内容。
四、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发展绝不是对传统阅读推广模式的推倒重来,而是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转变观念,依托技术赋能实现从推广主体、推广内容、推广形式、阅读主体、评价方式等要素的数字化构建。在构建过程中,需不断推陈出新,不断解决问题,渐进式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化阅读推广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令其在一个个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中,赢得更多的阅读主体,赓续中华文明血脉,传承中华民族精神,提升“中国气质”,复兴中华民族。
〔参 考 文 献〕
[1]韩建芳,游凤霞.基于媒介技术哲学观的在线阅读微探[J].理论观察,2022(09):150-153.
[2]赵信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研究[D].山东大学博士,2022.
[3]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7.
[4][德]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73.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4.
[6]陈新,彭刚.文化记忆与历史主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11.
[7]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06.
[8]郝帅.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促进黑龙江省文化旅游强省建设[J].理论观察,2022(09):90-93.
[9]王彬.数字化为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再添动能[N].中国文化报,2022-03-28(01).
[10]张文彦,武广宇.跨媒介阅读时代的全民阅读生态体系建设[J].出版广角,2022(08):28-30.
[11]黄琳,李桂华.图书馆阅读推广渠道融合路径及其对读者关系构建的影响[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9(06):16.
[12]Brigham TJ.Personas : stepping into the shoes of the library user[J].Medical Reference Services Qua-rterly,2013,32(04):443-450.
[13]靖鸣,蔡文玲.“信息茧房”负效应消解的路径选择[J].学习与实践,2020(06):128.
[14]彭兰.导致信息茧房的多重因素及“破茧”路径[J].新闻界,2020(01):36-37.
〔责任编辑:杨 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