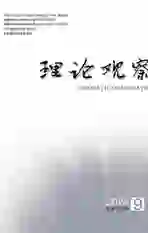早期海德格尔对笛卡尔二元论世界观的解构与阐释
2024-09-29罗永斌
摘 要:早期海德格尔对笛卡尔二元论世界观展开三重批评解构。第一,就世界、客体而言,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把世界作为广延物、现成存在的世界或自然,遮蔽了原初的世界存在、世界性。第二,就主体、精神实体而言,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回到一个无“世界”的孤绝的现成主体——“我思,我在”,并且未规定“我在”的存在,从而遮蔽和遗忘了此在的存在是“在世界之中”的与他人“共在”的存在。第三,笛卡尔将主客分离并赋予理性认识以沟通主客的优先性,这不仅导致了人与世界分离和对立,还遮蔽了原初的人的在世之在和通达世界的原初方式。但总体而言,海德格尔对笛卡尔二元论世界观持的是一种温和的批评,通过解构和阐释,以回到被它遮蔽的原初存在并为之奠基。
关键词:海德格尔;笛卡尔;世界;此在
中图分类号:B516.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9 — 0060 — 07
一、导言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导论表明,厘清存在问题的任务分为两重。[1]22第一重任务是海德格尔理论的正向构建: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基础存在论)——用以展露阐释一般存在意义的视野。在第一重任务的基础上展开“解构存在论历史”的第二重任务。也就是说,厘清存在的问题,还需要从“历史”入手,通过解构存在论历史,松动硬化的传统,把由传统导致的一切遮蔽打破,同时也从传统存在论中赢获一些原初的存在经验和积极可能性。[1]32解构存在论历史有三个决定性的思想“处所”,他们分别是康德、笛卡尔、亚里士多德。也就是说,这三位哲学家的思想构成早期海德格尔存在道路上重要的解构和阐释对象,但相对于早期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及康德思想阐释的成熟研究,其对笛卡尔思想解构阐释的研究还较少。比较著名的有马里翁(Jean-Luc Marion)的《还原与给予》,在其中,他重构了早期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评,并将重点聚焦于笛卡尔的“本我”(ego)与此在(Dasein)的异同关系。马里翁认为,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批评主要基于两个“耽误”:一是对世界的耽误:把世界等同于世内存在者的持存性——广延,从而耽误了原初的世界存在;二是对“我在”的耽误:“我思,我在”未规定“我在”的存在。另外,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此在一方面对笛卡尔的“本我”进行了六重拆解和解构,但另一方面,此在与“本我”又至少有四组相似性,从而此在与本我就构成悖论式的纠缠和关联。[2]129-183
马修·肖克(R. Matthew Shockey )在《海德格尔的笛卡尔和海德格尔的笛卡尔主义》中跟随了马里翁,认为海德格尔不是一个激进的反笛卡尔主义者,相反他们共享许多相似点,如方法论、第一人称(the first person)、主体性作为存在论追问的根基[3]。相较于马里翁和马修·肖克对于此在与本我异同关系的强调,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 [11]、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 [12]、S.马尔霍尔(Stephen Mulhall)等则注重海德格尔的在世理论对于笛卡尔二元论的认识论的突破和奠基。如在德雷福斯和查尔斯·泰勒合著的《重申实在论》[4]中,就将海德格尔此在绽出之生存的参与到、消散到(aufgehen;absorb)世界之中的“在世之在”与梅洛庞蒂的具身化的认识相结合,以突破笛卡尔的中介二元论的认识论传统。①S.马尔霍尔(Stephen Mulhall)在《海德格尔与〈存在与时间〉》中则将海德格尔的“在世”模式称为“世界参与者模式”,而把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模式称为“世界的旁观者模式”,并认为前者为后者奠基,这种理解无疑是很准确的[5]45-52。
基于这些已有的研究,大致可以看出,以往研究者,在海德格尔对于笛卡尔的解构阐释上,主要把重心放在“我在”与此在的关系,及人与世界的关系(此在的在世模式对主客认识论模式的突破上面)。但无论“我在”——主体,还是主客关系都只是笛卡尔二元论世界观的构成要素,笛卡尔的整个二元论世界观构架才是海德格尔解构的重点所在,同时也是他构建在世理论范式所要超克和奠基的对象。因此,本文无意进入此在与“我在”关系的细致辨析,以及德雷福斯等人的“此在在世模式”对“主客二分的认识论模式”的具体突破的讨论之中,而是一般地回到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文本解构与阐释,进入二者思想的对峙,从而尝试重构早期海德格尔对笛卡尔二元论世界观解构和阐释的整体思路。
根据这一拟定的核心任务,本文基于早期海德格尔的文本《存在与时间》《哲学史:从托马斯·阿奎那到康德》《时间概念史导论》等,分别对笛卡尔二元论世界观的res extensa(广延物、物质实体、客体),ego cogito(我思、思维实体、主体),及主客关系下的认识论的优先性进行批判解构②,以回到其遗忘的生存论根基。从而对二元论世界观导致的世界性被遗忘、原初的世界存在被跳过;人和世界打交道的原初方式:实践操劳被遮蔽;人和世界分离(主客二分)和无世界、无他人的孤绝主体等问题进行一一揭示。从而表明海德格尔在构建在世理论时所要处理和解决的问题。
二、世界作为广延(现成世界):对原初世界存在的遮蔽
海德格尔对笛卡尔《哲学原理》中关于物体的论证进行解读,他认为:笛卡尔是根据物体(现成存在者)的存在者层次的(ontic)本质属性——广延来通达物体的存在,因此物体的存在就是广延。而“世界”作为“物体的总和或存在者全体”也就等同于“广延”,亦即长宽高三个维度上的广延构成物体(世界)的本性,所以世界存在就等同于“广延世界”。笛卡尔认为物体的存在是广延(extension)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广延是物体的本质或根本属性。物体的形状、运动等其他的同类的属性,或颜色、重量等人们经验感受到的属性都奠基于它,并通过它得到理解。比如,物体的形状奠基于广延,只要物体的总广延范围保持不变,长宽高三个维度的量的配置可以任意改变,从而,同一个物体的形状也因为长宽高的量的配置不同而改变,但广延保持不变。如同量的蜡,变成液体和固体,形状改变,但广延不变。因此,形状、运动、颜色、重量、硬度等不是物体的本质属性,广延才是。第二,广延是物体总是持有的,因而是持存的属性。形象、运动等这些属性都是以各种方式进行变化,而广延是在物体身上始终持留下来的东西,这种始终持留下来的属性就是物体的真正存在。“所以,在世界的被经验到的存在那里,这种存在者的本真存在是由这样一种东西(广延)构成的——关于这种东西我们可以指出的是:它具有始终持存的性质(constantly remaining)。” [1]137因此,从广延作为物质的本质属性和始终持存的属性两方面来看,构成物体存在的是“广延”(extension),“它是在物质实体上始终持留下来的东西,因而也就是物质身上真正存在的东西。” [1]131因此,“世界”的存在就是广延。
海德格尔对此提出批判。第一,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忽视了存在论差异(die ontologische Differenz;ontological difference),即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或实体与实体性的差异,而只是通过存在者层次的本质、始终持存的属性——广延通达物质存在,这样不仅模糊了存在论差异和区分,而且还从根本上遗忘了物体的存在问题乃至一般的存在问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自在的存在者的存在,即实体性,称为substantia。这个术语一会儿意指作为实体的存在者的存在,即实体性;一会儿则意指这个存在者本身,即实体。Substantia的这种两义性不是偶然的,在实体这一古代概念中就已经有了这种两义性。” [1]127在海德格尔看来,笛卡尔通过实体、存在者的最突出和持存的属性——广延根本不能通达物体(世界)的存在、实体性,笛卡尔不过是以存在者层次的本质、持存的属性——广延来回避了物体(世界)存在、实体性的问题。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因为(在笛卡尔看来)‘存在’实际上不能作为存在者通达,所以存在就由有关存在者在存在者层次上的规定性亦即属性来加以表达了……(这种属性)首先的必要的‘指归’就是extensio(广延)” [1]135。
那么如何回答物质实体(世界)的存在或实体性问题?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只有澄清三种不同存在(上帝存在,精神存在、物质存在)为何可以统一于“同一存在意义”之下这一根本的存在意义问题,才能从存在论根据上规定物体的存在。具体而言,笛卡尔区分并定义了三种不同存在:上帝存在,主体存在,客体存在,前者是无限的存在,后两者是有限存在,三类实体不仅就其本质(分别是上帝、思维、广延)存在差异,而且具有“有限”和“无限”之间的差异鸿沟,如何可以统一于同一“存在”名称之下,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类比的统一性”,即存在在指称上帝、主体、客体时是同名异义的,即它们都是“存在”,但含义又彼此不同,但尽管它们各自的存在含义是不同,它们可以在类比意义上统一于存在之下。而笛卡尔则搁置了存在为什么可以统称三类实体这一根本意义上的存在问题,海德格尔引出了笛卡尔耽搁这一问题的关键文本“我们完全无法清晰地理解那用于上帝与其被造物的共同名称(存在)之含义”。①正是由于笛卡尔对这一根本的存在问题的回避,海德格尔认为他远远落在经院哲学家后面。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笛卡尔不仅搁置了这一根本的存在问题不加以追问,而且还认为它是无法通达的。从而以一种存在者层次的(ontic)属性——广延来解释世界存在,从而把世界存在等同于广延世界,遗忘了世界的原初、真正存在。
第二,笛卡尔把物质世界的存在等同于“广延”,而广延具有始终持存的性质,即持存性。这样“物质实体(物质世界)”就等同于“广延世界”就等同于“始终持存的现成存在(vorhanden,现成在手)的世界或自然”,这样就把物体(世界)的存在紧缩为自然物性的问题。世界的存在被狭隘化理解为无意义关联的“现成存在的物质自然”。这就使原初的世界——我们为上手事物操劳(Besorgen;concern)、为人操持(Fürsorgen;take care of)而生存于其间的周围世界和使世界成为世界的基础——世界性(意义关联整体)被遮蔽和跳过。正如马里翁精确地评价到:“在笛卡尔那里,对世内存在者的存在样式的解释最终耽搁了世界的现象,结果使得这一现象被现成在手之物 (Vorhandenheit)的最低限度的单义性的持存 (subsistance) 所取代。根据一个很著名但很含糊且持续时间很短的分析来看,与其说世界的世界性是通过现成在手( vorhanden) 的存在者的持存来显现,不如说是通过它作为可用的和上手的 (zuhanden) 器具的作用来显现。” [2]148需要表明的是,海德格尔当然不反对把世界理解为现成存在的物质自然的方式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它只是质疑现成的物质自然世界是原初的世界存在。他说:“不仅是在今天,也不仅是从近代以来,而且某种意义就是希腊人那里,世界之存在的结构问题都总是被当成是自然之存在的结构问题而被提出。”而海德格尔恰恰要“回到对世界的原本分析(这样的分析不把自然设为原初的东西)” [6]263。
总之,首先,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通过物体存在者层次的(ontic)根本的、持存的属性——广延来规定物体的存在,从而把物质世界的存在等同于广延世界,这是混淆了存在论的区分,以一种存在者层次的属性去充当存在论上的物质的存在。而对于物质实体的存在问题,必须要基于一般的存在问题,而笛卡尔搁置了这一问题。而重提和回答一般的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核心论题。其次,物质世界被等同于广延世界,而广延具有持存性,因而世界就被等同于持存的现成存在的世界、自然,这也就是现代认识论和科学的对象世界。海德格尔不反对这样一种理解世界的方式,但他认为这不是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也不是原初方式。把世界理解为现成存在的自然和世界恰恰遮蔽和跳过了原初的世界和世界现象,海德格尔恰恰要恢复原初的世界存在,并表明如何从原初的世界派生出现成存在的世界、自然。
三、理性认识世界的优先性和唯一性:对实践操劳的遮蔽
在上一节中,笛卡尔从存在者层次上的本质、持存的属性——广延出发,把“世界”的存在等同于广延,因而物质世界就被等同于广延世界、现成存在的世界与自然。那么笛卡尔通达广延世界的方式是什么?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方式是否是通达原初世界的方式呢?
笛卡尔认为通达广延物、广延世界的恰当和优先方式是理性认识或理性知觉(intellectual perception),并由此批评感官的感性觉知方式。首先,就批评的感性认识方式而言,笛卡尔认为,物体的本质——广延不能通过感知获得,感官所呈报出来的有色、有味、有软硬、有冷暖、有音调等洛克称之为的“第二性的质”,它们都是物质的非本质的属性,因而对于理解物质的本质无关宏旨,而且这些属性是否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我们也不得而知[7]99。但笛卡尔也没有完全否定感性知觉的作用,他认为感性的知觉能告知对于身心联合体有利或有害的事物。[7]99因而,笛卡尔认为感性感知方式不能揭示物质事物的本质。其次,就理性知觉而言,理性知觉的优先性来自于笛卡尔的真理的一般规则,笛卡尔也称之为知识总则——“凡是我能知觉得清楚、明白的(clearly and distinctly),都是真的。” [8]38其中,“清楚明白的知觉”其实就是“理性知觉”,理性的知觉为知识提供了充分的依据,只要是我清楚明白的或理性的知觉到的东西,都是真的。例如,“我思故我在”这一基本命题,它表明“我思维的时候必定有一个思维的我存在”,这一点是理性直观到的,清楚明白的,因而也是无可置疑的,必然为真。同样,笛卡尔认为,对于物质而言,理性清楚明白觉知到的属性只是广延,因而是物质的本质。硬度、重量、颜色这些其它的属性由于感官的作用,或多或少地都是不清晰明白的,因而不是物体的本质。最后,理性知觉作为通达广延物、广延世界的优先和唯一方式,就具体表现为数学的认识方式。因为物质世界的本质作为长宽高三个维度、向量的广延,广延的三个维度是可以计量和量化的,所以,通过数学的计量就可以认识、通达物质的本质。对于这一点,海德格尔十分精到地评价和总结道:
“世界的存在不外乎就是对于自然的计算性、测量性把握所通达的那种客体属性。与一切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关于自然的知识相对,现在物理学就成了数学物理学。在世界上,只有那些通过数学的手段可获得规定的东西,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可加以认知的世上物,而只有这种通过数学获得的认识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存在。” [6]281
所以,总结而言,笛卡尔认为通达广延世界的首要和唯一方式就是理性认识,而且是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认识。
海德格尔对此的批判是两方面的。第一,海德格尔并未否定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理性认识揭示广延世界的正确性、合理性。他甚至强调:“从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的具体情形和数学化的物理学的努力来看,笛卡尔的研究具有起码的积极意义。” [6]286海德格尔只是对理性认识是否揭示原初的世界存在提出疑问。在他看来,由于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理性认识揭示的是存在者层次上的广延世界。而广延世界(现成存在的世界、自然)恰恰是对原初的世界存在,即世界性的遮蔽和遗忘,所以在海德格尔看来,理性认识尽管能通达广延世界,却根本没有通达原初的世界存在本身。恰如海德格尔说:“(在此)世界并没有从它的世界性着眼而得到追问,就是说,世界没有按照它最初所显示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空间性就是由此所规定的)而得到追问。” [6]282
第二,理性认识作为揭示广延世界的唯一方式,这就排斥了其它方式(如感性觉知、实践操劳(Besorgen;concern)①等)通达世界存在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实践操劳、理性认识、艺术、技术活动等作为此在生存的可能性方式,它们都有揭示、通达世界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说:“在数学物理学知识意义上的对世界之存在的理解方式,是一种片面的方式。” [6]282是对“(世界)实在性追问的一种有害的狭隘化,而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克服这种狭隘化。” [6]286此外,海德格尔认为,理性认识也不是通达世界的首要、原初方式。在海德格尔看来“一切感性觉知和理智上的觉知都另有根基的性质” [1]141。这种根基就是“实践操劳”,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与世界打交道,通达世界的原初方式是实践操劳,理性认识是从实践操劳中派生出来的。
四、无世界的孤绝主体及主客二分:对此在在世结构的遮蔽
(一)普遍怀疑导向的无世界的孤绝主体——“我思,我在”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通过普遍怀疑获得完全不可怀疑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我思,我在”。“我思,我在”作为不可怀疑的、自明的“阿基米德之点”,成为构建整个科学知识的基点。这一基点的获得过程,也是我一步步从可怀疑的世界之中脱离出来的过程。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外部事物、身体的存在,怀疑数学、逻辑学知识的可靠性,乃至怀疑整个外部世界的存在,将自我从世界之中抽身、脱离,回到一个完全不可怀疑的基点“我思,我在”,从而通过“我思”之中理性认识到的“清楚明白的观念”,重建对整个世界的科学知识。这在认识论的基本立场上就导致人的存在回到了一个“无世界”的孤绝主体。这样的主体——“我思,我在”,首先,它是无世界的,或与世界抹除一切关联的,因为世界的存在严格意义上已经被怀疑掉、被悬搁了,作为思维主体的我是无世界的。其次,因为他人的存在也被怀疑了,所以我的存在也就是一个孤绝的单子的存在。对于这两点笛卡尔关于主体的原初规定,海德格尔是强烈反对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原初人的存在或此在不是无世界的主体,而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In-der-Welt-sein;being-in-the-world),此在作为绽出之生存早已参与到、消散(aufgehen;absorb)在世界之中为物操劳(Besorgen;concern)为人操持(Fürsorgen;take care of),无世界的主体只是此在在世的派生样式。其次,孤绝的单子式的主体也不是此在的开端,此在本质上与他人共在(Mitsein;Being-with),孤绝的主体的存在只不过是此在与他人共在的冷漠和残断模式。海德格尔强调道:“在世的澄清曾显示出:首先‘存在’的或一直给定的从不是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同样,无他人的绝缘自我归根到底也不是首先‘给定’的” [1]166。
(二)我在(sum)的存在问题
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录》中,通过第一沉思的普遍怀疑回到了一个不可怀疑的起点“我思,我在”,亦即我思维的时候必定有一个作为思维主体的我存在。那么我们不禁会接着问,作为思维主体的我是如何存在?或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恰恰是笛卡尔第二沉思要解决的任务。
在第二沉思中,笛卡尔从我们日常的对我们自身的理解出发,比如我们把我们自身即人构想成具有身体的,能够吃饭、走路、感觉和思维的人,而这些要素之中,首先身体是可以怀疑的,这一点在第一沉思已经完成,既然身体性可以怀疑,那么吃饭、走路、感觉三个要素因为与身体有关,也可以排除,那么剩下的就是思维(thinking)。所以,笛卡尔给出了他关于“我”的著名定义:“严格来说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精神,一个理智,一个理性。” [8]28笛卡尔把“思维”就界定为我,即主体的本质,所以主体本质上就是一个思维实体,与物质客体作为广延实体形成严格的区分。所以,我就作为在思维的实体而存在。“我思维多长时间,就存在多长时间,因为假如我停止了思维,也许很可能我就停止了存在。” [8]28笛卡尔接着问道:“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 [8]28从这一文本我们又可以得出,笛卡尔将“思维”这一精神实体的本质又细分出不同的样态(modes)或思维类型——感知、意志、理性、想象等,这些都是思维的不同样态,思维作为本质就渗透在它们之中。所以,总结而言,笛卡尔认为,我是一个在思维的存在者,思维是我的本性,“我的存在”就等同于“思维”,而思维又可以体现和细化为感知、意志、理性、想象等不同样态。
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尽管探索了“我思及思的模式”,但“我在”作为同我思一样原始的,笛卡尔却完全不经讨论。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将对“我在”提出生存论上的询问和规定。①笛卡尔在“我思,我在”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就是“我在”的存在意义。[1]35总结而言,海德格尔对笛卡尔批评的关键在于笛卡尔遗忘了或未规定“我在”的存在。针对海德格尔的这一批评,笛卡尔主义者马上就会反驳(也正如我在上一段已经表明了的):在笛卡尔那里,“我思”就等于“我在”,亦即我是一个在思维的存在。所以,笛卡尔已经把我的存在规定得很清楚了,就是“在思维”。那么,海德格尔的批评在什么意义上还有效,或者他在什么意义上认为笛卡尔遗忘或耽搁了“我在”的存在。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海德格尔认为“我在”不能等同于“我思”,我在或主体的范围要比“思维及其各种模态”宽广得多。笛卡尔不过是基于认识论的目的,经过普遍怀疑“构成我存在的要素(比如身体、思维等)”,然后得到“我在思维时的不可怀疑性”,从而把“我在”狭隘化和压缩为“我思”。正是在“我在”被狭隘化或还原为“我思”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说笛卡尔遗忘了“我在”的存在问题,因而他要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廓清“我在”的整全的生存论结构和要素(生存、向来我属性、在世界之中存在、与他人共在,被抛在世,现身情态、操心、死亡等,这些都是理解“我在”或人的存在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如马里翁在《还原与给予》为海德格尔辩护时所说的:“他(笛卡尔)把我在还原为我思(cogito)并把我思还原为本我(ego)。本我的特点仅仅由认识的规定性所构成,——这种规定性是绝对首要的原则……。” [2]145第二,另一种解释就是,笛卡尔的作为在思维的“我在”,是从一种存在者层次的本质的、持存的属性——思维,把“我在”理解为在思维中持存的现成之存在,即现成主体,而这遗忘了存在论生存论意义上的“我在”——此在,现成的主体恰恰只是生存论此在的派生样式。海德格尔对笛卡尔的“我在”给出解读:“sum (我在)的存在论含义是:必然现成,更好的情况:在任何思维中,都有(我的)在场之在。每当我思时,我一直在场存在。” [9]205所以,笛卡尔意义上“我在”就理解为在思维中持续现成存在的、在场的主体。但海德格尔认为,“我在”并非没有开端也没有结尾的持存的、绝对恒久的现成存在,而是它有其“在此期间”(Solange)。此在的绽出存在,自身只是延展于生死之间。此在的有限性的特定的存在论之在,并未认识清楚。[9]206亦即海德格尔认为,“我在”根基上并不是无时间的绝对、永恒的现成存在,而是有其时间性,这种延展于生死之间的时间性就体现了此在的有限性,而不是永恒持存性,笛卡尔的“我在”恰恰遮蔽了此在的时间性和有限性。所以,笛卡尔的“我在”作为“现成存在或主体”遗忘和遮蔽了生存论意义上的“我在”——此在。
(三)主客二分及对立:对此在的在世之在的遮蔽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笛卡尔的二元论的世界观的架构里,“二元”指的就是“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精神实体的本质是思维,笛卡尔对其的定义是“思维直接寓于其中的实体,在这里就叫做精神或心灵。”而物质实体的本性是广延,笛卡尔对其的定义是作为广延以及以广延为前提的偶性(如形状、位置、地点的运动等等)的直接主体,叫做物体(或肉体、身体)。[8]167因此,精神实体和物质(肉体)实体是两个本性截然不同、分开的实体。所以,笛卡尔这里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区分,人的本质存在(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广延世界、自然)的二元分离。其次,在主客如何沟通的关系上,认识论的关系就成为首要关系(当然这里先不谈一种特殊的主客关系——身心如何沟通和统一的关系,就指心灵实体如何认识外部世界的问题)。笛卡尔认为,我们通过我思“内部”的“观念(ideas)或认识”来表象外部的世界(客体),恰如罗蒂所说的“心灵是自然之镜”。精神实体或心灵通过“心灵内的观念或认识”来表象和镜现世界。笛卡尔将心灵内的认识与观念的正确与否诉诸理性的或清晰明白的知觉——“凡是我能知觉得清楚、明白的(clearly and distinctly),都是真的。” [8]38当我们的“观念或认识”被理性直观或认识得清楚明白,那么这些认识或观念就是知识,就是真理,它们如实地反映和揭示了外部世界的实在。
海德格尔不同意通过主客二分的方式来处理“我与世界”关系,因为它导致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主客二分的基本立场下人与世界的分离与对立问题。一方面是主客或人与世界在基本事实方面的区分和对立,在主体与客体的基于各自本质的基本事实区分下,主体作为思维实体(是非广延的、不在时空中的,不符合力学规律的等)是相对于客体作为广延实体(广延的、在时空中的、符合力学规律的等)而被区分的,并且二者根据区分可以看出是对立的。另一方面是认识论方面的分离与对立,首先,为了得到不可怀疑的科学知识,必须经过普遍怀疑从外部世界中独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无世界的理性静观的“我思”,也就是世界的旁观者[10]1-10;其次,为了在理性主体——“我思”的基础之上重新建立对整个世界的知识大厦,不可避免地要把世界当作一个与我相对而立的认识对象,这就导致了人与世界的主客分离,甚至对立。在二元论世界观的主导下,整个近代到现代的主流价值观是把自然对象化,认识自然,其次是通过科学技术征服、支配、利用、主宰自然,人类越发进入人与自然世界对立,不能和谐相处的时代。
第二,理论认识的优先性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不是主客之间的理论认识关系,而是此在在世的实践操劳关系。理论认识只不过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实践操劳的原初样式的派生样式,这一点上一节已经强调过。那么主客二分的认识关系为什么会成为人与世界的原初、优先关系?恰如海德格尔解释说:
“因为在存在论上还始终无法通达在世这种存在结构,而它在存在者层次上却已被经验为存在者(世界)与存在者(灵魂)之间的‘关系’;又因为人们在存在论上执拗于存在者从而把存在首先领会为世界之内的存在者,于是,人们就立足于这两种存在者并就它们的存在的意义来尝试着理解上述存在者之间的那种关系,也就是说,把这种关系理解为现成存在。虽然人们对于 ‘在世界之中存在’有先于现象学的经验和熟悉,但由于存在论上不适当的解释,在世却变得晦暗不明了。直到如今人们还在这种不适当的解释的阴影下来认识此在的建构,非但如此,人们还把它当作某种自明的东西呢。于是乎,这种不适当的解释就变成了认识论问题 或‘知识形而上学’问题的‘明白确凿’的出发点。因为:一个‘主体’同一个‘客体’发生关系或者反过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不言而喻呢?必得把这个‘主客体关系’设为前提。” [1]84
根据这段话及结合海德格尔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重构出他认为主客二分的理论认识的优先性的形成原因:1.笛卡尔遗忘、耽搁了此在的在世结构。在此在的在世存在中,此在作为绽出之生存参与到、消散于世界之中,在为此在生存之故中形成着意义关联整体(意蕴世界、原初存在的世界),在意蕴世界中理解存在者(他物及他人)。此在与世界的原初关系是一种生存论上的实践操劳关系,人的存在直接参与到世界的意义形成之中,人首先是世界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5]45-52。2.因为遗忘了此在的生存论的在世结构及原初的世界,以笛卡尔为代表的传统认识论从存在者层次上就把世界理解广延世界、现成自然——客体,把人的存在理解为精神实体、灵魂、现成主体,从而人与世界的关系就转变为主体与客体二元的认识论关系,或海德格尔称之为的现成主体与现成客体(世界)之间的现成存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被理解为世界的旁观者,人通过理论静观的认识和观念来表象世界。3.主客之间的认识关系被认识论或知识形而上学当作的“清晰明白”的出发点,由于近现代以来的知识论的统治地位,主客的认识关系就被认为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原初和主导关系,这就使得原初的此在与世界的实践操劳关系被遮蔽和遗忘。所以,海德格尔恰恰要通过对笛卡尔的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的优先性进行质疑,从而回到原初的此在与世界的关系。
五、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跟随和依托早期海德格尔的文本,重构了其对笛卡尔二元论世界观的解构性的阐释,具体而言包含以下几方面:
第一,就世界、客体一方面而言,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把世界作为广延物、现成存在的世界或自然,遮蔽了原初的世界性。具而言之就是,笛卡尔以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本质、持存的属性——广延,把世界存在等同为“广延世界”,从而导致原初的世界存在被遗忘,世界性及世界现象隐而不露。海德格尔将在《存在与时间》第三章回到原初的世界存在——意蕴世界,并证明如何在此基础上派生出现成世界、自然。
第二,就主体这另一方面而言,首先,笛卡尔为获得关于广延世界的清楚明白的知识,通过普遍怀疑回到一个无“世界”、无他人的孤绝主体——“我思,我在”,而海德格尔认为“我在”在开端处绝不是无世界的单子式的主体,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与他人“共在”的此在(海德格尔将在《存在与时间》第二章、此在的基本结构“在世界之中存在”,及第四章“共在”部分证明这一点)。其次,笛卡尔把“我在”压缩和狭隘化为“我思”,我就作为一个在思维的现成存在,海德格尔认为这恰恰遮蔽了或至少是狭隘化了“我在”的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要通过此在的生存论分析赢获此在的存在。最后,笛卡尔通过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基本区分,就导致主客或人与世界的分离与对立,而海德格尔看来主客二分不是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人与世界的原初关系是此在“在世界之中存在。”
第三,就主客二分主导下的认识论的优先性而言,笛卡尔把“世界”等同于“广延”,即现成存在的世界和自然,并认为数学物理学意义上的理性认识是揭示现成存在世界的唯一方式。海德格尔不想否定理性认识揭示现成存在的广延世界的合理性,但他否定广延世界具有世界性和世界现象,即它并不是原初的世界存在。另外,海德格尔也认为,理性认识只是揭示世界的可能方式之一,除理性认识之外,还有实践操劳、审美艺术等方式。并且,理性认识不是揭示世界的原初方式,实践操劳才是,只有此在的在世之在的实践操劳的揭示活动发生残断之后,才进入主客二分的理性认识的模式,因而笛卡尔的主客二分的理论认识的世界旁观者模式,恰恰源出于和派生与此在在世之在的实践操劳的世界参与者模式。
第四,笛卡尔二元论的世界观,通过存在者层次最根本、持存的现成属性——广延和思维,把世界和主体的存在理解为现成存在的广延实体和思维实体,从而把“存在”现成化、在场化、理论静观化为作为名词的现成存在,即把存在存在者化,从而构成了存在遗忘的存在论历史(在场形而上学)的一个思想处所,而海德格尔恰恰在解构和为它奠基的过程中,回到原初的从时间出发理解的、作为动词的存在本身。
〔参 考 文 献〕
[1]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2]让-吕克·马里翁.还原与给予:胡塞尔、海德格尔与现象学研究[M].方向红,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R. Matthew Shockey. Heidegger's Descartes and Heidegger's Cartesian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 (2):285-311 (2012).
[4] Hubert Dreyfus & Charles Taylor. Retrieving Realis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Edited by Charles Taylor (2015).
[5]Mulhall,S.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Heidegger and Being and Time. Routledge,2005.
[6]海德格尔.时间概念史导论[M].欧东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7]笛卡尔.笛卡尔思辨哲学[M].尚新建,译.九州出版社,2017.
[8]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录[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9]海德格尔.哲学史:从托马斯·马奎那到康德[M].黄瑞成,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
[10] Alweiss,L .The world unclaimed: A challenge to Heidegger's critique of Husserl. Ohio University Press,2002.
[11]Dreyfus,H.L. Bing-in-the-world:A Commentary o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DivisionⅠ.Cambridge:MIT Press,1991.
[12]查尔斯·吉尼翁.剑桥海德格尔研究指南[M].李旭,张东锋,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7.
〔责任编辑:侯庆海,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