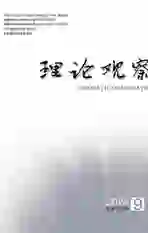古希腊哲学中“Being”的哲学诠释
2024-09-29刘瑞宏
摘 要:“Being”最初由巴门尼德提出,巴门尼德对“Bening”的思考,引向了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对立,将“Being ”译为“存在”,使得巴门尼德的‘是’的意义被湮没,是巴门尼德哲学本身的历史命运。经由柏拉图对“Being”的话语诠释,影响着理念论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在其形而上学体系中对柏拉图理论体系的批判与进一步诠释“Being”的本体论意涵。“Being”的发展历程与本体论息息相关,而这一切也与人相关,人本身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最终回归到“Being”问题的出发点——现实生活。
关键词:Being;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中图分类号:B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4)09 — 0054 — 06
对于外国哲学的当代研究者而言,文本语言的精确性始终是深入理解和诠释不同哲学话语体系的难题所在。因此,精确翻译外国哲学著作对哲学话语的时代性诠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从近代的陈康和贺麟到当代的李秋零、邓晓芒翻译的康德著作来看,每一代致力于外国哲学进行话语诠释的研究者的历程,都应具备卓越的话语诠释能力,以准确传达外国哲学话语的本质含义。从古希腊时期至今,“Being”与外国哲学的话语传统一直存在着,并且在未来会一直影响哲学的发展。翻译“Being”的准确性直接影响着外国哲学本体论研究的发展,中文对“Being”的翻译包括“有”“存在”“是”等多种译法,但是这些译法都无法做到真正的与“Being”对应。中国近代的翻译家严复,对于文本翻译的困难有着深刻的体会。其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1]7。严复所说的“求其信已大难矣”,在“Being”的准确性理解上的表现得尤为明显。“Being”的话语诠释影响着本体论研究,诠释好本体论哲学话语本身必须从“Being”的最初本源开始探寻。
一、巴门尼德哲学中的“Being”
存在(Being)是西方形而上学内部各个时代的不同哲学学派的基础性范畴,其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述。而要深入探讨“Being”与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的起源,我们必须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传统中。古希腊的自然主义哲学家从不同视角诠释世界的本原,泰勒斯“水本原”说、毕达哥拉斯“数本原”说等等都是对本原问题的不同诠释。这一时期,人们对“水”“火”“气”等具体的事物(Beings)作为世界本原的看法并未受到质疑,这体现了从自然中理解世界的话语传统。而“Being”本身是什么,它回答什么问题,具备何种性质,成为巴门尼德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在巴门尼德现存的残篇中,不断强调“Being”的重要性,并对之进行了哲学诠释。在古希腊哲学中,巴门尼德为柏拉图哲学的形而上学大厦构建了基石,柏拉图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证明他与巴门尼德在“Being”的“同一性”中得到了一样的答案,愈是“Being”的东西愈是可知的,“柏拉图实际上达到了与巴门尼德完全一致的结论:是者不在,在者不是”[2]541。作为古希腊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对“Being”的关注远超巴门尼德和柏拉图,试图以“Being”以基石构建一个科学的形而上学体系。在对“Being”的不断思考与追问下,亚里士多德将形而上学的发展推进到全新的高度,从而更好地巩固了形而上学的发展。古希腊哲学从巴门尼德思考“Being本身是什么”到亚里士多德构建的形而上学体系一直影响到当下。诠释好“Being”面临的困难与出路,在于回归到“Being”的话语传统中,在其内在的话语体系中从源初性诠释古希腊哲学中“Being”的丰富内涵,进而实现当代的哲学话语诠释。
巴门尼德是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不仅受到了柏拉图的推崇,而且得到了黑格尔的高度评价,近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对其哲学进行了深入探索,因而巴门尼德哲学一直备受哲学史家们关注。“巴门尼德哲学历来被视为西方本体论哲学的发端”[3]528。要深入理解“Being”的哲学蕴涵必然要从巴门尼德思想出发,尽管巴门尼德的著作大多数已经遗失,但通过现存的残篇进行解读,我们仍能一窥其哲学的精髓。巴门尼德哲学至今仍存在神秘色彩,但随着不断对其残篇和“Being”的解读,可以更好地去理解巴门尼德哲学的本体论的发源。“Being”是巴门尼德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不仅构成了其哲学的核心,其《论自然》的残篇中频繁出现,特别是在其残篇8中出现了四次。《论自然》是一部采用寓言诗的哲学著作,在现存的残篇中,巴门尼德在残篇1借用女神的之口向众人阐述了他的哲学思想。并在残篇4中阐述了其哲学的全部宗旨在于探寻找一条能够通向真理的道路,而不是要说明真理是什么。接着巴门尼德又在残篇2中说明了到达真理的两条路径,分别是“That [it] is ,and that [it] cannot not be”和“That [it] is not and that [it] needs must not be”[4]73。两条路径如何选择,在残篇2中,巴门尼德给出了一个明确的选择,那便是只有“Being”是通向真理的途径。但这两条路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仅凭这两句话无法得知,必须对“Being”是什么有所交代 。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了中文“Being”的三种基本译法“存在”“有”和“是”。这三种译法不论是从语法上还是思想渊源上都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依然不能够完全表达巴门尼德的思想以及其丰富的含义。
将“Being”译为“存在”是普遍的中文译法,“存在”基本上表达了“Being”的意思,这里将“Being”
译为“存在”是作为动词来 处理的,那么第一条路径就可以译为“存在物是存在的”[5]593或“存在就是存在”[5]668。“Being”本身是一个多义词,在希腊文中充当着系词的作用与英文中的is 的作用相当。这样的系词,在中文翻译中有时可以不用翻译。例如“she is good at playing the piano”,可以翻译为“她擅长弹钢琴”。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成“是”也没有问题的。就汉语的语法规律来看,能称得上是系词的只有“是”,将 “Being”译为“存在”便会无法看到其作为系词的意义,但当“Being”作为动词使用的时候,“存在”和“有”的意义便可以显现出来了。从希腊文的发音规则上来对上述翻译进行区别,可以发现作为动词时,要给“εστιν”的第一个音节标上重音,而做系词时则不需要标重音。“必须说明的是,在巴门尼德那里还没有作这样的区分”[5]594。另外,从同一律“S是P ”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存在是存在的”,巴门尼德等于是再说一句重复的话,将思想的内容与思想的形式弄混了。“从思想的形式来说,同一律是必须被遵守的;但从思想内容来看,说‘A是A’对于主语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信息。”[3]531因此在巴门尼德哲学中,将“Being”译为“是”更加准确。
在翻译“Being”这一概念时,中国学者遇到了理解上的困难,而西方学者在解读希腊文中“Being”的翻译“εστιν”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他们主要的困难来自语法。在基尔克、拉文、肖菲尔德编著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也将理解“Being”作为难题提出来,“而在几经权衡和文本分析之后,KRS 得出的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无论是将及其相关词按照 ‘是’ 来理解还是按照 ‘存在’来理解,都不会妨碍我们对巴门尼德主要论证的把握”[6]。 穆尼兹认为,“是”是一个包罗万象的词,这与“Being”的多重含义是相近的。与此同时,穆尼兹把对巴门尼德的论述分为两部分,分别是关于是的论述和是者的论述。这种解读方式更符合西方的语言习惯。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巴门尼德的“Being”作为“是”的基本含义是的。“西方哲学引入中国多久,把 Being 翻译为‘存在’就有多久。”[7]但随着对“Being”的概念的深入研究,在巴门尼德哲学译为“是”已经显示在外国哲学研究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对巴门尼德哲学中“Being”的研究,不应仅局限于语法和翻译上的分歧,而要深入到整个巴门尼德哲学的思想体系中去。毕竟“Being”作为巴门尼德哲学的核心,是与其哲学宗旨紧密相连的,因此要把“Being”融入对真理的追寻的路径之上。
“Being”是巴门尼德哲学的核心,巴门尼德专注于探索真理的本质建达成方式。平时思考真理时,人们总是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真理与谬误作为对立的范畴来去思考如何到达真理。而巴门尼德却是将真理与意见对立起来,同时巴门尼德是在思考如何到达真理,而不是局限于真理的定义是什么以要给出真理的具体是什么这样的答案。出现如此差异的原因在于先入为主地带入了自身的真理观,而忽视了问题最初的原貌。为了更好地理解巴门尼德哲学中的“Being”,我们必须去探寻其所谓的“真理之路”,理解和诠释在巴门尼德哲学中“真理”和“意见”的内涵。
巴门尼德关于“真理” 的思想是在之前的哲学家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尽管苏格拉底之前的多数古希腊哲学著作未能完整保存,使我们很难去追溯“真理”问题的最初发展轨迹。现有资料表明,米利都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并没有关于“真理”思想的描述,克赛诺芬尼在其残篇三十四中将自己关于神的学说称之为“真理”,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使用“真理”的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继承并拓展了赫拉克利特关于真理的思想,将“Being” 的认识也称之为真理。这表明“Being”自始至终从未脱离真理的范畴。
巴门尼德认为真理并不是仅仅靠“Being”的能力就能显现,需要人们去用自己的思维去探索和领悟。从自身出发去理解真理,诠释真理,真理是在现实中得到展现的,并通过“Being”得到更好地诠释。然而巴门尼德的真理并不是随意阐发的真理,它有着具体的规定性,也有其特定的含义。可以从巴门尼德现存残篇中关于“真理”的出处和用法,来诠释好巴门尼德规定的真理。
(1)残篇第一的第二十九行:“不可动摇的圆满的真理。”这里用的是名词,意思是说真理是完善的,圆满的,其核心就是“存在”是有的、真实的,而“非存在”是没有的、不真实的。
(2)残篇第二的第四行:这条途径是可以追求的,因为它通向真理。这里用的是名词,指认识“存在是存在的”就是真理。
(3)残篇第八的第十七行,说到另一条道路是不可表述、不可思想(设想)的,巴门尼德说:“因为这不是真理之路”。这里用了巴门尼德自己说到“真理之路”的,唯有这一处[5]644-645。
通过上述三则材料,可以看出巴门尼德对真理的思考已经形成了体系,他认为关于“Being”的认识才是真理,只有依靠人们的思想,再加之推理与证明的方法,便可以得到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因此在巴门尼德哲学中,关于“真理”的概念已经有了确定的哲学含义与意义。
在巴门尼德哲学中,与真理对立的是意见,而不是谬误,因此在诠释何为巴门尼德的“意见”之时,要注意不要与谬误弄混。在巴门尼德之前,仅有克赛诺芬尼使用过“意见”一词,巴门尼德继承并拓展了他的理论。他不仅相信真理是存在,并且指导人们如何找到真理,那就是不断地追寻“真理之路”。黑暗与光明是对立的世界,在巴门尼德哲学中,意见的居所是黑暗,而真理则存在于光明的世界。他认为意见给人的感觉是,其本性是不可靠的,同时也是欺人的。
在明确巴门尼德的真理内涵,需要去思考何为“意见之路”与“真理之路”以及二者的关系。如何去理解“意见之路”,巴门尼德残篇八中从第50行到52行指出的“在此我结束对你的可靠言说和关于真理的思考,由此转向凡人们的观念,且听我所说的这种欺骗性秩序吧”[4]91-92开始了关于“意见之路”的描述。而在接下来的第53和54行中,他却提出了关于“两个形式”的难题,“因为他们在命名时头脑里建立了两种形式,命名一种形式是不正确的,他们却在其中误入歧途”[4]92。尤格在理解“两种形式”时,认为两种形式是指“Being”和“non-Being”,巴门尼德在意见之路中试图提出的任何一个意见都是以“Being”和“non-Being”为前提,并且由二者组成,即使最深刻的意见也无法离开真理的范畴。
巴门尼德对于“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关系具体是什么,他并没有作任何阐述,在其残篇中,他用女神的口吻来引导人们去追寻真理,并且去思考体会意见之路的内容,最后让人们否定它,最终到达真理之路。“在巴门尼德心中,他坚信‘意见之路’是虚假的,既然如此,便谈不上它和‘真理之路’的关系了”[8]20。用现在的观点去看待“意见之路”,可以见到其荒谬之处,可是哲学研究最忌的就是用未来的思想去理解过去的智慧。因此应该看到“意见之路”在巴门尼德哲学中的作用,它是其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正是有着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对立,才有后世哲学家对于“Being”的不断诠释与思考。
巴门尼德关于“Being”的思考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是由于他提出的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对立,一般与个别、静止与运动等等一系列概念的对立才进入哲学家的视野。巴门尼德哲学在古希腊时期不仅影响了留基波等原子论思想的哲学家,也深深影响着柏拉图。原子论哲学家将“Being”与“一”改造成不可分割的原子个体,同时也将“存在不能从非存在中产生,也不能变为非存在”的原则,改造成了原子与虚空的永恒不灭和原子与虚空的统一。巴门尼德对柏拉图的影响散见于其对话中,在《泰阿泰德篇》中,他是这样评价巴门尼德的,“巴门尼德对我显得,用荷马的话来说,‘对我来说既可敬’同时又是‘可畏的’”[9]123柏拉图专门将“巴门尼德”作为《巴门尼德篇》对话的主角,可见其崇高地位,在《智者篇》中讨论的主要是关于“Being”与“non-Being”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将详细讨论巴门尼德对柏拉图哲学的影响。
“巴门尼德的‘是’的意义指被湮没,是巴门尼德哲学本身的历史命运”[3]569。然而,随着古希腊哲学进入到柏拉图时代,“Being”的概念不再是有着神秘外衣的存在,进入到可以言说的范畴。尽管如此,对于巴门尼德哲学的“Being”的真正内涵依然未能得到充分的揭示。“根据柏拉图以来所形成的传统去看巴门尼德,巴门尼德哲学之谜是无法揭开的”[3]571。幸运的是,从黑格尔开始,巴门尼德哲学再次被人们重视起来,并且也在不断地展现其本来的面目。“真正的哲学思想从巴门尼德起始了,在这里面可以看见哲学被提到思想的领域”[10]267。同时,近代的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研究也在推动着理解巴门尼德哲学中的“Being”,对于“Being”的意义的诠释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二、柏拉图哲学中的“Being”
柏拉图现存的作品主要是由四十多篇对话构成,但其写作年代尚未达到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内涵丰富,一直影响着外国哲学的发展进程。柏拉图哲学体系是在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进一步诠释,并融合了巴门尼德哲学。作为西方本体论研究真正意义上的开端,柏拉图对“Being” 的话语诠释从未离场,一直影响着理念论的发展。巴门尼德哲学思想的主要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同时这也是柏拉图对巴门尼德哲学中“Being”思想的继承与发扬。首先是柏拉图的通种论,其次是柏拉图在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基础之上,对世界的区分,分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
柏拉图的通种论即“相”论,通种是指对型相,在《智者篇》中,柏拉图列举了“是者”“运动”与“静止”“相同”与“相异”等通种。柏拉图直接从“Being”的意义出发,去证明这些通种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去论述其“分有”说的合理性以及实际意义。通种是永恒的,不朽的,通种的特征是与巴门尼德哲学中“Being”的特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由于‘相’是‘是者’的‘所是’,所以巴门尼德对‘是者’的描述都适用于‘相’,如不生不灭的、不动的、完整的、不可分的,没有缺陷的等等,总之是绝对的”[2]667。由此可见,柏拉图的通种论继承了巴门尼德的“Being”思想。关于“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区分,也是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延伸。柏拉图对于二者的区分,主要体现在其“线段比喻”中。巴门尼德完全否定了“non-Being”之路,而柏拉图在这里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将‘存在’和‘非存在’分为绝对的和相对的,绝对的‘非存在’和绝对的‘存在’是绝对对立的,不能互相包容结合”[8]23。柏拉图更加关注现象世界的存在,正是由于柏拉图的努力,让“non-Being”之路在哲学史的地位得到了应有的恢复。
柏拉图的对话录是其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通种论与理念论继承了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将对“Being”的思考不断深入。柏拉图不仅关注“Being”如何起作用,而且臻力于探究作用的本质及 其特征。在通种论,他去研究“相”,各种各样的“相”构成一个相界,而在其中依然能够感受到事物的对立。但就这一点而言,这与巴门尼德关于“Being”的思想依然存在着关联,他保留着巴门尼德哲学中关于“Being”的基本结构,即肯定“Being”,否定“non-Being”。在《巴门尼德篇》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对于理念新的演绎,这便是巴门尼德的新理念论。
柏拉图提出的“相”种类多,均具有积极的正面价值。在柏拉图的划分中,“相”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伦理方面的,如“品德”;第二类是数学方面的,如“一”,第三类则是自然物方面,如“火”。前两类是典型的存在,是无法用感官去把握的,是符合理性的要求的,因此应该肯定其存在,这与巴门尼德的“Being”是一样的存在。第三类的理想程度比较低,而这些自然物与人类的关系紧密相关。如人造的桌子等。柏拉图对“相”或者通种的区分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研究具体问题时用到的思考方法,因此也有“相”的区分进入到了对“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的区分。
柏拉图的理念论是西方哲学史的第一个本体论思想,是这一理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目前学术界接受的其前期理念论,即个别事物分有理念。在《巴门尼德篇》中,借巴门尼德之口,已经批判其前期的理念论,论述了分有说的困难。在《巴门尼德篇》中,批判一共有六点,前五点都是对旧理念论的批判,而第六条则是展现了新理念论的困难。《巴门尼德篇》中一共有着八组推论,关于这八组推论中的“其他”是什么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其他”是指理念本身,还是与理念相异的个别事物。展开这八组推论,并且结合“一”与“其他”的对立来看,“其他”便是理念本身。在理念论中,柏拉图思考着现象世界与理念世界的区别,而“Being”存在于理念世界,是一个概念,“non-Being”属于现象世界。我们在关注着理念世界的同时,也不能忽视现象世界的存在,现象世界是我们生活着的真实世界。柏拉图的本体论影响了整个的西方哲学传统,他对“Being”的理解与诠释,也让整个西方哲学开始思考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他第一次将哲学定义为研究通种间关系的学问,也就是关于概念之间的关系。柏拉图的本体论思想发展经历着三个主要阶段,同时这也是其本体论的三大进步之处,也在影响着未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第一阶段,是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前期理念论;第二阶段是从旧理念论走向了新理念论,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本体论的雏形开始出现;第三步,便是其通种论思想的思想。通种论思想是对巴门尼德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一阶段,思想训练的价值得到了展现,只有经过思想上的训练,才能够去弄清楚概念与概念之间存在的全部关系。
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中深入阐述了他的新理念论,并在《智者篇》中提出了通种论。但是不论是理念还是通种,都不能直接表述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它们的意义在于用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让世界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规定性。而去面对世界中的事物,还是去面对生活本身,去思考“Being”的真正内涵,以及要找到对“Being”的诠释。
三、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对“Being”的发展
柏拉图被誉为本体论的开创者,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在许多方面与其老师的理念相反。这一点从亚里多德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可见一般,这反映了他对柏拉图理论体系的批判,并在形而上学领域对本体论进行了深入探讨与拓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区别,哲学史家文德尔班和梯利也说得很明显,并且生动。文德尔班指出,柏拉图的理念论体系具有超越于现实的、经验世界的特征,“而亚里士多德则断言真正的现实是在现象本身中发展的本质”[11]189。梯利则指出,“柏拉图似乎把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所称之为永恒的形式者置于星体之外”。正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哲学与柏拉图哲学的不同,我们不能简单的来面对亚里士多德对“Being”的诠释以及对本体论的发展。
从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入手,探讨亚里士多德道德形而上学体系,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亚里士多德对理念论的批判主要散见于《形而上学》中,尤其是第1卷 的第9章,以及第13卷的第4和第5两章。尽管两处所表述的内容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主旨是明确的。“它根本否认有理念这样的东西存在,从而否认理念论是解释事物最终原因的理论”[3]297。“关于理念存在的那些证明方法都是不可信的”[12],根据这一论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亚里士多德反对理念论,并且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体系,清晰地表达一个事实,这个世界是可以经验的,而不是柏拉图哲学体系中的超越于经验世界的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理念世界。
《形而上学》一书完整地论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本体概念,同时也包含着对柏拉图哲学的批判。亚里士多德提出本体的概念的主要原因是批判柏拉图的理念,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本体的定义,并提出了很多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本体是既不能用来表述一个主体,又不依附于一个主体之中的东西。人也是一个主体,那“人”与个别的人又该如何区分呢,这也是亚里士多德要去思考的问题,而这在《形而上学》有着详细的展开。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第一主体”和“第二主体”。第一主体是指个别的事物,如个别的人,而第二本体则是包含了个别事物的“属”和“种”。其中第一主体是更加明确的主体,原因在于其他的一切东西都在表述第一本体。由此可见“种”可以用来表述“属”,却不能用“属”来表述“种”。
亚里士多德恶本体论思想在《形而上学》中得以展开,其理论基础源于他的四因说,关于四因说的系统性阐述,亚里士多德已在《物理学》第二卷中详细的论证。四因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质料与形式,即他所说的本体,关于本体的论述,是其《形而上学》的核心议题,书中分别讨论了存在、本体、理性、现实与潜能以及本体的原则与原因等一系列与本体原则与原因相关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在基督教神学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成熟,然后其哲学真正地进入到神学之中却是在公元12世纪之后。基督教最初不仅反对柏拉图主义,就连亚里士多德哲学也没有能够避免,教会“称他的著作是‘自然哲学著作’,这包括《形而上学》一书”[13]316。在波埃修翻译了《工具篇》之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开始为神学所用。
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不仅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哲学在神学中的价值,而且确保了其哲学体系在西方一千多年的黑暗的历史时期得以传承。并且对近代的本体论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休谟经验主义的独断论阶段,在康德和黑格尔之后,“Being”的价值和意义也开始回归,一切又开始回归到古希腊哲学时代。是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关于“Being”的思考早已不是巴门尼德那时的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在当代也开始面临着困境,也在找寻着其合理性的出路。
四、结语
关于“Being”的思考,当代面临的困难,与其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有关,但是这并不意味“Being”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关于本体论的发展,需要找到其存在的合理性,而这要求证明本体论存在的完满性,“实在界统一地被给予我们,这便要求一个同一的本体论根据”[2]1163。要对经验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提问,而并不是所有的提问都是科学的,确认在本体路提问中的合法性,便是思想本身必须是纯粹的存在,因此思考“Being”问题,要使其本身成为可思想的或者具有思维的。
本体论的基本命题,具有自明性,这种自明性要求被我们对其进行深刻洞察,,而不是简单地证明。本体论探讨的不是一个事物的定义,而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就如同巴门尼德引导着人们追寻真理之路,必然离不开探寻真理。探寻真理的道路离不开现实生活,因而对于“Being”的思考以及其出路,也要回归到现实生活本身。
任何事物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Being”也不例外,而所有事物都是真实的,并不是空中楼阁。我们作为个体时,以及人类整体,都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因此我们思考“Being”的真正内涵与意义时,必须以生活作为其出发点。生活本身是有一定界限的,而这个界限是必须清晰明确的,因此,在探讨“Being”的时候,要注意生活的界限,以及生活原本最初的不可还原的形式。不论是本体论 ,还是“Being”本身都是人自身所做的哲学思考。人作为一种现实世界生活的生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有着生活的界限。生活之前的和生活之外的事物对人自身的意义不大,因而对“Being”的真正内涵和本体论的出路,要回归到以人为主的生活本身。
〔参 考 文 献〕
[1]伍杰.严复书评[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2]宋继杰.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3]余宣孟.本体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巴门尼德.巴门尼德著作残篇[M].李静滢,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聂敏里.“是”与“存在”——对西方哲学中Be动词的再考察[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4-10+111.
[7]王路.“Being”的翻译[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76-87+160
[8]周冬冬.巴门尼德存在思想研究[D].上海:华东理工大学,2013.
[9][古希腊]柏拉图.泰阿泰德[M].溥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10][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1][德]文德尔班.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2]韩秋红,史巍.从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看近代知识论哲学[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3):110-114.
[13]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侯庆海,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