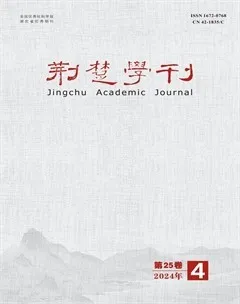从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诠证孟、荀人性思想的内在同构性
2024-09-23谭忠诚郭齐阳
摘要:郭店竹简《性自命出》篇论“性”之两大特征:一是“以气论性”,即“喜怒哀悲之气,性也”;二是“性随心动”,即“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这两大特征既是引发后来孟子“性善”与荀子“性恶”之分歧的根源,又是洞悉孟、荀人性思想之内在同构性的关键性钥匙。
关键词: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情;性;命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768(2024)04-0015-06
《性自命出》篇所洋溢的重“情”论堪为郭店竹简中儒家心性学说的一道亮点( 1 )。可是,在郭店儒简之心性整体结构中,“情”又是隶属于“性”的,即“情生于性”(《性自命出》简3)。因此,若要全面理解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的“情”,还必须对此“情”之上格——“性”进行一番深入考察。然而,在郭店儒简心性学说之逻辑系列中,这个“性”又是隶属于“命”,即“性自命出”(同上)。因此,若要真正掌握这个“性”,又必须对其“性”之上格——“命”进行相应的解读。这种介乎“情”“命”之间的“性”,正是郭店儒简心性学说的一大核心范畴。
一、以气论性与性随心动:孟、荀人性分歧的根源
郭店儒简的心性学说可谓代表了早期儒家心性思想的雏形,这是郭店儒简在先秦儒家伦理史、乃至整个儒学思想史上的重大学术价值。因为,在郭店儒简文献之前的孔子学说中,并未见诸有关儒学心性思想的论述。尤其在整个《论语》中,孔子直言“性”的地方仅有一处,其“性”字在《论语》里出现的频率亦仅二次:
子曰:“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
然而,对于《论语》仅存两处“性”字,近人傅斯年曾经质疑过,结合他在《性命古训辨证》一书中考证式统计,他说:“统计之结果,识得独立之性字为先秦遗文所无,先秦遗文中皆用生字为之。”[ 1 ] 3并进而断言说:“今人各先秦文籍中,所有之性字皆后人改写,在原本必皆作生字,此可确定者也。”在傅斯年看来,这种对“生”“性”二字做出区分的,无疑是始于秦之后,“其分别生、性二字者,秦后事也。”[ 1 ] 60
对于傅斯年这种判定“生、性”二分乃属秦后之说,现结合郭店楚简文献来看,无疑有臆断之嫌。首先,单就文字书写来说,郭店楚简文字中业已出现了这种“生、性”二分的现象,如郭店简文中的“生”字多写成“ ”或“ ”,而“性”字多写为“ ”或“ ”,今之整理者释读为“眚”字。可是,对于这个“眚”字,傅斯年亦表示曾见诸相关金文如“既眚魄”之中,却又被傅疑为“生”之异文。其次,既然傅说“生”“性”二分乃秦后之说,可上述所引“性相近,习相远”一句,在现今出土最早的汉代《论语》竹本(即1973年出土的河北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本子)中仍然书写成“生相近,习相远”[ 2 ] 82。不仅这样,在与郭店竹简同时期的楚简文献中,那种“生”、“性”既“分”与“不分”的情形也是同时并存的,例如郭店儒简《性自命出》开篇“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的“性”字即被书写成“眚”,无疑反映了这种“生”“性”相分的趋向;而在另一篇与其大约同时且内容相似的上博简《性情论》中,其开篇却是“凡人虽有生,心无定志”,这又展示了一种“生”“性”不相分的传统。
当然,囿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我们现在有幸得以目睹的郭店楚简和定州汉墓竹简都是傅斯年一辈在当时无法获得的考古新材料,就其当时的现成材料而论,他们的研究结论也是经得起史料考证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些后人基于今天的历史幸运而拥有了前人所未见的新材料,这也只能成为我们足以修正前人结论的新证据,而不能当作是我们苛求于前人的新理由。尽管这样,傅斯年这种考辨对于我们探究先秦儒家之“性”论依然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线索,这就是西周以来的那种“生之谓性”的“即生言性”传统。
仅以古汉语字源学而论,事实确如傅斯年先生所考辨的那样是“生”在“性”先。在现有甲骨文、金文等考古文字资料中,只有“生”字而无“性”字,从“心”之“性”字无疑是后来派生的。从字源学来说,先有的“生”字包含了后来从“心”所派生之“性”字的一切含义,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生之谓性”显然已包含了后来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的全部内容,也可以说,后两者应该都是对前者“生之谓性”的具体化延伸。对此,梁涛先生也说:“即生言性乃古代人性论的大传统,这一传统又可概括为‘生之谓性’。”[ 3 ] 326 在《孟子》一书中涉及孟子与告子之间那段“生之谓性”的对话,则可视为这一传统的残留痕迹。不仅如此,这一“生之谓性”的传统,还渗透到了后来荀子与庄子学说中,如《荀子·性恶》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和《庄子·庚桑楚》的“性者,生之质也”皆属此例。具体在郭店儒简文献中,我们还可以明辨出这种从“生之谓性”到后来孟、荀之性善与性恶之分化的义理同构性。这种义理同构性之具体表现就是《性自命出》篇的“以气论性”说。
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性自命出》简1-3)
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善不【善】,【性】【也】。所善所不善,势也。(同上,简4-5)
这些论述“性”的简文,揭示了郭店儒简关于“性”的两大特征:一在“性”与“气”的关系上是“以气论性”,即“喜怒哀悲之气,性也”;二在“性”与“心”的关系上是“性随心动”,即“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可以说,后来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都是在围绕着郭店儒简关于“性”之两大特征上的各自偏差而产生的分化。现详而析之如下。
郭店儒简是“以气论性”,认为“性”是人之喜怒哀悲之“气”形于内而“未发”的本然状态,这正是荀子所谓的“性者,本始材朴也(《荀子·礼论》)”的思想来源。然而,这种“性”不独性,必待“心”之“志”而后发,即“凡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性自命出》简6)”,“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同上)”,这种“性”即已由隐而显为“已发”之“情”了。在荀子看来,放纵这种由“性”而生的“情”之顺养而无“节”的话,这就是人性之“恶”的来源。如荀子说: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礼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恶性》)
荀子这里的“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有好声色焉”,就是因袭了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所谓的“好恶,性也”之儒学内部所衍生的固有传统来“照着讲”的——即荀子所讲的“性恶”就是指人内在的那种“性之气”已发于外而为“情”且无“节”(“顺是”)的“犯分乱礼”之后果。其实,对于荀子这种顺乎人之自然之情以言“性”的观点,孟子早已深切明察之,如孟子说:“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这样,荀子所言的“性恶”实即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的“情恶”,由于这种“情”是生于“性”的,且从这种“喜怒哀悲之气”的“已发”“未发”层面来说,这种“情”是“已发”之“性”,而“性”是“未发”之“情”,“情”“性”本无二致,故荀子又将此“情恶”归之于“性恶”矣。
孟子则是沿袭了郭店儒简另一种“性随心动”的特质来即“心”论“性”,即“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既然郭店儒简说“凡人虽有性,心弗取不出”,而“心”又是“无定志”的。这种“心无定志”,孟子亦是认同的,并有其所据的孔子之言为证,即“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之其乡。’惟心之谓与?(《孟子·告子上》)”但是,孟子一方面既在肯定了这种“心无定志”的“莫之其乡”时,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心”必有其“同耆”的“心之所以同然者”,即他所谓的“理”也、“义”也。对此,孟子又说: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这种“心”不仅有“同耆”之“理”或“义”,而且他还吸收了郭店儒简的观点,认为“凡心有志也,无与不【可】”(《性自命出》简6)。不过,在孟子看来,这种“心有志”且“与”,就是所谓的“气”。所以,孟子眼里的“气”与“志”不仅是同一层面的概念,即所谓的“志至焉,气次焉”、“持其志,无暴其气”也,而且还兼具了一种互动相向的依存关系,即所谓的“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孟子·公孙丑上》)。这种寓“气”于“志”以返“心”的观点,亦是孟子对于郭店儒简“以气论性”说的一种继承与改造,即孟子把郭店儒简那种本属于“性”之层面的“气”(即“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根植于“心”(即“苟得于心,必求于气”)的层面。由于孟子是先验地赋予了其“心”具有“同耆”的“理”或“义”的道德属性,因此,作为“心之志”的“气”也同样地被孟子赋予了道德色彩,这明显体现在孟子那种“养浩然之气”的“养气”说。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敢问何谓浩然之气?”
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这种“配义与道”、“集义所生”的“气”,是孟子“气”论的一大特色。由于孟子沿袭了郭店儒简的“性随心动”说,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既将郭店儒简的“心”赋予了“理”“义”之“同耆”的道德内容,另一方面还将这“心之志”的“气”也改造成一种“集义所生”“配义与道”的“夜气”(即“善气”)。因此,孟子的“心之动”也好,“心之至”也好,都是“有乡(向)”的,这就是循“理”而动,由“义”而行,故“无有不善”也。这样,“性随心动”之“性”也自然地“无有不善”了。所以,孟子的“性善”是就着人有向善的“心之乡”——即“心之端”而言,说白了,就是“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上》),如《孟子》一书说: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鼓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人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
上述对话中所引用的“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若追溯这些观点之源头的话,则可能就是郭店儒简所讲的“善不【善】,【性】【也】”。在孟子看来,人之性有善,是来源于“心之乡(向)”,就好比水之性本然就下一样。他说:
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孟子·告子上》)
在孟子看来,人之性是“无不善”的,其所“使为不善”的,乃是迫于外力之“势”所然。对于郭店儒简的“所善所不善,势也”,孟子则独取其“所善”为“性”,其“所不善”者仍为“势”也。
二、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孟、荀人性学说的内在同构性
颇富意味的是,尽管孟子的性善与荀子的性恶酷似迥异,他们却共同遵循了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立场而主张“尧舜皆与人同”,并一致强调了“礼乐”教化的必要性。其原因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是荀子和孟子皆沿袭了先秦时期在人性问题上所共有的“生之谓性”的传统,二是他们在“性”之来源——即“性”之上格问题上均秉承了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的观念。这种由先秦时共有的即生言性的“生之谓性”再到郭店儒简的“性自命出”,既可揭示出后来孟、荀两家关于人性思想的内在同构性,又体现了早期原始儒学对人本身——即人性来源问题的思考渐趋深刻而深入的认识过程。如荀子在人性问题上虽持“性恶”之说,但又从其“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的观念出发,认为“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既然凡人之性事实上皆同(注:皆同于性恶也),何以会在结果上又有“尧、舜”与“桀、跖”之分,“君子”与“小人”之别呢?荀子认为其根源就在于“可以而不可使也”,对此,荀子具体解释是:
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为禹则然,塗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荀子·性恶》)
导致这种“可以而不可使”的原因,在于君子肯顺应后天之“良师”、“益友”的习染,而小人则不然。故荀子又说:
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汙漫、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荀子·性恶》)
如上所述,荀子的观点似乎又明显地存在着一个问题:即这些所事之贤师、所择之良友的“贤”与“良”又是缘何而生呢?荀子认为,这里即存在一个后天所教化之“礼”的积习而成——即他所说的“积伪”问题。这个“伪”即“礼”也,如荀子所谓的“文理隆盛也”(《荀子·礼论》)。由此可知,尽管荀子在“礼”之来源问题上依然存在着诸如“圣人化性起伪”之类的悬而未决之遗憾,但他仍然秉持了孔子的“礼后”说。( 2 )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虽然秉持与荀子不一样的性善说,但是在“性”的无差别问题上亦提出了一种与荀子“塗之人可以为禹”的类似命题,这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这样,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一方面沿袭了郭店儒简那个“性随心动”的特质来即“心”论“性”,所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孟子·尽心上》);另一方面他又继承了孔子思想中“仁者爱人”( 3 )的内容与郭店儒简的“仁者,人也”(郭店《竹简残片》,又见《礼记·表记》)的观念来以“仁”存“心”,形成了孟子所说的“仁者,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但是,孟子又同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个“仁心”又常易为人所疏忽而不知内求,即所谓的“放其心而不知求”(《孟子·告子上》)。这种情况下,孟子也同样强调了后天礼乐教化之学问的必要性,且认为人之学问的目的就是为了重新找回其当初已放逐而不知求的那个代表着“仁之端”的“心”,故孟子又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同上)。
孟子与荀子在人性问题上一致认同的“塗之人可以为禹”或“尧舜皆与人同”的观念,在郭店儒简中亦可以见诸相关论述,如郭店儒简说:
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其生而未有非志。次于而也,则犹是也。虽其于善道也亦非有怿,数以多也。及其博长而厚大也,则圣人不可由与墠之。此以民皆有性而圣人不可慕也。(《成之闻之》简26-28)
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性自命出》简9)
显然,郭店儒简这种“其性一也”的思想一方面是来自于对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继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当时流行的“生之谓性”传统的因袭。在这一点上,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论立场都是一致的,故而均主张人“性”是同构的。然而其所表现出来的性善与性恶的分化,则在于各自对“其用心各异”的理解上出现了分歧:孟子一方面既秉承了郭店儒简的“性随心动”特性来尽“心”知“性”,另一方面他又承袭着孔子思想中尚仁贵质(4)的传统来以“仁”存“心”,故而得出了“性无不善”的性善论;而荀子则因循郭店儒简的“以气论性”的思路,走向了一条与孟子对立的“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的路向,采取“以顺(即“利”也)为本”的做法,将人性本有的“已发”之“情”无限放任而无“节”,故而得出了“从人之性,顺人之情”的性恶论。不仅如此,这种性善、性恶的分化,还反映了孟、荀二人对体现着人“性”之终极来源的那个上格——即“命”的认识上,亦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三、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孟、荀天人关系的宏旨要义
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篇在论述“性”之终极来源问题时涉及了一个重要命题——即“性自命出,命自天降。”可是,正是对于这个“命”的把握上,却又有着“见仁”“见智”的价值取向性选择。如陈来先生说:
在《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降”相当于《中庸》的“命”,故《性自命出》的“命”本身是由天命令或赋予来的,具有一定的独立的存在意义,这应当与古代文化中对命的信仰有关。而这里的命,我觉得也具有生命(如后世道教所说的命)的意思。“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意思是:性根于生命躯体,而生命是天所赋予的。这就与全篇以生论性,以气论性的思想一致了。这个解释虽然还需要找到更多的训诂的根据,但就思想的理路而言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4 ] 87-88
那么,陈先生这种基于《性自命出》篇“以生论性”的语境出发,将“命”理解为“生命”或“生命躯体”。这在训诂学上究竟又能找到多少“训诂的根据”呢?以下兹引傅斯年先生的训诂考证材料以详析之。
傅斯年先生综考了清人阮元《性命古训》中所有关于“命”字的古训,其结论是:“命之一字,作始于西周中叶,盛用于西周晚期,与令字仅为一文之异形,”而“令之一字自古有之,不知其朔。”[ 1 ] 3因此,傅斯年进一步推论说,最先只有“令”字,“令字在甲骨文字中频出现”,而“命字则无之,足知命为后起之字也。”[ 1 ] 8对这“令”“命”两字的关系,傅斯年则认为:“今可质言者,即令命实为一词,因语法变化,虽为一词而有两读,古者令、命两体古为一词。”[ 1 ] 65 而且,傅斯年还对“令、命”二字之字义的衍变作过一番疏理,他说:
令、命之本义为发号施令之动词,而所发之号、所出之令(或命)亦为令(或命)。凡在上位者皆可发号施令,故王令、天令在金文中语法无别也。殷世及周初人心中之天令(或作天命)固“谆谆然命之也”,凡人之哲,吉凶,历年,皆天命之也(见《召诰》)。犹人富贵荣辱皆王命之也。王命不常,天命亦不常;王命不易,天命亦不易。故天命、王命在语法上无别,在宗教意义上则有差。天命一词既省作命,后来又加以前定及超于善恶之意,而亡其本为口语,此即后来孔子所言之命,墨子所非之命。从此天命一词含义复杂,晚周德运之说,汉世识谶书之本,皆与命之一义相涉矣。[ 1 ] 66
可是,从上述傅斯年对“命”字的古训辨正来看,我们却觉察不到“命”字作“生”或“生命”来解的丝毫痕迹。事实或许正像陈来先生所言,那种把“命”理解为“生命”的做法可能是根源于《性自命出》篇“以生论性”的观念,而这种“以生论性”实际上又秉承了先秦时固有的那种“生之谓性”的大传统。而且,这种大传统还延续到了汉代,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以“生命”之“生”来释“命”,如《论衡·骨相篇》云:“命谓初所禀得而生也。”可知,汉代时即有释“命”为“生”之义。郑玄注《礼记·中庸》时亦如是,如在注《中庸》“天命之谓性”时,郑玄则引《孝经说》曰:“性者,生之质。命,人所禀受度也。”所以,近人陈柱在把《中庸》的“天命之谓性”解读为“天生之自然者谓之性”后,又特作按语说:“命犹生也。所生命连言。”[ 5 ] 1显然,他所附加的这个按语确实也有一番汉代经学家之依据。
综合上述对“命”字的古训梳理,可知,虽然从字源学来讲,“命”乃是“令”之后起字,但是,“命”字自出现后,即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字义,且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做为“天之生物”的人所具有的生命(躯体),二是伴随着这种人之生命之躯而来的“凡人之哲,吉凶,历年,德运”等命运之类的“受度”。所以,李零先生在其整理《性自命出》篇的“余论”中,也有同样的一番释“命”之词,他说:“‘命’则是人所具有的生命和命运。‘命’是由‘天’赋予人的。简文说‘命自天降’。”在谈及“天”之所指时,则又说:“‘天’是人(不管是单个的还是总称的)以外的世界(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或两者兼而有之的)。”[ 6 ] 151
上述“命”字含义,在儒家早期的《论语》中,也都能找到出处。如“可以寄百里之命”、“宾退,必覆命曰”、“君命召,不俟驾行矣”、“降命者出户”、“舜亦以命禹”等,这里的“命”皆作“令”也。又如“不幸短命死矣”“士见危致命”等之“命”字即“生命”也。又如“亡之,命矣夫”“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等,此处的“命”均作“命运”解。只是,这种作“命运”的“命”及其所连带的“天”,在孔子那里,一直是属于“不可得而闻也”的“天道”层面。如孔子弟子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在《论语》中,孔子有时是把“天”与“命”分开而言的,如“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吾谁欺,欺天乎”;有时又是合“天”与“命”而言,如“五十而知天命”、“畏天命”。
傅斯年认为,孔子之“天道”的“不可得而闻”,亦只局限于子贡而已。“今统计《论语》诸章,诚哉其罕言,然亦非全不言也。”[ 1 ] 121据此,傅斯年还就《论语》中有关“天道”的语录做过详细的列举,并归纳说“孔子之天道观有三事可得言者”,现择其要点如下:
其一事曰,孔子之天命观念,一如西周之传说,春秋之世俗,非有新界说在其中也。孔子所谓天命,指天之意志,决定人事之成败吉凶祸福者,其命定论之彩色不少。
其二事曰,孔子之言天道,虽命定论之彩色不少,要非完全之命定论,而为命定论与命正论之调和。
其三事曰,孔子之言天道,盖在若隐若显之间,故罕言之,若有所避焉,此与孔子之宗教立场相应,正是脱离宗教之道德论之初步也。[ 1 ] 123-124
从上述傅斯年的归纳可知,孔子的“天道”观实乃春秋时代之矛盾的集大成者,其中既有命定论与命正论的调和,又有其宗教立场和欲离宗教以趋道德的矛盾。这种矛盾的集大成特征也预示了孔子后学之分化的必然。如其命定论则为继汉而来的公羊学所发挥,孟子则沿袭着孔子的命正论,走上了一条去宗教以返人伦的道德论路向。然而,约孔子“天道”观的核心以言之,实乃“天道”如何决定人事与人事如何顺应“天道”的“天人关系”问题。而这种“天人”关系论又构成了先秦之性命说的基本内容,具体在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的命题上仍然不能脱离这种“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即所谓的“性自命出,命自天降”。这就是说:命自天降,而受之者在人,性自天降,而赋之者亦在人也。因此,这种郭店儒简“性自命出”的性命说,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说,又可以看作是先秦时代的一种天人观。围绕着郭店儒简“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性命说,孟子开辟了一条“尽心”、“知命”以“知天”的天人合一论,而荀子则走向了一条“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的天人相分论。
注释:
(1)参见《郭店儒简的重“情”论》,谭忠诚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19-23页。本文后文中采用“郭店儒简”这一表述。
(2)孔子的“礼后”说,载诸《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3)语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4)孔子的“尚仁贵质”思想,可参见《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和《论语先进》:“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参考文献:
[1]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定州汉墓竹简《论语》[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3]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陈来.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与儒学人性论,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009.
[5]陈柱.中庸注参[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增订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马好义]
收稿日期:2023-05-16
基金项目:2019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正邪之辨与王船山的儒释道关系研究》(项目号:19YBA345);2021年中南大学“高端智库”项目《中国儒佛道思想融合发展史》(项目号:2021znzk07)
作者简介:谭忠诚:(1971-),男,湖南祁东人,中南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伦理学史研究;
郭齐阳:(1998-),女,河南新乡人,中南大学哲学系202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