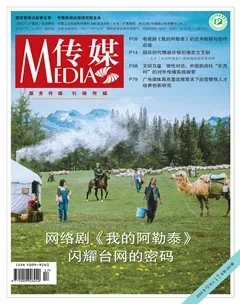技术可供性的实践:非遗文化的数字化展演与仪式化建构
2024-09-17陈红王奕诺
摘要:数字技术的发展给非遗的活态传承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非遗文化有了新的展演形式。作为一种自带仪式属性的特殊文化记忆,非遗的数字化展演重新建构了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播仪式,通过仪式化的建构,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认同。未来,技术可供性将提供给非遗传承更多的可能,这提醒我们需要不断关注技术与文化共生互构的关系,以媒介化手段推进非遗文化的创造再生产。
关键词:技术可供性 非遗文化 数字化展演 传播仪式
伴随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VR、AR以及动作捕捉等技术也逐步应用到非遗数字化展演过程中,让非遗在智能媒体时代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笔者基于技术的可供性视角,从非遗的数字化展演与仪式化建构角度出发,探讨非遗数字化展演在现实中的实践。
一、可供性:技术与物质实践中的新可能
技术可供性最早由心理学中的“可供性”概念演化而来。1986年,美国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提出了可供性这一概念,阐述了可供性的详细定义:“环境可供性是指环境提供给动物的东西,及一切环境提供或给予的东西,无论好坏。”吉布森认为可供性是人在特定场所行动的可能性,即环境是客观存在的,它可以导致行为也可以限制行为。这一理论被引入新闻传播领域,逐渐演变成为媒介技术的可供性。技术可供性被界定为一个用以描述在技术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概念,探讨行为体与行动环境之间的连接关系。作为一种多结构多因素的动态概念,它的实现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功能特征,还取决于行为主体的专业特征、组织能力等。潘忠党率先将“可供性”引入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并构建了涵盖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等在内的研究框架。国内学者对于技术可供性的实践,大多以某一具体技术或平台为切入点。例如,视听技术的可供性对视听文化再生产的研究,VR技术的可供性对于数字出版行业影响的研究,技术可供性对顾客消费的影响研究等。注重活态传承的非遗文化在最近几年也愈发注重数字技术的应用。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生成于农业手工业时代,以师徒之间言传身教的场景性传承而传播。在没有数字技术的时代,非遗受地域空间和“口口相传”的限制,传承和保护十分困难。非遗的数字化生存不仅使非遗文化在传播中升级增量,而且为非遗“活态”传承创造了条件。现行的非遗数字化技术手段主要是基础性数字技术,即非遗数字化采集、记录、整理、展示的主要手段是通过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基础性数字技术实现。在数字技术的支持下,非遗的展演形式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图文信息,基于2D、3D技术的动态形式也成为非遗展演的常态模式。在此基础上,伴随着智能媒体技术的兴盛,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极大拓宽了非遗展演的途径和内容,虚拟展馆和元宇宙纷纷上线,助力非遗文化重获新生。同时,借力于社交媒体平台上UGC和PUGC的传播,非遗实现了形式多样的规模化内容生产、数字化保存以及具有强大社交属性的虚拟场域下的具身视听,突破了地域与时间的限制,得到更广泛、更接地气的传播。
二、技术可供性的生产:非遗文化的多维数字化展演
从技术自身的角度出发,作为非遗文化展演的承载体,数字技术的发展提供给了非遗更多的展演方式,最大程度地还原了非遗本身的形态,在展示非遗完整形态的同时,也将非遗独特的文化内涵传递给大众,以此实现非遗文化在智能媒体时代的传播和发展。
1.短视频视觉化数字展演:他者视角与情感链接。短视频的兴起,给依赖影像和口语传播的非遗文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活力。非遗文化的短视频展演多以他者的视角呈现,更多强调的是主体的隐退和他者的凸显。对于非遗短视频而言,他者的范畴有两种。一种他者是身处屏幕之外的短视频用户。在用户的他者视角下,非遗短视频中的参演者通常会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讲述非遗故事,展示非遗技艺,通过影像声音表达,调动用户的感官积极性,进而将其带到展演者的场景中去。而另一种他者,则是相对于非遗传承人而言的他者,如快手、抖音等平台上生产非遗短视频的PGC或PUGC内容创作者。
PUGC专业性内容生产更注重于还原非遗本身,最大程度地过滤掉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给用户提供最佳感官体验。同时,作为参演者的内容生产者,用“他者”视角下独属的叙事方式对非遗进行展演,吸引自己粉丝和平台其他用户驻足观看。平台上的用户虽然身处不同的地方,却可以被同一个短视频吸引停留,通过观看得到情感上的链接,在一次次观看、点赞和转发中,平台用户实现了对非遗意义的共同认可和情感链接。
2.虚拟展馆的数字化展演:主体在场与交互体验。目前,国内的非遗虚拟展馆以传统展馆为基础,利用虚拟技术将陈列品以及影像和声音资料移植到互联网上,通过对媒介空间的整合,用三维互动体验的方式进行非遗展演。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许受时空限制无法线下亲临非遗展馆,却可以通过人机交互,“云”游非遗虚拟展馆,实现线上“在场”体验。
“在场”是主体在现场与“场”发生了关系。“在场”是显现的存在,是直接呈现在“面前”和“眼前”的人和事。梅洛庞蒂认为,在知觉活动中,人们对事物的感知具有整体性、关系性和情境性,身体是知觉活动的本源。在非遗虚拟展馆的展演中,参观者可以在VR和AR等虚拟技术的支持下,通过视觉、触觉、听觉以及身体的其他感觉,对周边环境进行全方位感知。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灰塑为例,用户进入灰塑虚拟展馆,在系统引导下可以进行灰塑工艺体验和建筑性能的虚拟仿真实验,全方位体验灰塑技艺。在宝鸡岐山县非遗展览馆,用户通过VR可体验岐山非遗,参加周公祭典,欣赏岐山转鼓。
在杂糅复合的媒介空间中,依托技术与多元身体形态(智能身体、人体、意识),感官可以借助想象获得沉浸感,提供主体在场的机会,赋予参与者更具真实感的交互体验,实现交流的在场,也实现了非遗活态化的展演。
3.元宇宙与非遗数字展演:具身感知与文化沉浸。元宇宙的出现为非遗数字化展演提供了新思路,使非遗的虚拟化展演得到进一步发展。元宇宙是集成与融合现在和未来全部数字技术于一体的终极数字媒介,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连接,成为超越现实世界的、更高维度的新型世界。
在元宇宙的非遗展演中,用户通过可穿戴传感设备和VR等终端设备,将自己的身体嵌入到元宇宙设置的特殊非遗场景中。这种嵌入不单是用户感官的加入,更包括用户意识和情感的上传。相较于沉浸式传播,元宇宙场景更强调用户身体的在场,即人的身体参与传播过程与活动。体验者能在短时间内全身心参与其中,身体的持续在场和完整场景的搭建,让原本陌生且遥远的非遗文化变得触手可及。元宇宙所承载的更多是属于这个地区的非遗文化集合体,用户在亲身体验以综合性的完整形态出现的非遗技艺时,也能回归到由元宇宙搭建的非遗诞生和存在的生活环境中,在更具仪式化的传播中实现文化沉浸。
三、技术可供性的互动:非遗文化数字展演的仪式建构
非遗并非现代化社会的产物,因而很多现代人都对非遗文化感到陌生,但是技术提供给了现代人与非遗“互动”的机会,在互动中重新构建起古老的非遗与现代人之间的仪式空间进而产生情感链接。
1.文化回溯与情感蓄积搭建的仪式空间。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传播符号,非遗的数字化展演可以看作“仪式”的再现过程。重回非遗的诞生地可以更好地搭建非遗展演的仪式空间。从詹姆斯·凯瑞的仪式观来看,传播是一个文化共享的过程,通过这种文化共享,文化符号在仪式中转化成为文化的认同感和集体记忆。罗森布尔的仪式传播观认为仪式的最终目的是巩固社会的共同文化信仰,实现对社会共同体维系,这种社会共同体的维系在现代社会需要通过文化回溯来搭建仪式空间。
在非遗短视频展演中,短视频的拍摄场地多会选择非遗文化的发源地。例如,在侗族大歌的发源地——贵州黔东南地区拍摄有关侗族大歌的短视频,在醒狮的发源地——广东佛山拍摄醒狮文化。这种重回非遗发源地,再次构建非遗诞生环境的文化回溯,实际上是通过文化的数字化再生产,重新塑造现代传播模式下的集体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留存已久的记忆遗产,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即使身处不同的地方,身为不同的民族,在数字化再生产创造的仪式空间里,观看者对于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和特殊情感也更容易被重新激发和唤起。
2.文化自信与宏大叙事自带的仪式感知。对文化自信的个人维度而言,文化自信就是在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人面前,所展现的对于自己民族、国家文化的自豪感和文化的独立性;从国家层面而言,是在世界舞台上所展现出来的文化独立性、独特性和文化的创造力和创新性。传统文化构成了一个国家的“信仰体系”,整合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群体的统一意志,并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合法性依据。因此,非遗的传播可以说是自带“仪式”属性。
文化自信在非遗展演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井喷式出现的主题多样的非遗短视频和“打卡非遗”类的展示非遗文化的社交动态。而仪式作为文化自信的情感“在场”,让文化自信得以直观呈现并实现广泛传播。正是基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可和文化自信的增强,非遗展演才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内容呈现,这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并反过来进一步增进了人们的文化自信。非遗文化本身独有的文化自信构造了宏大叙事的风格,契合了仪式建构的底层逻辑。例如,国家级非遗“黄帝陵祭典”在线上直播间中展示无人机远景视角下气势恢弘的祭典现场,给直播间观众带来最直观的视觉震撼和情感冲击,通过媒介仪式唤起炎黄子孙共同的集体记忆,加深了文化认同。
3.符号意指与仪式脚本塑造的仪式过程。仪式符号是文化类展演中塑造仪式过程的关键元素。在非遗展演中,使用表演符号是较为常见的,这种展演往往具有特定的流程,置身于特殊的仪式情境中,具有规模化和程序化特点。特定的展演形式是通过展演召唤仪式的重要环节。在西安鼓乐的直播展演中,演奏者通过模拟与唐代宫廷演奏相似的情境,与直播间网友隔空互动,身处现代生活的观看者通过这种形式的展演,完成了古代与现代之间的时空链接。
语言符号是非遗展演中应用最多的特殊仪式符号,阐述背景的普通话旁白,遇上非遗传承人的方言独白,这种令观看者熟悉而又陌生的语言环境链接起与陌生文化的交流之路。物件符号同样承载着非遗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通过非遗技艺最终得到的物件,是非遗文化具象化的最直接体现,因而在非遗的数字化展演中,通常会采用具体的物件开展非遗展演。除了特殊符号的应用,在非遗展演中仪式脚本的塑造也尤为重要。仪式脚本在非遗短视频展演中,主要体现为具有戏剧性的故事讲述和趣味性的情节冲突。在由参演者制造的情节冲突。例如,揭秘非遗的秘密、探访非遗的发源地等一波三折的过程中完成仪式脚本的塑造,使得非遗展演的仪式过程更加真实具体,展示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将更多观看者带到仪式中。
四、技术可供性的进路:非遗文化数字展演与仪式建构的未来
当下,智能媒介技术已经全面渗入信息生产中,非遗的传播也必须顺应智能媒体的发展潮流,才能在现代社会得到更好的传承。因此,非遗文化的传播也需要在仪式构建的过程中,充分结合数字技术,让非遗文化得到更好的发展。
1.技术协作与非遗传承的融合推动多方参与。目前的非遗传承过程中,数字技术被视为非遗传承的工具和附加品,数字技术与非遗的融合更体现在表层技艺和技术应用上的融合。但伴随着各类新技术的成熟与应用,人们对于非遗的认知会更注重精神层面。未来,将数字技术的科技力量、政府的组织力量和非遗传承人的文化力量相结合,互相利用传播优势,将更多的资源整合到非遗传播中去,弥合技术与非遗传承人之间的鸿沟,才能扩大非遗影响力,使其持续焕发新的生机。
2.多样态建构与非遗传承强化社会集体记忆。哈布瓦赫认为仪式就是一种集体记忆的存在形式。作为带有特殊文化记忆的仪式展演,非遗的存在感越强,越有利于社会集体记忆的强化。在个人记忆依赖社交媒体存储的今天,非遗展演的多样态建构有助于非遗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以及集体记忆的强化。
在社交媒体时代里,单一的媒介呈现形式显然不能迸发出巨大的传播能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非遗传承人和部分非遗组织因其资源优势,仍旧会是非遗传播和传承的主要承担者,但多样态的媒介内容和形式使非遗的身影遍及互联网更多角落,从而实现社会集体记忆的强化。在当今比拼传播声量的时代里,这显然是不容忽视的。
3.数字化非遗的编码再生产构筑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在一个民族共同体中长期生活的人们形成的对本民族文化的肯定,在社交化传播时代,点赞、评论、转发以及“打卡”是对某一事物认可的最直接的体现。一些品质优良的非遗相关内容,通过关注者的点赞、评论和转发完成非遗信息的编码再生产,有效构筑了文化认同。
(作者单位 西安工业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2020年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渭河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红色资源开发与传播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0M017)、2023年度陕西高校青年创新团队“西部地区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研究创新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GIBSON J J.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visual perception[M]. New York:Psychology Press,1986.
[2]ZAMMUTO R F,GRIFFITH T L,MAJCHRZAK A,et 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ing fabric of organiz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2007(05).
[3]王蕾.守护灯塔:基于“第二个结合”理论探析文博文创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路径[J].出版发行研究,2023(07).
【编辑:曲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