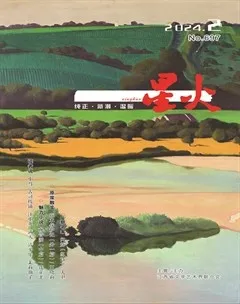有束微弱的光投向我(新人说)
2024-09-11蔡红
在我十三岁那年的暑期,我用圆珠笔在一本笔记本上抄写下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当时我并没有与《红楼梦》这部巨作相遇,我手边是一本父亲的手稿本,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父亲摘抄的经典段落或诗文。当时的情境,我不太记得了,但我确定,十三岁的我被它震撼到了。
也是在这本手稿本上,少年的我逐一遇见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牛虻》里的亚瑟等。我在想,文字,或者说文学吧,本就是在我的血管和心脏里流淌着的。那是父亲留给我的。
时间过去得太久了。那些与书相伴的日子,早已陪同我的青春一起离开了我,只留下了零碎的记忆和画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乡村孩子的精神生活太过于匮乏了,连青春期都是单色的。于是,那些书以及书中的故事,便成了匮乏生命里的救赎,以及对更广阔世界的向往和探索。
与学校完全脱离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被生活吞噬。挣扎在生存和迷茫的漩涡里,我关上了与文字连通的大门,也一并把爱与浪漫、激情和理想锁在里面。只剩活着,像一条在海里,没有意识,只是寻找食物的鱼。
有一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好像是十七岁吧,或者十八岁,这并不重要。这一年我离开家乡离开母亲,去了温州,在舅妈的早餐摊上做帮手。每天凌晨三点多起来去市场占位置,做繁琐的清扫工作,等舅妈来了再支起摊位。某一个凌晨,我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后,舅妈还没有来。我蹲在安静清冷的市场里,街上的灯还没来得及熄灭,有几家做夜宵的店铺还在做扫尾工作。这时,二楼的住宅区凭空响起一首女声英文歌曲。那个旋律恐怕我这一生都不会忘掉,只第一声出来我的头皮就开始发麻,然后跟着手和脚一并麻了,眼泪紧跟着哗啦啦地淌下来,它们都没经过我的同意。是卡朋特乐队的《yesterday once more》。
它像一束光,照进了我混沌窘迫的生活,让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
我第一次接触的哲学类书籍是《苏菲的世界》,可惜相遇得还是太晚了。我开始在文学里寻找除了浪漫爱情之外,更为深邃的、严谨的、对生命个体的打量与思索。
我是谁?
苏菲这样问,我也这样问自己。
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就像生母孕育我并坚定把我留了下来,又因诸多缘由我来到洪村,来到当下的这个家庭,和现在的父亲母亲相遇。这种与大部分人都不同的生命际遇,于我是更为饱满丰富微妙的人生体验。我该如何诠释,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我在文学里找到答案,又同样找到新的问题,乐此不疲。
成年后的某一段时期,基于对乡村的怀念,我开始慢慢回忆和记录过往,很好,它们还躺在我的身体里,在我的记忆里。
我忘了说,我的大姐是个作家,她一直鼓励我写,并投稿。她说,你敏感而丰富的内心,你独特的人生经历,都适合书写。她还说,你也许比我更适合当一个作家。我知道她的话里更多的是一种情感认同,但我突然有了一种崭新的热望,一种用文学去表达与安放的热望。原生家庭的遗弃和回归,再生家庭的爱、羁绊与责任。以及我自己人到中年后,回顾以往生命历程的体验和感悟,都是有血有肉的,都值得被记录,被看到。这一路走来的遗憾、残缺,都成过往,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用文学去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和探索。
于是这篇关于少年时期经历的那场特大洪水,在一个十三岁少女的记忆里汹涌而来。我对过往的岁月,以及我笔下的文字,都饱含着深情。
这篇处女作之所以投给《星火》,是因为我被它的栏目深深吸引了,“蝉的地下时光”,多棒的表达与意象呀,我几乎为它热泪盈眶。我想做一只蜕变与新生的蝉。感谢《星火》,接纳我的“第一声”,在我即将迈入不惑之年的当下,它有着非凡的意义。就像是那年,初听到卡朋特乐队的《yesterday once more》,有种如梦初醒的振奋,又有一种梦被点燃的勇气。
文学的大门被重新打开,有束微弱的光投向我,我与它更接近了。
或者说,我一直在它的怀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