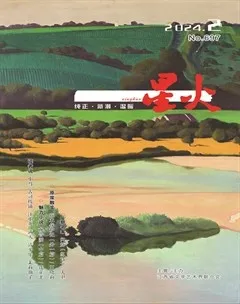一个老人的使命
2024-09-11欧阳娟

一
我认识姥姥的时候她已经九十多岁了,九十几没人说得清,那个时代的老人大多不记得自己确切的出生年份。她总是说,过两年我就一百岁了,要做老神仙了。过了两年,她仍然这样说,仿佛一百岁是《等待戈多》里的戈多,永远即将到来,永远无法抵达。
我没好意思问她要身份证,也不知道她到底有没有身份证。她从早到晚坐在一个木桶椅上,一手扶着乌木拐杖,一手搁在椅圈上。她的牙齿掉光了,下巴因此瘪着,形成一条条横向拉开的皱纹。下巴上的皱纹跟脸上的皱纹衔接在一起,层层叠叠的,让我联想到她被衣裳遮盖的部位亦是如此层层叠叠的。她喜欢戴抹额,脑袋上总是勒着一条黑布带子,再配上老式斜襟褂袄,看上去像某种泥塑的娃娃。塑造成型后,又用手指抵住头顶和脚心捏一下。她有一种从两端向中间聚拢的趋势,安坐在木桶椅上的姿势显得极其稳定。在我记忆中,她从未离开过那把木桶椅,乌木拐杖似乎只是一个预备行走的象征。夏天,木桶上垫着草席,她整个人显得凉飕飕的;冬天,木桶里烧着炭火,她又拥有了暖洋洋的气息。她是个冬暖夏凉的老人,令人感觉舒适。
我唯一一次见到她离开那个木桶椅,是在一个深秋的早晨。那天我背着书包去上学,空气中有干草浸透了秋露的气味,那个木桶椅空荡荡摆在那里,也被深秋的冷露濡湿过似的。我放学回家时,木桶椅不见了,姥姥也再没有出现过。我想,也许那一天她真的正式抵达了一百岁高龄,做向往中的老神仙去了。
我认识姥姥时刚满七岁。按理说,住在相邻的两栋房子里,我应该早就认识她的,但我脑海中并没有关于她更早的记忆。也许她曾经跟着我大表舅在城里生活过几年?也许她曾在老房子幽暗的雕花大床上卧病过一段时间?没人向我证实过这两种猜想的真实性。每一个被问到这两种可能性的长辈都隐约其辞。有吗?不记得了。好像是吧……包括姥姥自己。这让我觉得拥有了记事能力而从未见过姥姥的那两年异常神秘,仿佛姥姥那段时间生存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总之,我是满了七岁之后正式取得了入学资格,头一次背着书包上学时在二表舅家的老屋门口看见她的。她叫了一声我的小名,问我妈说,今年报上名了呀?我妈说,报上了,快叫姥姥。她连忙说,叫了、叫了。我以为她年纪大了耳朵不好,明明我还没开口,她却以为叫了。长大后才明白,那是一种体恤和客套。
姥姥是我表舅的奶奶,按标准的称呼,我本不该叫姥姥的,但我表弟叫她姥姥,我妈也就让我跟着表弟一样叫了。严格来说,其实表弟也不该叫她姥姥,也不知怎么就那样叫了。人说南方“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我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老家,却是连每个村庄的风俗都不尽相同的。即便是同一个村子,每户人家遵循的习俗也有微妙差异,对长辈的称呼也就不一而足。我叫爸爸“爸爸”,村里不少小伙伴却叫“一爷”;我叫妈妈“姆妈”,而村里不少小伙伴叫“奶子”。那是一个融合了现代与传统的小村庄,有人大谈“即将迎来知识爆炸的年代”,有人伏在墓地里研究碑刻上的书法。
村里的小伙伴们都没有姥姥,只有我和表弟们有姥姥。每天上学时,姥姥都要问一句:“好崽,去上学呀?”放学时,她又要问一句:“好崽,放学了呀?”我和表弟们神气活现地应答着,她的问话让我们觉得上学放学都是值得骄傲的事。别的小伙伴是没人这么殷勤问候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田里地里搁着干不完的活,即便有姥姥,他们也不一定能享受到这种待遇。繁忙的劳作,磨灭了长辈们的耐性和温情。
我以为姥姥是我亲姥姥。除了血脉之亲,我想不出还有什么理由让一位老人对孩子如此亲昵。更何况,我和表弟们可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小东西,骂人打架不用说,放火烧篱笆、放牛吃庄稼都是常犯的事,严寒酷暑照样在外面疯跑,七八岁就饱经了风霜,挂着皮肤干燥皲裂的老脸,半点粉嫩娇柔的样子都找不到。再熊的熊孩子也不过如此,不仅言行举止熊,连长相也熊,完全没有凭借自身实力赢得长辈亲昵的可能性。可妈妈说,姥姥只是表外公的“带娘”。所谓的“带娘”,就是养母。表外公的亲娘死得早,姥姥原本只是他父亲养的一个小姨娘。排在这个小姨娘前面的,大约还有别的姨太太,因此她并没有获得继母的身份。别的姨太太去世后,表外公就把她当亲娘一样孝顺。
我不知道一个小姨娘怎么一步步俘获我表外公的孝心,更不知道一个做姨娘的怎么会对家里的孩子们怀着那么深的宠爱之情。姥姥的心路历程,在我心目中就是一座神秘而又温馨的古堡。
二
在我七八年的人生阅历中,小姨娘无非分为两种:一种尖酸刻薄憋着满肚子坏水,专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算计家族地位和财产;另一种受尽压迫忍辱负重,等待着亲生子大鸣大放之日一洗冤仇。像姥姥这样既不算计又不受辱还无子无女的小姨娘,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当然,我那时有限的经验中,关于小姨娘的认知都是来自港台影视剧。
十几岁读了《红楼梦》《金瓶梅》之后,我渐渐认识到,小姨娘的待遇和地位,也可以靠自己的本事去争取的。姥姥究竟有什么本事呢?村里人都说我表外公对她百依百顺,我也亲眼见到过二表舅对她关怀备至。
农忙时,二表舅会特地叫表舅妈早点回家做饭。“忙人饱,闲人饥,坐着吃得一筲箕”,他常说,姥姥一天到晚坐着,昼不得昼,夜不得夜,肯定早就饿了。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农活忙起来,别说旁人的饥饱,连自己的健康都顾不上。累了,先撑着,忙完这阵再说;病了,先拖着,忙完这阵再治。我眼睛里进过一粒秕谷,爸妈拖了五六天都没时间带我去医院看,致使我现在右眼仍然视力不济。不是爸妈对我格外残忍,他们对待自己也不过如此。时令不等人,双抢时,一旦错过了收割时间,天一下雨成熟的水稻就要倒地了,就算不下雨,水库里的水也要下来了,一年到头的辛苦,很可能因为一两天的延误就此泡汤。二表舅能让表舅妈提前回家做饭给姥姥吃,实在需要拥有强大的孝心。
姥姥心里也跟明镜似的,看见有人路过就要叫住说:“篮仔又提前收工赶回来帮我做饭了。”篮仔是我表舅妈的小名,她名字里有个兰草的兰字,乡下人没那么雅致,都把她当作摘菜、洗衣时提着的竹篮子,于是她父母心目中的兰草就变成了旁人嘴里的篮仔。路过的人听了姥姥的话,免不了赞许我篮仔舅妈的德行:“你老人家福气好哦,讨了个好孙媳妇。”姥姥就连连点头,“福气好,福气好。”蝼蚁抢食般不顾生死的农忙时节,因了这样的对话而有了一丝温馨的人情味。村里人有样学样,都比对着我二表舅和表舅妈的德行孝敬老人,即便做得不够周全,也不好过于怠慢。
忙得实在难受时,篮仔舅妈也会说:“家里那个老的呀,哪管你什么春插、双抢?就算是打仗,她要吃酒还是要吃酒,要修脚还是要修脚。”
说起姥姥吃酒和修脚的“典故”,村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日本鬼子打过来的时候,姥姥的酒正好喝完了,她踮着小脚要去隔壁村上打酒。表外公不肯让她去。她看看天看看地,晃着酒壶说:“嫁到你们何家后,我这壶子就没空过,打个仗就让我空了?真打进来了,左右是个死,哪里的土不埋人?埋到隔壁村里也一样。”我听到这件事时,既佩服姥姥的胆色,又害怕她的鲁莽。如今历经了些许世事,对她生存的那个年代也有了一定了解,才知道所谓胆色与鲁莽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揣测,对于姥姥来说,也许死亡在她的一生当中,本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没什么大不了。
于是表外公提出要外出逃难时,她不紧不慢修着她的脚讲条件:“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我样样都随你,你说逃难就逃难。只有一样,逃到哪里,都要弄盆热水给我修脚。”她五岁开始缠脚,一辈子没有松开过。她把裹脚布缠上脚趾的那一刻就知道命不在自己脚下了,因此只想活一天得一天的自在和干净。
我问过姥姥:“如果外公非要拉着你走又不给你弄洗脚水怎么办?”她笑笑地说,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实在走不动了,他们扔下我也不怨。我在她绵软的语气中听到了惊心动魄的凄惨,攥着拳头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做个独立自主的人。那一天,我细小的手掌心里全是汗。
姥姥用一盆洗脚水阻挡了表外公逃难的脚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位无力主宰自我的小脚女人,又在无形中影响着家人的命运。谁也无法预测逃出去的结果。留下来未必是死,跑出去了未必是生,反之亦然。
实际上,姥姥对家人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她像一个强劲的磁场,无形地牵引着事态的发展。
我三表姨患有癫痫,发作的次数多了,神经系统受了影响,脑子也变得稀里糊涂。有一回,三表姨突然不见了,两三个月音讯全无。表姨父在我二表舅的监督下带着家人找了一阵,大约早就厌倦了这么个病妻,找得并不认真。姥姥也没多说什么,只是盯着墙上的全家福看。二表舅一见她盯着全家福,就又揪着表姨父出去寻人。三表姨回来的那天,姥姥一把将她搂在怀里恸哭,问她这几个月吃什么、睡在哪里。三表姨说她吃菜地里的青菜、辣椒,睡牛棚。表姨父听得眼眶发红,接了病妻回家精心照顾。没有姥姥对三表姨的挂念,不知道二表舅和表姨父的寻人之旅能够坚持多久。没有姥姥那一场恸哭,我也不知道表姨父对精神失常的妻子还能残留多少温情。姥姥用她长久以来支付给二表舅和表姨父的情感,换取了二人的重视,再用这份重视,兑换成二人对三表姨的感情。
我有个姑外婆嫁在两百里外的一座城市,交通不便的年代,来回一趟至少需要三天,亲戚间都不太爱走动了。但是姥姥还在,姑外婆必须回来拜年。拜了年,又至少要把老家这些亲戚接去吃餐酒。姑外婆也知道,一旦去了就不可能是一两餐酒的事,可为了这餐酒,她必须料理一切相关事宜。老家的亲戚并不稀罕这餐酒,可姑外婆已经来给姥姥拜了年,他们就必须要登门回拜。两个无意交往的家庭因而勉强被扭结在一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小表舅去姑外婆家拜年时,听说他儿子想做保险柜的生意,恰好我老家附近有个乡镇企业在做保险柜,就帮着从中联络了几回。十年后,我小表舅做保险柜发了家,彻底结束了遛着土狗抓野兔、扛着气枪打八哥的二流子生涯。梳起了背头开上了宝马的小表舅常说,要不是姥姥逼着他去给我姑外婆拜年,他可能还在面朝黄土背朝天,连气枪也没得扛野兔也没得抓了。
姥姥的存在,让家庭内部良性循环起来。
三
人老了,容易滋生无用感。孱弱的身体,衰退的器官,既无法再为他人作出贡献,也无法让自我享受到生活的甘甜。近年,对安乐死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很多人认为老到一定程度的自己,就是一块于人于己毫无作用的废料,不仅产生不了任何价值,还为儿孙徒增麻烦。如果不幸患上恶疾,更是精神、肉体与金钱的多重灾难。
老了的人究竟有没有用?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就像讨论文学到底有没有用一样。
姥姥也常把“我年纪大了,没用了”挂在嘴里,可我看见她的眼神里,分明流露着成竹在胸的笃定。
她对生活,保持着适度的参与和疏离。有人找她闲聊,她会稍稍应对几句,话不多说。有人向她讨主意,她也会帮着分析分析,不下结论。她人在家中坐,耳听八面风,村上大事小情一清二楚,却又从不上心。她应该是知道自己多少还有些用的,颇有些气定神闲遗世独立的风范。
对家里的晚辈,姥姥同样保持着这样不多不少刚刚好的关注。小表舅年轻时嗜赌,表舅妈跟他闹脾气,栓上房门不肯同床。小表舅气得一脚把房门踹开,闹着要离婚。姥姥不紧不慢说了一句:“要是我,也栓上房门不准你进去。”小表舅就不再闹了。表外婆炸油子时,不小心把热油溅到了刚从城里回老家玩的二表姐脸上。二表姐当时只有两三岁,疼得哇哇哭。表外婆只知道抽自己的嘴巴子,一边抽一边骂:“个老不死的东西,叫你嘴馋!叫你嘴馋!姑娘要是脸上留了疤,你这张嘴就该死!”姥姥指着自己的床头柜说:“我留得有一盒狗油,擦了不留疤。”谁也不知道她的狗油从哪儿来的,又在床头柜里留了多少年。如果是她自己熬的,恐怕还要追溯到十几二十年前。她总是不紧不慢不着痕迹在关键时刻稳住人心。她不打人不骂人,不责备谁也不教育谁,大家都爱听她的。
我发蒙不久,有一天放学回家,见家门紧闭,就跑去问姥姥。姥姥说:“你娘砍柴去了,等下子就回来了。”我就坐在门槛上等。对于七岁多的我来说,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以前妈妈总是在家的,妈妈跟家似乎是一个整体,走到家门口,大门必然是敞开的,穿过大门,屋子里就会有个妈妈等在那里。我家住的是晚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老房子,大门又高又厚,杵在我背后像一堵封闭的墙。我突然感觉那扇门永远都推不开了,妈妈永远都不会回来了。我哭着去找姥姥说:“这么晚没回来,我妈可能被狼给吃了。”姥姥抱着我,跟着一起哭。我设想着妈妈的各种悲惨遭遇,姥姥一边陪我哭一边帮我擦眼泪。她没有纠正我,没有拒绝我,给了一个孩子最大的尊重和保护。每每回想起这件小事,我就似乎明白了表外公对他这个“带娘”尽心孝顺的原因。在他跟我坐在门槛上一样幼小时,也曾扑在他父亲这个小姨娘怀里痛哭吧?也曾向她倾吐过无数莫名的恐惧吧?幼小的他,也曾得到过这样无条件的尊重和保护吧?妈妈砍柴回来时,姥姥亲手把我交到她手里,还特地叮嘱说:“这孩子有孝心,担心你出意外,急得哭了好几个钟点。你要给她收个惊。”妈妈掏出手帕给我擦鼻涕时的表情,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农村妇女的宠溺,不是轻易能见到的。
姥姥偶尔也会支使我做点小事,帮她抓抓虱子掏掏耳朵之类。每抓到一只虱子,她就会表扬说“我崽眼尖”“我崽心细”“我崽能干”。三句话交替着说,从不重叠在一起,让我有一种被认真对待的满足感和被人需要的崇高感。如果说陪伴我一起等待妈妈砍柴归来的姥姥让我看到了她的爱,支使我掏耳朵抓虱子的姥姥则教会了我爱别人。
在我与姥姥接触的短暂光景里,她一直坐在那里,连离开木桶椅的能力都没有,看上去确乎是没什么用的。而她分明又在整个家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她负责爱。负责让爱在家庭内部流动。她就是那爱的源头,有她的存在,家族内部的爱意就是一泓源源不断的活水。
四
某一天,坐在姥姥门口扒白饭吃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她居然拥有“自己的东西”。有人可能会因为我的惊讶而惊讶,拥有自己的东西不是很平常的事吗?有什么可惊讶的?可是,我跟姥姥在一起的时候,她连路都不会走,连饭都要舅妈端到手里吃。这样的人,不应该是凡事都依靠别人吗?衣食靠别人置办,住行靠别人照管,怎么会有自己的东西?
但她有,而且东西还不少。她叫着我的小名说:“吃光了菜啊?我碗橱子里有一碟霉豆腐,你夹两块下饭。”我走进厨房打开碗橱,她大约拥有听声辨位的本事,纠正我说:“不是这个碗橱,是旁边那个小的。这个碗橱是你舅妈的,她的霉豆腐不好吃。”我仔细在暗角处搜寻了好一阵儿,才找到一个放着四五个碗碟的柜子,柜子里有一碟霉豆腐,是晒干了的。姥姥得意地说:“我的霉豆腐比她们的好吃多了吧?我每年都晒过的。”晒干了的霉豆腐有太阳强烈照射过的香味,确实好吃。我那个年龄,也不懂什么保质期,无所谓吃进嘴里的是多少年的古董。
她还有一盒樟脑,装在油亮的红木匣子里。梅雨天,我家的衣柜生了虫,她让我爬到她的雕花老木床上找到那只匣子,取出晶莹剔透的两颗送给我妈,我家衣柜里的虫就灭了。她告诉我鉴别樟脑的方法,我妈和表舅妈常常买到假货。
小表弟说,姥姥的枕头下还有一套算命抽机会的签。在所有玩具都靠自家手工制作的年代,这是能让孩子们心尖发痒的东西,其受欢迎程度不输于现在安装了网络游戏的智能手机。那时候,算命是乡下人最高档的娱乐享受,当中最受欢迎的,又是一种被命名为“抽机会”的算命方式。抽出一张纸签,就在幻想中拥有了一次改写命运的机会,这大概就是它分外令人着迷的原因。每隔三五天,算命抽机会的先生就会到村里来一回,闲得无聊的村民们则会合起伙来撺掇某个经济条件稍好些的人物,拿出几个小钱来抽上一签。算命先生有一套纸签,纸签上画着各色漫画式图像,图像旁边配有简短的文字。抽到哪支签,签纸上的图像和文字就代表着抽签人某方面的命运。说是算一命,实则大半个村子的人都围在旁边听,脸皮厚些的,顺势插进手去给自己来一签,算命先生也抹不开脸阻止,往往是只收了一份钱却算了五六条命,一下午的时光就在七嘴八舌中津津有味地流逝。现在看来,有点心理学家给人做心理咨询的意味。小孩子不敢插进手去抽签,看得见摸不着,因而越发对那些构图夸张颜色鲜艳的签纸好奇。小表弟爬到姥姥床头去偷了好几回,可惜未能得手。他无数次构想过自己摆出一整套纸签在小伙伴面前指点江山的样子,无数次空留遗憾。姥姥说,算命的东西,不是玩的。
我想不通姥姥是怎么把这些东西弄到手的。是亲戚朋友送的?还是她行动方便时保存下来的?行动方便的长辈们都没有的好东西,她却有,就算是保存下来的,也彰显出她本性上的与众不同。第一次看到“独立女性”这个词时,我想到的是姥姥。一个缠着小脚的女人,却让我在第一时间将她与独立女性联想在一起,这有些不合情理。而我脑海中映现出姥姥扯着又长又白的裹脚布坐在一盆热水前修剪脚趾时,她的身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分明是怡然自得的。我,以及我所交往的大部分经济独立行动自主的女性,精神上未必拥有这份怡然与自得。我们时常被裹挟,或被时代或被权欲或被金钱或被爱情。我们大多数时候陷在焦虑、压抑、纠结、无助里。姥姥不抱怨、不谄媚、不强求、不委屈,在精神上从未依赖过谁。在灵魂深处,我将她定位在当之无愧的独立女性范畴里,尽管她的身体困囿在无法奔跑的三寸金莲上。我时常想象,她若是站起来奔跑,该是怎样的情景?
我在她床沿的抽屉里翻出过一个银制小方盒,小表弟说,那是用来装香烟的。小方盒里搁着一根嘴部被锤扁了的弹壳样的玉管子,小表弟说,那是烟嘴。我不太相信小表弟的话,因为那时他实在太小了,很不可靠的样子。直到姥姥去世后十几年,偶然在旅游区的小摊上看到一模一样的小方盒和扁嘴弹壳般的玉管子时,我虽然尚不能确定姥姥的小方盒是否真为银制的,也不确定扁嘴弹壳样的管子是否真是玉器,但我终于确定了,小表弟的话是真的。
我在那个小摊前想起妈妈和三姨父的一次对话。妈妈问:“过滤嘴有什么用?”三姨父说:“就像水烟的烟筒。”妈妈问:“可以消烟吗?”三姨父说:“可以消一点。”大约是因为正值春节期间,三姨父心情好,又补了一句:“你抽过水烟吗?”妈妈笑起来,“小时候偷她外婆的抽过一口,呛得要死。隔壁老外婆抽。”妈妈嘴里的隔壁老外婆,就是姥姥,我当时没听明白而已。
又过了十几年,读林徽因的传记时,我在徐志摩的一封书信中看到:“林小姐风度无改,谈锋犹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在徐志摩眼里,能吸烟卷喝啤酒,显然是独立女性的一种标志。
姥姥的银烟盒玉烟管,赶的是时髦?抑或追求独立?青山黄土不语,她无法给出答案。我能做的,只是在后人只言片语里追寻她的足迹。
我婆婆呀?痛不说痛,苦不说苦,病成那样了,还是笑眯眯的,真是……
后里姥姥啊?后里姥姥我晓得,田地是下不得,屋里的活都会干,切出来的麻片风都吹得起。手脚方便的时候,左邻右舍都请她帮忙切麻片……
那个老人家?我记得我记得!她大爷、大娘、二娘,都是她送走的。她又不会走路,不晓得她怎么搞的。她也从来不说……
这个“不会走路(指的是缠了小脚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行走)”却帮一个个亲人料理了后事的小姨娘,这个左邻右舍都请她切芝麻片的何家媳妇,这个浑身是病却从不叫苦叫痛的老人,如果不曾拥有独立的人格,靠什么支撑起怡然自适的晚年?
五
长大后,我和表姐表弟们四散各方,起初是一年难得见上一面,慢慢变成十年也难得见上一面。各人拥有了自己的家庭,分布在不同的行业,既没有互相联系的需要,也没有聊得拢的话题。混迹于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们对于彼此的意义,似乎跟陌生人没什么不同,甚或还比不上拥有某类相似价值观的陌生人。有那么十几二十年,我是宁可开启一段与某个陌生人的交往,也不愿回过头去跟表姐表弟们取得联系的。
微信兴起后,有位表姐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拉了个家庭群,失散多年的亲友又一个个通过虚拟的空间聚集在了一起。入群的短暂兴奋过后,很快又恢复了平静,群内经年累月见不到一个信息,以至于我在不知不觉中忘记了这个群的存在。
某天,我正在一座古镇拍照,群里突然跳出一张照片。照片里有个老人坐在花窗下咧嘴憨笑,勒着抹额,穿着斜襟小袄,脸上的皱纹层层叠叠的。群里瞬时热闹起来,“姥姥”“姥姥”一行行相同的信息刷了屏。点开照片细看,花窗下的老人与姥姥的五官并不相像,但脸上的皱纹、咧开的嘴角、头上的抹额、身上的衣裳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的。那不是姥姥,又确乎正是姥姥。那明明并不是姥姥的老人,却让我和其他表姐表弟们一样有种忍不住要叫声姥姥的冲动。那是姥姥曾经给予过的爱护,在我们假寐了多年的心灵上苏醒。
“我记得姥姥特别喜欢吃桑葚,桑葚一熟,姥姥就怂恿我爬到树上去摘。”
“我记得那棵桑树,就在武武家门口,有一回同时上去七八个人,把树枝都压得驼了下来。”
“姥姥还喜欢养蚕,十几天就能把芝麻大的蚕宝宝养成腰果那么肥。”
…………
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共同话题,原来我们毕竟跟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是不一样的。数十年的隔阂,一谈起姥姥就消弭于无形。
我和我的表姐表弟们,身上或多或少带着一些姥姥的遗迹。表姐聊起她看到小区里的棕榈树时,时常想掰一挂棕叶下来扎粽子,在她小时候,姥姥就是用棕叶扎粽子给她吃的;大表弟则喜欢穿手工纳的鞋垫,他小时候的鞋垫,大多数是姥姥纳好了存放着慢慢用的;我也想起自己喜欢拍摄古镇,最初就是因为在古镇上可以找到与姥姥居住的老房子相似的气息。
当然,姥姥对我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我记得第一次去深圳时,初恋男友让我靠在一棵大榕树下拍照。榕树根须太多,挡住了我的脸。我转过身去就往树上爬,把举着相机的男友惊得目瞪口呆。那天我蹬着十一寸的厚底鞋,留着斯斯文文的披肩发,穿着紧身牛仔裤,怎么都不像能爬树的样子。可是,那棵树实在是太好爬了。武武家门口笔一样直、腿一样粗的桑树我都能随便上下,树干足足可供四五人合抱、枝叶旁逸斜出的大榕树,岂不是如履平地?不要说穿着紧身牛仔裤,就算是穿着鱼尾裙,我照样一转身就能爬上去。事实上,第一次去北京我就做过类似的事。那天,身无分文的我跟着一位刚认识不久的北京朋友去蹭饭,途经一座小公园时,一向开着的铁门上了锁。朋友说,要绕过那座小公园,必须穿过好几条胡同。饥肠辘辘的我二话不说就从锁着的铁门上翻了过去。他看着我一身雪白的紧身吊带裙,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他的神情告诉我,一个长相温婉的姑娘不该显示出如此出色的攀爬能力,但在姥姥的督促下习得的攀爬能力早已融入我的血脉里,一不小心就泄露了出来。
很久以来,我只知道自己善于攀爬,却早已忘记了最初学习爬树是为了给姥姥摘桑葚,直到表姐表弟们在群里聊起来,才重拾了这个记忆。
我的根,和他们的根是搭在一起的。而那丝丝缕缕的根系,是需要像姥姥那样的长辈来进行链接的。链接系统若是出了错,根系就散了、乱了,甚或彼此倾轧与攻击。
我不知道这世上有多少人像我和我的表姐表弟们一样,操持着从一位老人身上获得的本领或者习得的性情在远离故土的陌生城市里生存。我们这些人散布在哪里,便将这位老人的本领与性情带到哪里。如果这位老人是温馨和煦的,我们携带的性情里面,也必然有一分与温馨和煦相关的东西。
如果这位老人是暴戾的……
如果这位老人是暴戾的,我会因为曾经拥有过一位温馨和煦的姥姥,将有关暴戾的一切自行屏蔽。
欧阳娟,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长篇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刊,已出版并发表长篇小说《深红粉红》《路过花开路过你》《交易》《手腕》《最后的烟视媚行》《婉转的锋利—林徽因传》《天下药商》,散文集《千年药香—中国药都樟树纪事》,撰写纪录片《千年药都话樟树》。其中《天下药商》获江西省谷雨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