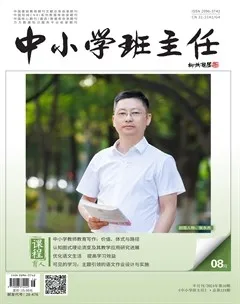论教育写作的目的:阐释学的视角
2024-08-26宁中孟
[摘要] 从阐释学的视角看,教育写作是关于教育者写作过程本身的意义研究。重视教育写作展开过程体现了写作的真正目的,突破了以往教育写作经验性、零碎化的表达形式。以目的为导向,以过程为核心,推动教育者对自我身份的寻求及认同;将经验性的知识整合转化为审美意识的能动觉醒;“写”的过程推动教育者价值观念的重构;教育者与他者构成的多元主体在时空交错的多向维度中,形成互动性的辩证循环。最终,有效化解教师“写不出”的担心和“写不深”的焦虑。
[关键词] 教育写作;目的;阐释学;视角转换
人生活在意义世界之中,而意义世界是由语言和阐释搭建起来的。语言蕴含着意义可能性,阐释则使意义可能性显现为现实性。阐释是语言的重要功能之一。人类世界离不开语言,也离不开阐释。意识到阐释的重要性,就有了专门探究阐释奥秘的学问,即阐释学。
教学写作是运用文字符号的形式呈现教育工作结果的有效途径,其中包含教育者、教育对象和表达形式。当下的教学写作,要么重视教育者自身的经验性总结,要么强调教育对象的复杂和多变,却忽视了写作表达形式的有效意义,教育写作本身是教育者对自我身份、自我行为及自我价值的一种具体表现。
一、寻求身份的认同
教育写作的表达及呈现方式多样,如教案、教学论文、读书笔记、下水作文、文学作品等。教师在繁重的日常教学工作之中写下的作品,是否能表现出写作者的内在情感体悟和独到思考,便成为一个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写作,不是为了应付常规性的教学检查、职称评定和业绩考核等事务,而是用文字的形式表达作者自身的形象,以及作者通过写作的方式寻求最真实的自我。其具体表现在,写作欲求的冲动、写作情感的真挚、写作意志的坚定。
曹禺在《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中说:“我想写作要有对生活的真实感受,逼得你非写不可,不吐不快。”作家因为对现实世界有发自内心的感触,所以不得不用“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正如笛卡尔所言“我思,故我在”,它强调意识自为自在,肯定意识的怀疑反思能力。人的自我身份,在此等于纯思的意识。笛卡尔式主体的身份认同不仅强调“思”与自我的一致和自足,他还坚信思想的我就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内在核心。来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思考是激发教育者写作的动力,一方面是对教育活动的经验性总结,将教育感受转化为独特的内心体验,借助文字的形式表达给他者,从而推动经验的不断传播和交流;另一方面是教育者对自身教育方式的反思,是对教学方法的总结性回顾,将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整理在册,从而不断推进对教师身份的自我思辨。
以往的教育写作更多注重教育经验的总结,强调对教育心得的优化,注重教育感想的传播,如同优秀教师传授心得一般,是个性化、碎片化的经验性汇总。这忽略了每一位教师主体身份的唯一性、差异性。真正的教育写作要求落实到每一位教师自我层面,用发自内心的欲望作为创作动力,才能激发出对教育活动独特的、鲜明的思考。正如《毛诗序》所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不仅呈现真切的教育感悟,更是教师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同时通过写作完成对自我情感的塑造。
于是,确立具有启蒙价值的身份认同,通过写作的形式实现自我精神世界的整合。人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统一体,具有理性、意识和行动能力。换言之,教师通过真实的教育写作过程唤醒自我对主体价值的认同,将过去具有零散性、单一化的教学感想整合为体系化、多维度的教学成果。
二、审美意识的觉醒
如果说教育写作的内在动力是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寻求,那么,写作所呈现及表达的内容便是教师真挚情感的流露。华兹华斯说:“因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并且,虽然这点是真理,但是凡是有点价值的诗篇,并不是可以随便拿一类主题来创作的,而都是出于一个具有异乎寻常的官能感受力,而且经过深思久虑的诗人之手。”诗人通过栩栩如生的诗行传达对世界的思考,以求真求善的态度看待世界。艾青用一生的坚守书写“诗人必须说真话”的信念,“真是诗底唯一深固的始基,诗是真底最高与最终的实现”(《〈诗与真〉序》)也说明了这一点。对于教育写作而言,更需要一颗求真务实的心去观照教育活动的意义和价值。
真挚的情感表达是对教育活动的审美创造。用“心灵唤醒心灵”的方式打开教师的审美意识,创造出主体与客体互相契合的审美空间,唤醒教育对象的审美共通感。正如鲍桑葵在梳理休谟的“共通感”时所言:
美给予人的快感大部分是从便利或效用的观念中产生的。因此,这个似乎值得注意的论点正是把效用观念和美感精确联系起来的方式。因为休谟极其明确地判定,美一般来说总是由于效用而起。这种效用同产生美感的观赏者根本无关,只牵涉所有人或直接关心对象的实际特性的人。因此,只有通过共鸣,观赏者才能感受美。
教育写作的过程不仅关系到教师自我与过去的有效共鸣,感同身受,更需要重视教学活动中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沟通,即师生之间的情感共鸣。而情感共鸣的核心在于审美意识的契合,如刘勰笔下的“神与物游”,谢赫画上的“气韵生动”,王士祯诗行中的“兴会神到”,王国维词话中的“无我之境”。回顾性的教育写作是将曾经体验过的审美共通感再次凝练,并运用形象的文字形式将其再现出来。写作的过程即审美意识的再次唤醒,重新回到教学过程之中。这就打破了时间上的距离,将教师再次拉回课堂之上,不仅是知识层面的温故知新,更是审美方式的再次重构,如阐释学所言的“视域融合”,即将当下的主体自由再现在自然形象之中,于是,自然形象的各组成部分在主体性作用下融合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生命整体。
写作的意义就是将外在于时间、空间的自然事物,再一次“靠心灵灌注给它的生气”而形成审美的共通感。此刻的教师不再局限于对经验的阐发,或者对现象的追问,而是转向审美意识的创造。于此,教育写作的目的便唤醒了教师内在的自我,“他仿佛忘记了历史,像古人一样,开辟一片艺术的新天地,使之从虚无堕入毫无掩饰的混乱的状态”。将自我与过去经验世界连接在一起,同时关注学生的课堂表现。一方面,把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知识性理解传达给学生,达到“授业解惑”的目的;另一方面,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将教学内容的审美体验分享给学生,唤醒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深度理解,打开审美共通感的窗口。与此同时,写作的过程也再次激发了教师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教师去探寻课堂内外的深层意义。
由此,教育写作的核心内涵转变为写作教育。这表明,把知识性层面的教育活动实践转化为审美创造层面的主体重构。换言之,教育写作的过程是对教学经验的累积和加工,更多的是呈现教师对知识的整合能力。而关注教育写作的目的,就是重视教师写作过程本身,即通过写作达到对教学过程的再次创造,唤醒教师内心的审美意识,并且将其审美意识传达给读者,特别是反馈给学生,让他们再次巩固课堂内容,同时深化对自我审美意识的理解。
三、价值观念的重构
从本质上讲,教育写作的目的是关注“写作过程本身的意义”。因为教育写作更多的是教师对其主体价值的思考和追问,以“写”的方式再次回溯教学的全部过程。主要体现在:“写”是“思”的目的,“思”是对“写”的重构,“写”与“思”构成辩证统一的整体。
其一,教育写作是“思”的目的。胡塞尔认为阐释的本源在“回到现象本身”,海德格尔强调“世界关联的目标就是存在者本身——此外无什么;一切科学研究借以发生、从中辨析的那个东西就是存在者本身——此外无什么;唯有存在者——此外无什么”。对于教育写作而言,亦是如此,以往的教育写作“人们聚焦的始终是‘经验构成’,即‘写什么’,至于‘如何表达经验’,即‘怎么写’,要么降入技术层面,要么干脆束之高阁,在‘书写’惯习的支配下无意识运行”。教育写作不能离开教师的能动思考,“思”是教师对自我价值观念的不断提问,对教育活动的追问才能不断更新教学知识,而存在于意识观念层面的“思”又不能被长时间保存,更不能传递给学生,所以需要教师不断地“书写”,将潜意识形态的思考转化为可见形态的文字符号。
其二,“思”是对教育写作的重构。正如“唯有变才是不变本身”,教育写作的过程是对教师价值观念的不断重组,扩充主体的想象力。想象是人对不可能存在、不存在或此时此地不存在的东西的呈现能力。想象作为一种意识,它只能表示意识与对象的关系;换言之,它是指对象在意识中得以显现的某种方式;或者如有人愿意这样说的话,它是意识使对象出现在意识中的某种方法。因而拓宽教师关于写作的想象力,将经验习得性知识不断重组、加工、整合,获得知识层面的提高。此时,写作能带给写作者一种不断发现生活新意的习惯,甚至是不断创造新生活的动力,而这便是一个人创造性的基础,最终能让人形成创造性的职业人格,从而也会改变教师的职业生活,使其免于平庸和职业倦怠。由此,教师通过写作的方式打开了关于“认识自我”的窗口,提炼整合原有价值观念,归纳拓展新的价值原理,创造出新颖的、具有启发意义的教学思想。
其三,教育写作与教学思考构成动态性辩证循环。“写”与“思”不仅仅具有共时性关系,还处于历时性的不断重组过程之中,即“思”的本身在于对教学活动的反问和质疑,而“写”是对教学结果的总结和调整。通常认为,“思”在“写”之前进行,“写”是“思”的被动结果。其实,在阐释学视域下,“教育写作”的过程一直是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既是在“思考‘写作’过程中的问题”,又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思考’问题”。
归结起来,教育写作是教师自我与教学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无休止的对话;写作的过程就是将过去经验所得与自身实践相结合,以文字的形式将记忆形象化、再现化。实际上,教育事实就是关于个人的事实,不过,不是孤立状态下的个人行为,不是关于一些真实的或想象的动机,教育写作记载的是关于社会之中个人之间彼此关系的事实,是关于个人活动结果所产生的那些社会力量的事实,这些结果带有个人经验的鲜明特征,同时也呈现出教师在时代背景下的共性样貌。
用阐释学的观点看,对于写作过程的思考,阐释学反思所揭示的并非一种封闭自身的心灵、一种纯粹内在的自身呈现,而是一种朝向他者性(otherness)的开放状态,一种外化的、不断超出自身的运动。只有把自己呈现给世界,我们才能把自己呈现给自己;也只有把自己给予自己,我们才能对世界有所意识。教育写作是教师对自我教学活动的不断重构,用“写”的方式打破对以往经验的思维定式,此刻的“写”不再是静态的文字书写,而是具有动态性的思维活动。教师在写作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思”的深度,而“思”的力度又不断推动教师去探寻“写”的奥秘。
四、主体超越的崇高
通常意义上,教育写作的主体是教师或者从事教育教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但实际上,教育写作的主体并不局限于此。一方面是经验主体的互动,具体是指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的互动交流,形成多元主体的融合;另一方面是历时性主体的融合,具体是指教师通过写作将过去、当下、未来三维时空连接在字里行间。
其一,教育写作是多方主体经验的互动。虽然写作表达主体是单一的教师,但是教师在将教育活动结果呈现出来的过程中,包含了对教育对象的引导、教学内容的整合、教师同行的切磋,以及与家长之间的沟通。诚如海德格尔“将生活世界刻画为周围世界、共同世界和自我世界这三个领域的相互渗透,并主张作为世界体验者的此在从来都已经和他人共在(mitsein)”。对于教师而言,将自身习得的知识传递给学生,使其学会并掌握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教育写作的回溯进一步深化教师对知识世界的理解,并且以“写”的形式重新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
写作结出的果实——文章,再次反馈给同行或家长,此时,教育写作的过程才算正式开始,因为读者的阅读是打开作者心灵之窗的钥匙。文本世界的展开是读者与作者相互融合的开端,用沃尔夫冈·伊瑟尔的话讲,写作本身包含着“隐含的读者”,包含作者对读者的“召唤结构(appeal structure)”。对于教育写作而言,以往教育写作的终点,即教师文章的完成或者发表,标志着写作任务的完成。而实际上,教育写作的文字没有被读者阅读,没有反馈给学生或家长,没有引领学生参与教师的回顾性反思,这样写作本身的“召唤结构”也就未被打开,教师的写作也就并不具有现实意义。
其二,在寻求教育主体多重互动的过程中,加深教师对自我时空限度的认识。以写作的形式联通当下与过去的时间,在文本世界中展开当下自我与过去自我的有效对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教育生活,很容易造成新鲜感的消退、创造激情的淡化,而对备课、作业、考试这些日常生活的审视与重建,不仅给平凡的教学生活带来新鲜感,也能不断积累对教育、对儿童、对课堂等十分丰富的感性经验,这些恰好形成了一名教师专业成长的资源库”。写作,此刻不再是为功利性的教育考核服务,而是回归自我教学生活的一种途径。
用海德格尔阐释荷尔德林的诗句“人充满劳绩,但还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所言:
“诗意地栖居”意思是说:置身于诸神的当前之中,并且受到物之本质切近的震颤。在其根基上“诗意地”存在——这同时也表示:此在作为被创建(被建基)的此在,绝不是劳绩,而是一种捐赠。
从本源上看,时间与空间不具有可回溯性,不能逆向发生。然而在教育写作的展开过程中,教育者置身于事物的本质,也即“在世界中存在”。写作将主体的自我带回历史时空的场域,通过文字的梳理将思考诉诸当下,而此刻的当下又凝结着过去的自我情感,打破时空阈限,生成新的主体价值观念。
此刻的主体价值观念,不再是单向维度的观念判断和价值选择,而是具有三维向度的崇高超越,在连接过去的同时,把当下的写作投向对未来的思考,具有“向死而生”的超越。可以说,写作的完成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生命终结,“写作”赋予了人的生命的无限希望,打破了存在主体对生命有限性的焦虑,突破了“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羁绊。显然,教育写作,成为教师个体生命不断延续的有效形式,既能够将过去经验汇聚成知识性成果,又能够在不断“写作”中消解时空间隔,同时也把当下的感悟诉诸未来,延展个体生命的三维空间,超脱当下认知的束缚。
总之,基于阐释学视角对教育写作的思考,更加重视“教育写作过程本身的意义”,突破以往教育写作过多重视原因与结果、问题与措施、策略与方法等层面的考量。回归本源性问题,落实到“写”的过程本身,其中隐含着教育者主体对自我身份的寻求,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之中,唤醒自身对写作意义的审美创造,同时激发被教育者对美的追寻。由此,推动教育者从经验性的知识积累和感悟性的审美欣赏转变为对教育写作观念的反思,把“写作”与“反思”融合在文字表达的过程本身之中,形成互动性的辩证循环,不仅消解“写不出”的担心与忧虑,而且打破“写不深”的畏惧与虚无。最终,写作过程本身便成为连接主体与他者视域的桥梁,成为贯通主体时空阈限的纽带。
[参考文献]
[1]曹禺.和剧作家们谈读书和写作[M]//曹禺全集(第5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369.
[2]赵一凡,等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5,466.
[3]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9:1.
[4]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3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6.
[5]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235.
[6]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18.
[7]李政涛.教育经验的写作方式——探寻一种复调式的教育写作[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1(03):149-159.
[8]让-保罗·萨特.想象心理学[M].禇朔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25.
[9]颜莹.教育写作:教师专业表达和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人民教育,2020(06):66-68.
[10]丹·扎哈维.现象学入门[M].康维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74-75.
[11]庄华涛,等.教育写作离我们有多远[J].小学语文教师,2015(04):21-25.
[12]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