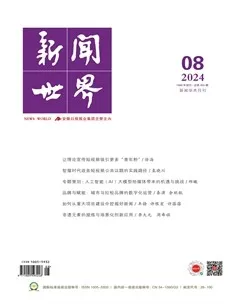社交货币视角下MBTI在青年社交中的传播研究
2024-08-21吕岩松
【摘 要】传播技术发展赋予了青年全新的社交模式,MBTI(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作为青年追求高效和精准交友的社交货币受到大量追捧,MBTI凭借文本形式多样化,传播过程游戏化以及测试反馈精准等特点成为青年社交新型模式。但无论使用哪一种交友模式,青年在享受MBTI带来的社交便利的同时,也需警惕其带来的刻板印象与社交鄙视链等弊端。任何交友都需传播双方抱着平等友善的态度,才能为彼此创造更多的可能。
【关键词】社交货币;MBTI测试;青年社交;传播研究
MBTI是一种常用的性格测试工具,它基于卡尔·荣格的人格心理学理论发展而来,由美国作家迈尔斯和她的母亲布里格斯在 20 世纪 40年代编制共同开发[1],旨在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近几年,MBTI测试每年都会登上各大平台热搜,根据千瓜数据显示,2023年第二季度 #MBTI 话题浏览量环比增长4239.67%,势头强劲;小红书爆款话题 #万物皆可MBTI 浏览量高达13.85亿,总互动量达到407万;相关的种草笔记总量增长272.53%,互动总量增长253.57%,分享总数增长272.77%。从十二星座到塔罗牌占卜,再到如今的MBTI测试,作为一种由媒介技术、社会文化和青年自我意识互相勾连而形成的社交实践,不断嵌入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并且演变为一种备受追捧的时尚文化,折射出当前年轻人社交方式的衍变。相较于塔罗牌或星座“迷信式”社交,MBTI测试从认知、判断、外向、内向四个维度测试出16种不同的性格类型,每一种性格对应着不同的社交模式,青年可以根据其显示出的具体细则去接触符合自身交友预期的好友,青年之间相互了解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I人还是E人”。在网络二次创作与自媒体营销下,MBTI测试不仅充当着交友的选择标准,更是被青年视作为消除隔阂的社交货币。乔纳·伯杰指出,当产品可供人们大肆共享和谈论,并使人们看起来更优秀、潇洒和时尚时,这些产品便成为社交货币,从而使人们获得更多关注、好评和更加积极的印象。[2]这让我们不禁思考,MBTI测试为何能在青年群体如此风靡?这种交友模式折射出青年怎样的心理状态与交友观?过度依赖测试交友是否会产生逆反作用?
一、作为社交货币的MBTI传播表征
(一)生产:文本符号的多种形态
MBTI作为一种人格类型指标,其低准入和可创作性使得参与者不再局限于讨论测试本身,而是走向了“文本盗猎”之路,助推次生的表情包以及各种让人忍俊不禁的热梗入侵到青年间的交流当中。亨利·詹金斯将粉丝阅读并对文本进行二次创作的再生产经验行为描述为“文本盗猎”,指具体创作过程中青年由被动的意义接受者转化为积极的创作者和意义的操控者。MBTI测试对不同人格类型所呈现的详细解读,成为了青年二次创作中最原始的资本,青年结合自身经历通过“拼接”“恶搞”“同构”等手段对这些开放性文本进行了各种自主性的符号阐释,重新赋予了MBTI人格全新的意义。[3]
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助推MBTI的传播,与MBTI相关的meme成为了新的社交符码,青年往往在介绍自己的人格类型之后,还会配上一个代表自己MBTI类型的表情包,甚至许多经典影视中的角色也被网友贴上了MBTI标签,在聊天时发送相应的表情包来进行情感表达。例如,KPBL性格人群将自己称为“卡皮巴拉”,并配一张黄色水豚的可爱表情包图像以彰显自身可爱形象。这些二创内容满足了青年群体的猎奇心理和娱乐需求,使MBTI成为社交媒体上新型社交礼仪与社交货币,当他们交流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时,例如彼此喜欢的甜品,热爱的运动,其内容本身也被赋予了某种性格特征。这种万物皆可MBTI的交流方式拉近陌生青年间的社交距离,为进一步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MBTI测试已成为一种新兴青年亚文化现象,各种语言符号与图像符号的结合,给青年带来全方位的视听刺激,成为青年在各个社交平台进行互动时必不可少的互动符号。社交货币的生产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这些形式在网络用户持续进行的二次创作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传递:基于趣缘的游戏传播
在web3.0时代下,新媒体技术几乎以日更的迭代速度为青年一代提供了更多的社交便利,青年群体逐步挣脱了传统社会中地缘与血缘关系的桎梏,逐渐倾向于以趣缘为核心的社交模式。信息传播方式的演变改变了青年间的社交模式,媒介和商业资本所创造的社交话题与场景不断重构青年的社交理念,为个体身份塑造和群体交流实践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MBTI测试这一社交货币,基于认同形成的网络圈层正全方位地渗透至现代青年群体的生活之中,以不同的人格类型匹配相应好友,极大程度上契合了青年基于自身兴趣、爱好、价值观等方面进行交友的社交习惯。青年传递MBTI这一社交货币消费的是图片、文字、表情包背后的情绪价值与情绪满足,将具有相似兴趣爱好的个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一种跨越地理、血缘以及地缘关系的社交网络。[4]
当青年群体将MBTI作为传播内容时,他们往往抱着一种游戏测试的心态,体现在他们乐于参与并根据自己的性格特点,与他人分享和交流有关MBTI的内容。美国传播学者威廉·史蒂芬森提出了“传播游戏观”,他将传播行为分为“工具性传播”和“消遣性传播”,他认为传播行为本身也是一种游戏,媒介就是传播者自我取悦的工具,人们在传播的过程中能够收获满足。MBTI测试自身带有一种游戏属性,通过一系列问题的填答就可以对自身性格属性有较为清晰的认知。诸多测试网站依据个体不同的性格特征,生成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以及相应的卡通角色,从而赋予了测试游戏化的特质。这种游戏化的设计吸引了大量用户参与,使其抱有娱乐心态与好友分享个人性格,去感受共情传播所带来的快乐,以进一步探索和了解自身的性格特点。在以兴趣为主、游戏体验感为辅的传播模式下,MBTI测试也在社交媒体用户的追捧和讨论中不断延伸,更多的网民基于“乐队花车”的从众效应积极参与进来,营造出一场盛大的群体狂欢。
(三)反馈:社交符号的同向解读
斯图亚特·霍尔在《电视话语中的编码和解码》一文中提出了与受众相对应的三种解码立场:统治-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对立立场。大多数青年在测试过程中倾向于采用统治-霸权立场来解读测试文本,这种倾向具体体现在测试后的言语表达,如:“很对!这不就是我嘛”等。青年这种解读方式 的背后折射出其对于符号的认可,使得个体间交往与熟知变得更加高效。青年在进行测试时经历着人内传播过程,即有的个体测试后对自身性格有了新的理解,或是出于兴趣和他人推荐,从零开始建立对自我的认知,这一过程是主客我之间的信息交流过程。这种同向解读的前提是测试的准确性,具体体现在它的科学性、能动性、实用性。
就科学性而言,MBTI是基于心理学理论开发的一种心理测量工具,它严谨地设计了一系列测试题目和评分规则,通过对回答问题的量化分析和数据统计进行结果解读,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信度。
就能动性而言,新媒体的崛起赋予了青年自主选择权,他们从互联网的海量信息中筛选出自己所需要的内容。MBTI测试强调个体的特质和行为模式,个体通过主动答题得出自身性格类型,从而更好了解自身。
就实用性而言,MBTI测试不仅是一种测试工具,它还能为个人提供实际的指导。智联招聘根据不同性格发布了《MBTI 职场性格类型大数据报告》,推测出不同行业人员的不同性格比例。通过了解自己的MBTI类型,个人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优势、弱点和发展方向,从而在职业、学业和人际关系等方面进行更好的规划和决策。
这种符合Z世代群体的符号社交,在满足青年亚文化话语逻辑的同时,进一步以认同式解读的方式迎合了青年求同思想与社交困难矛盾的现状而产生的自我“展示”与“认同”。 随着社交的深入,表层的语言符号与深层的性格展示相互交织,而以性格为基础的框架伴着“万物皆可MBTI”为青年提供了交流契机与下一个话题的期待,加固了MBTI的互动链条。
二、MBTI社交潜在风险及规避
MBTI作为新型社交方式,带给青年个性化的社交体验。但青年身处快节奏生活方式之下,在享受精准交友带来舒适感的同时,也需警惕这种单一化测试所代表的工具社交带来的隐患。
(一)刻板印象:社交形象的标签化
近年来,青年群体倾向用特定词语去描述自身状况,例如佛系、躺平、打工人等,其初衷可能是对于自身状况的自嘲,或者是对深陷困境的激励,如今这种打标签的行为已延伸到青年社交行为中。青年利用MBTI测试充当交流资本,将社交过程简化为工具性测验时,双方建立的社交关系既缺乏了解和信任,也缺乏承担责任和彼此奉献的基础,最终得到的仅仅是基于自身认识的刻板印象。
戈夫曼提出的“印象整饰”观点认为人际互动过程中,行动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运用某种技巧塑造自己给他人的印象,从而使他人形成对自己特定看法。这种打标签行为,虽然能够将个人融入某一群体,达到由“我”到“我们”的转变,但也将个人行为囿于群体中,放弃了个人探索自我的可能性。当个人展现出自身MBTI社交名片时,个体就会极力维护测试所呈现出的“前台”性格,甚至为了强行融入某群体,随意选择测试回答,以达到特定性格分类的目的。在社交环境中,当个体被简单地赋予身份标签时,双方之间的交流往往停留在表面印象层面,忽略了标签背后人的主体性和差异,限制了人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导致双方无法全面了解,也无法触及彼此的精神世界。
(二)圈层社交:鄙视链下的优越感
当个体融入群体之后,其社交模式由人际社交转化为圈层社交。相关研究表明:相似性在人际关系之初具有重要作用,而兴趣爱好则是人与人相似性的主要来源。以豆瓣上的MBTI中心站小组为例,该小组有20888名成员,成员们围绕性格类型、美食、交友和恋爱等话题展开讨论,小组成员看到感兴趣的帖子,出于自我表达和身份认同等动机进行留言和转发,从而巩固圈层的高黏性特征。然而,小组成员间存在受教育程度等差异,他们往往会歧视甚至鄙视持有不同观念的人,进一步加剧了社交圈层的排他性。
需要看到,MBTI社交的初衷是帮助每个人认识自己,理解他人,提高沟通和合作的效率和质量,而在圈层的排斥与隔离下,有人甚至为了满足自身虚荣心而多次测量修改答案并进入准圈层之中。这种以测试作为入圈门票的行为,已失去了测试交友的初心,成为助推鄙视或偏见的“令牌”。
(三)社交困境:亲密关系的工具化
近年来,青年社交范围不断窄化,甚至将自身封闭在自我世界中,以“社恐”当作自己拒绝社交的挡箭牌。一方面,生活质量高速发展所致的快节奏工作模式不断压缩青年社交时间;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虽赋予了青年选择权,但层出不穷的虚假信息和功能复杂的交友软件使青年陷入“社交泥潭”。
青年利用MBTI测试以寻求好友,然而刻板印象的存在和交友功利性使得其关系网络中充满着弱关系,缺少长期稳定的强关系。对其自身来说,长期依赖于测验交友,可能导致其面对陌生人时,处于“无言以对”的尴尬场面,甚至是社交能力的退化。[5]“快餐式交友”等现代交往模式以迅速联合、即时脱离、持续更迭的特点,为年轻人提供了充满新鲜感和激情的体验,然而它却忽视了个体在关系建构中的主体性,以目的和效率为价值理念正慢慢地将工具性带入人们的交往中。
MBTI社交虽然对交流内容进行了补充,无需花费精力和时间去揣测对方兴趣和爱好,但始于高效性和功利性的社交关系极易断裂,过度依赖MBTI测试,人们会忽略交往中真正追求的东西,进而影响深层次的情感交流,在得到短暂性的情绪弥补后,青年可能会产生孤独与空虚感。
三、结语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用户对于信息数量和质量要求不断提升,媒体为了迎合用户对平台内容进行个性化处理,再产出符合用户喜好的内容,用户信息收集方式也从被动摄入转变为主动汲取。虽然用户在内容浏览上的悦己程度不断增强,但与人沟通议题却陷入了尴尬境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MBTI的出现为青年社交提供了具体切入点。本文从MBTI的流行入手,从社交货币的角度探究MBTI的表征,从青年的社交方式转变折射出当前青年交友理念的高效化转型。虽然使用MBTI作为交友工具可能会带来刻板印象等问题,但这种与快节奏生活方式相吻合的新型社交方式,让每日忙于工作且害怕交友的青年能够借助共同话题结下新友谊。当然,对于青年来说,MBTI只是开启友谊的起点而非终点,无论是以什么内容打开话匣子,友谊建立的本质依然是深入真诚的了解而非最初的印象,如果能以MBTI为契机与好友建立深层次的情感共鸣,或许能实现交友时的初心。
注释:
[1]汤欣雯.社交媒体时代MBTI测试流行现象探析——以B站用户视频为例[J].新媒体研究,2022(08):83-87.
[2]刘威,温暖.从“快乐水”到“社交货币”——Z世代新式茶饮消费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2(06):92-100.
[3]葛彬超,孟伏琴.青年身份认同的“微”建构[J].中国青年研究,2020(06):107-113.
[4]宋金鸿,刘佳正.探究网红空间青年拍照打卡行为[J].新闻传播,2019(12):6-8.
[5]郭喨.你我有别:关系如何影响道德责任归因[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4):23-29.
(作者: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传播学)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