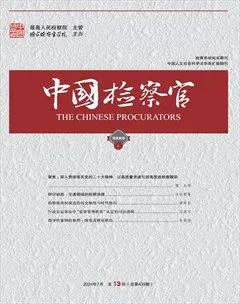检察机关贯彻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的实践*
2024-08-19李弘博张铁英梁国武
摘 要:“双向保护原则”是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基本原则。贯彻双向保护原则,检察机关既要充分保护社会利益,对涉罪未成年人惩处和约束,又要考虑涉罪未成年人利益,对其进行教育改造和挽救。目前,贯彻双向保护原则还存在惩治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力度不够、办案效果不理想、履职不全面等问题。要增强检察工作主动性,严厉打击涉未成年人重大、恶性、多发暴力犯罪,积极拓展工作维度,促进未成年犯罪社会治理,创新技术应用,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检察工作现代化水平,适应未成年人保护新形势,不断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
关键词:未成年人检察 双向保护 综合保护 犯罪治理
党中央高度重视少年儿童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祖国的未来属于下一代。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检察机关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按照“双向保护原则”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质效。
一、当前检察机关贯彻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的做法
2020年4月,最高检下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指出“从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向同时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转变”,充分肯定了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的重要意义。从检察实践看,贯彻双向保护原则,重点是一体落实“保护、教育、管束”措施,深化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构建未成年人社会支持体系。
(一)一体落实对未成年人犯罪治理的“保护、教育、管束”措施
“双向保护”就是在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既用心帮教涉罪未成年人,又全力关爱救助未成年被害人;既注重维护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也切实维护未成年被害人权益,对涉罪未成年人和未成年被害人同等保护。[2]“双向保护”原则必然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教育、管束”一体落实。
1.保护方面,严格落实附条件不起诉等司法保护制度。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属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可以附条件不起诉。依法封存符合条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记录。推行“督促监护令”,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督促涉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家长依法履行监护、管教责任。
2.教育方面,贯彻落实好法治副校长制度,加强普法宣传、法治教育。针对未成年人不同犯罪情况实施分级干预,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者,实施专门矫治教育。
3.管束方面,对于涉嫌严重犯罪、社会危害性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当捕则捕、该诉则诉。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惩戒教育,监督司法行政机关做好涉罪未成年人强制教育、社区矫正工作。
(二)坚持惩戒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与加强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并重
预防犯罪就是保护,惩治违法也是挽救。对于尚不构成违法犯罪的“小错”,应该及早干预教育,避免滑向犯罪深渊。而对确有违法行为甚至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坚决依法处置,当宽则宽、该严则严。[3]检察机关应从严追诉性侵害、虐待、暴力伤害等案件,落实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处遇制度,对未成年人犯罪早发现、早预防、早矫治。
1.坚持综合履职。在办好刑事案件的同时,推动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理。多部门联动,建立线索移送、信息互通机制。如公益诉讼检察与行政检察相结合,推进与未成年人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校园安全、食品卫生、网络环境等方面问题整治。
2.加强涉未成年人犯罪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刑事执行监督工作。重点整治有案不立、立而不查、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特殊管教措施虚置、社区矫正空转等问题,确保对涉罪未成年人惩处到位。
3.加强司法救助工作。对受侵害未成年人,结合未成年人个体的身心特点和发展需要,给予特殊、优先和全面保护。
(三)以检察能动履职促进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未成年人保护离不开社会的共同参与。社会支持体系是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和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及不良行为的重要支撑和保障。
结合案件办理,检察机关协调社会力量给予未成年被害人足够的保护。对遭受犯罪侵害,特别是遭受性侵害或暴力伤害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家庭,开展涉未成年人民事支持起诉工作,并与相关单位协作采取必要的心理干预、经济救助、法律援助、转学安置等保护措施。
二、检察机关贯彻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所面临的实践难题
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既需对未成年人个体权利的保护,也需维护社会权利。当前,客观上需要严厉打击未成年人恶性犯罪,人民群众对此期待很高,但检察力量有限,还不能有效惩治未成年人犯罪,遏制犯罪上升趋势。
(一)面对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增多的趋势,检察机关惩治未成年人犯罪任重道远
2018年至2022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32.7万人,年均上升7.7%;其中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从2018年4600多人上升至2022年8700多人,年均上升16.7%。[4]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较多的罪名包括:强奸罪24332人、猥亵儿童罪11013人、抢劫罪4103人、寻衅滋事罪3529人、强制猥亵、侮辱罪2887人,五类犯罪人数合计占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68.3%。办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呈上升趋势。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0063人,同比上升15.5%。[5]
从以上数据可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重大刑事犯罪案件数逐年增加,特别是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更加严峻。虽然未成年人保护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但法律执行层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未成年人家庭保护缺位、家庭教育令实施效果不佳、学校强制报告制度执行不力、性侵害犯罪预防机制不健全等。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维护好社会利益,检察机关任重道远。
(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相对复杂,办理效果不理想
一直以来,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都具有发现难、取证难、指控难、修复难等特点。[6]有的案件如性侵涉及隐私,当事人和家庭不愿报案。有的受害者害怕被报复,不敢报案。有的案件行为被犯罪单位或个人包庇纵容,对被害未成年人多次侵害,导致严重后果。有的案件发生地偏僻、封闭,没有目击证人,没有监控录像,加之未成年被害人表达不清楚,证据意识弱,从而造成指控犯罪困难。
除了查清事实、固定证据、精准指控、修复受害者心理等方面存在困难,还有一些情况也直接影响案件办理。例如,有些案件中没有严密保护好未成年被害人,使其再次遭受侵害。
(三)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任务繁重,履职不全面
目前,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由未成年人检察部门集中办理,实行“捕、诉、监、防、教”工作一体化。随着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增多,办案难度增大,检察官需要具备综合性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业务能力,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犯罪学等知识,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干预、心理疏导,还要熟悉当地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政策和相关社会组织情况。
办好一个案件,检察官要深入了解案件情况,剖析犯罪所涉及的法律规定、社会救助、司法保护等方面问题。在完成案件审查逮捕、起诉的同时,还要围绕惩戒涉罪未成年人、保护好未成年被害人,研究制定和落实惩戒、矫治、帮扶方法措施。由于工作内容多,往往顾此失彼;加之能力不足,往往纰漏百出。办案中,社会调查不及时不全面、检察监督不到位、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帮扶救助较少等情形仍然存在。还有,一些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量刑不均衡,对重罪未成年人判罚过轻,也会助长个别未成年人犯罪,影响社会稳定,破坏司法公信力。检察机关需要重点加强精准量刑、精准抗诉工作。有的检察机关尝试利用大数据技术收集、分析全国裁判文书,提高量刑建议、抗诉精准性。但是,各地检察机关建设、推广大数据模型工作差异很大,有的检察机关重视程度不高,存在数据获取难、数据处理难、数据更新难、大数据模型应用培训不足等问题。
三、检察机关贯彻未成年人双向保护原则的建议
最高检《2023—2027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明确要求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制度,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工作机制,加强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促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等。未来,破解未成年人检察“双向保护”难题,需要“双向”同时用力,综合运用社会力量推动工作,以技术创新提升质效,以完善法律破解难题。
(一)增强工作主动性,严厉打击涉未成年人重大、恶性、多发暴力犯罪
1.从社会关注度高的恶性暴力犯罪入手,提高办案效果。治理未成年人恶性暴力犯罪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未成年人检察要强化犯罪溯源治理,做好针对性犯罪预防工作。从个案到类案,能动履职,以案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为牵引,加强社会综合治理。
2.加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保护和关爱,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社会环境。未成年人心智没有成熟,力量薄弱,人生之路还很长。办理案件需要付出更多爱心,做更多工作。例如河南省南阳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吴某姐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综合保护案。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性侵案件时发现,未成年被害人吴某甲及其妹妹吴某乙的父母均没有监护能力,监护缺失,遂督促吴某姐妹户籍地村委会向法院申请,由其伯父吴某丁担任监护人。检察机关协调民政部门将吴某姐妹二人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范畴,为其发放基本生活保障补助金3万元;又通过司法救助工作,为被害人发放司法救助金3万元;针对被害人突遭家庭变故、犯罪侵害带来的心理创伤,委托心理咨询师对被害人进行心理疏导。在此案基础上,检察机关与民政部门联合排查困境儿童情况,会签了《关于建立困境儿童三级联动帮扶保护工作机制的实施意见》。
3.落实好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和入职查询制度,及时排除隐患。按照处遇个别化、分级化的原则,一旦发现未成年人有违法犯罪情形,检察机关要及时介入侦查,区分不同未成年人的犯罪角色、危害程度,进行不同处理。
(二)积极拓展工作维度,协同推进未成年人犯罪社会治理
1.拓展工作内容,从办案监督向更加注重保护转变。立足监督办案,综合运用预防、教育、感化、惩戒、帮教、救助等手段,实现未成年人双向保护。
2.从事后保护向事中保护转变。督促文化旅游、市场监管、劳动监察等部门严查违法使用未成年工、利用未成年人销售毒品、引诱未成年人吸食毒品、向未成年人销售危害身心健康的食品药品等行为。与网信、宣传、市场监管等部门协作,打击各类宣扬色情、暴力犯罪音视频、书籍的出版、发行、销售,打击有害网络信息、网络游戏、网络赌博、网络猥亵等侵害未成年人行为。同时,做好法律援助、犯罪记录封存、心理咨询、帮教服务、社区矫正等工作,形成良好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
3.深入群众开展工作。走访街道、社区、村委会等地,了解和掌握涉未成年人犯罪家庭、单亲离异家庭、流动人口家庭、困难家庭等情况,关心爱护帮助留守儿童、残障未成年人等特殊群体。
(三)创新技术应用,运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检察工作现代化水平
1.思想上高度重视。各级检察机关要深刻认识、高度重视数字检察工作,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加快推进、实施数字检察战略,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更好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中国式现代化。[7]
2.加强大数据技术应用工作。应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有利于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维护未成年人权益,提高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效果。要做好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设顶层设计和优秀模型的推广。基层检察院技术应用能力较弱,建议由最高检不定期筛选优秀模型在全国推广,并组织专题培训,提高各级检察人员运用模型办案能力。
(四)适应未成年人保护新形势,不断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
1.针对各类不良文化对未成年人造成的负面影响,以文化强国战略为指导,加强立法,以法治促德育,完善国家文化、教育法规,治理校园不良文化,促进师德建设和学生品德教育。
2.针对未成年人犯罪背后存在的家庭溺爱、纵容、包庇、虐待等因素,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分级干预法规体系,提高家庭教育指导和矫治教育专业化水平。
3.针对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络隐私泄露、网络诈骗等,出台有针对性的法律或司法解释,深入治理电信网络犯罪,为未成年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