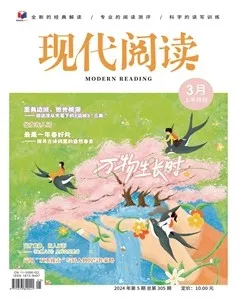在摇摆中看见人心世相
2024-08-02梁开喜
对《变色龙》这篇课文的内容结构,教材“思考探究”第一题中有这样的表述:“小说中,随着对‘狗的主人是谁’的猜测不断改变,奥楚蔑洛夫的态度和裁断也左右摇摆。”这里的“摇摆”一词,可以理解为字面意思上的游移不定,也可以理解为小说的一种常用技法。
摇摆是小说情节运行的一种方式。大多数小说的情节不会毫无波折就直奔结局,而会像河流一样蜿蜒而下。小说情节发展中表现出的曲折回绕、反反复复的过程,就是摇摆。作家曹文轩在《小说门》中说:“小说之所以吸引人读下去,关键在于情节的推进要依循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不停摇摆的法则。”肯定与否定的不断转换,使得每一次摇摆都走向原来的反面,摇摆的过程也就变成了不断的自我否定的过程。说得简单浅白一点,摇摆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波三折”。
循环往复的摇摆艺术
俄国小说家、剧作家契诃夫的《变色龙》正是将摇摆艺术发挥到极致的典范。小说的线索十分简单,内容基本上由对话构成,但因为情节的摇摆,同样取得了摇曳多姿和扣人心弦的效果。
概括起来,小说一共写到了五次摇摆。第一次摇摆:“摇出去”——人群中有人说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摆回来”——奥楚蔑洛夫对狗咬人提出质疑,认为赫留金是想借机敲诈。第二次摇摆:“摇出去”——巡警说将军家没有这样的狗;“摆回来”——奥楚蔑洛夫认定赫留金“受了害”,承诺要教训一下狗主人。第三次摇摆:“摇出去”——巡警收回自己肯定的说法,人群里也有人说狗确实是将军家的;“摆回来”——奥楚蔑洛夫骂赫留金是“混蛋”。第四次摇摆:“摇出去”——将军家的厨师说狗不是将军家的;“摆回来”——奥楚蔑洛夫认为案情已经明朗,用不着再白费功夫。第五次摇摆:“摇出去”——厨师说这是将军哥哥的狗;“摆回来”——赫留金又成了“这家伙”,奥楚蔑洛夫临走前恐吓说早晚要收拾他。
经过梳理,我们不难发现,赫留金的身份在不断变化,一会儿是肇事者,一会儿是受害
者,一切都取决于狗的主人是谁。与此同时,狗的身份也在不断变化,一会儿是“野畜生”“疯狗”“下贱胚子”“野狗”,一会儿又“说不定这是条名贵的狗”“那么小”“还不赖,怪伶俐的”,一切也都取决于狗的主人是谁。
对奥楚蔑洛夫这样的沙俄政权的维护者而言,真相其实并不重要,站在哪一边才重要。在他眼里,底层人民与无主的狗在本质上或许是一样的,他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们的命运都由自己说了算。赫留金的手指头到底是狗咬伤的,还是“给小钉子弄破的”,抑或是“开玩笑,把烟卷戳到狗的脸上去”之后的自作自受?小说始终没有给我们答案,因为这已经无须追问了。小说的重心不在破案,而在破案过程中对世道人心的揭露。
普遍存在的“变色龙”
所谓“变色龙”,首先是指小说的主人公奥楚蔑洛夫。这是一个媚上欺下、首鼠两端的人物,一个在狼面前是羊而在羊面前是狼的人物,一个内心没有法度的执法者。唯其如此,“狗咬人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才会被他变成“狗的主人到底是谁”的问题。毫无疑问,当一个人的正义、良知与悲悯荡然无存,他才会在对利益的考量中如此切换自如。一直在变的是立场,一直不变的是兽性与奴性。《变色龙》的不朽魅力和普遍意义,也正是源于对这种人的刻画与讽刺。
小说中还有谁是变色龙呢?“独眼鬼”是小说中只有一句话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特别耐人咀嚼的人物。当奥楚蔑洛夫知道那有可能是将军家的狗,并且开始质疑赫留金的动机时,他说:“长官,他本来是开玩笑,把烟卷戳到狗的脸上去;狗呢——可不肯做傻瓜,就咬了他一口……他是个荒唐的家伙,长官!”在整篇小说中,他似乎是唯一的目击者,然而,他却是个“独眼鬼”,这样的一个生理标签无疑使他的证言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导致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当我们分析这一人物时,或许只看到他话里隐含的讥讽与鄙薄,实际上,他说话的时机才是最值得推敲和发人深省的。如果他的目的是在指陈真相,那么,在赫留金讲述被狗咬的经过并提出自己的诉求之后,他就应该把真相说出来。可他偏偏没有,而是把自己绘声绘色的“助攻”放在了奥楚蔑洛夫说赫留金不过是“想得到一笔什么赔偿费”,斥责他是“鬼东西”之后,因为在此时,他让自己的证言与奥楚蔑洛夫的表态保持了一致。而当赫留金反驳说他“什么也没看见”,完全是“胡说”,尤其是赫留金抬出了自己当宪兵的兄弟之后,“独眼鬼”就合情合理地销声匿迹了。可见,这个人物的突然现身与后来无声消失,也是基于对情势的权衡。在见风使舵、欺软怕硬和趋炎附势这几点上,他与奥楚蔑洛夫是完全一样的。
赫留金作为当事人,不幸也是这样的一条“变色龙”。对比一下小说对他的两处语言描写,我们就会发现他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到恼羞成怒、低声下气的变化。第一处他的话主要是围绕事件本身,而在第二处,他的话已经与事件本身没有多大关系,而是针对决定事件性质和“案情”走向的其他因素了。他赌咒发誓,他强调自己的兄弟是宪兵,他称奥楚蔑洛夫为“老人家”,巴结他是“明白人”。他或许早已看清,或许突然醒悟,原来狗是否咬了人并不重要,狗咬的人是谁才重要。
课堂指引
在情节的摇摆之中,那些围观者,那些如赫留金和“独眼鬼”一样的底层受压迫群体的面容也逐渐浮现出来。在腐朽没落、穷凶极恶的沙俄专制统治之下,他们的情感变得浑浊,内心蒙上灰尘,鄙视弱小、崇拜权力的观念已经侵蚀到他们的骨子里,弥散到他们的潜意识中。他们其实更希望那条狗是将军家的,因为他们更乐于看到赫留金被羞辱和被损害,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不是底层中最底层的、不幸中最不幸的、苦难中最苦难的。在小说结尾,众人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看客的心理得到了极大地满足。一出喜剧终于落幕,然而同时,我们又仿佛听到了一曲时代和人性的悲歌。
在对《变色龙》中的人物作了一番解读之后,回看小说开头的环境描写,我们或许会体会到特别的意味吧:“四下里一片沉静。广场上一个人也没有。商店和饭馆的门无精打采地敞着,面对着这个世界,就跟许多饥饿的嘴巴一样;门口连一个乞丐也没有。”这一片萧条与死寂,无疑是对当时沙俄整个社会生存状况的隐喻和暗示,而“变色龙”之所以会普遍存在,也在这里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