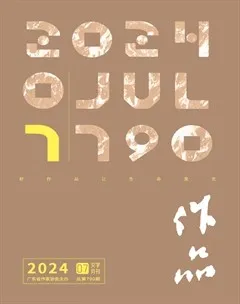当时只道是寻常(散文)
2024-07-31赵晏彪
1.“熬”出风采
我喜欢作家刘墉的一句话:“‘平常心’也是‘心常平’,让你的心总保持在平静的状态,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如何能以不变应万变?只要面对荣辱那颗心总保持在平静的状态,定会“熬”出精彩。
2004年6月,五十四岁的林常平获得自由。往事不堪回首,三十五岁因“投机倒把罪”入狱,如今他身无分文且中年丧女,这一连串的打击,许多人都认为林常平要对生活妥协了,不会有斗志了。然而,林常平并没有倒下,他以平常心、心常平的心态继续锤炼自己,在人生第三次创业的进程中获得了成功。
林常平曾对我说:“我喜欢‘三’,‘三’在中国文化中是个很重要的数字,《说文》中说:‘三,天地人之道也。’老子的《道德经》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三’是万物的基础和本原。”
林常平有过三次创业。第一次创业在三十五岁时因“投机倒把罪”无功而终;第二次创业也是因为“不合时宜”而失败;在他五十四岁的时候,开始了第三次创业,就在这奇妙的“三”字上他成功了。
林常平的传奇人生无外乎一个字:“熬”。这个“熬”并非是混日子,磨时间,而是以一种平常心、心常平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过往。
唯有苦熬方能挺住,唯有精熬方能化险为夷,唯有慢熬才能柳暗花明!林常平从不将磨难、痛苦放在心上,而是将感恩放在心里。他的传奇人生就像是那一锅文火慢炖的老汤,在岁月的熬炖下,熬出了沁香扑鼻的味道,熬出了经年累月的斑斓色彩。
一位哲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的心脏是一座有两间卧室的家,一间住着欢乐,一间住着痛苦;人不能在痛苦的时候大喊大叫,否则会吵醒隔壁房间的欢乐。”林常平有痛苦,有悲伤,有失去过宝贵的年华,有大喊大叫的资本!然而,他却怕将“别人的欢乐”吵醒,独自痛苦着、忍耐着、苦熬着。这,或许不是某些人眼中的伟大,但绝对可以称之为自律和无私的榜样。
那年我随大陆作家代表团走访我国的宝岛台湾,台湾著名作家郭枫老师一路陪同。一天傍晚,他提议说,带我们去一个吃牛肉面的小店,那是个百年老店。
我不禁思忖,牛肉拉面馆在北京随处可见,其中不乏一些味道纯正、汤料十足的老店,台湾地区的牛肉面口味能好到哪里?
这家牛肉面馆坐落在一条小而窄的巷子里,还没有见到店面,却看见了一条长长的队伍,人们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摆出各式各样的姿势,从小巷深处曲曲弯弯地延伸出来,异常壮观。郭老师回过头来,笑着对我们说:“这家面馆营业面积不大,不能同时招待许多人,所以天天排长队,生意火得很。”同行的作家们都感叹这家面馆的生意会如此之好,如此这般招人,那口味肯定是非同一般啦,眼睛里便多了几分急切的渴盼。
大约四十分钟后,我们才安稳地在桌前坐定,一碗蒸腾着热气的牛肉面端了上来,香味也随之而至。好家伙,几块大如鹅蛋般的牛肉顶在面条上,看着诱人无比,咬上一口,软软的、糯糯的,入口即化,满口盈香,果不其然,这算是我吃过的最美味、最实惠的牛肉面了。
郭老师不无感慨地说:“这家店在台湾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他们有几条经验值得我们沉思。一、他们永远不开分店和连锁店;二、从来没有搬过家,更没有更换过门脸;三、肉量永远这么大,口感永远这么好。在我记忆里无论是大饭店还是小吃店涨价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地点和门脸也是经常更换,说什么地段不好,风水不佳;菜也是经常换,口味经常换,美其名曰担心顾客吃腻了。可这家牛肉老店就是在这里默默地卖牛肉面,一熬就是百年。现在牛肉面馆多得很,可这家面馆永远是从早到晚排着长队。”
这件事总是让我想起一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可是在物质极其丰富的今天,像这家仍在巷子深处的百年老店可谓不多,不知它“熬”过了多少风霜雨雪!
人生在世,又有谁不希望能够轻轻松松度过?然而命运又怎么可能就这样轻易地放过我们!百般折腾的事业之路、风吹雨打的挫折之途,是每个人必须面对的生活境遇。当我们熬过了所有该熬的苦,就会遇见所有该遇见的甜;当我们熬过了所有的乌云闪电,就会遇见绚丽无比的彩虹。人生,恰如那碗香气四溢的牛肉面——“剩者为王。”
在最困难的时候,林常平是如何熬过来的?他的日记给了我们答案:“人的一生漫长而又短暂,难免会遇到困难,事业也难免会有起有落;谁也无法保证一帆风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想明天的太阳;事业固然可贵,但生命只有一条。熬下去,将会看见不一样的明天;熬不下去,只能望而止步,永远是今天。”
“遇到困难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面对困难的勇气。我不怕死,但我怕死得没有价值,名誉诚可贵,生命价更高,阳光出云日,再踏商海潮。”
熬得住才能出众,熬不住就会出局。只有咬牙死犟,才能乘风破浪。
有诗为证:“人生恰似一浓汤,苦辣酸甜味自尝。火候疾缓照肝胆,蒸煮日月出奇香。”
人生,只有熬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
2.达真的家园
记得很清楚,3月10日这天的京城,晴空如洗,窗外的玉兰、桃花、柳树都有了春意,河水也清亮亮地映照着蓝天白云。“当当当”,有人敲门,打开快递的包装,“家园”两字跳入眼帘,心便为之一动。好温馨的标题,我们都生活在家园当中,各自都希望生活在怎样的家园里?达真,你为我们营造的是怎样的家园?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家园”的大门。
十余年前,达真以雄心的规划拟创作康巴三部曲,《康巴》和《命定》两部作品相继出版,在等待了十年之久后,终于迎来了康巴三部曲的收关之作《家园》。
达真,一个不喜张扬的藏族作家,依然是那样悄然地带着我们走进了这块陌生又充满渴望的土地。《家园》,取材于长江源头和源尾汉藏两家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年轻的知识分子王本昌以右派的身份来到藏东的桑戈草原,结识了达瓦志玛,并结为夫妻,以他们为中心,铺展开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藏地民主改革到千禧之年半个世纪的故事,以及他们后代的生活图景,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动荡、最复杂、最波澜壮阔历史背景中的人物群像的爱恨情仇。两家人与流亡藏人、与二战时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所发生的情感纠葛,站在更为宽广的高度和视野看待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相互依存,讲述长江源头喝第一口水的人和源尾喝最后一口水的人,在百般磨难中所形成的伟大共识:有水就有家园,保护好养育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天然水塔,需要有信仰的力量和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国家精神。使这种一衣带水的命运依存关系,成为刻在中华民族每一个个体心灵上的永恒胎记。
长篇创作无疑是个苦力活,耗神,耗时,耗心血。我们这个时代人都很着急,急着挣钱,急着出人头地。稿费助力,千字千元,大奖助力,一奖在手,千万不愁。可达真却觉着陈忠实的模样,当年陈忠实读了路遥出版的小说《人生》大受触动,于是辞去工作,从西安搬回老家,耗时六年完成了《白鹿原》的创作。远有陈忠实近有阿来,他用二十年的时间创作完成了他的三部长篇小说,特别是第三部《家园》竟然写了十年才见到了天日。
我曾这样感叹,达真,你怎么如此之慢呀,你难道不知道当下人们捞钱的滋味有多么美好吗?你难道一丝这样的信息也没有接收过吗?中国的长篇小说,有的人一年一部,有的人一年可以造出两部。当下中国长篇小说一年出版总和超过了一万部,真是厉害了我的长篇。
著名评论家白烨当年说过,每年长篇小说超过一千部,他觉得太多了,一千部,能够到评论家手里的最多不超过三十部,能够评奖,留下来的小说,可能也就十部八部的。随着经济的迅速膨胀,一万部长篇小说横空出世,真实反映了我们社会在各个领域求大、求虚荣的心态,却永远不会考虑历史与时间是“无情无义”的。
我跟随着小说的进度,与文字和那淡淡的墨香共同来见证了一个人,一个历经多年用脚丈量藏地,用心思考世界,用热血去体味汉藏融合,用激情和青春抒写他理想中的《家园》的人。
当我小心翼翼地窥望达真营造的“家园”里那一桩桩的喜怒哀乐、一件件悲欢离合,大开大合的气魄与写法,让我遥望这位千里之外的讲述者,他是一位最不像康巴汉子的汉子。《家园》以连接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川藏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康定为故事的起源,串缀了沿线的汉、藏、彝、纳西、羌、傈僳、白、独龙等十多个民族,涵盖了各种语言与文化,它所碰撞出的“火花”就是因交融而共生,精确地表达了地球上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们的心理祈盼,成为多民族多种文化互相交融相互渗透的经典交汇地。
达真的成长历程,也可以说是成书历程,他有记者经历,走遍中国西部的山山水水,视野的半径随着行走而逐渐扩大;他同时又有着封闭而快乐的创作过程,走得出,坐得下,写得稳。他更有一颗这样的心,他不太在乎中国文学评论界的好话,反而很在意豆瓣的打分;他不在乎书卖掉了多少册,但却在乎冠冕堂皇的认可——2012年“骏马奖”、十五集大型广播剧《康巴》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18年依照《康巴》改编的电影《金珠玛米》获第十七届华表奖优秀影片提名奖。这就是文学带给他最真实的力量和最踏实的自信,也是给予他真心付出的认可与回报。
中国作协历来提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达真的《家园》正是他读书与行走双轨制的最好的证明;他的小说特点之一是语言好,为何?也是双轨制。他写作用汉语,人到藏区的时候,他是可以听懂藏语的。一位蒙古族作家说,我来牧区,进入蒙古语的言说里面,感觉蒙古语把我的脑子拆了,露出天光,蒙古语的单词、句子和比喻好像是树条、泥巴和梁柁,像盖房子一样重新给我搭建了一个脑子。我的心仿佛在蒙古语里融化了,剥落掉核桃一样坚硬的外壳,露出粉红色血管密布的心,一跳一跳,回到童年。母语的魅力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几年前我去巴金文学院讲课,阿来兄前来捧场,在发言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创作一部小说时,在描写爱情的时候,他想用一个词或者一句话表达男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不渝。阿来是寻求创新的作家,可他找遍了汉语,都是别人用过的词,白头偕老,海枯石烂……他苦恼几日不得其词。一日,他步出书房,在大街上漫步,偶遇一位藏族同胞,对方用藏语同他打招呼,那一瞬间,藏语在他的血液里翻腾,他在藏族的海洋中寻找着,终于有一句话让他浑身一颤:当一个失恋的男人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时,大家都感受到他的骨头都轻了。“骨头都轻了”,这句话远比骨瘦如柴要更有文学质感。
达真亦是,他在藏语和汉语的相互交汇中得到了语言的升华和独特。
如果说达真的《家园》有什么不同,一些作家对人生曲折道路的描写是充满仇恨的,对人性的描写是嫉恶如仇的;而达真对人生曲折道路的描写是积极向上的,对人性的描写是充满体谅和友善的。达真的创作观,在那个特殊年代完全体现在他的笔下,是人间的光芒和大爱。他的作品具有史诗般宏大构架的“百年气魄”,将现实与荒诞巧妙结合的一部能够让读者感受到不同“味道”的大餐。
3.序《作家好书画》
戊戌年秋,二十余位中外作家齐聚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载歌载舞之余,王羲之“兰亭盛会”景象突映脑际。机缘巧妙,何不效“兰渚山”之乐,邀诸作家以书画之技助兴?
古有文人王羲之、苏轼、王维、唐寅等能文善画,今亦有王祥夫、叶梅、李浩、兴安、张瑞田等能文善画。黄淦波董事长闻之大喜,迅速安排,条案毛毡,笔墨纸砚,样样俱全。大厅内,作家中好书画者兴致勃勃,纷纷蘸墨运笔:画虫者,左手把酒右手挥毫,一只小翅细腻如丝;有书者,“大江东去”,狂草如歌;画山水者,奇峰竞秀,跃然纸上……
夜半月朗,书者、画者各展其技,兴趣盎然,观之悦心,随口吟出——
作家书画香满坡,
一笔诗意一笔墨。
举杯望月邀羲之,
文人书画有衣钵!
此情此景,“作家好书画”之意境,嵌入心底。
回首2014年,时逢《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改版,为使杂志封面设计和内容皆与大刊相符,开拓创新乃唯一路径。结合前些年创办《中国化工报·文化周刊》的经验,版面的美化以图文并茂为佳,而将此法移植到杂志上,须加以改革、创新,将作家的文学作品配之自己的书画作品同时刊出,达到“文与书画两相宜”,真正做到文章书画的结合相得益彰,如此创意还属首次。于是,环视作家中能文善书画之大家,首先向两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洁女士、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中国作协副主席贾平凹先生说明创意并发出邀请,每人选一篇自己的精美短文,配上十幅自己的书法或画作,形式不拘一格。如此打造的新刊犹如“大姑娘上轿”,围观者众也。
悠悠数载,凡举办采风活动亦必邀作家中好书画者和书画家同往,酒过三巡,星月满天之际,书画笔会便成为每次采风活动的亮点及保留项目。
一日,望着书画家们忘情挥毫,看众人围观索要书画场面热烈,忽生一念,若组织作家中文笔书画俱佳者出一套图文并茂的散文集,定会大受追捧。
此念萌生,立即行动。2023年一个春光烂漫的日子,与中国纺织出版社有限公司的编辑一拍即合。满足以下要素者,方可入选“作家好书画”集:此书画者须是作家身份;书画要有作家趣味;艺术作品不以追求价值为目的,贵在不像之像的神似;凡书画作品乃为文学作品之延伸或曰万丈豪情寄于山水花鸟;作家之特点每篇作品杜绝自我重复,其书画艺术须秉承文学创作之创新理念,皆通过作家笔墨创作出会说话、巧思考、有新意、别具一格的书画作品,配之美文,此集风格独特,文与书画相得益彰,可谓出版新风尚。
“众里寻之千百度”,王祥夫、叶梅、李浩、兴安、张瑞田五位大家的散文与书画作品珠联璧合,特色彰显,成为“作家好书画”第一辑的受邀者。
组织书稿时,边赏边赞,五位作者不愧为大家,以文而言,小说散文皆得心应手,以书画而论,四位擅画,一位擅书,皆为业界翘楚。
作家王祥夫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将散文创作的视角投射到日常生活中,以犀利的目光探寻人性,用文字描写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记忆。他以描写特定场景为主题所创作的《绿皮火车穿过长夜》,文中藏画,画中显文。其文如画,信手拈来,不刻意为文,皆从生活中、性情中、思想中流淌而出,是非“作”之举,是一种独特的生命体悟。
作家叶梅以生态为主题创作的《知春集》,以对生态环境的细致观察立经纬,运用清新自然的文字,寻找、挖掘人性中本真的美。叶梅《知春集》中的插画别具一格,梅花之美不在花艳,而在梅格。从叶梅的画中恰能看出画中深意,那正是一种梅花气质,使人深刻地领略到人生意义。物质、金钱或将化归尘土,唯有文章书画之精髓可流传于世。
作家李浩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在记忆、行走和思考之间》这部散文集中,他以新锐的视角去解读现实生活,赋惯常予新奇,在他的笔下,树、瓷、蜜蜂、狐狸和兔子不仅闪现生命之光,还透着缕缕哲思的痕迹。李浩在书中的插画文人气质浓郁,其中多是临摹黄宾虹、朱耷、石涛、沈周,但个人特点清晰,他将古典的雅致、妥洽、安静,以及重笔墨、重意趣的诉求,乃至对空白处的苦心经营都纳入自己的作品中,使画面的表现力更为丰沛。
作家兴安的散文创作一直突显直观、率性的特点,让读者感受到一个蒙古族汉子内心傲视生活、敬畏草原的精神世界。他以画马在文坛、画界声名鹊起。究其根由是在中学时期练就了扎实的绘画功底,使其创作在写实和抽象、工笔与写意的转换中游刃有余,其独创的抽象性极强的各种姿态的马,辨识度很高,表现了自然与生命的深刻要义,每幅作品都让人驻足久观,透过其潇洒的笔墨,深悟其奥。
作家张瑞田以艺术记趣为主色调创作了《且慢》散文集,以侠气素心著称,且书且文,引领读者走进文人的斑斓世界。张瑞田少年学书,问古临帖,伴随他的生命成长与文学写作。因此,在他的书法中能够领悟到氤氲的书卷气,以及日渐稀少的文人品格。他的隶书倾向“朴实”,在其隶书中,没有头重脚轻的结构颠倒,也不刻意营造一个字与一幅字的视觉冲突,沉稳中显露泰山之气。
五人风采,观之甚喜,效昔日文人之情怀,展当代作家之才艺,文章书画巧融一体。心潮澎湃之际一段文字涌出心底:
雄鸡不常鸣,一日只一啼,但却让黑夜变成了白天。
绘画不说话,文字默无声,但却让观赏者感慨万千。
张张素纸,笔走龙蛇,让汉字与山川有了想象空间。
行行宋体,铅华无饰,文善事善内心充盈锦瑟无端。
“作家好书画”且文且书且画,以这般整体而新颖的形式隆重出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如一缕檀香,渐侵脏腑。画淡了封面,晕开了文章,以画为幕,以文为歌,序幕入眼,尾声入心。随着“作家好书画”的问世,激发读者对“新文人”的推崇,由此,可窥见作家文字以外的“心灵与技能之光”。
南宋邓椿《画继》中言:“画者,文之极也。”作家画家历来强调文学修养,而邓椿的理论则是把文学修养强调到了极致,认为绘画不仅仅是技艺,而且是人文之极。这可谓中国作家书画的点睛之句,用到王祥夫、叶梅、李浩、兴安、张瑞田诸君身上,恰如其分。把文学作品不易表现、内心表达无法张扬的情境,以风趣的书法、灵动的画面,呈给读者赏鉴,携士气、文气、灵气、笔气、墨气而出,凝目而思时,或精神外延,或暗含深邃……
正所谓,抚其书,一泓清溪沁润肺腑;览其文,襟胸顿阔流连难舍;犹舀一瓢“真水”,涤目清心;似取一抔“厚土”,育善养德;亦餐一顿药膳,身心俱健。惟此、惟此,幸甚、幸甚。
是为序。
4.当时只道是寻常
凡出差回京后,第一件事就是去父母家吃晚饭。
往往是刚刚推开楼道的大门,还没有进入家门,一股酒香便扑鼻而来,不问便知,父亲正在饮酒。
母亲素来不沾酒,父亲顿顿不离酒。所有我见到的场景都是一样的。父亲坐在餐桌前,依旧放着三只奶白色的酒杯,这三只酒杯于我太熟悉不过了,祖父祖母的遗物父亲家几乎没有,因为祖父祖母是和我老叔住在一起,祖父去世特别是祖母被 汽车撞了以后,一直住在我的房子里,祖母去世时,老叔早已搬家,所以祖父祖母的许多物件也随着老叔入住了他们的新家。唯有祖父和祖母生前与父亲喝酒时用的酒杯一直在我们家。一只端在父亲的手里,另外两只则放在餐桌两侧,旁边各摆一副碗筷,酒杯里盛满了酒。桌上依旧是三碟小菜,一盘糖拌西红柿,一盘酱肘子,一盘油炸花生米。虽然父亲年过八旬,已是白发苍苍,但他老人家竟然没有掉一颗牙,耳不聋眼不花,红光满面,精神状态特别好,七十九岁前还骑着车去学校给学生们上课。每每看着父亲喝酒,母亲都会对我说,你爸现在就两件事让他高兴,一件事讲课,只要讲课回来就满脸放红光,看着他是从里往外高兴;另一件事就是无酒不吃饭。讲课喝酒,这两件似乎不搭界的事,竟然是父亲最为得益和快乐的事。
桌上那三样凉菜都是当年祖父和祖母每天为父亲备下的酒菜,也是祖父去世后,祖母和父亲在喝酒时永远保留的三样酒菜。自从祖母去世后,每天父亲喝酒时都是这样的阵式:三杯酒,三碟小菜,三双筷子,三只小碗。望着父亲一个人自斟自饮,有一丝英雄寂寞、孤独求饮的味道。
“爸,这是给您带的。”父亲非常高兴地看着我手里提着的酒瓶说:“呦,茅台,好酒。”我见母亲不在家,坐在父亲对面,拿起筷子加了一块西红柿放进嘴里。
“你妈出去散步去了。”父亲边喝边说道。
望着父亲略显孤独的样子,我知道他老人家在喝闷酒。自从祖母去世后,凡是父亲一个人喝酒时,总是闷闷独饮。
“你也喝点吧。”父亲没等我答话,便将另外一只杯子递给我,然后去开茅台,边斟酒边自言自语道:“你奶奶生前最爱喝茅台了。”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了祖母,无论是饭桌上,祖母最爱吃酱肘子、糖拌西红柿,还是祖母常用的那只酒杯,不见到则罢,见到便会让我的大脑飞速地转着,回忆着。突然,我意识到今天是祖母的祭日!
“今天是你奶奶的祭日。”父亲说完喝了一大口。
“酱肘子和糖拌西红柿都是你奶奶生前最爱吃的。”父亲说着用筷子夹了一块酱肘子放进嘴里边嚼边念叨着,“天福号的酱肘子没有原来的香了。”
望着父亲喝酒的样子,我小心翼翼地问:“爸,没有人陪您喝酒是不是有点……?”
父亲放下酒杯,说道:“孤独没有什么不好,只是看你如何看待孤独。孤独就像一杯水,没有颜色,没有味道,但它可以维持你的生命;对了,你写的《真水无香》就是这个意思吧。你是搞写作的人,你不觉得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孤独的吗?”父亲吃了一口西红柿接着说道,“我为什么每天都摆上三只酒杯和三双筷子?就是你爷爷奶奶还在,还是在和我一起喝酒。我从内心里,永远陪着你爷爷奶奶,不会孤独的。”
听着父亲的话,我怎么想流泪!他老人家明明在思念爷爷奶奶,却偏偏说不孤独。父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悠悠地说:“现在整天都是噪音,今天那个楼门里装修,明天小马路开膛破腹,后天小花园铺砖。你想看看电视吧,不是群魔乱舞,就是哭哭泣泣,再不就是相亲节目,我觉得孤独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林则徐的‘慎独’也有此意吧。我有时会想起你爷爷奶奶,想起咱们贤孝牌的家,有时也什么都没有想,只是喝酒吃菜。凡事只要你不自作自受,你就不觉得孤独,想想你奶奶,在你爷爷离开十三年后你奶奶才去世,你就不觉得你奶奶也很孤独吗?”
父亲的话说得平静,在我心里却是翻江倒海,泪水悄然而出。
“爸,太晚了,您少喝点吧。”我抓起酒瓶想要将酒收起来,父亲酒兴未尽,将酒瓶又抢了过去。
那晚,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度过的。回到家中,我和妻子坐在客厅,说到祖母的祭日,便勾起从小祖母把我拉扯大的种种回忆,悲从心生。谈到父亲当年虽然已经六十多岁了,给学生们上课后,还要骑车往和平里跑去照顾祖母,风风雨雨近五年,直到祖母去世。“爸是咱们的榜样,孝道是要传承的。”妻的话,让我更加止不住地流泪。
“父亲也许不会有需要我们照顾的那天,他身体好,如果有,我也会像父亲照顾祖母一样。”妻点点头,迅速转身而去,她知道我对祖母的感情,她心里也一定不好受。
父亲一生只喝醉过两次酒。一次是他被员工出卖受到了冲击,挨了批斗,回到家来,祖母为他准备了酒菜。父亲是很有酒量的,但那次父亲竟然喝醉了,边吐边说,我不是走资派。最让父亲伤心的是他手下的那名员工,平时吃父亲的,喝父亲的,但出卖父亲的恰恰是他。父亲百思不得其解,“他说喝了我的毒酒”……睡了整整一天一夜。然后,他又去单位继续“享受”挨斗了。
父亲第二次喝醉酒是在爷爷去世后的第三天晚上。祖母心情一直不好,中午没有吃饭,我和老叔怎么劝她老人家也不吃。晚上父亲处理好祖父的丧事后,祖母便下厨房为父亲做饭。饭菜做好后,我们都默默地坐在饭桌上,没有人动筷儿。祖母倒了三杯酒,我想祖母一定是习惯成自然了,祖父已经去世了,但祖父的酒杯还在。祖母坐下后突然说:“晏彪,用你爷爷的酒杯吧,二十三岁是大人了,咱们满族人没有空杯子的习惯。”
祖母说得平淡、镇静,腔调中没有半点悲伤,但我一阵阵地心酸,儿时祖父最疼爱我,端起酒杯,便想起祖父,眼泪流个不止。父亲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酒,才喝几杯便醉倒了,吐了一地。祖母边收拾边喃喃地说道:“你爸今天是怎么了?才喝几口就醉了。”我流着泪扶父亲进了里屋,灯光下父亲脸上挂着泪珠。这是我生平见过父亲的两次醉酒。
从此以后,每天父亲回来便与祖母一起喝酒,桌上永远是三个酒杯、三副碗筷和三碟小菜。悠悠十三载,便也成了一种习惯。许多年后,每当端起酒杯,脑海里反复出现的,全是当年父亲和祖母快乐地喝酒时的影像。
1991年秋天,那几日北京的天气有些反常,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一天我突然接到弟弟打来的电话:“哥,快到协和医院来,奶奶让车撞了。”放下电话,头“嗡”的一声,我自幼是祖父祖母带大的,对二位老人感情很深,祖父已经去世,祖母千万不可再出事了,这种心情非言语所能尽表。当我急匆匆赶到协和医院的急诊室时,祖母正在抢救中。
祖母在昏迷了七天七夜后,终于被抢救过来了,遗憾的是祖母有些失忆,一会儿认识人,一会儿又不认识人的。医生说,如果恢复得好,环境又是老人家熟悉的,恢复起来会很快的。祖母平时是跟着老叔住的,满族人有个习惯,长子长孙尊贵,但却喜欢跟着老儿子一起过。这期间老叔家里也出了大事,老婶突然病逝,家不成家了。
父亲是家里的长子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弟弟家遭难,父亲直接将祖母接到家中。父母和弟弟一家五口人住一套五十九平方米的小两居,弟弟三口住一间,父母住一间,客厅只有八平方米大,放一张小餐桌而已。祖母住哪呢?
父亲是大孝子,他跟母亲商量后,让祖母跟母亲睡在一起,自己睡客厅。这样住了几日还是不方便,祖母每天晚上要去卫生间,一家人都不得安宁。
我看出母亲的为难,也看出来了父亲的无奈。一日跟父亲商量:“奶奶总住家这儿不是个办法,咱家花家地的房子空着,我和建平商量了,我们住过去,您和奶奶住我们的宿舍楼,和平里近些,我们上班得空也可以去看看奶奶。虽然是筒子楼十二平方米有点小,但做饭用水很方便,平时可以请一位保姆照顾奶奶,建平的单位就在宿舍楼边上,可以随时照顾奶奶。”
父亲听后认为可行,又不无担忧地说:“那你们上班就远了,多不方便呀。”
“没关系,我们能克服。”就这样,祖母被接到了和平里。
“爸,建平给奶奶请了个保姆。”父亲看了看我,缓缓地说:“医生说了,你奶奶需要多跟熟人说话,有助于恢复。不用请保姆,我跟你奶奶住这儿。我跟校方说好了,把我课时减少点,尽量放在一早和下午,一天三顿饭没问题。有倒不开的时候你们伸把手就行了。”
父亲的孝顺是出了名的。当年祖母得了直肠癌,祖母是A型血,当年医院的血库里这种类型的血很少。父亲对医生说,我是儿子,是O型血,输我的吧。他老人家对祖母的孝心天地可鉴。我们这个家虽然是父亲养家,但祖母才是这个家的主心骨,父亲自结婚后就单独过了。这次父亲认为是上天赐给他的一次机会,可以好好陪着母亲尽尽孝心。
搬进筒子楼后,祖母还处于一会儿清醒,一会儿又糊涂的状态。令所有人惊讶的是,每当我看望祖母时,她老人家总能认出来:“我大孙子来了,是晏彪呀,快坐着陪陪我,一天一天的没有人跟我说话……”
前几句还清楚的,越说就越离谱了。
父亲一周的时间都奔波于东直门外的学校与北三环和平里的筒子楼之间,他老人家那辆自行车是立了功的。祖母被撞那年八十一岁,父亲六十一岁,一个老人看护着另一个老人。平时父亲上课,母亲看护祖母,妻子中午和下班后都会来帮助照看祖母,周六周日我和弟弟便替父亲照顾祖母。
见到父亲和祖母最温馨的画面并不是父亲为祖母洗头,陪着祖母在楼下晒太阳,而是父亲和祖母两人对坐在餐桌前,桌上永远是三副碗筷、三个酒杯、三碟小菜,仿佛永远是祖父、祖母和父亲三人在对饮。有时由于我的到来,祖母特别高兴,她老人家总是让我用祖父生前用的杯子:“晏彪是大人了,用你爷爷的杯子喝吧。”令父亲和我惊讶的是,这句话祖母从来都不会讲错。
我很享受陪着祖母和父亲一起吃饭喝酒的时光。祖母和父亲一人一口酒、一人一口肉地喝着聊着,真是其乐融融。每逢这个时刻,父亲的脸上总洋溢着一种光彩,祖母的脸上也泛着幸福的微笑,虽然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一旦想起这画面我心里依然会涌出无限的幸福感。父亲是大孝子的榜样,父亲的形象永远镌刻在心里。
最令我难受又让我感动,还有些无颜以对的是,同事对我和妻子说,你们家老爷子真够孝顺的,不但把老太太侍奉得舒舒服服的,还给老太太洗屎裤子。老爷子怎么说也是六张的人啦,还是个教授,能做到这份儿,让我们特别佩服。我们大家都说你有个好父亲,老太太上辈子一定是积了大德行善修来的。
记得那年我七岁,祖母五十多岁,她得了直肠癌,手术很成功,只是从此祖母肚子上开了个肛门。对于一个非常爱干净的人来说,从肚子上解大手,这是一种折磨。所以祖母最怕的是吃坏肚子,一旦拉稀闹肚子,就会拉一裤子。祖母平日特别注意饮食和卫生,受伤后祖母神志不清时,或者是肚子受了凉,时常拉肚子。
筒子楼的厨房是公用的,一排水管,对面是一排的炉灶,厕所也是公用的。虽然大家都在厨房洗衣服,但父亲每每为祖母洗屎裤子的时候,却一个人躲到厕所里洗,怕人家嫌弃。父亲的自觉与孝道让我的同事们很感动,更让我和妻子惭愧。一日,妻子对父亲说,以后奶奶再拉肚子您打电话告诉我,我来洗,您别再洗了,不然我们没法做人。
父亲侍奉祖母近五年的时间,老人家在八十七岁的时候无疾而终。住在筒子楼里的同事们都说,老太太这几年真是享福了,好吃好喝的,有那么一个孝顺的儿子,是前世修来的。
祖母去世后父亲再也没有去过筒子楼,直至2001年妻分了房子,在搬家时父亲才又回到那间让他充满快乐又怀有悲伤的筒子楼。屋里的东西一直没有打理过。床,还是那张床,摆设一样都没有动过,那张小餐桌还支在屋子的中央。父亲站在屋里,看看这儿,摸摸那儿,久久不说一句话,我知道,父亲一定是在想念祖母。
父亲依然是每天一顿酒,只是一个人自斟自饮,少有与祖母对饮时的那种快乐和光彩的样子,常常是寂寞独饮。我这个年龄对寂寞和孤独似无深刻的理解,直至我生病住院时,一个人躺在病房里,望着白色恐怖的墙壁,夜不能寐时,我才体味到了寂寞与孤独的滋味。
世上有多种多样的孤独,姜子牙垂钓溪边,严子陵隐居富春江,诸葛亮躬耕南阳之野,以上种种是他们不求闻达,淡泊恬静的孤独;君平卖卜,达摩面壁,子晋品箫,是一种修道参禅,清静无为的孤独;而坚持文学创作,不为金钱利益所惑,是一种锥处囊中的孤独。孤独是一种精神感受,一种境界,不同的人境界也就不尽相同了。有人乐于孤独,追求孤独;也有人苦于孤独,难耐孤独;有人在孤独中思想升华了,也有人在孤独中精神沉沦了,而真正的孤独,是属于一种内心深处的精神独处——独钓寒江雪的意境。
人,若耐得住寂寞,方能不寂寞,孤独亦是。一个人主动地、理智地、淡然地驾驭自己、驾驭孤独,这是有为与无为的分水岭。
父亲是孤独的,自斟自饮犹如一副心灵的修复剂;父亲又不是孤独的,因为父亲的孤独是可驾驭的。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