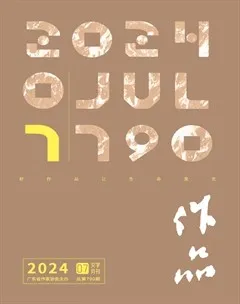米粉的故事(散文)
2024-07-31赵荔红
1
我给国清留言:“找个做线面的人家,想去现场看看。”半日,他回复:“线面没有,米粉有。”线面是我家乡一种手工面,带咸味,极细极长,又称长寿面,我会在另一篇文章里谈它。我家乡的米粉,不是粗粗的桂林米粉、云南过桥米线,而是细如发丝的兴化米粉,只流传于福建莆田、仙游一带,别的地方的我没见过,福州、厦门的米粉,类似港粤一带的星洲炒米粉,还是偏粗了。
人与人的缘分,真是奇妙。譬如,初中、高中,无论怎么个分班、合班,国清和我,总在一个班上。许是家中排行老大,又或经历过什么,国清从小就显得少年老成,心事重重;他既行事稳重,凡事又肯担当,似乎比我们这些毛毛糙糙的少年少女早熟,大家自然而然视其为大哥。往后分开,就算长期没见面,平日也不怎么联系,回到家乡,但凡遇点什么事,自然而然会找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自由之风吹遍大江南北,一切刚刚复苏,一切在蓬勃兴起,这种风气,兴盛于大城市、大学,吹拂到我的南方小城中学之末梢。我们才读高一,虽说高考是重中之重,还是为时代风气感染——办文学社,读王朔小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在“我的青春小鸟般一去不回头”歌曲伴奏下跳交谊舞;办黑板报,抄写舒婷、北岛的诗……国清是组织者之一。后来我在校文学社办了份铅印《蒲钟》报;在班上,又与国清等办了份刻蜡纸油墨印小报,名曰《求索》,取自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时国清与父亲、弟弟住在城里,母亲和妹妹在乡下,他家楼顶有个大平台,我们七八个人常在那里聚,讨论小报稿子,主要是玩儿。国清搬来寸枣、瓜子,新上市的荔枝、桂圆,我们喝着啤酒,背诵“黑夜给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若是国清妈妈进城,我们就会有夜点心吃。常吃的点心,是汤米粉。莆田的汤米粉,最便当最常有的,是“饮糜汤烫米粉”,就是煮稀饭时,等“饮糜汤”(米饭汤)沸腾时,拿一把米粉在碗里,舀上一大勺“饮糜汤”,往米粉上一浇,再加一小把虾米、一些葱花调料、一勺猪油就可吃了,又清爽又美味;再有是“豆浆烫米粉”,煮沸豆浆,浇在米粉上,又鲜美,又丝滑。既是夜点心,也无“饮糜汤”,也无豆浆,国清妈妈煮的汤米粉,不过是清汤中加点虾米、青菜、紫菜或蛋皮,下了米粉,沸腾一下就舀起,再滴几滴芝麻油或一勺猪油,一人一碗,国清端上来,我们就吃得唏哩嗦啰、浑身冒汗,天下美味也不过如此……想起来,那时城市的灯光还没那么刺眼,头顶的星星也还闪闪发亮……
高考后,我们这些人就散了。我去上海念书,国清考进省内一所银行学校。九十年代,下海经商者是弄潮儿,国清会动脑子,定会在商界、金融界闯出一片天地吧?!后来我读研究生,国清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各自忙碌,也只在我回家乡时聚聚。
1998年寒假我回莆田,那是爷爷在世的最后一个春节。国清带我去逛广化寺。尾祭已过,春节未至,寺内除了金身菩萨,竟只有我们两个游客。高大的菩提树,枝叶婆娑,树下一方洁净石桌椅,我们坐着听叶片疏疏落落地在风中响,近旁一株迟桂花正开着,香气似有若无,淡淡的不如秋桂浓郁,正殿右侧短垣上摆着两盆三角梅,一株紫色,一株大红,在阳光下恣肆开放,闪闪发亮。出寺门,顺泥路走,遇见一条小渠,是延寿溪的支流,通往东圳水库。冬日小渠裸露着大片青色河床,一道细细的水流蜿蜒着,在阳光下好似浮动着一条银缎带。左近一片片深褐色稻田,短短的稻茬,沉默地泛着浅褐光色。稻田被暗绿树木环绕,越过树梢,是南方村舍的弯翘屋檐及白得发光的墙面,回看寺庙,明黄围墙、枣红寺门掩映在绿树丛中,自有一种轩丽恬静。
我们沿小渠边走,穿过田间小路,绕到广化寺后山去。国清说,后山有条小道,环绕凤凰山,可从广化寺一直走到石寺岩去,没多少人知道这样走。南方冬日,微微寒意,国清毛衣外加件单夹克,我兀自穿大衣戴蓓蕾帽,一派北人打扮,爬上后山小道,已有汗意,脱去大衣,风从树丛穿过,舒爽极了!小渠、田畴、树木,村舍,皆在脚下矮了下去……广化寺的黄琉璃屋顶反射着耀眼光芒,遥远的村舍道路,模糊的城市楼宇,更远的山峦水域,全都笼罩在淡淡青色雾霭中……顺小道走。一路走,我一路絮絮叨叨地说些琐事,学业,老师,同学,爱人,父母,爷爷奶奶。我像是一个自我中心者,任由自己絮叨,并不在意听者的想法,又或者说,因为听者是国清,我就很放松,变得絮叨、好倾诉。短暂的沉默,我才意识到国清的倾听与陪伴。国清小时沉默寡言,长大后,依旧是沉默寡言,一如既往是个好的倾听者。我意识到一直只是自己在讲,猛然刹车问道:“你怎么样?”国清顿了顿,脸上闪现一个好看的笑容,说:“我挺好。”在我追问下,他才挤牙膏似的说起他的工作和生活,他爱人也在金融系统,女儿上幼儿园了。他身上,似乎去除了少年时的重负阴郁,眼神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欢乐轻松,虽依旧寡言,但整个人显得明朗、健康、自信。他笑说:“你也挺好的……”那是九十年代末,我们正告别旧世纪,迎接新世纪。我们这一代人正在成长。所遇之事,并非皆能如意,但总觉得只要自己努力,一切都有希望,一切都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顺小道向石寺岩方向走。遇见七八座小寺庙、小庵堂、小道观。我家乡人,一辈子忙来忙去,只追求三样事:嫁娶,起房,修庙。各村乡都有自己的小庙,有供奉如来、观音、弥勒、韦陀的,也有奉玉皇、三清,或斗姆星君、月老、文曲星,地方性的海神妈祖、修木兰陂钱四娘、莆仙戏保护神雷海青,还有供奉桃园结义刘关张、唐三藏孙悟空、汉太傅萧望之,等等。在民间,佛、道、儒三家往往混同,只要被塑为偶像,便得享香火。我自小受爷爷奶奶耳濡目染,见偶像须存一分敬意,不得胡乱拍照、不说不敬之语,一路行来,见着种种神龛,闻着香火气味,便觉亲切。我们正走着,迎面五个妇女排成一队行来,皆身着红衣,每人挑一担,每担一对红漆竹圆盒:最前面一担,左边盒内堆着高高的线面,右边盒子是码得整整齐齐的米粉,各贴一个“寿”字,盒子提梁皆扎了红绸,紧接的一担,是涂红的寿桃糕和猪脚,后面几担盒子盖着,不知是什么。国清说,是女儿送父亲过寿的“盘担”。我问:“线面是长寿面我明白,送米粉是什么意思?”国清龇牙笑道:“米粉像不像寿星的胡须?又白又卷。”又说,送“盘担”的,须从出嫁女儿家挑盒子,一直走到父亲家,传统叫“一盘担”,每担挑十盒,一边五盒,大大小小的盒子套在一起,但这样太重了,所以也有分开挑的。我目送那些红色身影远去,叹息道:“我在上海,那么远——”
回转市区,天已向黑。菜市场与电影院之间那条街边,立着一个个红色帐篷,亮着灯,远看好似蹲着一个个红灯笼。帐篷外支着炉子炒锅、立着手写菜单榜,帐篷内大多只摆三四张矮矮的木桌椅。国清和我挑了一张座头,点了几种莆田特色菜:炒米粉,炒白螺,牡蛎煎蛋,花蛤汤。牡蛎与花蛤冬日里最肥美,花蛤大、肥、无沙、味鲜美;牡蛎得挑野生没泡水的,加鸡蛋拌地瓜粉入油煎透,要放多多的香菜;至于白螺,只比瓜子大些,外乡人吃不到,也不会吃,本地人舀一大勺子放嘴里,竟能一个个嗦出螺肉,吐掉螺壳,这个菜专为下酒,边嗦螺子,边饮酒,边慢慢“搭聊”闲话。至于炒米粉,那是硬菜、功夫菜,正宗不正宗,要看食材和手艺:须是我家乡的上好兴化米粉,纯米做的,细如发丝,却韧劲强,有嚼头;配菜须是发过的干香菇切丝,豆芽,肉丝,干虾仁,香菜,芹菜,若炒得米粉根根竖起,是油放少了,若是米粉煳了,是水放多了,要炒得油而不腻,顺滑入味,又不焦黑贴底。只是一盏小灯,将帐篷照得红红彤彤,我们坐在小木凳上,吃着炒米粉,嗦着白螺子,抿一口名叫“蜜沉沉”的甜米酒,随便聊一些日常琐碎之事,外面是炒菜落锅的声音、车轧过青石板的声音,远远地,齐秦哑着嗓子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在冬季……”
2010年,国清来上海出差,住在浦江饭店,就是原礼查饭店,一幢维多利亚时期的巴洛克建筑,中国第一家西商饭店,濒临黄浦江。他已是某保险公司老总。我预备请他吃西餐,他却说:“明天是中秋,要不要请你去吃正宗的家乡菜?”我心想,上海哪来正宗莆田菜?就有人开车带我们去闵行区——走出家乡的莆田人只有两种:读书人和生意人。国清带我去的区域竟有个莆田生意人聚集区,有经营木材、瓷砖、外墙玻璃的,做鳗鱼、虾米生意的,进口咖啡烘焙分销的,经营医疗器械及药材的,出租公寓楼做寓公的,销售山寨手机的,开发电脑软件的……小车七拐八扭停在一户人家楼下,上楼进门就是一张大圆桌台面,满满当当围坐了一桌人,抽着烟喝着铁观音眼巴巴在等。国清一一和他们招呼、递烟、用莆田话打趣,很熟络的模样,在上海,我反成了客人。主人家招呼着,流水端来大盘大碗,有莆田家常菜,焖卤水豆腐,板栗捂小鸡,笃蛏(蛏子去线后插立在罐里,加酒清蒸),牡蛎煎蛋,还有莆田中秋节必吃的飘着枸杞的老鸭汤,炖到酥烂的去皮香芋,一大“脸盆”的中秋主食,炒米粉。国清舀了满满一碗米粉给我,笑说:“吃吃看正宗吗?”又说,食材都是当天从莆田空运到上海,厨师也是地地道道莆田人。在那样的夜晚,吃着家乡菜,听着浓浓的乡音,看国清红着脸与他们拼酒……日子,似乎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温馨的……
又过了些年。某日,国清电话同我说,他离职了,不在保险公司了。我颇吃惊,不知何以变故。他只淡淡地说,体制也束手束脚的,不如自己单干。中年离职创业,于我保守性格,难以想象;但生意之事,我一无所知,说不上什么,便也不多问。往后,就听他一忽儿做茶叶生意,一忽儿做干果;股票狂飙那年,他将几套房子卖了,砸进股市,股市却一路跌到谷底……疫情前,他颇兴奋地与我说:如今是电商时代,正与人合股做电商。我心中颇不安:虽不懂生意,也知道电商最烧钱,大鱼吞小鱼,小鱼吃虾米,很可能抽走小生意人的最后一点资金;这些年,我所认识的不多的创业者,或关闭公司,或融入大集团,或移民,或躺平……这些话,终于没说出口,见他朋友圈兴兴头头搞企业文化,想来是不错的。往后各自忙乱,长久无消息,忽一日想起,三年疫情已过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高中毕业十周年,我们在莆田湄洲岛聚会。沙石粗粝,海水湛蓝。涨潮时,我们一群同学手拉着手,排成一排,直立着迎着汹涌的浪头,浪头将我们抛到高处,大家就狂笑……那时,竟是那般明朗、自信,我们自以为是弄潮儿,可与时代搏浪。人到中年,头发斑白,才觉得,我们每个都只不过一条小鱼、一颗贝壳、一粒沙,涨潮时分,被抛到高处,站在浪尖,随海浪发出巨大喧响,便以为是自己的声音,潮水退去,或一个浪头打来,便跌下来,甚或被海水吞没。就像那些鱼儿啊,贝壳啊,沙子啊,或被海水卷走,沉寂在大海深处,或侥幸停留在沙滩,留点痕迹。
2
约国清到涵江区城隍庙接我,一同去看米粉加工。那一带原有戏台、教堂、旧市集、花鸟市场等,如今四下起高楼,比邻还有一幢八爪鱼状巨型商场,城隍庙旧戏台陷落其间,好似钢筋水泥肌肤附着的一块牛皮癣,陈旧,寒碜。
国清的车准时停在路边。他还是那般瘦削,只是两鬓略斑白,眼角有鱼尾纹,眼神略显疲惫,其他也没啥变化。我坐进车,自然而然,好似昨天才见过他。前排还有一人,国清介绍说:“我学弟阿林,我们去他老家看做米粉,黄石镇惠上村,莆田有名的专做米粉的村庄。”
从涵江区到惠上村,一个多小时车程。有国清介绍,阿林相当客气,一路上絮絮说个不休,说他自打出生,就在米粉堆里滚,惠上村目前有八千多人,基本做米粉为生,但多是老人、妇女,年轻人多离村另谋出路。他叹息说,儿时是手工做米粉,现在则是机械或半机械制作,手工艺要失传了。我就请他说说传统手工米粉制作的工序:
1. 洗米。将大米搅拌、洗净,浸泡五小时朝上。地道的要选兴化平原出产的黄尖米,做出的米粉是微黄色的。纯大米做的米粉,韧道好,口感好,若是掺杂淀粉,虽降低了成本,但吃起来有塑料感。
2. 磨浆。以石磨磨浆,再过滤去粗,口感更细腻。
3. 压干。以布袋裹紧米浆水,压上巨石或重物,逼出水分成半干米团。
4. 炊粿。将生米团上笼蒸熟。
5. 打粿(礁粿)。蒸好的米团放在石臼中,脚踩石锤,反复锤打,直锤到米团晶莹,这样做出的米粉才能又柔软又有韧劲。锤打时间不够,米粉易断,一煮就煳。
6. 压丝。锤好的米团放进压榨桶,靠杠杆作用,将米团压出桶叫压丝或出条;米粉丝粗细与网格细密有关,最细可达0.2毫米,细如发丝。
7. 炊粉。将压好的米粉丝摊在蒸笼架上,再蒸一遍,韧劲更好。
8. 摊凉。蒸好的米粉丝尽快摊开吹凉,否则会糊成一团。
9. 洗粉。蒸好凉透的粉丝以冷水淘洗,去掉黏糊的米浆水。
10. 切断。将长粉丝切成均匀的一段段。
11. 摊把。用两根竹筷将粉丝撑成四方块一把一把分摊开。
12. 晾晒。摊把后的四方块粉丝一把把排到竹篾帘上晾晒几小时直至干透。
阿林笑道:“我对米粉的情感,是又爱又恨。说爱,以前我一家老小的生活、我们读书的学费,全指着这米粉。说恨,就是太苦了。每天夜间浸好米,天蒙蒙亮父母就起床,磨浆、蒸粿各种忙乱,到打粿时,喊我起床帮忙,因为父母亲两个人得一起踩几十斤重的石锤,需要我蹲在石臼边翻米团,石锤下落瞬间,我得快速将米团翻转,每锤一下,我就得翻一下,手的动作得配合石锤下落的速度。小孩子早上睡眼惺忪、迷迷瞪瞪,稍不留神,手慢了,就被石锤锤到,痛得哇哇叫,还要挨父母骂。到晾晒米粉时,又得抢地盘。一村人都在做米粉,到处摆放晾米粉的篾帘,村中没抢到地方,就得驮着篾帘爬到山坡去晒,山坡干净无灰尘。但米粉又不能暴晒,最好有薄薄的阳光;又最好风大,风大,米粉就吹得蓬蓬松松。可是那篾帘多重啊,我瘦瘦小小的,要驮几十斤一大片篾帘爬山坡,还得小心排在上面的米粉不要倾倒,又要和别家小孩子抢地盘……闽南这地方,常常刚出太阳,转眼就下起雨,又得赶紧去抢着驮回篾帘,唉……别提多辛苦了……就这样,一家子一天也只能做二十来斤米粉……”
说话间,小车拐进惠上村。道路洁净,多新盖楼房,门外停有摩托车或小货车。与莆田多数乡村楼房不同,檐角无弯翘,屋顶不倾斜,楼顶皆有露天平台。后来知道,如今米粉篾帘不用背到山坡去晒,而是晒在自家平台。我们要拜访的是方师傅,村中善做米粉的老法师。
一个老人站在一幢五层楼房门前仰着脖颈张望,我们一下车,就迎上来握手。正是方师傅。看上去只有六十来岁,头发乌黑,只两鬓微白,皮肤黢黑褶皱,身子干瘦挺拔,双目炯炯有神,阿林说他年近八十,真是看不出!!老人热情引我们进门,介绍说:其他楼层是自家居住,二楼会客,底楼一半是米粉加工车间、一半是包装储存,楼顶平台用来晒米粉。他边说边带我们走进底楼左侧房间:大理石地面泛着白光,堆放着各种机器、蒸笼木架水桶,等等,操作台皆是不锈钢的,一尘不染。老人熟稔介绍各种机器及应用:磨碎机、压力机、挤压机、蓬松机、碾压机、压条机、蒸炉……以机器加工米粉,与手工制作工序大体差不多,除了如阿林叙述的、最辛苦的用石锤“打粿”环节,是以挤压机将米团挤成柱状,将米柱摆在一起送到蒸炉蒸熟,冷却后,再扔到蓬松机里去蓬松,然后放入碾压机压成薄片,再将薄片卷成团,放入压条机“出条”。方师傅说,机械加工除了节省人力、提高产量外,另外的好处,是精确,想做多少米粉就做多少,压榨、出条、蒸熟,设定好时间、压力、粗细,这样,出产的米粉质量稳定(当然也少了传统手工的独特性)。村中各家的米粉加工都不是大规模、全自动化的,都属于半机械半手工,比如蒸熟后的米粉丝,还得经过手工的漂洗、切断、摊把,再人工排到竹篾帘上去晾晒。
从加工车间向右穿过一道圆拱门,就是宽敞的仓储间,米粉的包装、储存皆在此。右侧有道旋转楼梯通向各层楼,楼梯边垂下一条粗麻绳,上面挂一个大竹篮,老人说,漂洗、切断后的米粉就放在这个竹篮内,通过滑轮绳索传送到楼顶平台去,篾帘全都竖在平台上,米粉就在平台上摊把、晾晒,与传统晾在大路边、山坡上相比,这样晾晒米粉更干净,也更省力、省时间。仓储间铺着闽南独特的枣红地砖,三面墙都整齐码着写有“米粉”字样的大红描金盒子,有十斤装和五斤装的,都是等待出货的成品。
老人带我们上旋转楼梯,两阶一跨,大家夸他腿脚敏捷,他笑说自小干活惯了,从前每天要驮几十斤重的米粉篾帘爬山坡,一天来回十几趟。二楼是个会客厅,南面一排落地窗,宽敞透气,靠窗一张海棠红实木长桌八把靠椅,方师傅居中坐下,我们四围入座,桌上一副花梨木长茶盘、一套紫砂工夫茶具,老人边殷勤泡茶倒茶,边用莆田腔浓重的普通话说:“呷茶,呷茶。”老人打小就做米粉,没怎么上学,身上却有一种从容自如、达观通透的气质;他身后墙上挂一帧放大的彩色全家福,大人小孩四世同堂,上书“78岁寿辰全家合影”。茶喝一轮,方师傅才问我是哪家媒体?显然,作为村中做米粉的老法师,常有视频、网站或报纸来采访,如何应答,如何宣传,他熟门熟路,很知道做好宣传关涉村中米粉的声誉、销售。我说,我是个作家,想写写米粉的故事,他和陪同者就神色茫然。我是想知道,何以当我吃一份滋味地道的兴化米粉,过去的一切,与米粉相关联的人人事事,那些沉埋在记忆深海的细节,会如沉渣泛起,如影像闪闪而过;我好奇的是,这兴化米粉,它的独特性如何能凝结转成兴化人的共同情感。去看一粒粒大米如何神奇变身为细如发丝的米粉,在对工艺知识的了解过程中,我或能寻找到这种凝结着时间与记忆,凝结着欢欣或痛苦、甜美或惆怅的一切一切情感的源头。我不知如何向老人道出这些思绪,只说:“请您老随便讲讲。”老人和陪同者就沉默着,不知从何说起,国清忙接口道:“就讲讲以前做米粉是怎么生活的,现在又是怎么样的。”
方师傅这才笑道:“做米粉,以前真是辛苦啊,现在日子好过多了。”
他便说起传统手工做米粉的艰辛,一如阿林描述的。他普通话夹杂着方言说道:“戏文里讲,‘卖油的女郎水梳头’,过去我们做米粉的人家,却吃不上米粉……舍不得吃啊……当年,米粉可是精贵得很,不像现在,有那么多东西吃,米粉就是普普通通的,小孩子都吃腻了不要吃了。以前,一般人家,只等生病了,吃东西无啥滋味,或者家里来客人了,才舍得下一把汤米粉吃吃,如果是炒米粉,那得费老多油,还要加各种配料,那得在中秋、春节,或者有侬结婚做寿,总之是大节大日子,蜀厝侬(一家子)只敢炒一盆,大人小孩围上来一人一箸(筷子)就吃光光了……你讲怎生做米粉人家没米粉吃?粮食不够啊。我们这边靠界外(沿海),田地本来就少,呆囝(小孩)又多,粮食就不够吃。我们靠着有手艺,做了米粉,拿去换稻米,五斤稻米,只能做一斤米粉;换来了稻米,却舍不得吃米饭,继续拿来做米粉……那我们蜀厝侬平常吃什么?吃红薯啊,一斤米粉可以换十斤红薯呢,米粉是精细食品,我们做工的人,米粉吃到肚子里,就溜下去,不饱肚,红薯能饱肚,靠着米粉换红薯,就养活蜀厝侬了……”
“一开始,每家做的米粉都由公家统一收购,价格阿没什么好商量,从前靠手工做米粉,起早做到暗暝,一天也只做二十来斤,勉强维持用度,大人呆囝要吃饭,呆囝还要读书,那是真真辛苦。到八十年代初,还没形成正规市场,米粉做好了,就担一担,一村一村、一乡一乡去转悠,偷偷去卖,当时大家都穷,平常肯买米粉吃的人家阿不多,有时候行阿一天,一把米粉阿卖不出。当时还不允许自由买卖,担一担米粉,竹篮上放点草枝遮遮,担心被人发现偷卖,被当作投机倒把逮起来,罚款,关几天,那就完蛋了,全家白干了……到后来,起鼓(开始)市场化了,有人到镇上去开店,米粉做好了,就送到店铺寄卖,有本事的人家,家己(自己)开一片店,家己做家己卖。不过竞争阿煞果(厉害),家家做米粉,就看谁家的米粉质量好、价钱低。做太多,卖不出去,米粉生虫发霉,不舍得扔,全家天天吃米粉,以前是做米粉人家吃不起米粉,到后来,小孩子看到米粉勒卜吐……”老人说到这里,咧嘴笑道:“现在好了,用机器加工,绝对准确,想做多少,就做多少。有专门批量卖给经销商、饭店,各家还开了网店零售,也有通过微信预订的,根据订单,做多少,卖多少,很精确,不囤积。我们全家,除了出去读书工作的,留在村中的全部做米粉,生产、包装、销售一条龙。全村家家户户如此。”我点头,心想,这也算是小规模电商的好处了,身在异乡,就能通过网络,买到地道的兴化米粉,不必如过去,须从家乡大包小包地带。
我们说话的时候,二楼靠近楼梯处还有一张小桌子,几个穿红衣的妇女围坐着,边用莆仙话聊天,边做手工活,脚下堆着印有“米粉”字样的礼品盒纸板,三个妇女正在折粘成盒子;桌上还放着好多卷红色金属扎带,两个女人正将扎带剪成四十厘米一段。儿时听爷爷说谜语,“四角四角方,用草缚腰方”,谜面正是米粉,米粉四四方方,腰间扎以稻草,如今是用红色金属扎带来绑缚米粉的。方师傅介绍说,是他的媳妇、女儿们,晴天可以做米粉,她们负责洗粉、摊把、晾晒、包装;阴雨天不合适做米粉,她们就在室内做做手工。说到这里,老人叹口气:“下一代离开村里了,不愿意做米粉了。不要说传统手工无人继承,就像我们这种半机械半手工,还保留点自家特色的,也无人继承了。往后就是工厂流水线生产的米粉,一模一样,反正大家阿吃不出是好是歹,是纯大米做的还是加了淀粉的,没比较嘛。现在好吃东西阿有许多,米粉就是普通食品,销量是比较稳定,但产量也不高,差不多维持吧……”
临别时,阿林各买了十斤米粉送给国清和我。老人拿给我们的是特级米粉,果真是细如发丝,白如莹雪。他亲手将米粉一把一把小小心心地放进纸盒,好似轻抚着一个个方头方脑白白胖胖戴着红肚兜的娃娃。
3
阿林走后,国清送我回家。他沉默地开车,我沉默地坐着。多少年了,我们并不陌生、疏离,也并非相互不信任;只是多年不见,许多话不知从何说起。我很想问问他这几年过得怎样,如今到底在经营什么,却不知从哪里问起。况且,若要他从头细细说来听,想必是很漫长、很烦人的。莆田人一向是报喜不报忧,喜乐大家共享,压力与艰辛默默独咽。而若谈及创业过程的艰辛与愁烦,我又能为他做什么?空有安慰的话,虚弱无力,隔靴搔痒。“说来话长”几个字,真真是人到中年的口头禅吧?就好比我自己的生活,我的日子,就算是面对一个极熟悉亲切的人,又从何处说起呢?“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别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这首词,少年时只是背诵,而今我们大家都斑白了头发、松弛了面庞,生命之重压在额头印上深深的沟壑,才能体会其中之意吧?回想九十年代末,国清和我从广化寺后山小道一路走到石寺岩,我一路絮絮叨叨,他虽是沉默不语地听,但整个人显得明朗、健康、自信,如今在他身上我似又看见少年时的重负阴郁。
车停在我父母单元楼底下,我终于问他:“你怎么样?”他转头笑笑,说:“还可以吧——你呢?”我说:“也可以吧。”沉默了几分钟,我打开车门,他帮我提米粉盒,放在我爸妈家门口台阶,笑着对我说:“今天太晚了,就不上去看你爸妈了。下次,下次时间宽裕点,我请你吃饭,我们好好聊聊。”
国清钻进小车,我站着,脚边放着米粉盒,看着他将车开走了……
母亲看见米粉盒,眉开眼笑,打开来,边看边啧啧称赞,说米粉很匀细,很干净,一看就知道是上好米粉。她又拎出一袋她自己在市场上买的,各拿一把摊在手掌上比较,说她买的差些,让我带好的去上海。我看着母亲倒腾米粉,那个样子,比我给她一万元都更高兴,我很理解她对米粉的情感。母亲小时家中稻米少,每以地瓜、海货补充生活,米粉更是精贵食品,只在生病了,或在中秋、春节这种大节庆,才可能吃到。母亲对我说:“你出生在莆田城里,坐月子时,你奶奶不时煮汤米粉给我吃,当时是最好的东西了。”后来父母亲在闽北工作,兴化米粉只能从莆田带过去,更是极珍贵的。而到我读中学时,米粉已是许多人家的常备食品了。早自习前,或下学后等吃正餐前,奶奶常会先下一把“饮糜汤烫米粉”给我垫垫肚子。奶奶常说,“食龙食凤,伓如蜀碗饮糜汤烫米粉”,意思将来无论如何富贵,也不忘记最初的那碗“饮糜汤烫米粉”。
吃罢晚饭,母亲要将米粉收拾起来,门铃响了几声,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子,母亲一见,就亲热地叫:“阿华来咯,阿紧进来。”原来是我表哥阿华,大舅舅的长子。他微微谢顶,面孔瘦削、发黑,眉目却秀气,眼神文雅和善。他躬着背,微笑着,似乎见着所有人,都要小心恭候的样子;左手拎一盒子景德镇瓷器,说是给我的,他站着也不坐下,母亲接了瓷器,边说“偌厚意”边叫他坐,叫了几声,他才屁股略略搭着椅子坐,局促,羞涩,手脚没地方放的感觉。
阿华只比我大一岁,我们同年上大学,同年毕业,但这是我第三次见到他。
第一次是我初二时,去铁灶村看大舅。我爷爷家在莆田城内,位于兴化平原,多产稻米,“山里”“界外”则少农田,大人吓小孩子总说:不好好读书,就送到“界外”去,那是贫穷吃不饱饭的地方。我外祖家在铁灶村,临近“界外”,田地少,又不直接靠海,海产也不多;三年严重困难时,更吃不饱饭,逢闽北农场招工,我外祖就与两个舅舅、我母亲一同去了农场,单留大舅“看家”。1985年我去铁灶村看大舅时,村中依旧穷,不像后来放开,沿海人做鳗鱼、养牡蛎、种蛏子,卖到全国、海外去,许多人暴富。彼时,我从城里乘公共汽车,再坐三轮车,到村口下来,过桥一条小路,一路走,一路问大舅的房子。我拎一个竹篮,装一篮子米粉,是爷爷教我送的礼物。有外人来村里,原是稀罕的,有人探头好奇盯着,有小孩子带我到大舅房门前。一平层泥屋,三间房尽是凹凸泥地,我坐在居中一间“厅堂”,无窗,光线单从大门入,一张方木桌、四把条凳外,再无别的家具,靠泥墙挂些绳索、斗笠、蓑衣,歪着扁担、木桶、麻袋及其他农具。我将米粉篮放在桌上,大舅笑眯眯一再说,“米粉偌好,汝阿公偌厚意”。表哥阿华站在泥地,瘦到佝背,胳膊细长,脖子也细,显得脑袋大而沉,面目却清秀,大舅喊他陪我“搭聊”,他却一句话也无,比我这个客人还害羞。好一会,阿华颤巍巍端来一个大海碗,满满一碗牡蛎,往我跟前一放,垂着头,一声不吭。大舅叫我“阿紧呷,全部呷光”。我吃了几口,实在难以下咽——那些牡蛎,只水中煮熟了,放很少盐,也无葱姜料酒,又淡又腥,满满一海碗,叫我全吃完。大舅说,接到我父亲来信,知道我会来,却不知什么时候来。家里没啥待客的,这些牡蛎,是阿华早上走几里地,到海边礁石那挖来,是新鲜的。我后来见人在海边挖牡蛎,须赶在涨潮前,用锤子之类工具将牡蛎从礁石上敲挖下来,再以海水淘洗,拎回家,剥壳剔肉,十来斤带壳牡蛎,只能剥出一斤牡蛎肉,阿华端给我吃的满满一海碗,大约有一斤半牡蛎肉,不知他挖了多久。乡下人也不晓得精细烹调,也没能放多多的油、再拌地瓜粉、鸡蛋、香菜,煎成可口的海蛎煎,用精致碟子端上来。——那碗牡蛎后来怎么样了,我忘了,只记得很辜负大舅及阿华的心意。
第二次见到阿华,是在闽北农场。那年,我考进复旦,阿华考到南昌一所大学。他来闽北度寒假,已是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瘦得有些佝背,裤子衣服过短地吊在身上,头小脸小,嘴上薄薄髭须,依旧是木讷害羞,不言不语。假期结束返校,我们一起从邵武上火车,我直达上海,阿华则去鹰潭转车。父母送我们到车站。母亲一再叮咛阿华照顾我,她见我平日木木哒哒、行动慢慢吞吞,想想我是挤不上火车的。阿华一手拎我的大行李袋,一手拎一纸箱兴化米粉——米粉是阿华从莆田带给我父母的,母亲舍不得吃,硬要我带到上海去——我单单斜背了个挎包。绿皮火车呼啸着喷着白烟气过来、抖动着喘息着停下,一开门,所有人发声喊,一拥而上。此时的我,如获神力,一边飞奔,一边回头喊阿华,我泥鳅般极其麻利地挤上了火车,阿华一手拎行李一手拎米粉,踉踉跄跄,眼看着挤上来了,又被一堆人推搡下去,左右上不了车。我就挤到一个车窗那,摇起车窗,大喊:“阿华!阿华!这边——”表哥将米粉纸箱托举过头顶,我伸手拽进车窗,有人就要从车窗爬进来,车内人都大喊道:“关上窗!快关上窗!”我夹在两排座位间,央求一男子把我的米粉箱子塞到行李架上,这才定定神回头去寻阿华,火车都快开了,才见他挤进车厢,一脸狼狈,一头的汗。父母亲还在车窗外隔着人群张望,我虚空地朝他们挥挥手,也不知道他们看不看得见,心中偷笑:还托表哥照顾我呢……
这是第三次见到阿华,离开上次,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都从少年青丝,转成鬓角斑白。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模糊寒暄着,说我几日回来,后天就要走,火车大概几点之类的闲话。虽是同龄的表兄妹,中间倒似乎隔了千山万水。阿华经历了许多事,眼神却平和,或是看透世事没什么怨气,或是秉性恬淡与人无争,或是心死了连欲望也没了?很难区分。
阿华的状况,母亲大略同我聊过。说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景德镇一家挖陶土的矿业,在办公室做文员,厂里大学生本不多,无奈阿华是个“古意侬”(我家乡话,指老实人,古,指古旧、久远、木讷、执拗),不会巴结领导,也不善交际,职务自然升不上去,好在坐办公室,工资不高,倒还固定。大舅在老家给他许了一门亲,莆田人结亲,原需一大笔聘礼,当时沿海放开,许多人家靠海产品致富,表嫂家在山里,想想能嫁到沿海,又是村里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就没要多少聘礼。没料到,阿华所在企业原就经营不善,后又出了矿难支付给家属大笔赔偿,工资渐渐就发不出,末了就是裁员。阿华在第一批裁员名单中,拿了一笔小小的安家费,就回老家去了。表嫂闲在家,原靠表哥一点工资过活,初时还能忍,见阿华下岗回家,怨气加重,成天唠叨数落。表哥在家受不了,就出去打零工,住在单位。如今是在我表弟的鞋厂管理车间。表弟只读到初中,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表哥读到大学,却要寄食人家,这一点,表嫂心中不受用,总埋怨职务低、工资少、事情多。表哥自己倒无甚想法,一心勤勤恳恳工作。
我和阿华说了会闲话,不知道再说什么。母亲问阿华吃晚饭没,表哥站起来摆手说:“厂里吃过了来的。”母亲说,吃过了也再吃一点。她从我带回的米粉中拿了一把,说给阿华煮一碗汤米粉吃吃。在我家乡,客人上门是不能空手的,多少带点礼品;主人也总要煮些点心给客人吃,这是老派的礼数。儿时春节,我跟爷爷去亲戚家拜年,每到一家,主人定规要煮点心给我们吃,或是热拌线面,或是汤煮米粉,至少也要水煮荷包蛋。人家煮了,客人定规要吃,吃了又不能全吃完,否则都是不懂礼数。比如,煮四个荷包蛋,只能吃两个,不可以四个全吃掉,以前是穷,才有这个规矩。当年我一圈子拜完年,总会吃到走不动,口袋里塞满糖果花生瓜子之类。我家里自然也早早准备了线面、米粉、红团,预备做点心,还有零食,会有别人家孩子来拜年。预备这些东西的意义,就在于此,在于亲人朋友的来来往往。如今物品丰盛,人情倒变得淡薄,米粉线面,零食杂饵,既不见珍贵,也稀薄了承载意义。
已过了晚饭时间,没有“饮糜汤烫米粉”。其实随便什么配菜做汤米粉都好吃。母亲将发好的干香菇、瘦肉、芹菜切丝,热油炒炒,放汤水,加一把虾米,烧滚,加入半把米粉,烧烧开就舀起来,撒一把葱花,滴几滴麻油。母亲喊:“阿华——来呷米粉咯——”阿华朝我笑笑,起身去厨房,边吃边絮絮地与我母亲说话。在姑姑面前,他话倒挺多。只听他说,昨天老婆又和他吵,说他没本事;说儿子大学毕业,读的是设计专业,毕业生太多,工作不好找,干脆不找了,蜀日届暗(一天到晚)窝在家里看手机、打游戏,愁死了;又说快三十岁了,也不谈女朋友,一说结婚,就要老爸在城里买房子,还要车……中间听我母亲高声叫道:“伊家己有本事家己去买!汝卜勒操孽命(劳碌命),养他那么大,吃穿都是父母的,还要这个,要那个……”
米粉香气从厨房飘出来,天已全黑了,我开灯,晕黄灯光柔和倾泻下来,照亮电视机、茶几、紫色三角梅、海棠色木沙发、沙发上的大红描金米粉盒子……夜静极了,只听见阿华与母亲的絮絮说话声,阿华的轻叹声,汤勺轻碰瓷碗的声音,喝米粉汤的声音……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