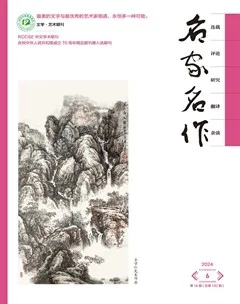玛丽·奥斯汀《少雨的土地》的土地伦理思想探析
2024-07-29韦清郭紫茜
[摘 要] 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观使人类重新审视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土地伦理思想向人类中心主义发起挑战,探讨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生物之间的伦理关系。从土地伦理视角分析玛丽·奥斯汀《少雨的土地》中超前的生态整体意识,倡导人类亲身感知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
[关 键 词] 《少雨的土地》;土地伦理;自然环境
基金项目:云南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基金项目“玛丽·奥斯汀《少雨的土地》的土地伦理思想探析”(项目编号:2024SKY085)。
一、引言
玛丽·奥斯汀 (Mary Austin, 1868—1934)曾被誉为 “美国环境主义运动之母” ,代表作《少雨的土地》(1903)确立了其在自然写作界的文学地位。《少雨的土地》共包含14篇散文随笔,侧重描写沙漠地区的地质与人文景观、动物与植物的生活痕迹。全书围绕土地是如何在人类与动、植物之间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质朴而纯粹的纽带。沙漠曾被人误解为荒凉与恐怖之地,但在奥斯汀笔下,沙漠不再是干燥与死亡的表征,而是一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灵动画卷。通过对沙漠长达十余年的细致观察,奥斯汀向读者展示了前工业化时期未被城市化建设洗涤的荒野图景。
20世纪前未曾有系统的理论明确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土地上的动、植物之间的伦理关系,直到美国“生态伦理之父”奥尔多·利奥波德 (Aldo Leopold,1887—1948)在其代表作《沙乡年鉴》(1949)中正式提出了“土地伦理”这一概念,将土地伦理定义为:“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动物,或者把它们概括起来:土地。”[1]利奥波德认为土地应当被热爱和尊重,人类维持土地健康是一种伦理观念的延伸。维护土地不仅仅是简单地修补受损部分,而是要深入理解并强化共同体在各个层面的协调运作,使之成为一个能够自我更新和持续发展的有机体。土地伦理不仅围绕土地展开,还延伸至人类与自然界动物、植物之间的关系。自然界的生物形成生物区系金字塔,土地则为动、植物提供物质能源。“土地金字塔”中人类不再以征服者的角色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与熊和松鼠一样处于中间层次。土地的良性循环依赖于金字塔中各生态系统层系之间的相互依存,人类需自觉维护生物多样性从而稳定生态系统。此外,利奥波德在土地伦理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应当具备“生态良知”。当今,人们普遍认为加强资源保护教育就能缓解资源过度滥用的现状,然而这未能从根本上消解人类对自然造成的创伤。生态良知要求人类将社会觉悟从人延伸至土地,发自内心地真正理解和教育国民如何维护资源,避免资源保护简单化。奥斯汀将对西部荒野的切身观察转换成独特的文学语言形式,精准地定义人与土地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她将土地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前瞻性书写,映射了后期利奥波德提出的土地伦理观。本文主要探析《少雨的土地》的土地伦理思想,转变过去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导向的价值观,以期达到深化土地伦理教育的目的。
二、《少雨的土地》的土地伦理思想
(一)土地金字塔
深受生物进化理论和食物链理论的影响,利奥波德提出“土地金字塔”理念。“每一个接续的层次都以它下面的一层为食,而且这下面的一层还提供着其他用途;反之,每一个层次又为比它高的一层提供着食物和其他用途。”[1]土地是孕育万物的根基,上层动物以下层动物为食物,形成自然界生物链体系。“也许我们从来没有充分相信野生动物之间的彼此依存,它们对自身事物的认识。”[2]沙漠中有植物的地方就会有昆虫,有昆虫就代表着有鸟类与哺乳动物的存在。以此类推,有哺乳动物就会有利齿类动物,有腐肉的地方就会有大量的红头美洲鹫。每一个体都在整体之间相互关联,无形中造就文中描述的“哪里有柳树,哪里就可能有鳟鱼”的自然规律。“它从来就不缺乏生命,无论空气多么干燥,土质多么恶劣。”[2]鲜有人居住的沙漠并不代表动物、植物寥若晨星,在贫瘠的地质环境下反而还生长着上百种植物。在奥斯汀的笔下,“人类和荒野没有对立起来,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形成一个个生物区域整体(或共同体)”[3]。生态系统中所有成员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每个物种之间似乎达成一种“默契”,看似相互独立的生物群体实则相互依赖。
“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和公民。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在《少雨的土地》中, 奥斯汀无处不透露出人类与自然界万物平等的生态观念。“土地忍受它,就像它忍受一只囊鼠或獾一样。在所有的居民中,它对人类最不关心。”[2]土地看待一切的事物都待以平等视角,人类并不比其他物种优越,这也是为何人类试图征服自然却屡次碰壁的根源。沙漠的美与恐怖之间有一种张力,二者在这种张力中保持平衡,成为和谐的整体[4]。沙漠中每年都有人死于恐怖的沟壑,截断的水源致使人们走向伤亡的边缘。当寻矿人经历一夜风暴的侵袭,是其所蔑视的羊群守护了他的生命。人类的力量在自然面前微乎其微, 他们无法控制环境灾难与自然死亡。奥斯汀以人与土地的关系为基点,“明显地批判了父权制的二元思维模式,消解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统治与被统治的二元对立关系”[5]。自然界所有成员共同栖居于这个大家庭之中, 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人不再是万物的中心,动物与人类的生命具有同等的地位。奥斯汀通过自然写作传达人类应以平等的身份融入自然的希冀与憧憬之情。
(二)土地共同体
土地伦理明确了“土地共同体”的概念:土地是一个共同体的观念,是生态学的基本概念[1]。相较于其他生态作家,奥斯汀更早关注人与土地的关系,并率先将写作笔触聚焦于西部荒野地带,向读者展示了土地如何孕育出一种特有的精神风貌。土地赋予人们面对困难时的坚韧以及对自然恩赐的感激之情,这种情感不仅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还渗透到动、植物与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之中。“你诅咒这片土地,却会一次次地回到它身边。”[2]尽管人类常常抱怨沙漠中无法直接饮用的水源、难以忍受的天气、来势汹汹的大风,但这些都抵挡不住人类对这片土地的好奇之心。沙漠同时也具有绚烂的阳光和最纯净的空气,并非只有苍凉与沉寂。正是因为沙漠独有的特质与无限的魅力,人们才一次次离开后最终选择归来。“少雨的土地”浸透了土地的元素,这里所有的动植物和人都贴近土地而生存[6]。特殊的地理环境下沙漠中的居民唯有主动去顺应土地的性质才能够维生。肖肖尼人在泉水边用木柴搭起茅屋,运用灌木烧柴,贫瘠的土地塑造他们善良、勤恳的美好品质。“土地的特性,有力地决定了生活在它上面的人的特性。”[1]对于派尤特人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家,自然界的万物塑造了他们的家庭结构,他们不依靠现代科技就能对沙漠的气候规律了如指掌。在这些逐步没落的族群眼中, 土地上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神圣的,是脚下的土地赋予他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沙漠中的每一粒沙砾似乎都在诉说着生命的故事,每一次的风起沙落都像是大自然的交响乐,赋予这片土地无限的可能。只有对自然界的每个生命持有深深的敬意与同情,他们才能在孤独和寂静之中找到真正的自由和内心的充盈。要在这般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自然环境中继续生存下去,人与自然之间就必须建立起一种深厚而复杂的联系,这种联系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的依赖,更包括精神和情感层面上的相互依存。葡萄藤小镇居民过着贫穷但安分的生活,当地编织者与葡萄藤一样被赋予同样的元素,他们的生活与土地紧密相连,仿佛是土地孕育出的一分子。他们不会抱怨环境,而是坦然地接受土地带来的馈赠。相反,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们逐渐将“不流汗就什么也得不到”[2]视为价值观。自我意识迫使当代人将唯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的观念嵌入大脑,这使得他们的精神世界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状态。“正是这片辽阔的褐色土地上存在着这般的慈爱”[2],奥斯汀认为沙漠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以及无比珍贵的精神体验,尽管金钱可以让现代人买到商品,却买不到自然伴随的归属感。自然就像一剂良方,为人类注入精神力量,缓解内心的不安,这是商业化盛行的今日难以复刻的存在。
此外,奥斯汀在书中提到了解自然的唯一途径是接近自然、归于自然,通过最直接的方式去观察、解析自然。人在沙漠停留得越久,就会对自然有更透彻的认知。“尽可能靠土地生活”[2],卸下现代式的物质你就能排除干扰、轻装上阵,寻找一寸心灵净土。唯有这样才能欣赏到怡人的峡谷和闪耀的瀑布,每一步都像在探索土地的奥秘。奥斯汀视自然是神圣的, 自然有它自己的意愿和情绪,并非没有灵魂的客观存在任由人类宰割;相反,人类应当满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真诚地投入自然的怀抱并亲身感知。
(三)生态良知
奥斯汀厌倦功利的社会环境,提倡人应当与脚下的土地融为一体。然而,不管是过去几十年还是现在,城市到乡村或荒野的交通使得人类跨区域流动越来越便捷,但这也打破了沙漠原有的宁静。愈多的人进入荒野,自然就要遭受愈多的破坏。比起自然界的狂风暴雨、动物界的弱肉强食,更可怕的是人类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毁灭性伤害。利奥波德认为荒原正在面临耗竭,并意识到荒野迅速消失会导致人类忘却文明的起源。我们依然是在每前进一步时就要往回滑两步[1]。当下的环境教育并未正向引导我们建立一个绿色、健康的精神和生存家园。环境保护不是简单地将土地看作是经济问题,以利己主义为导向的治理方式终将致使土地保护脱离正轨。人类面对的问题是要将环境保护视为伦理上的道德责任,在人类意识形态中构建“感知能力”,形成由内向外的生态良知。在功利主义盛行、商业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下,人们缺乏对野生动植物与荒原的保护意识,生态环境维护尚未引起普遍重视。在西部农业发展的同时,一些工业中心也在形成,如食品加工、造船等,特别是矿山开采得到了长足的发展[7]。失踪的金矿传说,吸引大量的人流涌入西部荒野地区。“有足够的金子、足够的时间,在你之后还会有足够多的人到来。”[2]人类将土地纳为私有财产,试图通过土地谋取利益而占据野生动物的家园,并开始涉足这片未被污染的土地,抢夺土地与水源的所有分配权,这一切完全脱离土地伦理所提倡的应当对土地持有爱与尊重的态度。第七节《我邻居的土地》中,土地在经历永不停歇的易主之战后,田园仍然花开满园,甲虫仍然成群结队,鸟群也仍然翱翔天际。自然界的万物在这片土地上其乐融融地相处着,创造着专属于沙漠的惬意。土地的生命力并不会因人类的贪婪而被削弱,它仍然如同往昔那般充满生机与活力。土壤中的每一滴营养物质都是植物茁壮成长的源泉,每一块坚实的土地都是动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
《少雨的土地》将写作的重心聚焦于土地本身,并未长篇赘述人类对自然界造成的损伤,但我们仍可以感受到作者对人类曾犯下的错行的强烈抵制情绪。“那是自然的经济学,但是人类的索取永无止境。没有任何食腐动物像人那样吃锡罐头,没有任何野生动物会给森林造成这样的破坏。”[2]经济发展与贪欲驱使人类肆无忌惮地将呈土地颜色、全然无害的蜥蜴做成标本贩卖,甚至将动物做成罐头以食用。丰富的动物种群吸引大量的白人入侵沙漠,狩猎区域充斥着步枪与弓箭,就连身为捕猎者的狐狸也担忧自己终将成为他人的囊中之物。奥斯汀强调自然的精神价值对构建人类的道德认知的重要性,认为同情心是一种教养。人类若继续无情地过度剥削自然以满足私欲, 长此以往生态金字塔就会失衡, 能量循环不畅甚至中断循环, 最后则会危及人类自身生存安全。生态良知是人类内化的道德意识,人类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自身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维持生物区系金字塔的稳定,万物才能够和谐地生活在地球家园。人在荒野,实际上就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8]。自然资源和生态的保护不仅仅是一种行动上的义务,更是一种心灵上的呼唤,人类与土地之间的和谐共处关系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探讨人与土地的关系,奥斯汀为人类正面临的生态危机建立了坚实而持久的伦理基础,促进人类正视和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从而迈向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三、结束语
奥斯汀极力批判追求经济发展从而舍弃生态以及动、植物的生存发展的行为。生态危机已成为时代亟须解决的难题,重视生态问题不会随时代洪流而浅化它的重要性。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地矛盾和环境恶化问题,生态文明建设刻不容缓。本文通过探讨玛丽·奥斯汀超前的土地伦理思想以警示人们要充分意识到人类与自然界万物在土地之间相互依赖的金字塔关系。土地共同体表明人对于土地的态度应当是尊重与热爱,而不是无休止的剥削。同时,人类仅凭借行为上的付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加强思想上的教育工作,形成生态良知,将保护自然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终身事业。
参考文献:
[1][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2]玛丽·奥斯汀.少雨的土地[M].马永波,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3]张建国.玛丽·奥斯汀散文代表作的生物区域主义意识[J].广西社会科学,2014(1):165-169.
[4]张雅萍.沙漠仙人掌:玛丽·奥斯丁的自然文学创作[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7(4):66-71,101.
[5]周燕.《少雨的土地》的解构主义解读[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5):81-84.
[6]宋洁.玛丽·奥斯汀笔下的沙漠意象[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9(3):88-93.
[7]侯文蕙.十九世纪的美国西进运动[J].兰州大学学报,1986(2):8-15.
[8]程虹.荒野情结:写在《寻归荒野》增订版之前[J].读书,2011(2):108-112.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