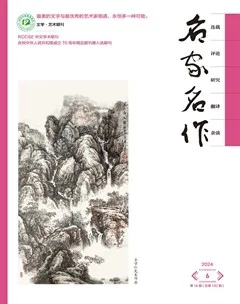咚咚与孟姜女——由民间故事引发的思考
2024-07-29刘欣
[摘 要] 民间故事作为百姓日常生活中口头创作的作品,代代相传。在各地区交流及民族融合发展中,民间故事得以传播和传承,所到之处,经过当地百姓的再次创作与表达,成为极富地域特色的民间文学作品,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对当地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等都有一定的积极影响。正因如此,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民间文学受到官方的青睐,并积极撮合民间文学与地方建设互利互惠、共谋发展。在文化赋能基层社会建设的语境下,民间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资源与文化财富,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在立足民间文学特点、价值及功能的基础上,分析其在传播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变故”,并探讨地方社会对民间文学作品活化利用应有的态度和思考。
[关 键 词] 民间文学作品;功能价值;民间故事
一、 湘西人也有自己的“孟姜女”
咚咚是谁?和孟姜女有着怎样的联系?
湘西土家族有一种传统乐器叫作“咚咚喹”,它是一种用笔杆粗细的小竹子或生禾秆做成的吹奏乐器,长约4寸,可使用右手食指在打音孔上快速地上下滑动,以此模拟虫鸣鸟叫及风泉之声。这一民间乐器吹出来的声音并不是“咚咚咚”的响声,那又为何会取名为“咚咚喹”呢?其背后流传着这样一个民间故事:秦始皇修长城时,抓走了土家族青年巴列。他的妻子咚咚日夜盼望丈夫早日归来,天天上山张望,但始终不见丈夫的身影。咚咚就采来一根竹子做成笛子,日日独奏,寄托悲思,一直吹到哀怨而死。后人为了怀念咚咚,也学着她的调子吹起竹笛,后来此笛被命名为“咚咚奎”。这则土家族民间故事与家喻户晓的汉族孟姜女的故事情节十分相似。第一,时代背景一样,故事都发生在秦朝,秦始皇为了修筑万里长城劳民伤财,不顾民生;第二,遭遇一致,丈夫都被抓去修长城做苦力,夫妻被迫分离,日日不得相见;第三,结局悲惨,一个投河自尽,一个香消玉殒,同为天涯沦落人。对故事文本分析进行分析,也发现了二者的不同之处:其一,流传于湘西的故事版本中加入了对土家族传统乐器“咚咚喹”的解释;其二“等夫”情节代替了寻夫的情节;其三,没有哭倒长城的类似桥段。这些不同之处作为故事的副线,并不影响故事主题及核心要义,其中“上山张望”“采竹子”等描述,与土家族的自然地理特征相匹配,是典型的汉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被“本土化”的表现。通过对“原版”故事的再度创作,一个“接地气”的土家族民间故事由此产生并传播开来。
历史上,孟姜女的故事随着朝代更迭,出现过多个版本,我国研究孟姜女传说的集大成者顾颉刚先生,通过对“孟姜女”不同版本的收集、整理、研究,将其故事原型追溯至《左传》中“杞梁妻”拒绝在郊外吊唁战死丈夫的故事,文中记载:“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一个有礼有节、冷静理性的女性形象被刻画出来。随后,在战国时期《孟子》一书中对“杞梁妻”又增加了“哭”的部分,“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因战国时期的齐国人爱好唱哭调,故借用“杞梁妻”善哭来解释这种风俗的成因。至此,这则故事里都还没有出现秦始皇抓壮丁及修长城的情节,“杞梁妻”倒是先哭了起来,其形象从原来的冷静理性变得柔软感性。
西汉《列女传·贞顺篇·齐杞梁妻》中有了突破:“杞梁之妻无子,内外皆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动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上则无父,中则无夫,下则无子。内无所依,以见吾诚。外无所倚,以立吾节。吾岂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1]与现在流传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版本越来越接近。随后又经历唐、元、明、清等时期的不断改编及加工,故事内容日渐丰满并富有“时代特征”,“杞梁妻”也逐步拥有了自己的姓名“孟姜女”,而“秦始皇”也闪亮登场,被描述为:“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2]这一描述使得秦始皇“暴君”的形象深入人心,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悲惨命运与秦始皇联系起来,认定他就是人们凄惨命运的始作俑者。
以上是作为历时研究的讨论,在共时研究的维度下,不同空间和地域的孟姜女故事也会出现不同的版本,甚至在同一地区版本也不相同。在湘西土家族聚居的永顺县就出现了“……土司为修宫殿,派人抓走了巴列……”的故事情节,残暴的统治者已经由秦始皇变成了土司。
湘西州境内流传的这些版本,更换了作为符号的主角姓名,在保留核心情节的基础上,变更故事枝节,是对民间故事的再加工和再创作,实现了汉族民间故事的异地传承与传播,让湘西人也有了自己的“孟姜女”咚咚。
二、民间文学的特点及其“在地化”解读
民间文学的“在地化”,是指民间文学作品流传到某一地区,经多方加工后形成的符合本地风俗的民间文学的地方版本,也是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整个民间文学作品特点的具体体现。民间文学来源于民间,是人民群众集体口头创作并传播的文学艺术,因此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口头性、流变性成为其主要特征。这三个特征相辅相成、互为关联,具体表现为:个体作为集体的组成部分,均可以参与到故事的创作及改编中来,又因为个体表述的差异及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导致在口头传播的过程中出现无数版本。
民间文学的口头性表明其被再次创作的难度并不大。现当代作家文学讲究谋篇布局,注重艺术性和逻辑性,而民间文学更随意、自由及松散,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当下的思想和情感,“当歌且歌”“说唱就唱”,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不需要物质上的准备,“可操作性”强,门槛也不高。
民间文学的集体性则表明其被再次创作的主观能动性。因为民间文学原本就是集体创作的,是没有个体版权的语言艺术。人人都是作者,都可以参与到无数个民间文学作品的创作改编中,造成频次多、变化快、版本杂。但不论它如何被加工再造,都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基本相符。
民间文学的流变性则表明民间文学被再次创作的客观必然性。不同地区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审美趣味、自然环境等都有所不同,人民的情感诉求也不同,各种文化及情感交相辉映,造就许多类似但又不同的民间文学作品。类似是指故事主题和中心思想基本一致,但其故事背景,如时间、地点、人物姓名等方面却有所不同,如上述的“咚咚喹”与孟姜女的故事。
三、新时代背景下民间文学属性及功能价值的转变
民间文学作品伴随农耕生活而产生,并为农耕生活而服务,具有实用功能,譬如流传至今的各类劳动号子,其句式简单、节奏感强,配合劳动动作,有协调发力、鼓舞干劲、调节状态的功能,既能提高劳动效率又能调节劳动情绪,是劳动人民喜爱及需要的精神伙伴。劳动之余,各类谚语谜语、歌谣说唱、相声小戏等为劳动人民提供情绪价值,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民间文学还有教化功能。它涵盖了生产知识、生活常识、民族历史、技艺技能、仪式礼俗等方面的民间智慧和地方性知识,是人们管理社会、教育子女、约束言行、继承传统的重要载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故事原有的生存空间被压缩,在时空流转及社会变迁中,民间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属性有所减弱,我国四大民间传说故事《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许多民间文学作品,已经脱离了单纯的故事文本而存在,变成更具功能性和符号性的文化资源,具备资源属性,甚至受到争抢,成为地方社会建设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例如,湘西州花垣县的苗族人民通过追溯苗族始祖与蚩尤的各种历史关联,利用蚩尤的传说故事,作为地方发展的重要资源,开展了一系列蚩尤文化建设活动,如召开蚩尤文化论坛、出版蚩尤学术论文集与创办蚩尤文化研究基地等,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
这些案例与地方建设发展的政策和方针有重要关系。首先,在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从项目申报文本填写到具体保护政策推行,民间文学特别是民间传说及故事,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申报文本中的项目历史渊源来看,作为缺乏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口述史是对汉语书写的历史文献的补充。其次,项目简介中加入关于该项目的传说故事,在丰富项目内容的同时,也侧面言明该项目在特定社区或人群中的知名度及影响力。譬如上述关于“咚咚喹”的民间故事,被视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省级非物质遗产代表性项目“土家族咚咚喹”官方释义的一则民间传说补充。“传说的历史真实性,不在于历史记载的准确与否,而在于真实记录和反映民众的历史感情,是一种基于生活的艺术的真实性。传说可以作为历史的参考和佐证,但一般不具备可考性。”[3]
除此之外,民间文学在新时代背景下还具有连接过去社会和现实生活的重要的桥梁式的连接属性,具有积极的释义功能。人们需要通过民间文学对一些传统观念及行为做出合理且令人信服的解释,特别是在民间信仰、传统节庆活动中尤为突出。早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随之形成的习俗、信仰、仪式等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逐渐被遗忘、被取代甚至走向消亡。那么在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要维系这些传统习俗在当代的传承与传播,需要有符合现代民众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的说法,才能得到认可并保留及继承下去。比如中秋节,据《周礼》记载,周代已有“中秋夜迎寒”“秋分夕月(拜月)”的活动;农历八月中旬,又是秋粮收获之际,人们为了答谢神祗的护佑而举行一系列仪式和庆祝活动,称为“秋报”。中秋时节,天高气爽,月朗中天,正是观赏月亮的最佳时令。因此,后来祭月的成分便逐渐被赏月所替代,祭祀的色彩逐渐褪去,而这一节庆活动却延续下来,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及沿袭中秋节的内容和内涵,其间的各类习俗都需要得到新的解释,才能与时代发展相匹配、相衔接。比如吃月饼的习俗,月饼最开始是古人祭拜“月神”的重要供品,作为中秋节的一种重要食物,月饼与嫦娥、朱元璋等传说及历史人物产生化学反应,以赞扬美好爱情、歌颂胜利及人月两团圆的意蕴得到了民众的青睐,从而世代延续下来。
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遗迹也与民间传说有着密切的“来往”。
位于湘西州永顺县的老司城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世界文化遗产,这里的民间传说更丰富、更鲜活,还结集出版了一本《老司城地名故事》的书籍。传说赋予遗迹新的意义,而遗迹强化传说的可信度,为传说的广泛传播注入了能量,也使一些遗迹得到更多关注和重视,达到双赢的效果。
民间文学是地方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需要。民间文学作品对增加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内涵有积极作用,如民间文学作品可以融合地域风光、民俗风情和人文景观,塑造出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形象,向游客展现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和探索。此外,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中提及的地点、故事桥段等也成为文化旅游的经典打卡地和固定玩乐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探寻文学作品的背景和内涵。例如淄博市淄川区的诸多村落,都与孟姜女当年的活动有关:涌泉村有孟姜女寻夫途中被孟姓夫妇搭救的故居,齐长城则被称为是孟姜女曾经哭夫的地方。湘西州境内也流传着吕洞山的传说、红石林的传说、猛洞河的传说等,并将这些传说所在地打造成旅游景区景点。
除了景点景观,以湘西州为例,还流传着如饮食类、民俗类、传统技艺类等各类民间传说故事,为当地文化旅游产业赋能增值。 民间文学作品为文化旅游发展提供了资源和动力,通过与文学创意相结合,可以为文化旅游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和魅力,推动文化旅游的持续发展。同时,民间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也是传承和弘扬地方历史文化,促进传统文化在当代运用和转化的方式之一。
总体来说,民间文学的功能价值在转化为社会资源的那一刻起就发生了变化,为促进生产力增长和社会财富创造提供了动力和支持,同时为各类社会生产活动及推动社会全面发展提供了重要能量和条件。
四、结束语
民间文学作品因为其口头性、集体性、流变性带来的可塑造、门槛低、难考证、易传播等特质,成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优质资源。也正是因为这样,常常会出现一些过于急功近利的反面教材。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大背景之下,地方传说除了保存固有的教化、娱乐、交流以及传递信息的功能,在地方建设的呼唤声中更加经世致用。为了打造地域文化品牌,满足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民间文学承载了太多的责任和使命。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些旅游开发地区,民间文学的发明、创造与修改痕迹过于浓重,特别是意欲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项目,在严格的专家学者面前更需谨慎对待,否则不但会尴尬万分,也会让地方工作陷入被动。
文化工作者应该保持清醒且缜密的思维,在审慎的学术原则、地方建设与老百姓实际需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和突破口;普通民众有其自身精神与物质上的发展需求及文化选择和判断能力,在多方携手合作、共谋发展大计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如何在守正与创新中平衡三者关系,让民众、学界与地方能在同一层面对话是需要深入思考及探索的重要课题。生活并不是学术的批判对象,我们应该更多地去思考怎样把学术运用到具体的生活实践中来,指导生活、美化生活,这样的学术活动才会显得更有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向.列女传[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李惠芳.中国民间文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23.
作者单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