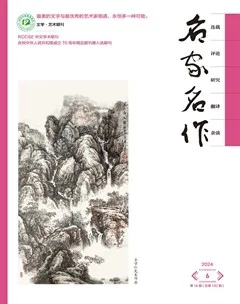爱、追求与生命
2024-07-29谢小练袁可歆张梦晗
[摘 要] 人文关怀强调对个体的尊重、理解和同情,关注人的价值和尊严。马克·李维的《偷影子的人》之所以深受读者的喜爱,不仅是因为其引人入胜的叙述内容、直击心灵的情感表达,更是因为其内含的人生哲理与人文关怀。以小说《偷影子的人》为研究对象,运用文本分析法,从情感、自我价值、生命观三个维度剖析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主题,揭示个体如何在爱的滋养下实现自我升华,如何在生命的波涛中确定方向,以及如何以温柔和尊重对待生命。
[关 键 词] 《偷影子的人》;人文关怀;自我价值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四川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马克·李维作品中的人文关怀”(项目编号:2023158)。
人文关怀意识起源于古希腊时的人文精神传统,其核心是人,主要体现在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与肯定,关注与重视人的存在与自我。在人文关怀的视角下,无论是现实世界中可见可感的个性追求与个体差异,还是内心世界里难以言表的隐秘感情与复杂欲望,皆可成为被尊重、被肯定和被重视的对象。马克·李维是法国著名的畅销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常常被赋予“温暖”“治愈”的评价,在不经意间流露对生命的思考与关怀。《偷影子的人》便是马克·李维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描述了一个被同学欺负的男孩因为“偷影子”的超能力,逐渐从懵懂走向成熟,成长为一个能凭借自己帮助他人的人,努力实现理想在生活中的意义[1]。在这部作品中,对真挚情感的剖白、对人生价值的求索、对生命差异的尊重,都体现出了一种对于人最纯真、朴素而又充满生机的温暖和力量,表达出了一种含蓄而又不失深沉的人文关怀意识。
一、情之所至——创伤与情感的交织共振
(一)亲情——爱与理解
马克·李维以第一视角塑造了一个并不完满的家庭:父母离婚,父亲离开后留下“我”与母亲一同生活。从家庭伦理的角度来看,夫妻是家庭的基础,其另一重身份——父母,则是子女的依靠。因而,当夫妻离婚后,长期生活在父母某一方角色缺失的单亲家庭中的孩子,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较其他普通家庭更严峻的成长困境。
“我”不止一次地认为是自己导致了父母的分开:“不管是以上哪种状况,我都是那个没办法让爸爸快乐、让他愿意留下的没用儿子。”[2]16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是家庭破裂带给“我”的负面影响——不可抑制地怀疑并将责任归于自己。然而,“我”并没有因失去了完整家庭而责怪父母,相反,“我”十分在意母亲的心情,也从未停止思念不知去向的父亲。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一直感受着母亲对“我”的关心,也从未怀疑过父亲对自己的爱,即使他再未出现。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阐述了爱的内涵,他认为爱是人所具有的一种主动力量,一种对他人主动地渗透从而使人克服寂寞孤独之感的力量,同时爱又允许人保存自我的完整[3]。只有一直沐浴在爱中,才更有感受爱的能力。正因拥有母爱这一味治愈心灵的“良药”,“我”才得以健康地成长,才得以愿意帮助他人,才得以一直相信父亲对自己的情感,才得以在读完母亲的信后,勇敢地挣脱童年的桎梏,去追求自己心中所爱。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本书还塑造了其他亲情关系,比如因觉得自己满足不了父亲期待而陷入自我怀疑的苏菲,因承担家庭责任而深埋儿时理想的吕克,因失去母亲而无法走出童年桎梏的伊凡,因儿女冷漠而喋喋不休的邻居老太太,他们都或多或少因亲情与家庭的缺憾而受到禁锢与创伤;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吕克父母在了解后的放手,克蕾儿父母对女儿梦想的倾力支持,以及父亲对“我”数年来的默默关注。不管子女还是父母,都应当尝试理解并包容对方,感恩彼此的付出。或许在亲情的羁绊里,每个人都不尽完美,但是包容与理解能够消融不完美带来的坚冰,带领家庭走向春暖花开的未来。
(二)友情——双向奔赴
在希腊语的概念中,友情(Philia)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爱,一种将朋友连结在一起的社会性纽带[4]。友情在人文关怀中的体现是多维度和深层次的。它不仅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普遍存在的情感关系,更是人文关怀精神的具体实践和社会关系的体现。友情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它的存续需要双方理解、包容、信任和支持,这些都是人文关怀的核心要素。
“我”有两位挚友——伊凡与吕克,与他们的相处总是给予“我”新的感受。伊凡作为长者,无论是“我”最初认定的“真命天女”与死对头在一起时,还是“我”深爱的母亲离世后,他都来到“我”身边,并且能够另辟蹊径地削弱“我”心中的难过,为“我”拨开眼前的薄雾。吕克作为与“我”一同长大的好兄弟,永远选择支持“我”,从看似毫无胜算的班长竞选,到“我”突发奇想的放风筝的愿望,再到听闻母亲去世时“我”在车站的情绪崩溃,吕克总是站在“我”的身边,成为“我”不变的拥趸与后盾。
友情的核心在于互信、互助、互尊和互爱,与亲情与爱情相同,友情也意味着双向奔赴。“我”通过影子得知伊凡的母亲早逝,他编造了一封并不存在的、来自母亲的信。伊凡撒谎了,但与其说他在欺骗“我”,倒不如说他是在自欺欺人。“我”不由得对此深深共情,决心帮助他摆脱桎梏。于是“我”让母亲以对刚出生的“我”的口吻写了一封信,又对信的外观炮制了一番,最后设法让伊凡读到了它。第一次感受到了母爱的伊凡终于决定辞职,离开学校,去找寻真实的自己,是爱让伊凡重获新生。数年后,同样在影子的推波助澜下,“我”促成了吕克对儿时理想的追求。“我”将他儿时的夙愿告知了他的父母,他们要求他离开面包店,去大城市寻找崭新的生活,作为朋友的“我”毫不犹豫地帮助并收留了他。虽然最后吕克选择回归过去的日子,但“我”也为他做出合乎自己心意的选择而开心。
“我”在伊凡离开后发出喟叹:“每次都一样,一部分的自我遗落在离开的人身上,就像爱情的忧愁,这是友谊的愁绪。千万不要跟别人产生牵绊,风险太大了。”[2]69这恰恰是作者的反语,因为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羁绊造就了情感的联结与对幸福的体验,即使彼此分离,美好的回忆也将在各自的心间永久留存,这是遗落的自我,亦是爱的痕迹。
(三)爱情——灵魂共振
爱情作为一种强烈的情感纽带,通常涉及两个人之间的深厚情感、亲密关系和相互承诺。爱情亦与人文关怀或人文主义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爱情关系中,人文主义的价值观体现为对伴侣的深刻理解和尊重,以及对双方个体性的庆祝和支持。
主人公一共与三位女孩发生过情感,首先是学校中的美丽女孩伊丽莎白,充满魅力的她与瘦小的主人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段单箭头的恋慕中,“我”无疑是自卑的。后来,即使“我”与她接吻,心中想的也只是战胜了与自己不和的马格。显然,他们二人间的关系并非爱情,而这也恰恰印证了伊凡的话,真命天女应该是给你带来幸福的人,而她不是。
第二位女孩是克蕾儿,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而是一位自闭症患者,这让她在年少时无法张口说话,人们常误认为她又聋又哑,但是在“我”眼中,她却是一个可以发出大提琴般音色、用风筝画出完美的“8”和“s”的特别女孩,“我”从未因她的不同而轻视她。事实上,相识之初“我”便发现了她的独特,亦着迷于她的魅力,“我”与她都有过孤独的经历,我们彼此吸引。她是与“我”最契合也是“我”真正喜欢的人,是“我”无可替代的真命天女。
在文学作品中,爱情经常被描绘为一种灵魂共振,一种超越肉体和物质层面的深刻情感联系。这种描绘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联是密切的,因为人文主义认为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尊严。当两个灵魂共振时,他们彼此认可并尊重对方的内在价值,这种认可超越了外在条件和社会地位的限制,“我”与克蕾儿之间的感情便恰恰是这样一种“灵魂共振”。
第三位闯入“我”生活的女孩是苏菲。她是“我”医学院的同学,对待工作认真负责,美丽又有趣,但“我”与她的关系却牢牢卡在“暧昧”与“爱情”之间动弹不得。“我”虽带她见了母亲,却并非想要与她进一步发展;即使同她待在一处,也总是心不在焉;唯一一次主动,却是危机感作祟。显然,这一切并非受爱情鼓舞,而是占有欲使然。最终,“我”与她回归了友情,这也是“我”和她之间最合适的关系。
作者眼中的爱情,既不是单方面、毫无希望的恋慕,也不是充满炫耀感与占有欲的偏执,而是只发生在两6742665fdfd5a4e983c871bcfc759f41d490054cc7623f619c09bb19d8581f30个人之间的纯粹感情,是独立人格间的共鸣,是独特灵魂间的共振。
二、心之所往——不懈探索的自我价值
人文关怀强调个体的价值、尊重和自我实现,它鼓励人们追求内心渴望,实现个人潜能,并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自我价值的探索与人生目标的实现是人文关怀的核心目标之一,而这往往也需要一个复杂且持续的过程。
好友吕克的人生追求在历经成长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年少时,他想要成为医生,但家庭的困难、父母的期待却让他无法将自己的想法宣之于口。成年后,他则继承父业学起了做面包,只为了家庭得到更好的保障。这一切看起来顺理成章,但是又好像不太对劲,仿佛他的追求永远是在考虑他人的需求,是在满足他人的期待。
“我”将吕克自小的“医生梦”告知了他的父亲,父亲最终决定支持他追求自己的理想,将他从面包店解雇,并送他来到“我”所在的医学院。吕克经历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医学院生活,那里充实、忙碌且疲惫,更需面对数不清的病患与生死。吕克最终选择向“我”坦白,他觉得自己的人生“缺少某样东西”,那便是“他的生活”,他曾说:“大城市让人抓狂,它榨干你的灵魂,又像吐口香糖般把它吐了出来。”[2]142他意识到,做出让品尝者露出满足表情的美味面包才是真正令自己幸福的事,是自己父亲“每天都在创造的奇迹”,与所爱家人一起经营的生活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唯有亲身经历,才能打破执念,领悟到自己真正的心之所向。对于吕克,家人与面包店就是自己的心之所向,做出美味的面包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在满足家人期待的同时,他又何尝不是在满足自己?
世人总是对体面的职业身份与更高的社会地位趋之若鹜,可幸福与满足感却并不总是与它们挂钩。在探索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尝试重视内心的感受,追求平静与满足,而不仅仅是物质与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回归家庭,或是承担责任,并非总是意味着退让与妥协,与家人共同生活也并不代表要牺牲自我,家人的期待亦可成为自己的追求。每个人的人生抉择都不尽相同,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尽可能做出不让自己后悔的选择,尽全力追求真正的自我价值。
三、思之所及——平等、尊重的生命思考
具有人文关怀的生命观是一种全面关注人的各个方面——身体、心理、情感和精神——的观念,它强调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拥有自己的情感、思想和追求,其生命本身及精神需求都应当受到尊重和理解。
作为医生,“我”见证了生命的种种变化。面对不愿进食的小男孩,“我”利用超能力,在不伤害孩子心灵的情况下寻找原因,只为孩子能得到及时的治疗。在面对受伤仍喋喋不休的邻居老人时,“我”尽可能满足她的要求,对她展现善意与尊重。即使在童年时期,“我”也没有对克蕾儿产生过任何偏见。虽然她心中不断强调着社会对残疾人的轻视,以及难以抑制的自卑与恐惧,“我”还是将她的不同视作独特的魅力,在误以为她听不见的情况下表白自己,释放自身的爱和善意。不管面对的是幼小或垂暮的身体,还是年轻或苍老的灵魂,“我”始终对生命保持着温和、尊重的态度,也始终愿意给予他人充满温情的人文关怀。这是“我”身为医务工作者的职业操守,亦是具有人文关怀的生命观的体现。
将人文关怀的概念向外扩展时,这种生命观就变得更加包容和全面。所有生命体都应被视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都有权在生态系统中生存和繁荣。这使人联想到文学中的“生态关怀”,它指作家通过审美的方式表达对人与自然的关心,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珍惜,对大自然和一切生命的尊重;也包括那些对生态和生命所强加的罪孽进行的嘲讽、谴责、道歉或是忏悔[5]。除开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作品还表达了对其他生命的敬畏之情与对破坏环境行为的批评。
小男孩绝食的原因,竟是想为被吃掉的兔子赔罪。父母或许难以理解,但是在孩童眼中,动物是拥有和人类同等地位的朋友,也值得被尊重和善待;而久处成人世界的父母却很难意识到,正是他们对生命展现出的无意的残忍,导致了孩子天真的反抗。“我”幼时的许多思考也体现了这一观点,如:“许多动物被迫迁徙或灭亡,只因为人类爱钱爱到失去理智,真的很恐怖!”[2]59。“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我们继续把地球剃到光溜溜的什么也不剩,就像一颗光滑的蛋一样,地球就不再流汗,也就再也没有云。想想看,一个没有云的世界会有什么后果,尤其对我来说!”[2]59在人文关怀的视角下,人类、动物、植物,直至整个自然中的生命都有其生存的权利,都应当受到敬畏和保护;人类的行为应当考虑到对环境的长期影响,以及对其他生物的福祉。
四、结束语
在《偷影子的人》这部作品中,我们见证了主人公在爱、追求与生命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刻探索。通过对情感的细腻描摹,以及对人生追求与生命观的探讨思考,马克·李维展现了人文关怀的力量,一种如何在个体的生活中激发出温暖和治愈的能量。这部小说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经历的颂歌,也是对人文关怀精神的深刻体现;不仅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更是一次关于如何以温柔和尊重对待生命、如何以爱和理解拥抱世界的深刻反思。它提醒我们在生活的每个角落中寻找意义,珍视每一种关系,尊重每一次生命的体验。
参考文献:
[1]邓颖,张璐,石梅芳.马克李维“温情三部曲”的美学世界[J].语文建设,2016(6):73-74.
[2][法]马克·李维.偷影子的人[M].段韵灵,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3]邹媛园,魏书堂.论青少年亲子关系中的人文关怀[J].商洛学院学报,2007(3):110-113.
[4]Coulibaly, A. Le Voleur d’ombres de Marc Lévy: un hymn à l’amour et à l’amitié[J]. Estudios Románicos, 2013(22):17-27.
[5]罗瑞宁.论文学的生态关怀[J].文艺理论研究,2010(3):28-31.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