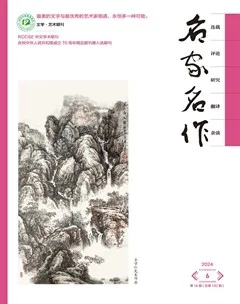背景惯例与具身应对:德雷福斯对海德格尔的借鉴与重构
2024-07-29高乐
[摘 要] 德雷福斯不仅是知名的人工智能哲学家,更是英美学界极具影响力的海德格尔阐释者,这两种身份看似孤立,实则统一在了他对传统哲学假定的批判以及对生存论的兴趣之中。在德雷福斯看来,人的认知与行为在背景与惯例中是具身和整体的。这一看法来自海德格尔,却又并不完全是海德格尔的本意。应当将德雷福斯的著作空间看作整体,其对智能策略的兴趣反诸对海德格尔的阐释,并最终导致他对海德格尔在人工智能时代下的重述与重构。
[关 键 词] 德雷福斯;《存在与时间》;背景惯例;具身应对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人工智能时代下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理论研究——从德雷弗斯的阐释、发展与应用切入”(项目编码:202210285066Z)的研究成果。
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作为现象学哲学家与人工智能哲学家的特殊地位与历史作用在当下已毋庸讳言,截至目前,国内学界已有成素梅(2013)、徐献军(2017)、徐英瑾(2021)、蔚来(2023)等多位学者就德雷福斯的技能获得模型、人工智能批判、具身性技能行动等观点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探讨,并就分析海德格尔式存在方式对认知科学与人工智能发展的影响及贡献给予了肯定,相关的综述文献和学位论文也在逐年增多。不过在众多的评价中,德雷福斯作为海德格尔阐释者的身份却没有得到过多的关注。那么,德雷福斯的海德格尔阐释与他的人工智能哲学存在怎样的关联?他的阐释中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接下来,本文试图以《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1990,下文简称《在世》)为中心,指出背景惯例(backgound pactice,或译作背景习惯)与具身应对(embodied coping,或译作涉身应对)在德雷福斯哲学思考与人工智能批判中的核心位置,并以此为据,说明德雷福斯对海德格尔思想资源的借鉴与重构。
一、此在之领会:《存在与时间》与背景惯例
在《在世》的前言部分,德雷福斯自述其之所以在20年的修订过程中始终如一地将笔记限于《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是因为他认为第一篇是这部著作中最原创和重要的章节,“因为正是在第一篇中,海德格尔发展了他对《在世》的阐述,并将之用作对传统存在论和认识论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①;在导论《为什么研究〈存在与时间〉》一文中,德雷福斯进一步开宗明义,指出海德格尔存在论清除了传统哲学的五个假定:清楚明白、心灵表象、理论整体主义、超然与客观性、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并将对此的强调遍布于《在世》全文,足可见德雷福斯对海德格尔之哲学史地位的维护和推崇,以及对所谓传统哲学假定的不满和否定。这一立场在文本中首先表现为他对作为“共享的日常技艺、辨别力和惯例——我们在其中社会化”(4)之背景的强调。
德雷福斯认为,生存是此在(这一术语被德雷福斯直接理解为人类,即human being)的存在方式,故此在之生存领会必然是具身化的,且总是深深地根植于社会背景之中。由于《存在与时间》中并没有社会背景将一种存在论具身化的例子,故德雷福斯引入了一组美国和日本养育婴儿之惯例的比较:美国母亲在照料的过程中总是激励婴儿做出行动和口头的反应,而日本母亲则做了许多安抚他、摇晃他的动作,试图通过身体而不是语言与婴儿交流,因此婴儿在学会说话之前就已经学会了成为一个安静自得的日本婴儿,或成为一个积极主动的美国婴儿。通过这个例子,德雷福斯指出“人类机体必须在某个时候通过突入人的可能性而对它自身采取一个姿态”(225),而对于所谓“可能性”和“姿态”的获得,都应当是社会惯例对人类机体的“突入”,并非仅仅是意向的、反思的或动物性的,正如婴儿在能够以人的方式进行应对活动之前,就已经通过模仿和经验的积累在集体之中被社会化了。在另一个例子中,德雷福斯认为,一个没有按时写完作业的美国学生,或许会通宵工作,或许会申请延期,或许会喝醉,或许会回家,但唯独不会剖腹自尽;这一方面是由于在美国学生的自身解释中,剖腹自尽并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美国这一常识背景和惯例世界中,并不存在剖腹自尽这一日本行为。
由此可知,对于德雷福斯而言,存在论不仅表象在个体心灵之中,还会通过社会与公共的背景惯例被施加以一种匿名的、普遍的教育行动,最终具身化为某些普遍性的反应、辨别力、运动技能。另外,在德雷福斯看来,这些尚未达到话语层次的实践状态本身已经意味着一种解释,就像有所应对的婴儿已经可以被视作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对意义有所领会和发明的此在了。
由此,德雷福斯对海德格尔核心观点“此在之领会”的重述乃至重构已初步得到彰显。对于德雷福斯而言,尽管背景实践具备前期海德格尔并不感兴趣的历史性维度,但活动首先且必然是一种惯例活动,所有排除或掩盖惯例背景的命题都将导致人们陷入从柏拉图到胡塞尔以来的对本质的纯粹直观这一被动的、超然的观看之中,并因而错失为所有视见奠基的生存论之领会。这一对背景惯例的强调在空间性中则表现为德雷福斯对公共空间的重视。在他看来,海德格尔不曾清楚地把公共空间与个人的栖居之所区分开来,而公共空间事实上不仅存在,还作为操劳的一个函数,“描述了生存所特有的空间类型”(155)。
二、此在之生存:《存在与时间》与具身应对
通过在上文中对背景惯例的关注,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在世》并非一本对《存在与时间》照本宣科的严格句读本,而是德雷福斯以“理解我们理解事物的能力”(12)为目标,在当代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的对立背景下对海德格尔诸论题在现象上的查验和辩护。不过尽管海德格尔说出了德雷福斯最感兴趣的内容,但却并非处处都那么令人满意。
在《存在与时间》中,生存着的此在并不必然是具身的,更不是在身体之中的,海德格尔甚至竭力避免他人将此在误解为是一个肉身:“‘在之中’意指此在的一种存在建构,它是一种生存论性质。但却不可由此来判断它是一个身体物(人体)在一个现成存在者。”①相较于其他研究者在“海德格尔哲学中是否有身体”这一问题上的迟疑或较真,德雷福斯毫不犹豫地将此在理解为具身化的,并纳入了他对于在世结构的全部分析中,正如他在背景惯例中对具身化之领会的强调那样。
在德雷福斯看来,类似于对上手之物的领会,此在的栖居与操劳并不是什么超然客观的科学认识,而是身体性的关心和投入;不存在完全脱离于身体的感受与认知。就在操劳活动中与此在共在的存在者而言,此在对其采取的姿态并不是什么内在的思想或体验,而是此在的行动方式,正如使得一个日本婴儿成为日本婴儿的并非婴儿的思想,而是他的行为以及事物对他显现的方式。这一对具身实践及因缘意蕴的强调首先体现在海德格尔对于上手事物(readiness-to-hand)和在手事物(presence-at-hand)的分析之中,面对用具这类存在者,我们并非首先“知道什么”(know-what),而是先“知道怎样”(know-how);我们总是先去使用它,并在使用中通达一种源始且实际的领会。同时,当我们本真地上手,用具总会有一种消失或隐退的倾向,正如当盲人纯熟地使用拐杖在公园里散步时,他不会意识到拐杖的存在,而只是享受清新的空气与鸟语花香的烂漫,甚或在温暖的阳光中心无旁骛地陶醉,以致遗忘了他自己。故而,恰恰是在用具(equipments)真正地被居有的时候,它实现了它通透的自在存在,又恰恰是此在在全力以赴的专注的身体中时,它实现了它通透的自在存在,拥有了不触目的和未被思考的实践性循视。
同时,此在的“定向”(oriented)、“去-远”(de-severance)等海德格尔生存论意义上的空间概念,也都先行地受具身化之寻视(circumspection)的引导,例如“左”与“右”并不是超然的概念或主观随意的假定,而根本在于人本身便是一个身体,所谓“前”“后”“左”“右”的空间概念,则完全是通过物体在身体的“前”“后”“左”“右”而获得的。因此,尽管海德格尔坚持认为身体不是根本,但他的生存论依然依赖身体的存在。另外,就现身情态而言,德雷福斯认为情绪并不是一种内在的心灵情感,而是一种影响(affect,或译作情动),既可指涉一个时代的情感、文化、脾性,亦可指个人的畏与烦,但在根本上,它们都是事物被遭遇到并紧要起来的可能性条件,并且正因为是具体的、遭遇的,所以必然是具身的。
由此可见,通过强调此在之存在与领会中的具身化结构,德雷福斯已在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与解释学中补上了身体的位置。在德雷福斯看来,海德格尔极有贡献地指出语言、空间、时间、用具等是人类已经在活动中上手和熟悉了的,就像知道了有关骑自行车的知识并不代表会骑自行车,而骑自行车的人也不必知道在骑车时肌肉和关节应该怎样活动、手臂和大腿又应怎样配合一样。但或许是为了避免再次落入传统哲学结构的循环,海德格尔排除了事实上在他的生存论中无处不在的身体现象。不过,尽管德雷福斯对于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具身化重构并不忠实于《存在与时间》原文,但考虑到当下学界对于海德格尔之身体描述的逐步重视,这一点或许不仅并不需要指摘,也可作为相关论说的借鉴和参考。
三、惯例与具身:《存在与时间》与人工智能
在为“斯坦福哲学百科”撰写的“海德格尔”(2011)词条中,惠勒(Michael Wheeler)共引用德雷福斯16次,其中有10次来自《在世》。作为自1968年起广受欢迎的“海德格尔抄本”(前言,vii),《在世》标志着德雷福斯在英美学界作为海德格尔阐释者的重要地位。然而,正如《在世》中随处可见的专家系统、计算机与信息处理方式所暗示的,相较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人工智能时代下人类的认知方式与智能策略才是德雷福斯的首要关切。正因此,《在世》牢牢抓住了此在非表征、非反思、情境化且总是已经在操劳中对存在有所领会的在世结构,并在与约翰·塞尔(J.R.Searle)《意向性》的持续对话中,将海德格尔重构为一位生存论的“认知学家”。由此,存在事实上是可理解性,此在是进行着活生生的自我解释活动的人,而领会是实践知识,是“我知道如何去处理我在做的事情,在每一个情境中我都能做恰当的事情”(223)。在这一意义上,《存在与时间》也被德雷福斯重述为一种对于智能和技术的批判。
在德雷福斯著名的人工智能批判作品《炼金术与人工智能》(1965)与1972年出版的三版《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中,他指出尽管人工智能假设在生物学、心理学、认知论、本体论层面犯了传统哲学已经持续了2500年的错误,但依然被纽厄尔(Allen Newll)和司马贺(Herbert Simon)等从事认知模拟与人工智能研究的专家奉为圭臬。有关这四个假设的概括与《在世》中对五次翻转的描述异曲同工,譬如心理学预设将人脑的“信息加工过程”看作是在技术和经验上自明的,计算机因而可以使用信息加工语言来模拟人的思维过程。然而德雷福斯指出,尽管这一“思维即计算”的假想可以被追溯到柏拉图、康德和休谟,但最终在现象学的工作上被证明为非,因为人并非计算着或遵循着规则的心灵表象,人对活动的解释与表达也并不等于人行动的规则;认识论预设退而求其次,仅将人的智能行为视作是规则化的,并试图将其形式化为计算机的程序。德雷福斯却同样指出其对物理学逻辑未经证实的滥用,认为有关能力的理论并非有关活动的理论。可见,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判与他对《存在与时间》的理解是统一的,即认为人类世界是按照技能性和具身性的活动生成起来的,指引人去思维和行动的并非概念、规则和理性,而是以惯例为背景的具身化需要。
事实上,若将《在世》与《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互参,二者在较大篇幅上的相似就可以直观地显现出来。在以身体、情境(situation)、需要(need)三者为支点对传统假设进行更换的过程中,背景惯例与涉身应对的思想资源更是随处可见。以模式识别为例,德雷福斯指出人类的模式识别应当是最基础的躯体智能行为,但恰恰是这样“低级”的动物性行为阻碍了“高级”的计算机理性对人类智能的模仿。这不仅是因为人是复杂的、处于情境之中的、在背景中预先勾画好了某些非确定性期望的躯体,而并非独立的灵魂,更在于“高级”的智能行为或许恰恰来自“低级”的形式并需要受其引导,且始终处于这一非形式的循环结构之中。
因此在德雷福斯看来,人工智能首先并不是一个工程和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人一定是一种可按规则对原子事实进行计算的装置。这种观点是由两股巨大的水流汇合而成的一股浪潮。这两股巨大的水流中,一是柏拉图把全部推理都规约成明晰的规则,二是发明了计算机,一种通用的信息加工装置”①。既然人工智能假设与传统形而上学假设是同一的,那么海德格尔关于清扫传统哲学假设的全部论述,便可借用为对人工智能与认知模拟的批判;同时,海德格尔关于人之存在特性的描述则为一种更加智能的“海德格尔式AI”提供了依据。
四、结束语
考虑到《在世》出版前长达20年的修订时间,以及在它出版前《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1972)已经掀起轩然大波,我们不难想到二者之间的相互指涉关系。经过上文以背景惯例与具身应对为参照点的观察,我们认为《在世》与《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事实上统一于德雷福斯对人类智能模式与生存处境的兴趣,而他后期的大众读物《万物闪耀》(2011)则将这一种对生存与技术“是什么”的关切转移到了技术时代人应“如何”的探讨之中。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注释:
①[美]休伯特·L.德雷福斯:《在世: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一篇》,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第1-2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以下只注明页码。
注释:
①[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63页。
注释:
①[美]休伯特·L.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