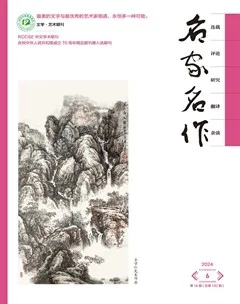从《生死场》看乡土中国
2024-07-29姚思凡
[摘 要] 《生死场》作为萧红创作的乡土小说的代表,文中处处充满了对于农村环境、人、物的描写,乡土气息浓厚,反映了当时新旧交替的中国乡村广阔的生活面貌。从萧红在《生死场》中对环境的描写,以及对动物和女性形象的刻画来看当时的乡土中国。
[关 键 词] 《生死场》;环境描写;动物;女性
在现代文学中,乡土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谓乡土小说指的是靠回忆来描写故乡乡村(包括城镇)的生活,带有很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1]。乡土小说主要以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乡土小说为代表,而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乡土小说向农村题材小说转变。农村题材的小说主要展现了在阶级压迫下,劳动人民的觉醒与反抗,偏向现实主义。萧红创作《生死场》正是处于乡土小说转向农村题材小说的转折期。小说真实地再现了东北一个偏僻小农村的生活状况,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作者在传统乡土小说的基础上开创了自己独特的乡土书写形式,不仅展现了20世纪20年代北方劳动人民所生活的乡土环境,而且更加关注农村女性。从乡土女性的悲惨命运深度思考人的存在处境,文章中也充满了对生与死的思考。“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2]已淋漓尽致地展现其中。
一、乡土气——环境
萧红笔下的乡土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小说从夏季开始,写了乡村春夏秋冬的变化。夏天的村庄是火热的,“全个村庄在火中窒息,午后的太阳权威着一切了”,“没有人想要出门,除了蝴蝶”[2];秋天的村庄是萧瑟而凄惨的,人们要为了过冬做储备,没有储备只能等死,“深秋秃叶的树,为了凄厉的风变,脱去灵魂一般吹啸着”[2];冬天的村庄裹上了厚重的大衣,“山上的雪被风吹得想要埋蔽这傍山的小房”[2];而春天的村庄是繁忙的、是甜美的,“田庄上绿色的世界里,人们洒着汗滴”[2]。
太阳与乡村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那个贫困的年代,人们凭借太阳来判断时间、安排农事。太阳也是小说中描写的重要意象之一,太阳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变化,在文中起到了渲染气氛、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麦场》中写道:村民在电闪雷鸣中忙乱,而雨却没有下。第二天早晨“东边一道长虹悬起来,感到湿的气味的云掠过人头,东边高粱上,太阳走在云后,那过于艳明,像红色的水晶,像红色的梦”[2]。人们的慌乱与太阳的随意自然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突出人们的着急忙慌是多么的荒诞,给人一种强烈的冲击感。《刑罚的日子》中,“房后的草堆上,温暖在那里蒸腾起了。全个农村跳跃着泛滥的阳光。……温暖的季节里,人们忙着生产”[2]。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道:“乡下人离开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3]。在农耕的日子里人们的心情是美好的,默默耕耘,期待收获。太阳驱散了冬季的阴霾,变得温暖起来。然而美好的日子并不长久,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生活便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传染病》中写道:“太阳血一般昏红;从朝至暮,蚊虫混同着蒙雾充塞天空。”[2]如血一般的太阳在文章开头便出现,为下文描写传染病的惨状渲染出沉重压抑的气氛。不仅是环境,一切好像都没有了生机,死气沉沉。太阳的升与落、灿烂与昏红随着村庄的兴衰和人们的心情而变化着。
萧红笔下的东北小村庄是一个幽闭的乡土环境。尽管村庄很贫困,甚至有时连活下去都是问题,却没有一个人想着要离开这里。“生于斯,长于斯”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扎根,土气也因不流动而产生。土气一方面是乡村所带有的泥土的气息,另一方面20b08dc92c67a9d268b17987ae4b813f是人的无知与愚昧。他们每天就是耕作、放羊,过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属于典型的中国农村。直到日本人侵略中国,才打破了村庄原有的平静。在不安与恐惧中,人们也开始另谋出路。男人们组建了“义勇军”去抵抗日本人的侵略,金枝作为女性离开了乡村,来到都市,体验到都市生存的艰辛,她逐渐从一个单纯的农村女性沦落成了为了赚钱而出卖身体的人,“羞恨又把她赶回来农村”。她的灵魂始终没有离开乡村。“我看哈尔滨还不如乡下好,乡下姊妹很和气。”[2]金枝还是属于乡村的,她想念她的母亲,怀念她的村庄。
二、乡土奴——动物
“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2]人与动物看似是两个对立的生物群落,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城市中的宠物不同,农村的动物很大程度上具有关乎生存的功利性商品价值,是农民的一种谋生手段,因此在乡村它们才算是真正成为主人实际生活的一部分。动物是农民们耕作的帮手,是他们谈心的对象,更是他们饿死前最后的救命稻草。
(一)二里半与山羊
小说以二里半一家找山羊拉开序幕。二里半在得知山羊失踪后,破口大骂偷羊的人,半青色的面孔变得更青了,喊着邻人一起四处寻羊。“二里半比别人叫出来更大声,那不像羊叫更像是牛叫。”[2]他急切地想要找到羊,仿佛羊就是他的生命一般。但是当找到羊以后,他又想要卖了羊,认为山羊让他丢尽了脸面,而且在找山羊的过程中丢了帽子,和别人还吵了一架,留下来不是好兆相。但由于深厚的感情,二里半还是没有卖掉山羊。到后来,当人们宣誓之后要杀羊时,二里半不知从什么地方找来一只公鸡,救下了山羊。老婆和孩子死在日本人手下之后,就只剩下二里半和山羊。二里半最终还是加入了“义勇军”的队伍,要为家人和祖国抵抗侵略,把山羊托付给了赵三,自己踏上了征途。“二里半不健全的腿颠跌着颠跌着,远了……羊声在遥远处伴着老赵三茫然的嘶鸣。”文章以山羊开头,以山羊结尾,首尾呼应。从山羊和二里半最后的分别中我们仿佛看到了福贵和老黄牛的影子,他们都是陪伴彼此到最后的家人,山羊已经成为二里半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老马与王婆
临近深秋,家里已是揭不开灶,为了交上地租,王婆只能把心爱的老马送去屠场。听到这个消息的老马眼睛湿润而模糊。一辈子为王婆家勤勤恳恳付出劳力,结果还是逃不掉被杀的命运。年轻时候的王婆无法体会到老马、老牛命运的悲凉,只有老的时候才真正有所体会。“被血痕所恐吓的老太婆好像自己踏在刑场了!”[2]王婆从老马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来:老了没有用处了,所有的价值在年轻时就已经被剥夺完。只留下一具躯体,都要被榨干,然后迎接死亡的到来。没有一点尊严,没有一点对生命的怜惜,只有不断的剥削和压迫。在麦场上沉默地拉石磙磨麦子是老马的活法,在屠马场里被扒皮是他的死法,这腥味的人间便是它的生死场,同时也是王婆的生死场。“她哭着回家,两只袖子完全湿透。那好像是送葬归来一般。”[2]离开屠场时的王婆好像不是之前那个麻木残忍的王婆,她展现了藏在心底柔软的善良。在那个年代,贫困的农民和做奴隶的老马的命运殊途同归。年轻的时候被黑暗的地主阶级所奴役,老了又被榨干最后的价值。“王婆半日的痛苦没有代价了!王婆一生的痛苦也没有代价了!”[2]“代价”的意义是为了某种目的所耗费的物质、精力,或所做出的牺牲。而王婆的痛苦是没有代价的,换句话说她的痛苦是没有来由的。被剥夺、压榨的一生是痛苦的,而这个痛苦是时代造成的,王婆不需要付出代价。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诗论》中曾指出:“使用隐喻是一种独运匠心的事,同时也是天才的标志,因为善于驾驭隐喻意味着能直观洞察事物间的相似性。”[4]当山羊和老马临死之际,二里半和王婆都表现出极大的不忍,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为这片黑土地默默耕耘的农民,这一刻人与动物在精神上达到了共鸣。温顺的山羊和老马也若隐若现着人性深处的温柔与善良。作者有意将人与动物进行同构与对照,将人性与动物性均匀分给人与动物,使他们共同“活着”。从人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动物性:男人们的兽性,女人们的奴性。动物又是人性的折射,老马心疼小马被打,于是代替小马去磨麦子体现着她的舐犊之情,这正是当时人们所缺失的慈爱与善良。
三、乡土囚——女性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阶段,虽然飘来了民主和科学的新消息,但是农村所感受到的思想解放力量是微乎其微的。处在地主阶级压迫之下的农民苦不堪言,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更甚。萧红本人曾说:“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痛苦的人生经历使她的文学创作呈现灰色的格调,在《生死场》中,萧红就以细腻的笔触对王婆、金枝、月英为代表的女性的婚姻、生育进行了描写,将黑土地上那群被压迫的女性推到大众的视野。她们被男人所奴隶,成为生育的工具、出气筒。饱受肉体和精神折磨的女性想逃却无法逃离,因为她们的思想早已被这片土地束缚。在表现女性的苦难命运的同时,萧红也对女性的生命价值和独立意识进行了探索,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对女性群体的关怀。
(一)母爱的隐藏
母爱本是女性身上与生俱来最伟大、最无私的情感,在《生死场》中却被藏了起来。男性把他们看作是生殖工具,践踏她们、辱骂她们。女性心里一直有着怒火,只能发泄在孩子身上,最典型的便是王婆。当小孩把小马牵到麦场里磨麦子却弄得麦子溅出场外时,王婆便责备孩子“总偷着把它拉上场……死啦去吧!别烦我吧!”[2]出于好心的孩子在她眼中连一粒麦子都不如,足以看出王婆对待孩子的冷酷和麻木。但是这并不是她自愿的,为了不被丈夫指责,她只能尽全力保证产量。王婆的第一个孩子小钟的惨死是令人痛心的:“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我一看到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也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可是,邻人的孩子却长起来了!……我又想起来我的小钟”[2]。孩子没有了,能不伤心吗?可是伤心又有什么用呢?地里的活还要干,不干就没有收成,没有收成死的就是自己。她也不是不想悲,只是不能悲也来不及悲。如果将自己的痛苦告诉丈夫收获的可能不是关心而是责备,自己的疏忽害死了孩子,她只能用不断的劳作来麻痹自己。当终于有了好的收成时,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在长大,这仿佛是一个开关一般,王婆又想起自己死去的孩子,内心的母爱也有所浮现。
女性受着社会和男人的压迫,她们所要顾虑的太多,以至于无法顾及自己的孩子。连失子之痛也都要封闭在自己的内心,不能表露。她们必须以坚强和冷静来武装自己,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她们是麻木冷酷的存在。但是他们何尝不是一个善良的母亲。
(二)独立意识的缺乏
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女人是靠男人活着的。萧红笔下的女性不仅受着阶级的剥削,还受到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以及落后文化习俗的扼杀。传承下来的老规矩规范着女性的言行举止,她们只能一直照着规矩而活,靠着男人而活。
她们嫁到男方家里便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劳作,“夙兴夜寐,靡有朝矣”。她们不仅要劳作还要传承香火。但是丈夫却不以为然,把她们当作是情欲发泄的对象和生育的工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说过:“女人是一个子宫、一个卵巢;她是雌的,这个词足以界定她。”[5]在《刑罚的日子》中写道:“大肚子的女人,任胀着肚皮,带着满身的冷水无言地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他的男人。”[2]她们十分在意丈夫,又害怕丈夫,她们以活成丈夫眼中的自己作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她们把丈夫神化,认为她们应该听从丈夫。造成女性独立意识缺乏的不仅仅是她们的丈夫,还有她们在家庭中的处境。《礼记·内则》里专门叙述妇女在家庭中的行为规范:“妇事舅姑,如事父母”“子妇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凡妇不命适私室,不敢退。妇将有事,大小必请于舅姑”[6]。在那个年代,女性在男方家里不仅要听命于丈夫,还要听命于公婆,侍奉公婆像侍奉父母一般,言听计从便是最好的选择。
但是女性的独立意识也并未完全磨灭,文章有几处地方若隐若现地体现了女性的独立意识,在王婆身上就得到了突出体现。首先,王婆在找羊的时候“她为着要作出一点奇迹,今后人要看重她”[2]。她想凭借自己的智慧找到羊,来向丈夫证明自己;王婆很早就意识到男人的不可靠,她不像金枝那样孩子被丈夫摔死了,还能麻木容忍。对于第一任丈夫的不满,她会选择离开。而这恰好也是作者萧红的一个映射,小说中所表现的独立意识也是她性格特点的体现。其次,王婆从朝夕劳作的生活中解脱出来。“她每天钓鱼。全家人的衣服她不补洗,她只每夜烧鱼,吃酒。”[2]也许正是因为经历过一次“死亡”之后,王婆对生活也释然了。她不再像之前那样日日操劳,开始放任自我。这也从另一侧面展现了女性的独立意识。此外,王婆与其他女性的区别还在于她关注社会大事、勇敢、有冒险精神。赵三和李青山在组织“镰刀会”反抗加地租时,村里其他女人都沉默了,而她却默默关注着这件事,甚至还帮他们弄来了一支枪,连男人都敬重她。
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女性必须遵守三纲五常。但是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萧红笔下的女性虽然绝大多数还是没有摆脱对婆家言听计从的命运,但是也有少数像王婆一样有着反抗意识、独立意识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在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萧红的影子:一个被封建制度束缚却不断挣扎想要逃出去的新女性形象。
四、结束语
幽闭的小村庄、奴性的动物、麻木的人性、饱受思想桎梏的女性,这些都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阴暗、封建文化的腐朽、封建思想的落后。这片土地是一个弥漫着血腥味的“生死场”,万物忙着生,忙着死。《生死场》所反映的乡土中国是20世纪20年代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当今社会还保留的乡土气的回溯。然而不仅是那个年代,直到现在这种乡土气也还保留着。人生就是一场忙着生、忙着死的谬剧,这是中国人对生死的观念,也是乡土性的一种体现,而这种生与死的谬剧还会继续上演。
参考文献:
[1]钱立群.中国现当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萧红. 生死场[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
[3]费孝通. 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4]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M].颜一,崔延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5]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6]戴圣.礼记[M].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