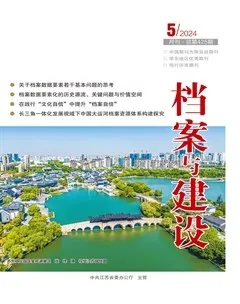世界记忆项目的价值旨趣、空间向度与中国话语
2024-07-29周林兴殷名
摘 要:《传承人类记忆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研究》是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世界记忆项目的教科书级著作。世界记忆项目的逻辑性、理念性与导向性,承载力、形塑力与建构力,以及中国作为参与者、支持者与领导者的独特视角和经验值得重点关注。
关键词:人类记忆遗产;世界记忆项目;文献遗产保护;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中国话语
分类号:G112
The Value Connotation, Spatial Dimension, and Chinese Discourse of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Concurrent Evaluation of Inherit Human Memory—Research on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Zhou Linxing, Yin Ming
( School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
Abstract: Inherit Human Memory—Research on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is the first textbook-level work in China to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Among them, the logical, conceptual, and directional nature of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as well as its carrying capacity, shaping power, and constructive power, as well as China’s unique perspective and experience as a participant, supporter, and leader,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Keywords: Human Memory;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me; Protection of Documentary Heritage; Archives Documentary Heritage Protection of China; Chinese Discourse
2023年10月7日至8日,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1]。不仅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于近年在多个重大国际场合阐明对全球文化、文明发展和交流互鉴的一系列中国立场、中国方案,强调“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交流互鉴,支持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共同守护好全人类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探究如何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暨世界珍贵记忆遗产是当前我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三大遗产旗舰项目”之一“世界记忆项目”的系统梳理和总结有助于发扬文献“记忆之场”价值、发掘文献“世界意义”,促进全球范围内文献遗产的保护、利用和传播,推动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提升文献遗产保护水平,助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1 价值旨趣:世界记忆项目的逻辑性、理念性与导向性
世界记忆项目聚焦“文献”这一视角独特、呈现度高、富含人文精神的记忆体,将浩如烟海的世界历史和文化以具象化的形态加以挖掘、保护和传播,构筑其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及情感价值,具有深刻的逻辑性、理念性与导向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塑造“跨越国家、民族、时代、媒介的宏伟记忆宫殿”[3]所擘画的壮美蓝图。
1.1 于“记忆之场”中探寻“世界意义”
文献被称作是一种“记忆之场”。诺拉在《记忆之场》中指出,“记忆之场”是记忆的有形化,它既封闭又开放,将记忆锁在最小空间中,实现“主体—记忆—场所”的记忆有形转向。[4]换言之,“记忆”是当下的、具象的、活着的、情感的现象,“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的、功能的符号。在此语境下,文献作为一种“作为记录的记忆”[5],以“被历史纠缠的记忆形态”[6]成为人们从历史中寻找记忆的切入点,是典型的“记忆之场”。这里的文献并不单指文书实体,而是“文献记录以及集体记忆”[7],涉及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对象、物态和精神态的双重空间。此种作为“记忆之场”的特殊性质使得文献在不同场景中具有不同表现,指向不同的意义及其再造场域。基于此认知,世界记忆项目将文献遗产作为研究对象,以文献遗产保存、获取和传播为基本任务,以“记忆”和“意义”的相互导向为深层逻辑,探寻文献遗产这一“记忆之场”的“世界意义(World Significance)”[8]。具体而言,自1997年世界记忆项目核心成果《世界记忆名录》进行评审以来,以时间、空间、形态与价值四个维度作为鉴定视角,已然汇拢了一大批反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文化的珍贵记忆文献。这些记忆文献因其深厚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而具有“独特性或稀有性”[9],又同时具有“世界意义”这一核心要义,不分主流支流、中心边缘,共同巩固世界各国人民的集体记忆,描绘人类社会思想的演变、发现和成就。对“世界意义”的追寻进一步强调了世界记忆项目“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的根本理念、“促进文献遗产保护获取”的首要目标,以及“找寻逝去的记忆”的人文呼唤。[10]
1.2 于“共同遗产”中明确实践方针
世界记忆项目是延续并发扬“共同遗产(Common Heritage)”理念的最新实践。在其纲领性文件《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方针》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强调世界记忆项目的愿景是“世界文献遗产属于所有人,应为所有人充分保护,并在尊重不同地区文化习惯与实践方式的前提下,推动文献遗产无限制、永久可获取”[11],体现了“共同遗产”这一核心理念。针对此理念,《传承人类记忆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研究》(以下简称《传承人类记忆遗产》)一书作出了详细的概念阐释。[12]第一,全人类共同拥有世界记忆遗产,尽管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有国别之分,但其价值属于全人类。第二,全人类要用最合适的技术共同保护世界记忆遗产,保护全世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文献遗产,同时加强国际合作和跨界合作。第三,保障每个人获得文献遗产的权利,促使文献遗产被广泛获取,以文献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世界记忆项目遵循“共同遗产”理念,不仅强调文献遗产属于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突出文献遗产的“世界意义”,而且将全世界共同享有、共同建设作为实践方针。此书提到,教科文组织一方面识别世界记忆遗产的公共性,确保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遗产可为公众所利用,并鼓励世界记忆遗产相关研究工作,助推多元文化认同与教育;另一方面采取分级管理、广泛参与、共同申报、联合公众的实践方式,建立记忆遗产分级管理体系以识别多层集体记忆,确保《世界记忆名录》专家评审的广泛参与性,鼓励跨国、跨区域的联合申报并积极发动社会力量与民间组织的参与。[13]截至目前,世界记忆项目已制定系列规范性文件,举办大量活动,推动“数字形式”文献遗产保护,并针对一大批高价值文献进行识别、保护和传播,其中《世界记忆名录》收录了来自126个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432份文献。
1.3 “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
“于人之思想中构建和平(building peace in the minds of peopl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目的,是其所有工作的基本理念,也是世界记忆项目的根本目标。这里的“和平”并非物质层面上的消除战争,而是精神层面上“人人都享有充分而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不受限制地追求客观真理,自由交流思想与知识”[ 14]。这是一种植根于个人和集体意识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强调了教育、文化和对话在建立长期和平过程中的关键作用,意味着可以通过个体和集体思想意识的培养来形成更加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世界。冯惠玲在《传承人类记忆遗产》的序言中指出,世界记忆项目正是以推动各国文献遗产的共建共享为途径,打通不同文明的共存、交流与相互理解之路,进而打下人类和平的文化根基,实现助力世界和平的宏伟愿景。[15]世界记忆项目以“开放获取”为核心做法,将所有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文献遗产及相关信息公布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世界各国人民均可自由获取这些真实反映不同主体、不同文化历史发展的立体记忆。同时,世界记忆项目关注不发达国家和边缘人群,给予落后地区更多保护援助,助力这些地区本土文化的开发、保护和传播,重视和保障不发达地区公众的文化权利,甚至由此带动了援助地区的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不仅如此,世界记忆项目还将文献遗产作为文明交流的手段,引导不同国家、民族、文明以文献遗产为纽带,通过联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合办展览和研讨会、共同参与研究项目等方式合作交流、相互借鉴。正如此书所言,“实现文献遗产无障碍获取、为不发达地区提供援助、推动文明间的交流互鉴等措施致力于促进世界文献遗产的无差别保护与利用,构建更加多元、繁荣的世界文化”[16]。
2 空间向度:世界记忆项目的承载力、形塑力与建构力
阿莱达·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跳出时间向度的束缚,转向空间向度对文化记忆进行立体化审视,认为空间向度为文化提供承载力、形塑力与建构力。纵览《传承人类记忆遗产》一书,其也从空间向度出发,描述世界记忆项目的组织机构、政策体系和参与国别,突出世界记忆项目的承载力、形塑力与建构力,强调记忆的关联性和连续性,呈现世界记忆项目的多维关照。
2.1 “国际—区域—国家”三级管理体制
《传承人类记忆遗产》深度阐述了世界记忆项目自1995年确立实施的“国际—区域—国家”三级管理体制,并对各层级机构的形成发展、机构组成、职能特征、运行现状等进行了细致梳理和分析总结,这是世界记忆项目承载力的来源。[17]国际层面,依靠国际咨询委员会的主导,世界记忆项目秘书处为国际咨询委员会及其下属机构提供支持,已然成为世界记忆项目相关事务默认前线联络点,负责项目日常管理。区域层面,世界记忆项目已成立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非洲地区3个地区委员会。地区委员会集自愿性、互助性、合作性为一体,推进地区世界记忆项目建设,并提供平台以供地区内部国家间的合作交流。国家层面,世界记忆项目通过在各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国家委员会或等同的实体组织推进项目工作,现已有89个国家和地区成立国家委员会,世界记忆项目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由此,以《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方针》为指导,“国际—区域—国家”三级管理体制具有统一指导、开放多元、因地制宜、相对独立等特点,能够发挥各级自主权,充分调动各级机构的积极性,构建开放包容、专家主导、政治中立的评选机制。设立“国际—区域—国家”三级记忆名录评选体制并以之构成世界记忆名录体系,已然助推世界记忆项目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文献遗产项目。然而,通过梳理和比较,此书提到世界记忆项目地区委员会和国家委员会均存在发展建设不平衡的问题。[18]国家委员会总体覆盖率只有37.77%,且存在受西方权威遗产话语体系影响,各国建设程度、文化遗产可视度、认知度和保护水平参差甚至两极化明显等问题,世界记忆项目的全球推进道阻且长。
2.2 “纲领—专题—成果”多层政策体系
《传承人类记忆遗产》系统梳理了世界记忆项目相关的11部政策法规性文件的内容,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文献遗产管理和组织机构管理两个层面对文献遗产保护工作做出规范,将文件分为纲领、组织机制、保护数字遗产、成果性文件和其他五个类别,并归纳政策关系,这是世界记忆项目形塑力的体现。[19]在教科文组织文献遗产保护政策体系中,《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方针》是核心纲领和政策基石,围绕该纲领,其他政策文件分别为针对其数字遗产、开放获取、数字化方面的补充,以及对于其部分章节内容的展开表述,形成了“纲领—专题—成果”的多层政策体系架构,为世界文献遗产保护搭建了工作框架,奠定了政策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记忆项目曾因政治力量的介入而遭受重创,政策方向也因此调整。日本数次企图通过政治手段影响《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并在该项遗产成功入选后否认史料真实性、批判该申遗项目[20],甚至采取外交手段封锁该项入选遗产、进行撤资威胁[21]。2017年至2021年,受日益激烈的国家冲突影响,世界记忆项目接近停摆。经过全面审查和改革,世界记忆项目于2021年底再度回归,并公布新版本《保护文献遗产的总方针》(以下简称《总方针》)。通过比对,王玉珏团队研究指出,2021年版《总方针》将世界记忆项目治理机制由“专家导向”调整为“专家政府混合治理”模式,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代替总干事成为世界记忆项目的最终决策机构,同时从对执政党相关资料的申报进行限制、增加文献遗产保管单位和有关组织的申报权利、要求政府履行对文献遗产保护的义务(包括制定保护计划、维护保护成效等)等方面入手,试图确保世界记忆项目远离政治纠纷、持续平稳发展。[22]现有的多层政策体系使世界记忆项目以审慎的处事态度与安全的保全策略寻求专业性与政治性之间的平衡,如何避免政治化倾向,在鼓励“成员国参与”的同时作出“专业判断”,在纲领性政策的带领下推动专题性和成果性政策文件的实践,发挥世界记忆项目在文献遗产的开发、研究、教育等更多方向的引领作用成为难点。
2.3 “发掘—宣传—合作”多元发展模态
《传承人类记忆遗产》全面展现了世界记忆项目五大地区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并于各地区选取代表性国家作为案例,探求其发展特征与趋势,这是世界记忆项目建构力的落实。[23]欧美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缘优势、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高度发展的文化事业和良好的经济支撑成为参与和推进世界记忆项目的主力军,拥有占总数比52%的《世界记忆名录》文献遗产,呈现出政策环境良好、参与机构多样、国际合作密切、保护体系健全等特点。亚太地区、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因内部国家众多,历史发展、政治形态、语言文化、经济发展差异明显,采取以地区委员会为纽带,持续推进国家委员会建设,完善世界记忆项目第三级管理体系的方式协调并鼓励国家文献遗产保护工作,以不断提升的文献遗产保护意识和极大的工作热情制定实施工作方案,展开了系列特色项目和活动。不仅如此,两地区还关注社会公众对文献遗产保护的认同和参与,以网络化建设和国际交流合作积极推进世界记忆项目宣传。非洲地区和阿拉伯地区则因各类客观因素影响,对世界记忆项目的整体推进缓慢,但两地区悠久的历史文明、独特的地域文化、多元的领域建设极大丰富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因此,两地区注重各国多元文化保护,以共同历史为基础积极进行国际合作,立足本国发展的关切问题展开宗教信仰、战争地区等特别文献遗产的保护,大力推进《世界记忆名录》的申报,加强文献遗产保护能力建设。可以看出,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世界记忆项目在各大地区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已然形成了“发掘—宣传—合作”的多元发展模态,即挖掘本土特色文献遗产资源、推进世界记忆项目推广宣传、加强国际和区域间交流合作,通过保护本地区、本国的文化多样性,建立各民族文化基因库,强化各民族文化认同感和传承感,形成主流支流均衡、中心边缘并重的世界文化多维呈现。
3 中国话语:世界记忆项目的参与者、支持者与领导者
我国于1996年成立世界记忆项目中国国家委员会,此后,在理论与实践领域均有深入的发展,已然凝聚成了享誉世界的中国姿态、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不断提升。[24]
3.1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力度不断攀升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在国际、地区、国家、地方各层级全面开花,发展态势蓬勃。[25]国际层面,自中国传统音乐录音档案1997年入选首批《世界记忆名录》以来,我国至今已有13项文献遗产成功入选,在数量上位列全球第8,亚太地区第2。从甲骨文、《黄帝内经》到《南京大屠杀档案》,从纸张、音像到甲骨、丝绸,从政治、文学领域到民族特色,中国以厚重的历史文脉和沧桑的民族赓续赢得了世界的瞩目。地区层面,中国已有12项文献遗产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占比超过总数的20%。国家层面,我国于2000年启动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建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是世界上最早建立世界记忆项目国家名录的国家。至2023年,国家档案局共完成了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申报和评选工作,共计198项珍贵档案文献入选,地域分布广泛、载体形式多样。[26]地方层面,浙江、江苏、云南、福建等11个省级行政区先后颁布了省级档案文献遗产评选办法并出台地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实现地方文献遗产资源的集中整合和呈现。不仅如此,中国还成功开展了以专题为单位进行集约化建设和推广的中国记忆项目,以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特别是文献遗产为目的的“城市记忆工程”,以挽救档案文献、历史建筑、方言乡音为落点的“乡村记忆工程”等多项记忆项目。综上可见,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意识持续提升、力度不断加大、体系逐渐形成、研究步步深入,受到官方和民间、科研和实践领域的多重重视。“申遗”工作各级参与、如火如荼,已涌现出大批理论成就和实践成果,相关建设和研究覆盖面广、内容丰富、传播范围大、知名度提升,我国正向文献遗产保护高质量纵深发展迈进。[27]
3.2 世界记忆项目学术中心热度持续高涨
目前,全球共有7家世界记忆项目学术中心,其中澳门(世界首家)、北京、福州、苏州4家位于中国。各学术中心自成立以来便立足国内、着眼全球,在学术交流、宣传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同时打造精品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学术交流方面,中国的学术中心单独或联合举办了多项世界级学术会议,同时设立了多个交流基地,聚焦国内外文献遗产保护工作实效,如澳门学术中心参与主办古典今耀──功德林文献遗产与女性地位国际学术研讨会,福州学术中心设有“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福建侨批展示基地”等。宣传教育方面,打造了多个线上线下展厅,并开展主题竞赛和校园活动,如福州学术中心开展的“百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档案”展先后在美国、日本等国家近20个城市巡回展出,北京学术中心主办“世界记忆·中国文献遗产创意竞赛”,苏州学术中心开展世界记忆项目进校园活动等。人才培养方面,中国的学术中心积极培养文献遗产保护领域的专业化、国际化人才,如北京学术中心开展“数字记忆”厚重人才成长支持计划等。不仅如此,苏州学术中心还打造了“第七档案室”创新IP,已有互动解谜书《第七档案室》、互动密室第七档案室之“漳缎疑云”、互动剧本杀《第七档案室:查无此人》、实景解谜活动“第七档案室之追踪者的倒计时”、“第七档案室之迷途者”、“东观梦”行进式实景演绎推理活动等多个“年轻化”活动,引发不小的“档案热”。中国的学术中心“出圈”的背后是对世界记忆项目的深化和活化,在为世界记忆项目和文献遗产保护领域学术研究和交流提供平台的同时,扩大了世界记忆项目在中国的知名度和关注度,也将中国记忆推向世界各地。
3.3 全球文献遗产合作引领风度逐渐凸显
自世界记忆项目开展以来,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参与项目建设,与项目共同发展进步,一齐探索全球文献遗产工作正确发展方向,在合作中展现了引领姿态和大国风度。一是资金投入力度大。中国是193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中最大的常规预算缴款国,2019年占世界总额的15.5%,遥遥领先于第二大缴款国(日本占比11%)。二是人力资源参与深。2001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档案处处长朱福强(Simon CHU)当选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专家,2003年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档案处助理蔡长青(音译)(Cheung-Ching CHOY)成为观察员。2011年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李明华等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第10次会议。2014年,李明华当选世界记忆项目亚太地区委员会主席。近年来,国家档案局一直积极向世界记忆项目国际咨询委员会、秘书处推荐专家和工作人员,向“直指奖”推荐候选人。[28]三是政策修订落实强。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记忆项目的规则修订,推动并广泛实施《关于保存和获取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文献遗产的建议书》中的相关决议,并于2019年向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提交了执行情况报告。四是申遗项目实效高。在《世界记忆名录》《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世界记忆项目学术中心”申报和建设中都取得了突出成就。五是合作交流主导牢。如中国于2016年联合韩国及相关国家、地区的民间组织申报“‘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于2017年联合葡萄牙申报“清代澳门地方衙门档案(1693—1886)” [29]。六是宣传推介范围广。《本草纲目》、“清代样式雷图档”等多项文献遗产亮相国际世界记忆项目展览,侨批档案、丝绸之路相关主题于多国巡回展出,国内项目资讯宣传全覆盖,学术界形成多维度研究业态,在公众中形成大基数认知模态。[30]综上所述,中国是评估、保护、获取、改善和宣传包括数字遗产在内的世界文献遗产的领导者之一,是世界记忆项目的中坚力量,在实践过程中向世界展现中国力量。
4 结 语
《传承人类记忆遗产》是我国首次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进行的整体系统研究,其中既有全局观照,又有专题切入,纵深结合,全方位多维度地呈现了世界记忆项目全景。在未来,中国将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做好文献遗产资源挖掘整合,探寻国内文献遗产的世界意义,以更丰厚的资源储备参与《世界记忆名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建设,深度建设中国世界记忆项目学术中心和论坛,以专项资金抢救、保护、使用以及数字化文献遗产,积极组织开展国际合作交流和相关宣传,为世界记忆项目给出中国方案、作出中国实践、传递中国声音,引领世界记忆项目正向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添砖加瓦、踵事增华。
作者贡献说明
周林兴:论文选题、框架设计与修改;殷名:文稿撰写和修改。
注释与参考文献
[1]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OL].[2023-12-20]. http://www.qstheory.cn/ yaowen/2023-10/08/c_1129904934.htm.
[2]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EB/ OL].[2023-12-20]. http://www.xinhuanet.com/ politics/leaders/2021-07/16/c_1127663629.htm.
[3][15] 冯惠玲.穿透记忆的意义[J].档案与建设,2021(11):10-11.
[4][5]诺拉.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M].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20-29,66-67.
[6]科利.记忆,历史,遗忘[M].李彦岑,陈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12-13.
[7][9]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General guidelines to safeguard documentary heritage(1995)[EB/OL].[2023-12-20]. https://unesdoc. unesco.org/ark: /48223/pf0000105132.
[8] 王玉珏,朱娅,辛子倩.“世界意义”标准视角下的中国文献遗产申遗策略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3(4):124-134.
[10][12][13][16][17][18][19][23][24][25]卜鉴民,王玉珏.传承人类记忆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1:9-20,72-75,75-82,12,83-120,114-120,121-144,181-254,5-10,257-260.
[11][14]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Companion [EB/OL].[2023-12-20]. https:// en.unesco.org/sites/default/files/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companion en.pdf.
[20] 签原十九司,芦鹏.日本政府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居心暴露于世——关于《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问题[J].日本侵华史研究,2017(1):126-133,139.
[21]日本拒缴会费彰显其不愿正视历史[EB/ OL].[2023-12-20].http:/www.mod.gov.cn/ imsd/2016-10/21/content 4750495.htm.
[22]王玉珏,施玥馨,严予伶.全球文献遗产保护政策“风向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总方针》(2021)研究[J].档案与建设,2022(1):19-24.
[26]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出炉[EB/ OL].[2023-12-20]. https://www.saac.gov.cn/daj/ya ow/202301/87201eba75f94156ac9bdb6c1bdaca3b.shtml.
[27]卜鉴民.世界记忆项目在中国[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9:1.
[28]李文栋,刘双成.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深化对外合作交流——党的十八大以来档案外事工作稳中有进[N].中国档案报,2017-09-18(01).
[29]周玉萱,王玉珏.世界记忆项目的中国参与和贡献[J].中国档案,2021(11):74-76.
[30]宋飞.数字人文档案与国家记忆工程的相互关系与作用研究[J].档案管理,2024(1):65-68.
(责任编辑:张 帆 陈 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