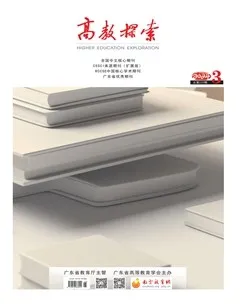美国博士生教育:国家战略、资助制度与改革动向
2024-07-09孟卫青吴开俊陈鸣敏唐婷
孟卫青 吴开俊 陈鸣敏 唐婷



摘要:美国博士生教育是世界上培养年轻一代研究者和大学教师的典范模式之一。博士生教育是美国学术研究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教育和研究相结合,美国将博士生教育成功纳入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体系中,服务于国家目标和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为保障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联邦政府和大学密切合作,建立了强有力的资助体系,尤其是经济资助和学术训练一体化、践行财政公平和体现学科差异。
关键词:美国博士生教育;国家战略;资助制度
在知识和创新驱动的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中,各国政府普遍意识到博士生教育,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性。处于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端,当代博士生教育不仅恪守“为学术工作而训练”的传统目的,更是被纳入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体系中,服务于经济繁荣、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等目标。美国博士生教育具有一百余年历史,被誉为“一个成功的且富有创造力的体系”[1],“代表了世界领先的培养年轻一代研究者、大学教师的成功模式。它是美国强大的核心力量之一,也被世界其它学术机构效仿”[2]。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和博士生教育在保持国家繁荣、健康和安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本研究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型博士生教育为研究对象,分析博士生教育在美国国家战略中的贡献和地位,以及联邦政府-大学为确保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提供的强有力的资助机制,并探讨了美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的三大挑战及改革动向。
一、美国博士生教育: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与美国经济体系的强大具有历史的一致性。1861年,耶鲁大学授予美国历史上首批三个哲学博士学位,自1870年以来,美国就创建并保持着一个强大和富有活力的经济体系。一百多年来,在为美国人提供高质量生活,实现卫生健康、安全和经济繁荣的国家目标上,教育、研究、新思想和技术创新扮演着核心角色。尤其是“二战”后联邦政府-大学形成了独特而密切的合作关系,建立了教育和研究高度一体化的博士生培养体系,有效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
第一,博士生是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一支力量,是美国研究和开发(R&D)及人力资源的重要构成。在知识和创新驱动的经济体系中,R&D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因素,R&D投入经费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二战前,除了在农业和公共健康领域外,联邦政府、研究型大学及其博士生教育在美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中只发挥很小的作用,工业部门主导了R&D活动及投资。战争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重塑了R&D结构中联邦政府-大学的关系及各自角色。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克拉克·克尔所称的“研究型大学获得了美国联邦政府投入的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经费”[3]。1958-1968年的十年间,美国学术性R&D经费增长了417%,学术研究开支增长587%,联邦政府资助的学术型R&D增长618%,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增长702%。[4]这直接刺激了研究型大学及其博士生教育项目的激增。这十年是美国博士生教育规模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博士学位授予人数从1958年的8873人增长到1968年的22937人,十年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12%,达到60年间(1958-2019年)的最高水平(图1)。
在联邦政府经费支持的大学R&D活动中,博士生是一支非常重要的科研力量。“美国的博士教育与学术研究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博士生更是研究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5]联邦政府一是通过助研机制引导在校博士生参与导师、大学的研究项目,二是通过奖助学金、论文资助机制,鼓励博士生将学习尤其是论文研究与国家战略结合起来。根据2019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调查(Survey of Earned Doctorate,简称SED),助研金是博士生第一大资助来源,占资助金总额的33.4%;第二大资助来源是奖助学金和论文资助(24.8%),二者合计达到58.2%,在整个资助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图2)。毕业之后,博士学位获得者从事R&D活动的比例也很高。2019年,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共55703人,从就业部门看,学术领域占43.4%,工业部门占36.5%;在主要活动类型上,总体上从事R&D的比例高达44.9%,尤其是工程领域和基础自然科学领域更高,工程领域达71.4%、物理和地球科学有65.8%、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占68.4%(表1)。
第二,博士生教育是培养美国精英人才的摇篮,承担着为美国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培养顶尖的教师、学者和科学家的使命,以确保美国在科学、技术和学术上的领导地位。“确保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是美国联邦政府科学和技术预算政策的首要原则。早在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在《科学、技术和联邦政府:新时代的国家目标》报告中,提出了联邦政府科学和技术投资的两个国家目标:第一,在所有主要的科学领域中,美国应该居于世界领导行列;第二,根据美国的国家目标和其它非研究的标准,遴选一些科学领域,确保美国在这些领域中处于非常清晰的世界领导地位。[6]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和博士生教育被认为是美国保持创新活力、竞争力,乃至全球领导力的核心力量之一(heartbeat)。“100多年来,研究型大学通过研究和博士生教育促进美国的创新和繁荣。美国要有能力继续领导全世界进入21世纪的发展中……美国的博士生教育要和研究结合起来,研究活动整体上要与国家的学术地位、经济生产力和世界领导地位紧密结合。”[7]在这些政策刺激下,博士生成为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研究、教学人力资源的核心后备力量。1999-2019年的20年间,博士生毕业后在学术领域就职的比例较高,一直在50%左右,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生命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术性就职高于工程、物理和地球科学领域(表2)。从活动类型看,教学和R&D活动是主要的就业方向,前文表1数据显示,2019年两者合计达到75.2%。此外,博士后研究也是博士学位获得者很重要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1999-2019年,博士生就业比例从1999年的69.8%下降到2019年的61.6%,而同期博士后研究的比例从1999年的30.1%增长到2019年的38.4%。
第三,博士生教育保持精英规模且呈现学科差异,服务于美国在健康、能源、环境和安全领域的国家目标。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博士生教育一直保持精英教育模式,其规模呈现震荡上行、缓慢增大的特点。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博士生教育的“黄金时期”,1961年美国博士学位授予人数首次破万,达到10413人,1971年达到31867人,这11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4%。这个时期博士生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主要原因是联邦政府支持的大学R&D项目和经费激增,大学需要大量的低成本的学术劳动力,并试图通过实施博士学位计划获取研究型大学的地位和提高学校声望。[8]即使算上20世纪60年代的“黄金时期”,从长时段来看(1959-2019年),六十年间美国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年均增长率只有3.23%;尤其是2000-2019年间,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6%。虽然博士生教育总体规模增长缓慢,但呈现明显学科差异,增幅最大的前三个学科依次是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生命科学、工程学科,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博士学位授予规模增长约20%,物理和地球科学、人文和艺术领域的总体规模相对稳定,而教育学科呈现下降趋势(图3)。2008-2017年,STEM领域博士学位获得者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从2008年的23654人(占当年全部48776人的48.5%)增长到2017年的29459人(占全部54554人的54%),10年内增长了24.5%,远高于整体增幅11.8%的水平(图4)。
二、美国博士生教育:经济资助和教育目标、学术训练紧密结合美国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得益于联邦政府-大学的合作关系,尤其是联邦政府强有力的资助体系。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是一项成本高昂、耗时较长的教育投资决策。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四所研究型大学为例,根据学校官网资料,博士生学费基本在4万-5万美元/学年,生活开支评估相当于学费的60%以上,全学年学费与生活基本开支在7万美元左右,而且学费逐年攀升。2019年,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49763美元。[9]博士生学习、生活总成本明显高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在高学费背景下,强有力的资助制度是保证博士生教育吸引力的关键因素。早在1957年,美国《国防教育法》从国家安全的高度,首次确立了联邦政府资助博士生教育的法律基础。自此,联邦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和博士生资助计划,引导顶尖人才投入到国家战略产业中。2012年,美国大学协会向国会提交《研究型大学和美国的未来:美国繁荣和安全的十大突破性举措》报告,向国会和联邦政府提出十项优先行动事项,首要一条是“在国家创新、R&D战略中,联邦政府应该对研究型大学的R&D活动和博士生教育提供稳定的、有效的政策、实践和经费支持。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获得促使美国持续强大的新知识和精英人才,才能实现卫生、能源和安全的国家目标,确保美国的持续繁荣和安全”[10]。总体来看,联邦政府的博士生资助计划立足于“确保美国在科学领域,尤其是一些关键科学领域的世界领导地位”目标,建立了经济资助和博士生教育目标、学术训练密切结合的资助模式,为博士生教育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固的经济基础。
(一)坚持财政公平理念下的保障和普惠原则,建立有力的需求型资助机制
从资助目标上看,博士生资助可以分为两类:需求型资助和绩效型资助。需求型资助(need-based aid)是基于博士生身份实施的普遍性资助,主要目的是满足博士生的学费支出和生活支出需求,体现经济保障功能和财政公平理念。绩效型资助(merit-based aid)主要从财政效率出发,根据博士生的科研投入、学术成就和科研潜能等表现提供资助,目的在于引导和激发博士生从事高水平的研究活动。在学费和生活费不断增长的背景下,联邦政府、大学、私人基金会等各种资助来源共同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资助体系,这一资助体系的首要原则就是财政公平,尤其是横向公平,资助资源分配呈现普惠性格局,且资助力度大。自1999年以来,博士生获得各类资助的覆盖面一直在90%左右。其中,无偿性资助形式覆盖面高达60%-70%,助研和助教的资助比例在2011-2012年最高,达到62.2%(表3)。从资助水平看,居民可支配收入是美国博士生资助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学术型博士生所获得的各类资助的平均额度(不含教育贷款)占美国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0%-90%。如果加上各类教育贷款,博士生所获得的经济资助额度明显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
(二)在资助机制上,服务型的助研、助教占主导,经济资助和学术训练一体
按照资助性质,博士生资助有三种类型:一是赠与型或者非服务性资助(Non-Service),主要形式有研究资助金(fellowship)、奖学金(scholarship)、助学金(grant)、论文资助和学费减免(tuition waiver);二是报酬型或服务性资助(Service Assistant ships),包括助教金(TA)、助研金(RA),以及勤工助学(work-study)雇主支付的各种劳务报酬;三是偿还型资助,包括联邦政府教育贷款和商业/私人贷款。1998-2018年,美国博士生资助的主要机制是助研、助教,这两类资助金的比例一直稳居45%左右,其它资助来源合计约占55%(图5)。具体来看,助研金是第一资助来源,且该项资助所占的比重也逐年上升,从1998年的26.5%上升到2018年的33%;第二大来源是无偿型的奖助学金和论文资助,从1998年的16.3%上升到2018年的25.3%;第三大资助来源是助教金,它所占的份额从1998年的17.8%上升到2018年的21.5%。其它几类资助来源包括自筹、储蓄、贷款和家庭支持,其比例逐年下降,从1998年的32.2%下降到2018年的15.2%。在对自有资源(own resources)的依赖程度上,女性博士生的比例(19.8%)要高于男性(11.4%)。
以助研、助教为主的资助机制体现了美国博士生资助体系的一个重要理念:资助不仅具有经济支持的功能,更重要的是,经济资助要服务于博士生教育目标,经济资源分配要和博士生培养、学术训练紧密结合。从经济保障看,博士生从事助研、助教的报酬水平很高。2020-2021学年,普林斯顿大学助研博士生的人均资助额是30800美元,助教人均资助额是33800美元。[11]麻省理工大学助研津贴为3378美元/月,一年合计约40536美元;助教津贴为3458美元/月,一年合计约41496美元。[12]2019年,美国人均消费支出44276美元。[13]博士生助研、助教津贴完全可以满足正常生活支出需求。从博士生教育目标看,助研、助教经历对博士生的学术融入、论文研究和未来学术生产力都具有积极影响。博士生在助研、助教活动中,可以习得科系、研究小组等学术共同体的规范和文化,并融入教学或研究团队[14];具有助研、助教经历的博士生在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方面往往更加活跃;助研制度发挥着研究学徒制(research apprenticeship)的功能,有助研经历的学者的学术产出和获得研究基金的数量是没有助研经历的学者的2.5倍。[15]助研、助教机制有力辅助了研究型大学的本科生教学活动,也促进了大学的研究活动和博士生教育目标的达成。
为了使经济资助更好地服务于博士生教育目标,大学还会根据博士生所处的学业阶段,将各类资助实行动态搭配。美国博士生教育模式主要由课程学习、资格考试和论文研究三个要素构成。一般来说,博士生在学习的第一、二学年,可以获得接近于生活支出的、无偿的固定生活津贴(stipend),此举可保证博士生在低年级专注于课程学习;在第三、四学年及之后,大学更鼓励博士生从事助研、助教活动,不仅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入,而且能够强化科学研究与教学能力的训练。在博士学习后期,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除了助研、助教金外,论文资助金也是一项精准设计的资助方式。在这个阶段,博士生可以申请专项的论文研究资助金。1998-2018年,美国博士生论文资助金的比例不断上升,从1998年的16.3%上升到2018年25.3%(图5)。
(三)资助结构呈现学科差异,体现不同的学科文化和博士生培养模式
美国博士生的资助结构呈现明显的学科特点。如前文图2所示,2019年的SED显示在第一大资助来源助研金方面,工程领域的助研金水平最高,占全部资助金额的57.4%,其次是物理和地球科学领域(50.5%),生命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助研金占比都在37%左右。助研金水平高,意味着这些学科领域的博士生获得的助研机会多。2019年,美国理工领域的博士生具有助研经历的比例最高接近90%,如物理和地球科学领域的助研比例是88%、工程领域是84.7%、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是70.6%,明显高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61%)、人文和艺术(38.8%)、教育领域(37.4%)(图6)。奖助学金和论文资助金是第二大资助来源,图2数据显示,二者合计资助金较高的是人文和艺术(37.8%)、生命科学(33%),接下来是心理学和社会科学(26.3%)、工程领域(20.2%)。从覆盖面看,图6数据显示,人文社科领域中获得奖助学金和论文资助的博士生比例要高于工程和自然科学领域,如人文和艺术领域的奖助学金覆盖面达到84.7%,论文资助比例为42.8%;生命科学领域84.3%的博士生可以获得这两项资助,工程领域约71%,物理和地球科学合计约74%,都属于较高水平。第三大资助来源助教金对于人文社科领域和基础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生非常重要。2019年,人文和艺术、物理和地球科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具有助教经历的比例分别高达88.1%、86.3%和84.6%,工程领域(66.35%)和生命科学领域(53%)的助教覆盖面都低于总体助教水平(68.3%)。由于助研、助教机会有限或者资助水平低,教育、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三个学科领域的博士生对自身资源(个人储蓄、家庭支持)和贷款依赖程度比较高,尤其是教育领域50%的博士生有教育贷款,67.2%的博士生要依靠个人储蓄。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人文和艺术领域的博士生的教育贷款比例也较高,分别达到40.8%和38.7%(图6)。
分析美国博士生资助结构的学科差异的原因,一个因素是政治层面的考量,即博士生财政策略服务于国家创新、研究和开发战略,有助于实现在健康、能源、环境和安全领域的国家目标;二是学术因素,反映了不同的学科研究文化和博士生培养模式。[16]应用学科如工程领域和纯理科研究倾向于团队研究方式,博士生培养模式相对结构化,且置于团队的科研共同体中进行,博士生的学位论文选题通常和导师的研究项目相关,助研促进研究且与培养目标一致;人文和艺术、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教育学科更崇尚个体研究文化,博士生教育更多是一种个体式的、非结构化的培养模式,论文选题通常反映研究者的个人研究旨趣。这些领域的博士生助研机会少,需要承担大量的本科生教学辅助任务,或者依靠家庭支持、个人储蓄、教育贷款等。不同资助方式支持的学术活动的性质不同,影响了不同学科领域的博士生的修业年限、学业完成率和资助满意度。研究发现,助研能促进博士生的学业完成,而助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流失。[17]助研工作给博士生提供了融入教师科研项目和机构文化的机会,助教虽然有助于博士生获得就业机会,但教学任务更多的是他人取向、劳动密集的半专业性工作,这与学科对博士学位论文的系统而独创的研究标准似乎是冲突的,过多的教学工作占用了博士生的研究时间,提高了淘汰率和修业年限。[18]从美国博士生注册10年间(1992-2001年)的累计流失率看,流失率最高的都是助教比例较高的学科领域。在资助满意度上,人文和艺术、教育、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的满意度分别为55%、58%和59%,明显低于生命科学领域的资助满意度(73%)。[19]在修业年限上,人文社科领域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所用的时间明显比其它学科领域更长,助研金和奖助学金比例较高的学科领域如工程、生命科学的博士生学位获得时间更短(表4)。
三、美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的挑战和改革动向美国联邦政府与研究型大学通过将教育和研究相结合、资助和学术训练一体,保证博士生教育服务于创新、研究和发展的国家战略,并为世界提供了培养新一代大学教师、研究者的成功模式。在21世纪前20年,美国博士生教育所处的政治背景、经济环境和劳动力市场发生深刻变化。为了保持博士生教育强大的生产力和世界地位,“重构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教育、关注博士生的学术和职业生涯”成为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21世纪十大优先行动事项之一。美国国会、联邦政府和大学针对博士生教育的关键方面展开了积极讨论,并实施一些改革措施,展现了21世纪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新动向。
(一)联邦政府持续加大投入,革新资助机制,改进博士生学习体验
财政压力是美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的第一个挑战。由于近年来的经济衰退,联邦政府大规模缩减高等教育经费投入,大学尤其是公立研究型大学的资源减少。为确保博士生教育的高水准和世界声誉,联邦政府的责任在于从预算政策上确保博士生教育投入。从2012年开始,联邦政府计划每年新增5000个博士生研究奖助学金名额,且连续资助多年。通过该计划,联邦政府旨在向有潜能的博士生传递信号:他们可以获得充分的资助完成博士学业。此举可以增强博士生教育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与提高资助水平相比,资助机制更能影响博士生的学习体验。新增的联邦政府资助不仅要帮助博士生完成学业,而且要提高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改进博士生的学习体验。为实现这一目的,联邦政府考虑改变资助模式:从助研和助教模式转变为研究助学金项目或实习项目,从服务型资助为主转为研究培训型资助为主。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博士生教育大发展的时期,博士生资助模式就是以研究助学金为主。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大学研究项目和经费激增,需要更多的科研和教学劳动力,助学金模式就转变为助研、助教模式为主,一直延续到今天。虽然助研、助教机制有助于培养博士生的研究和教学能力,但这类资助的首要目的是提供低成本的学术劳动力,辅助研究型大学的研究和本科生教学工作。联邦政府资助计划从助研、助教金模式重新转向研究助学金和实习金机制,主要目的就是提高博士生的学习体验和教育质量,让获得资助的博士生能够更安心地从事研究工作,鼓励他们将研究和未来的职业生涯、专业发展活动结合起来,让资助更好地服务于博士生的个体成功和潜能发挥。
(二)研究型大学重构博士生教育过程,提高博士生教育资源使用效率
美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关于博士生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问题。博士生教育要有坚固的经济基础,但不能一味要求联邦政府加大投入。研究型大学的责任在于改进博士生教育过程,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在美国博士生教育体系中,流失率高、博士学位获得时间长是效率不高的主要表现。根据美国研究生院协会对29所大学、23个学术领域的调查,1990-2000年,美国博士学位完成率整体上只有57%,工程领域较高,达到64%,人文领域只有49%;尤其是博士生学习的第8年是一个分界点,50%的博士生已经在第8年之前获得博士学位,第8年之后,很少有博士生能够修完学业;在获得博士学位所需的时间上,从进入研究生院开始算起,2008年博士生获得学位的中值年数(median year)是7.7年,经过十年,2019年不同学科领域的博士学位获得时间都出现延长趋势,尤其是人文和艺术(9.5年)、心理学和社会科学(8.0年)、教育领域(11.9年)更加明显(表4)。
提高博士生的学业完成率、鼓励学生在最优的时间内完成学业,这成为研究型大学提高博士生教育资源使用效率的两个关键措施。这不仅关系到博士生的个体利益,促使他们能够尽快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从投入-产出的观点看,大学也可以节约资源,提高联邦政府投入以及其它来源资金的使用效率。为提高博士学位完成率和优化学位获得年数,大学需要从招生到就业、从学术指导到社会支持,全程、全方位优化博士生教育。首先,完善博士生的入学和筛选政策。博士学位完成率低,在一定程度上与博士生的入学选拔有关。博士生教育需要学生有研究潜质并热衷于研究活动,除非学生在本科生、硕士生阶段已经有足够的研究训练和经历,否则就不能保证进入博士生教育项目的学生能够保持研究热情和具备研究素养。因此,在进入博士生教育项目之前,学生要有足够的先行研究训练(advance training)、有研究探索和职业定向,博士生教育项目只接受那些有才华、做好充分准备、有热情坚持到底的学生。第二,加强博士生指导,包括学术定向和职业定向。在博士生学习过程中,大学和导师需要更紧密地跟踪博士生的教育过程,加强学术指导,促进博士生在所在系所的社会融入和学术融入,以及提供更多就业、职业信息。第三,优化博士生教育环境,提供管理和社会支持。在博士生教育的不同阶段,大学管理部门要制定政策和提供社会、经济支持,尤其是在论文写作这一关键阶段。为落实上述想法,大学需要认真审视、重构现有的博士生教育项目,尤其要清晰地确立研究型大学博士生教育项目的目标和使命,即最大程度发挥博士生的研究潜能,致力于促进学生的成功,为21世纪准备更优秀的精英人才。
(三)促进博士生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结合,帮助博士生做好职业准备
美国博士生教育面临的第三大压力来自于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的挑战。长期以来,大学在确定博士生教育规模时,通常会考虑大学的研究事业、本科生教学工作,以及学术生产力和大学声誉等因素,很少考虑博士生面对的劳动力市场。近些年,博士生面对的劳动力市场至少发生三个深刻变化:第一,博士生在学术领域之外,尤其是私人工业、商业部门就职的比例在增长。由于学术职业领域的薪资较低,而且终身职位越来越少,学术领域的就业吸引力不断减弱,在私人工商部门就职的博士生数量不断增长。1999-2019年的20年间,博士学位获得者在学术领域的就职率从48.8%下降到41.3%,工业、商业部门的就职比例从27.5%上升到38.5%,尤其是拥有博士学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超过60%在工业、商业部门就业。第二,在工业部门就职的博士生面临着专业硕士学位人力资源的冲击。近些年,美国科学领域的专业硕士学位的学生规模激增,从1997年的8个学位项目增长到2011年的239个项目,这些专业硕士学位项目向学生提供科学训练和专业技能,有效充实了工业领域对研究和开发人员的需求,直接冲击博士生的求职。第三,准备进入学术领域的博士生不仅要能够胜任研究活动,也要做好在学院和大学从事教学工作的准备。从近些年博士生毕业后的职业活动类型看,接近40%的博士生在教学型大学和学院担任教职,这就需要他们在博士生教育阶段接受充分的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的训练。
概括起来,在一个变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美国博士生的就业模式转变为:每一个准备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在硕士阶段都应该有先行的科研训练和学术定向;每一个博士或博士后都要做好从事高校教学工作的准备,而不仅仅是研究职位;每一个刚入职的新大学教员都要做好无法获得终身职位,或只在某些情况下才能获得终身职位的准备;每一个获得终身职位的大学教员都要有能力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项目负责人。大学要做好博士生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结合,确保博士生能为他们即将进入的广泛的职业领域,包括学术、工业、政府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做好就业准备。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研究生院委员会和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共同组织实施了一项为期十年的“为未来教师做准备”(Preparing Future Faculty)项目,旨在积极提升研究型大学的博士生的教学技能和教学胜任力。[20]除了教学能力外,还要给博士生提供更广泛的职业能力和学术职位的其它技能训练,比如研究项目和研究经费申请书的写作能力,学术成果出版能力和学术汇报、交流能力,以及在政府、私人工商业部门、非营利组织就职所需要的能力,如口头和书面沟通能力、项目管理能力、商业伦理和创新能力等。大学需要增强博士生的职业能力,才能保证博士学位获得者可以在短期内提供生产力,这对刚毕业的博士生、雇主,乃至整个美国社会都有益处。
参考文献:
[1]阿特巴赫.美国博士教育的现状与问题[J].教育研究,2004(6):34-41.
[2][4][7][10]Committee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Board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Workforce,Policy and Global Affairs.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Ten Breakthrough Actions Vitalto Our Nations Prosperity and Security[EB/OL].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Washington,D.C.https://www.nap.edu/catalog/13299/research-universities-and-the-future-of-america-ten-breakthrough-actions#toc.
[3]KERR C.The Gold and the Blue:A Personal Memoi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49-1967[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92.
[5]GRAHAM H D,DIAMOND N.The Rise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Elites and Challengers in the Postwar Period[M].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
[6]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Institute of Medicine,Science,Technology,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National Goals for a New Era[M].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3.
[8]赵世奎,沈文钦.中美博士教育规模扩张的比较分析:基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博士教育发展的数据分析[J].教育研究,2014(1):138-149.
[9]National data.GDP and Personal Income[EB/OL].[2024-02-03].https://apps.bea.gov/i-Table/iTable.cfm?reqid=19&step=3&isuri=1&1921=survey&1903=76.
[11]One of the Most Generous Programs in the Country[EB/OL].[2024-02-03].https://admission.princet-on.edu/cost-aid.
[12]Research and teaching assistantships[EB/OL].[2024-02-03].https://sfs.mit.edu/gradu-ate-students/guide/research-teaching-assistants/.
[13]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EB/OL].[2024-02-03].https://www.bea.gov/news/blog/2020-10-08/p-ersonal-cons-umption-expenditures-state-2019.
[14]Ethington CA and Pisani A.The RA and TA Experience:Impediments and Benefits to Graduate Study[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93(3):343-354.
[15]Roaden A and Worthen B.Research Assistant Ship Experiences and Subsequent Research Productivity[J].Research in Higher Education,1976(5):141-158.
[16]王东芳,高耀.美国博士生教育的流失现状与改革启示[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20(8):18.
[17]AMPAW F D,JAEGER A J.Completing the Three Stages of Doctoral Education: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J].Research Higher Education,2012,53(6):640-660.
[18]王东芳.学科文化视角下的博士生培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187.
[19]Midwestern Association of Graduate Schools.Show Me the Money:Funding Graduate Education.Proceedings of the 59th Annual Meeting[R].Marriott City Center,Minneapolis,MN,2003(4).
[20]GAF J G,PRUIT-LOGAN A S,WEIBL R A.Building the Faculty We Ne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orking Together[R].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 Universities,2000.
(责任编辑陈春阳)
收稿日期:2023-07-31
作者简介:孟卫青,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吴开俊,广州大学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鸣敏,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唐婷,深圳市龙华区行知实验小学教师。
*本文系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研究成果(18YJA880063)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