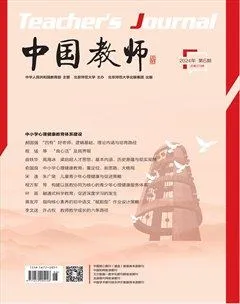自负·迷茫·曙光: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意象演变①
2024-06-25宝日
宝日
身为一名教师,在15年的从教生涯里,我不断地认识学生、认识教学、认识教育环境,同时也逐渐形成了对自我的认识。作为一种教师实践性知识的表征形式,“意象”反映教师的自我认知以及教师对教学、学生和教育教学情境的认知,融合了教师的“信念、情感与需求”[1]。2020年到2023年之间,我一直在中学教育最后“临门一脚”的毕业年级担任备课组长,短短四年,对自我认知的意象经历了堪称撕裂的巨变,陷入了人生从未有过的低谷,迷茫、困顿,像一个陷入黑夜的人寻找孤灯。
2021年7月,我参加了区“优秀种子教师”项目,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一些教育理念、理论和思想。在学习的过程中,我接触了 “三维叙事探究空间理论”。结合这一理论视角,我想通过教育叙事进行真实的自我剖析,展现我从最初的自负,到后来的迷茫,再到有些微曙光的短暂教学历程。
“得意忘形”:意象的自负
2019年秋季开学,学校领导让我担任毕业年级的备课组长。虽然任教十年,但仅仅带过一年毕业年级,教学经验极度匮乏,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地上岗。为了不辜负学生和学校领导的期待,我积极组织备课组教学工作,将工作计划细化到每一天;认真听老教师的课,反复揣摩;认真分析历年考试真题,仔细研读“学业质量标准”。在备课组的共同努力下,在期中、期末考试中,年级的成绩稳定领先。
2020年初突发疫情,教学被迫转到线上,我又制订了细致的线上教学计划,主干课程采用录播,学生可以暂停,记录,反思授课内容;解答学生疑惑则采用直播互动的方式,能更好地和学生进行互动,了解学生困惑的症结。那时,由于不熟悉录课,也不太会剪辑,说错了就重录,经常哑着嗓子录到深夜。最终考试成绩出来了,我所带的学生获得了几十个满分,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当时的我,感觉天是蓝的,花是香的,草是绿的,觉得自己特别厉害,整个人飘飘然。我觉得对得起这个年级的学生,对得起领导的期待。其实我不知道,浮华的背后也藏着一丝隐忧:没能好好分析取得成绩的原因,没能认真回顾一年的教学历程。
“故步自封”:意象的迷茫
因为学校领导的信任,我继续留在毕业年级,仍担任备课组长。没有了第一年的手忙脚乱,我变得更加“轻车熟路”。在我心里,这只不过是又一次辉煌的开始,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带领这一届学生,取得好的成绩。“一模”考试,我自认为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成绩出来的一刻,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全年级的平均成绩前所未有的差,差到我不敢相信。仅仅过了一个冬天,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
还记得那天的成绩分析会,我听不进去任何一个字,会后学校领导把我留下来,想询问这次成绩下滑的原因。一年前的辉煌又涌现在我的眼前:“几十个满分!我曾经带出几十个满分!我的复习路径一定是对的!出问题的一定是学生!是这次考题!是阅卷标准!”
那时的我,像一只浑身长满尖刺的刺猬,开启了防御机制,近乎执拗。学校领导让我调整复习计划,我坚持认为我做的才是对的,听不进去别人的建议。对自身认知的意象从一个“自负者”转向了一个“孤勇者”,我在一个“所有人都错”的世界里孤独前行。
那个时期的我,意象中一直浮现着一个“理想主义者”孤独的身影。写这篇文章时,结合约翰·杜威关于意志的一系列论述才发现,当时的我并没有清晰地意识到毕业年级教学的难度,对学生、对教育考试改革缺乏正确的预判,更无法克服困难,持久、有力地实现既定目标—很显然,我已经陷入一种意志上的困顿。但对自身的意象,却因为“几十个满分”而继续狂妄。我尝试分析这个“理想主义者”意象的内涵,惊觉其原型来自一部很喜欢的电影。电影的主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怀着公平的信念来到“鹅城”,打倒“黄四郎”,拯救百姓,但最终被所有的兄弟抛下。电影最后的镜头是,他孤独地策马,随列车远去。
接下来的备考岁月,我几乎没有在晚上10点前回过家,全部身心都扑在了学校,我渴望再一次辉煌,但已经迷失在前进的路上。我一直在用帕尔默的《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打发内心的焦躁。书中提倡教师要进行自我探索和成长,寻找内心的和谐和平衡。帕尔默认为,只有教师自己能够找到内心的和谐,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教育者[2]。只不过当时的我极度焦躁,极度不和谐,我用意象中的“理想主义者”平衡现实,以期达到内心的和谐。
“化茧成蝶”:意象的曙光
最终,2021届的成绩只能说不好不坏,既没有重现上一届的辉煌,又比糟糕的“一模”好一些。学校领导将我的教学任务调整为非毕业年级。在我心里,这就是对我极度的不信任和抛弃,我开始不停地担忧,担忧不能再回到毕业年级任教,担忧再也没有证明自己的机会,担忧再也不能帮助学生取得好成绩,最担忧的,还是整个世界对我的否定。现在回想,似乎有些“矫情”,但当时的我陷入了无休无止的自我怀疑当中。2021年夏天,工作站的杜老师让我在一个重要的论坛上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为题进行主题分享。这次分享的契机,强迫我从躁动走向安宁,澄清内心混乱的意象。
1. 自我意象的澄清
2020届成绩优异,2021届成绩平平,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哪些因素发生了变化?准备分享的过程中,为了探究问题的原因,我接触到了“三维叙事探究空间”理论框架,并将自己带进一个相对复杂、丰富的时空之中。三维叙事探究空间检视个人时间发展的经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个人与具体环境的联系。所谓三维,即时间维度、个人与社会维度、地方维度。时间维度,关注个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研究个人一段经历,必须要追溯过去和展望未来,不能孤立看待;个人与社会维度则体现人类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不可避免地与他人产生互动;地方维度,也可以称作“空间维度”,关注个人经历的情境性,即研究一个人的经历,一定要关注其所在的具体地点和环境[3]。
我运用“三维叙事探究空间”理论框架认真分析了这两年的毕业年级教学生涯,往事如画卷般伴随着自我剖析缓缓展开,仿佛明镜一般照射出我的成功与失败,照射出我的恐惧与无畏(见表1)。
通过对自身的深刻剖析,我发现,教育是动态的,哪怕仅仅一年,我面对的学生、面对的同伴、面对的个人与社会、面对的个人与空间,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2020届的巨大成功,无法机械地复制转移到2021届。但是,我依然没能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好硬着头皮,在论坛上平铺直叙地分享了2020届线上教学的一些经历。
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吴院长和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技术专家乔教授对我的发言进行了点评,他们都提到了“即时评价”。2020年时开展线上教学,学生很多作业都是在线完成,在线平台非常有助于积累学生的学习数据。丰富的数据加上教师的经验,有助于教师迅速判断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及时通过在线互动答疑进行教学反馈。这种反馈及时、高效,极具针对性。这种真正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最终带来了好成绩。
2. 内心意志的探索
我又重新看了一遍那部电影,有一个镜头跃入我的脑海, “理想主义者”举着两把枪,一把对准敌人、一把对准自己。我突然有所感悟,我根本不是一个孤独的“理想主义者”,我是一个想让学生取得好成绩的“功利主义者”。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应该是一把“枪”对准敌人,一把“枪”对着自己,即“批评与自我批评”。我应该带着审辩的眼光看待教育的历程,找到这些教育历程中哪些是对的,哪些做法促进了学生成绩,用研究的眼光思辨自身,“扎根”研究自己,才有可能找到认知自身的正确意象。
之后的我,积极参与工作站的各种理论、思想培训,不断汲取教育学的相关知识。在一次工作坊中,我遇到了研究教育考试的秦教授,他向我介绍了关于“形成性评价”的思想。布卢姆在《教育评价》一书中,将教育评价分为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及时反馈,帮助学生和教师了解学习进展,从而指导未来的教学和学习活动[4]。秦教授提到,2020届好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知不觉应用了形成性评价,精准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并进行了有效的教学反馈。
之后,我对“形成性评价”的思想如痴如醉,基于自身的理论和实践特点,开始基于学习证据的教学与评价实践。2023届,学校领导让我再一次回到毕业年级,担任备课组长。我积极地在教学中对学生学习证据进行收集。在我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2023届学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一回,好成绩没有让我再次“狂妄”,我开始像一个真正“理想主义者”一样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取得好的成绩,一定不是教育的全部,我想找寻到心中刚露曙光的美好教育,工作站将我带入的教育科研之路,我要在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毅然决定“高龄”攻读课程与教学论博士,在和导师朱教授进行深度剖析自我之后,导师将我的研究领域定在了循证教育实践,并鼓励我开创出一条基于一线教学和专业研究的新路。此时,一个“理想主义者”初步完成了自我突围,自我意象微露曙光。
参考文献
[1] 陈向明,等.搭建实践与理论之桥——教师实践性知识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114,116.
[2] 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十周年纪念版)[M].吴国珍,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 王青,汪琼.教育叙事研究——关于故事和生活经历的研究法[J].开放学习研究,2018,23(4):34-40+62.
[4] 布卢姆,等.教育评价[M].邱渊,王钢,夏孝川,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33.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职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