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风景:革命情绪的共鸣板
2024-06-15刘鹤翔王国祥
刘鹤翔 王国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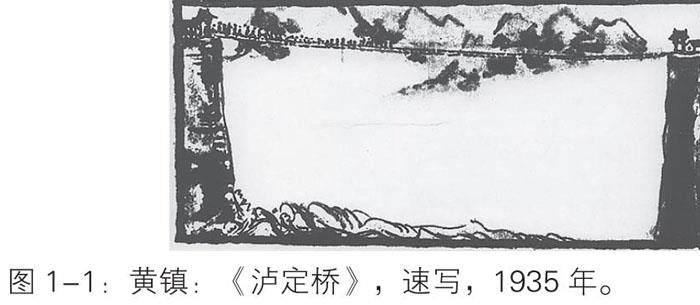


【导读】风景是被文化中介了的自然景观,那些著名的长征题材历史风景画也是如此。由于图像资料匮乏,关于长征历史记忆的重建更多地依赖于回忆录文本。在这些文本中,对途中雄奇风景与险恶自然环境的描绘是一个突出的要素。风景成为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的表征形式。这种通过风景表现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的方式,在中国的风景美学史上都是全新的。
在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笔下,与红军长征的壮举相比,“汉尼拔经过阿尔卑斯山的行军看上去是一场假日远足。”对国外的军事家和作家来说,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极具魅力的远征。穿行11个省,进行了大小600多次战斗,经历了无数奇险的地理环境,而主力仍然得以保存;对于探险家来说,长征也同样是一场伟大的传奇,红军的“荒野生存”显示了人类的生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
在欧洲绘画史上,对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描绘是历史风景画著名题材,对巍峨的巉岩,险峭的绝壁、壮丽的冰川的描绘体现了雄伟风格。相比之下,长征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地理空间,沿途有着更能激发想象力的丰富的自然景观。在这场苏维埃国家的“举国大迁移”(斯诺语)中,历史文献中提到的每一处风景,几乎都意味着巨大的牺牲。但无论是出于革命意志,还是普通人的生命意志,长征风景都显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强大的精神张力。
对长征风景的体验非亲历者不能真切。但由于摄影资料和绘画资料的匮乏,长征时期留下的图像文献很少。艺术上成熟的长征题材画作是在1949年后出现的。这些画作通过再现历史场景,表达对长征精神的崇高敬意,但这些绘画仍属于后建构的历史记忆。因此,本文试图从红军亲历者的绘画文献和回忆录文献入手,对文献中的风景话语进行分析,揭示长征风景作为革命英雄主义与乐观主义表征形式的起源,把握风景背后的精神意志。
一、黄镇的长征图绘
尽管长征纪实图像极其匮乏,但并非一片空白。长征队伍中有几位专业或业余的画家,如红五军团的黄镇、红二、六军团的陈靖、红四方面军的廖承志等,尤其是黄镇,他早年求学于上海美专,于新华艺术大学毕业,是唯一一位以纪实性长征题材美术作品传世的画家。
在长征途中,黄镇即兴而画,描绘沿途革命人事和自然风光,一路上共画了四五百幅,后来仅存二十四幅。黄镇本来无意传世:“我画画,是生活的纪实,是情感的表达,从来未曾想过辑集出版。在长征艰苦的行程中,许多难忘的场面,动人的事迹,英雄的善举,我仅仅做了一点勾画,留下一点笔迹墨痕。”1938年,这批作品曾以《西行漫画》为书名由阿英编辑出版,作者误作肖华。从题材看,黄镇的画作系以革命人事为中心,如《遵义大捷》《红军彝族游击队》等,但其中部分作品也可视为风景速写。这批画作尽管如阿英所说,在绘画技巧上并不成熟,但“在中国漫画中,有谁表现过这样伟大的内容,又有谁表现过这样的战斗”?另外,黄镇的画也不完全是画在纸上。有时画在门板上,有时画在石壁上,作为宣传画,它们传达的是“把所有的人联合起来的那种普遍的感情”。
西南地区是诞生长征传奇的重点区域,其中大渡河上的泸定桥争夺战是红军战史上最著名的战斗之一。这一题材最早出现在黄镇的《泸定桥》(图1-1)速写中。黄镇回忆说:“我亲临了飞夺泸定桥的场面,大渡河的汹涌、13根铁索的险峻和20名勇士身上燃起的烈火,使我不能不留下历史的画面。”他的速写采用了仰视视角,红军的队形呈现为高处一连串的黑点。对后人来说,这张作品令人难忘之处在于其奇异的视觉性,这种图式在历代绘画中都是未有过的。
川西的夹金山是当地传说中“鸟飞不过”的神山,黄镇的《翻越夹金山》(图1-2)画面采用几乎垂直的构图,山脚下的红军昂首阔步,在山道上作跑步状,随着时隐时现的山路,队列直达最高处的隘口。画作右边题作“雪山高,铁的红军铁的意志更高”。
《草地宿营》(图1-3)描绘的则是红军进入诡秘莫测的松潘草地的情景。近景中,两名战士从支起的人字形帐篷里探出头交谈。战士在帐篷之间挑水、拾柴,他们的头顶大风中是翻转的云团。这样的休憩场景透着一种松弛和乐观。
事实上,草地的险恶却也无处不在,含有毒素的水是黑色的,唯有草兜的根部才是可靠的落脚处,一脚不慎,泥沼随时可能将人吞噬。在险恶的自然中,红军部队的食物极为匮乏,最后仅靠煮皮带和草根充饥。黄镇速写中背着干粮阔步迈进的情景应该是初入草地时画下的。在接下来的行军中,由于饥饿、疲乏、寒冷、暴风雨和伤病的折磨,大批的红军在草地上耗尽了生命力最后的储备。走出草地时,三大主力的牺牲人数高达万人以上。
二、“战斗的乐观主义”
红军的长征突破了数十万敌军设置的封锁线,其中,红一军团就突破敌人封锁下的47道关隘,一些关隘中的战斗成为红军战争史上的传奇。1937年,丁玲在延安将长征将领们撰写的日记和追忆文章编成《二万五千里》一书,至1942年由总政治部更名为《红军长征记》,在解放后仅存孤本,系由朱德签名赠予埃德加·斯诺的一本,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2002年才被发现并公之于世。从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风景作为媒介在革命精神建构中的微妙作用。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月光下的行军”一节,描述的是红军从江西出发长征的情景。这一情景的更早版本出现在时任红一军团某师宣传科长彭加伦笔下。在一篇题为《别》的回忆录中,彭加伦所在的队伍是在一个晴天的下午从赣南的于都出发的。在红军长征记的众多回忆录中,彭加伦是最有文采的作者之一,他描绘了红军家属送别红军后夜幕降临的情景:
太阳在远山背后,渐渐地下去了,夜幕开始笼罩了大地。正在起着晚烟的村庄,和黄透了的田野,葱翠的山林,渐渐地模糊,在队伍的后面消逝了。红色战士们一面前进,一面谈笑着,他们活泼愉快兴奋的情绪,不断地在他们的笑容上流露出来。
这段话洋溢着温暖乐观的情绪,从中难以看出红军是迫于国民党的军事压力被迫长征的。其时,国民党在关于“围剿”红军的报道中频繁地使用“流窜”“进窜”这样的字眼,而在彭加伦的笔下,红军的长征是从容不迫地开始的。暮色中的于都,宛如江南故乡的风景,红色战士们欢乐地离开,似乎前路并不遥远,很快就会返回似的。而索尔兹伯里所谓“月光下的行军”也的确是事实,据时为红三军团政委的李富春回忆,为避免敌机的侦察和轰炸,红军长征多夜行军,特别是从出发到渡过湘江的前后,差不多都是夜行军。在他的描述中,夜行军呈现为一种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的景观:
特别是夏秋天气,乘着月光夜行军,却很畅快,月朗星稀,清风徐徐,有时虫声唧唧,有时水声潺潺,有时犬吠数里,野花与黄菜争香,夜中更觉幽雅。经过村落时,从疏疏的灯火中,看到一村的全部男女老幼,带着诧异而又愉快的眼光,望着我们这走不尽的“铁流”的红军。
而对夜行军的图像化描绘在另一个段落中达到了极致。举着无数火把的队列仿佛点燃了沉沉夜幕:
点火把夜行军,是很壮丽的,走平坦大道,真是可以光照十里,穿过森林时,一点一点,一线一线的火光,在树林中,时出时现,如火蛇钻洞,红光照天!过山时,先头的已鱼贯的到山顶,宛如一道长龙,金鳞闪闪,十弯十曲地蜿蜒舞蹈!从山顶回头下望,则山脚下火光万道,如波浪翻腾,一线一线一股股的奔来,即在钱塘江观潮,泰山上观日,也无此奇迹。
将长征中行军艰险再现为瑰丽的风景的情况,在《红军长征记》中比比皆是。将其看作一种刻意的修辞策略显然是对革命文化的误解,因为,其中的乐观主义基调作为一种精神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之一。按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恩斯特·布洛赫在《希望的原理》一书中表达一种坚信:“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无权成为悲观主义者。”按照布洛赫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已知的希望”基础上的“战斗的乐观主义”(militanter Optimismus),它既反对虚无主义的悲观主义,也反对自发的乐观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呼唤新天新地,致力于打碎旧世界,建立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在这个世界上人自己必须检查是否一切正常把他所期待的、可运作的事业照看好;于是幸福如意、戴着黑纱的、战斗的乐观主义向他招手。”
而在其他关于长征的回忆文本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这种高度自觉的乐观主义。在这些文本中,通过主体的介入,自然风景被再现为象征革命精神的“第二自然”。
作为四川人,朱德对川中风景深有体会。史沫特莱写道:“将军每次都会赞叹四川的壮丽。耸立在他家周围的群山,乃是大雪山向东延伸的一条余脉。”1908年12月,朱德与秦昆一起前往云南讲武堂,二人还特意在雄奇山水中流连。当长征的队伍进入滇川之间,朱德已是旧地重游。对于革命的行动者而言,对风景的感知未尝不是审美活动,只不过这种审美活动在长征途中有着超越了审美的国家意识。按照路线图,红军是先渡金沙江再过大渡河。穿行于川、藏、滇三省区之间的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这条河流的雄奇之处在于其巨大的水流落差。和金沙江一样,大渡河水也在深山峡谷中汹涌咆哮,其声势足以湮没激战的枪声。对冲过了无数生死关的红军来说,大渡河在他们的脑海中留下了重要的记忆图像。时任红3军团第11团政委的张爱萍后来回忆道:
大渡河水的惊涛骇浪犹如万马奔腾。水流的吼声,唤起了我们深沉的回忆:遵义、赤水河、扎西、娄山关、乌江、北盘江、金沙江这些令人难忘的地点和河流,那些英勇艰苦的战斗场景,又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
惊险的江势加上偏僻的位置,两条流域既非历代士大夫所乐游,亦非崇尚“卧游”的山水画家出入之地。在艺术地理学的意义上,近代中国对这两条河流的书写和艺术再现乃是艺术史上的创造,是对革命风景的诗性建构,在这种诗性的内在中体现出的正是对长征风景英雄式的建构逻辑,体现出亲历者在事件中展现出的乐观主义精神。
三、长征风景的崇高性
通常认为“崇高”是一个源自西方美学的概念,是古罗马时代的朗吉努斯在修辞学著作《论崇高》中首先提出来的。而崇高在中国则是一个现代性概念,是由近代的中国革命建构的新传统。从旅行家的视角看,红军在长征途中所经历的多样的地理环境,是一场伟大的冒险。
按《红军长征全史》的记述,在翻越夹金山时,随着山势增高,寒风卷着飞雪四处飘舞,战士一个个都成了“雪人”,皑皑白雪霎时就变得面目可憎了。当红一军团的前卫团第四团达到山顶时,发现这座飞鸟难过的“神仙山”其实也有人踪,山顶上有人为立起的旗杆,还有寺庙矗立于此,代表当地人的信仰。如果说雪山信仰的崇高性体现的是藏人的精神境界,红军翻越大雪山则是基于另一种崇高信念,即革命精神。此外,翻越大雪山的国家地理意义也是全新的。
相比于雪山的雄伟,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过渡地带的松潘草地则诡秘异常。当时,红十一团已经渡过了班佑河,走出了草地,军长彭德怀发现有几百人还没有跟上部队,就派王平带人去接。当王平带着战士返回到河边时,在望远镜看到河对岸有八九人背靠背整齐地坐在河岸上,喊话也无人应答,他就带通讯员和侦察员涉水过河察看,结果地上的红军战士一拉就倒,他们已全部牺牲,人类历史上可能从未出现过如此惊心动魄的生命现象。
而在对长征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中,一个共同的主题词就是集体的革命英雄主义。在接受史沫特莱采访时,朱德反复提到红军队伍中产生了新的英雄观念:
“英雄主义是个旧观念,”他说,“过去,个人英雄凌驾在群众之上,轻视群众,甚至奴役群众。红军体现了英雄主义的新观念。我们培养出革命的群众英雄,他们不自私自利,不为任何诱惑所动,决心为革命牺牲,一直战斗到我们的人民和国家获得解放为止。”
在与长征有关的记述文献和图像文献中,风景是一个建构性的要素,它体现了人与自然全新的关系。对于风景,旅行者的凝视或者“视觉占有”已失去了其传统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高度紧张的关系。在自然面前,主体的情感和意志被激发出来,且具有一种崇高感。“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如长征途中的纪实性文本和长征回忆录文本所体现的,长征途中的奇险风景是革命情绪的共鸣板。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斯诺. 红星照耀中国[M].董乐山,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 丁玲. 红军长征记[M].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
[3] 梦海.人的命运掌握在人手中——论恩斯特·布洛赫的战斗的乐观主义[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7(5).
[4] 艾格尼丝·史沫特莱.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M]. 梅念,译.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刘鹤翔,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副教授。王国祥,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获中南大学高端智库“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题材美术精品创作与国家收藏研究”(2021znzk10)项目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