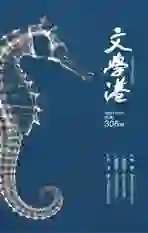观音像
2024-06-15侯晓蕾
侯晓蕾
早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当初文惠就不答应帮菲利普太太这个忙了。
菲利普太太的公寓坐落在乌节路商业街后面的一片山坡上,这个闹中取静的地理位置深得业主们的欢心,从购物中心到自家门口只是一脚油门的事,可文惠每次都爬得很辛苦。天气预报上说,这个东南亚岛国即将迎来新一轮热浪。尽管已经是黄昏时分,山坡两旁的灌木丛依然像烤炉一样,烘烤得路上的行人喘不过气。爬上坡顶的时候,文惠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感觉像有只冰凉黏糊的手紧贴在背上,怎么都摆脱不掉。
这个月以来,文惠天天进出这栋公寓的大门,那个黑皮肤的南亚保安不再像第一次时那样,追着她盘问不休,再看到她也只是冷冷地点个头。
入户电梯径直升到了顶楼,客厅里空无一人,空调却开着,厨房里隐约传来洗衣机的轰鸣声。文惠知道刘阿姨来了。菲利普太太回英国的这段时间,刘阿姨仍然保持着一个星期上门打扫一次的习惯。最近两次都是她前脚走,文惠后脚回来,没想到今天却碰上了。
文惠下意识地扫了一眼沙发后面,那张胡桃木的雕花长条桌上,摆着一盏亮晶晶的金丝鸟笼灯和一个黄铜古董拨号电话机。文惠总觉得这张桌子跟西式客厅的风格有些不搭。西方人不管是不是真懂,总爱往家里添置些富有东方色彩的摆设,也许是猎奇心理,越是觉得神秘的东西才越喜欢。
那里原本还放着一尊一米多高的观音像,文惠还记得那观音的样子很特别,她双手交叠,一条腿盘坐在高大的岩石上,另一条腿沿着峭壁垂进惊涛骇浪,脚踩一株从海里升起的莲蓬。可现在,观音像已经不在那里了,古董电话机的旁边空着巴掌大的一块地方。
那天夜里,就在客厅的这个角落,文惠跟一个男人在黑暗中激烈地纠缠起来,忘了是谁先失去平衡,两个人一起扑倒在桌边,随着一声巨响,那些巨石、海浪和莲蓬统统化作一地冰冷的瓷片。最后,在菲利普太太家那只黑猫的注视下,文惠悄悄擦干地上的血迹,把碎片收拾起来,连同那晚的秘密一起藏进了行李袋的最深处。
从那天起,文惠的心就一直悬着,她不知道被刘阿姨问起来该怎么解释,好在刘阿姨似乎并没有发现,不仅如此,两人已经彻底不讲话了。
这时厨房门一响,走出来一个戴着橡胶手套的中国女人,她五十岁上下的年纪,头发在脑后随意挽成个髻,一张憔悴的窄脸略微泛黄,那是菲利普太太那些白人女子在海边躺一天都晒不出来的古铜色。刘阿姨僵着脖子从文惠身边擦肩而过的时候,正眼都不瞧她一下,仿佛连身边带起的风都裹挟着一股怒气。
文惠没有理会她,径直去了厨房,一股地板清洁剂的清香夹杂着猫粪便的味道扑鼻而来。她看见主人房的床单和枕套正在洗衣机里快速地甩干,自己换下来的那堆脏衣服还原封不动地在洗衣篮里扔着。文惠叹了口气,现在凡是跟她有关的一切琐事,刘阿姨是再也不会沾一个指头了。于是她走到猫砂盆边清理了粪便,又往猫碗里舀上几勺猫粮,朝着门外喊了一声,小墨!片刻工夫,一只细瘦的小黑猫就静悄悄地出现在门口,像白色地砖上突然投下的一道黑影。
那只黑猫小心翼翼地绕着碗边嗅了一阵,才把头埋进去吃起来。文惠远远站在一旁等它吃完。黑猫晃晃乌黑油亮的脑袋,不时抬头瞟上文惠几眼,玻璃球似的黄眼珠里闪烁着洞察一切的狡黠,看得她心里发毛。
还好你不会说话,文惠心想。
这些年,在海外遇上同胞已经算不上是什么新鲜事,可就算是素昧平生的人,也总能从对方的磁场中敏锐地捕捉到相同的频率。在菲利普太太家,文惠第一次见到刘阿姨时,两人打了个照面就自然地说起了中文,当时的气氛还算融洽。
几句闲聊过后,她忽然听刘阿姨在喃喃自语,他们这些老外可真有意思,一个家要请好几个人伺候。文惠知道她多心了,忙笑着解释道,我就是临时过来看几天猫,您照常来就是了,您看这么大的房子被您打理得井井有条,换了我可做不来。刘阿姨淡淡地一摆手,嗳,这些本来也用不着你做,不像我没读过几年书,英文又不行,就是把粗活儿干出花儿来,也只够糊个口。文惠听了不好再说什么,低头提着行李进了客房。她心里清楚刘阿姨这些外籍劳工在海外的生活处境,通常一年到头辛苦做下来,拿到手上的钱也没有多少,还要扣掉一笔不菲的中介费。
刘阿姨不容易,文惠觉得自己也不容易。
在公司里,人人都知道菲利普太太是个厉害角色,这个谈吐优雅、行事干练的英国女人,曾在一年之内连升两级,取代了澳大利亚籍的前任,坐上了经理的位置。菲利普太太上任没多久,前任的助理就辞职了,当初文惠的这个职位还是这么空出来的。在菲利普太太手下工作的这几个月,文惠加班打杂的事没少做,每天还要提着十二分的小心。
菲利普太太一家来这里定居十多年了,她早已经在这个物质丰盈的亚洲国家生活得游刃有余,她总能买到性价比极高的美容套餐,也会掐着百货公司打折的日子去名牌店报到。菲利普太太等女儿一升入中学,就把住家的菲利宾女佣换成了一周几次上门打扫的钟点工,还专门指明要时薪最低的中国籍阿姨。这样一来,家庭的开销又节约了七八成。有人说菲利普太太真会算经济账,也有人说可惜她这样精明的一个人,选老公却失了算,菲利普太太省下的钱全都用来填补菲利普先生在开销上的窟窿了。
据说菲利普先生的能力远不及他的样貌出众,他不大过问家事,还有着某种相当昂贵的品位。前些年全靠着定期的婚姻咨询和专门的社区辅导,菲利普先生的状况才有了些好转。不过这几年两人工作都忙,总是聚少离多。
最近女儿的国际学校放暑假,菲利普太太请了年假准备带女儿回国,这时菲利普先生又去吉隆坡出差了,还要过上几周才能从那边直飞到英国与她们会合。这样一来,家里新养的宠物猫没人管了。一家人一走一个多月,请钟点工天天过来不划算,请朋友来帮忙又要欠笔人情债,于是菲利普太太就想到了她这个助理。
这时候离文惠试用期结束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文惠还要指望着菲利普太太批准她转正,所以这个差事她不但要答应,还得答应得心甘情愿。对于文惠的答复,菲利普太太也没有表现得特别意外,她甚至还一本正经地对文惠说,我家离公司这么近,住在我家里你早上能多睡半个小时美容觉呢。文惠听得一怔,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菲利普太太却又莞尔一笑,安抚似的在文惠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好了,我开玩笑的!等我从英国带礼物给你。
文惠刚住进来的时候,菲利普太太家的黑猫对她尚存着几分敬畏之心,总是远远蹲在角落里观察她。被文惠伺候了几天后,它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开始不断往她跟前凑,用尾巴尖扫,用后背蹭,撩拨个不停。文惠吃饭的时候,它居然跳上餐桌,把脑袋伸进水杯里。文惠不堪其扰,频频举胳膊抬腿地躲闪着,尽量避免跟它有肢体接触。到了晚上,它还会蹿上二楼,用爪子挠抓文惠卧室的门,吵得文惠在床上辗转反侧,整宿无法安睡。
一次文惠随手拿起菲利普太太家里订的《海峡时报》翻看,发现这只黑猫竟然躲到一边去了,才知道它不喜欢报纸上的油墨味道。于是她想了个办法,把报纸叠成一寸宽的纸条,睡觉前紧紧塞进门缝里。夜里黑猫果然不再上来骚扰。
一段时间过后,它渐渐对文惠失去了兴趣。
其实文惠不太喜欢猫。
她出国工作的第一年,在市区跟一个单身的女房东合租着一套房子。这家房东养着一只虎斑猫,平时总在房间外面的公共区域里大摇大摆地遛达。文惠第一天搬进去收拾东西的时候,这只猫跟前跟后地对着她细着嗓子叫个不停。出于客气,文惠伸手想摸摸它,不料那猫的眼中寒光一闪就扬起了爪子,她还来不及反应,手背就被狠狠地抓了一道,钻心的疼。
贯穿城市南北的滨海市区线开通之后,文惠所住的区域房价开始飙升,女房东变脸比她家的猫还要快,把租金涨了又涨,这就等于下了逐客令。搬家后文惠虽然省下点钱,通勤时间却变长了。后来文惠辗转换了好几份工作,工资的涨幅还是赶不上房租的增长速度,她只好把家搬得一次比一次更远。都说时间就是金钱,可文惠觉得她的时间一点也不值钱。
最近几年,彭兆平基本天天都在文惠的出租屋里过夜,每个月帮她承担着一半的房租。这对于买水果能去市场决不去超市的人来说,已经算是十分难得了。可他每次在付房租的时候,都会不住地埋怨文惠,这样多浪费,怎么就不能搬到我家里去住呢?可文惠总是下不了决心。
彭兆平是本地人,他五岁的时候,母亲改嫁到文莱,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跟着父亲住在城市西部的一套三房式的政府租屋里。他的父亲每月拿着退休补助,整天在楼下的露天食阁里坐着看方言连续剧,或是研究马票,盼着有朝一日能中个大奖。他们的祖辈都是来自潮州的移民,但是他父亲自己从来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的印象仅限于小报上的花边新闻。记得文惠第一次去彭兆平家,他的父亲用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文惠好一会儿,用带着浓浓潮汕口音的普通话问她,中国的公共厕所是不是都没有门?文惠只是礼貌地笑笑,假装没有听懂。
和一般的本地人不同,彭兆平不但不讨厌做家务,甚至可以说做家务是他的爱好。他自称有洁癖,不会放过文惠房间角角落落的一丝灰尘。这种洁癖也体现在精神上。文惠每天下班后,必须得按时发短信给他汇报行踪,晚一分钟都不行。走在路上,如果有陌生男子跟文惠搭话问路,甚至多看文惠一眼,他都会表现得十分不高兴。
生气的时候,他的坏情绪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恶毒的字眼会不受控制地从嘴里喷薄而出,也会不顾别人眼光地做出一些激烈的行为。一次文惠和朋友们在外面吃饭,没有及时查看手机,他联系不上她,就把文惠朋友们的电话都打爆了。前几天,两人又为了文惠到底要不要跟他回家住的问题吵了起来,他追着文惠一路从卧室吵到了客厅,眼看又要开始口不择言,文惠烦躁地起身要走,他一拳砸在铁门上,震得门框“哗哗”地颤动,声响惊动了好几户邻居。每次等他平复下来,又会紧紧搂着文惠道歉,说他只是害怕会失去她。文惠也忍不住陪着他掉眼泪。
可是这样循环往复的折腾,渐渐让她觉得身心疲惫。
这次文惠答应到菲利普太太家来帮忙,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把两人的关系冷一冷。没想到独处的日子让她的决心一天大过一天,她终于鼓起勇气,在短信里说出了当面说不出口的话,请彭兆平在她回去之前从出租屋里搬走。
彭兆平的电话还是会在半夜打过来,震铃的嗡嗡声骤然划破夜的宁静,听得文惠心里一紧。她已经不再接了,屏息凝神地等它自己挂断。那电话却来得越发频密,一通紧跟着一通,像狂风中的雨点似的,不让人有喘息的余地。
一个黄昏,刚下班的文惠终于被那个熟悉的身影堵在了菲利普太太的公寓门口,她不想在保安眼皮底下跟他拉扯,只好带他上了楼。两个人在菲利普太太家里独处了三个多小时,感觉简直有一个世纪那么长。最后,两个人仿佛耗尽了彼此全部的能量,像两尊没有生命的躯壳似的枯坐在沙发上。彭兆平点燃了一支烟,放在嘴边狠狠吸了一口。文惠懒得阻止他,只是默默看着那灰蓝色的烟雾在黑暗中弥漫着,飘过客厅墙上的那组家庭照。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里,菲利普夫妇都亲密地相拥在一起,他们脸上的表情在烟雾的笼罩下看着并不真切。
“砰”的一声,大门被重重关上了,巨大的声响吓了文惠和眼前的黑猫一跳,原来是刘阿姨收拾干净离开了。
文惠心里清楚,自己跟刘阿姨关系闹僵,就是从上次问她钱的时候开始的。那个装钱的信封明明就在行李外侧的那个口袋里放着,文惠绝对不会记错。可是那天她来到房间时,看到自己的行李口袋却是敞开的,信封不见了踪影,而那时候刘阿姨正在房间里吸地。
文惠早就看出来了,刘阿姨虽然手脚麻利,干活不惜力,但私心还是有的。她在一个房间干活的时候,都会随手打开那个房间的空调;每次工作结束,她也会在楼下的卫生间里洗一个长长的热水澡再走。现在钱不见了,难道问她一句都不行吗?
没想到文惠的话刚一问出口,刘阿姨的脸色就变得紫涨起来,她矢口否认,语无伦次地反复念叨着那几句话,你可要记清楚了,两千块钱不是闹着玩的,你身上带那么多钱做什么,我要你的钱做什么?
这几天,洪茂升的老板连着给文惠发了好几通信息,说如果她再不支付那两千块钱,那尊观音像就不给她留着了。
菲利普太太家的观音像在那晚被打碎后,文惠为了随时可以拼凑回忆出瓷像原来的样子,细心保存着所有的碎片。要想当成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她必须得赶在菲利普太太回来之前,买个一模一样的原封不动地放回去。
文惠在网上查过了,这个城市里卖佛具用品的店只有寥寥几家,位于武吉士路森林大厦的洪茂升是规模最大的一家。在一个休息日,她早早来到森林大厦,在售卖电子产品的店铺里绕了半天,才循着一阵《金刚经》的乐曲声找到了地方。洪茂升里的佛像从小乘到大乘,风格遍及整个东南亚,可菲利普太太的那种却没有看见。文惠跟老板描述了样子之后,老板说这是阿耨观音,以前店里确实在卖,可最近两年没有再进货了。文惠恳求了半天,老板才答应帮她联系一下生产厂家,看能不能再给订做,这几年原材料费和进口税都涨了不少,各种费用估算起来,大概需要两千块钱。文惠试探地讲了价,可是看老板很坚持,就没有硬砍,生怕把心中仅存的一线希望给砍没了。从此以后,她天天盼着店铺老板的消息。
两周前店家终于联系了文惠,说佛像到了,让她按讲好的价格付款。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准备好的钱却丢了。这两千块如果让文惠自己再重新凑,实在让她有些心疼,最主要的还是不甘心。
上次跟刘阿姨谈得不欢而散,她本来想把这事情放一放,看能不能有什么转机。可是随着日子一天天流逝,钱不但没有找回来,刘阿姨也开始躲着她了。文惠左思右想没了主意,整天在菲利普太太家里坐卧不安。
菲利普太太临走前,给过文惠一个紧急联系人的电话,这个人叫南希,是跟菲利普太太住在同一栋公寓的邻居。听说她是个全职太太,家里也雇着刘阿姨做钟点工。
文惠住进来不久,南希就不请自来地跑上楼来敲门了,她风尘仆仆的,据说和朋友们刚从柬埔寨做了义工回来。南希长着一副亚洲人的面孔,说的却是一口标准的伦敦音。她看出文惠对那只猫不够热情,煞有介事地给她示范怎么跟猫互动,那口气和姿态俨然菲利普太太家里的一位亲戚。文惠耐着性子听她说够了,客气地把她送到门口。后来她就没有再登过门。
钱和瓷像的事情,文惠犹豫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她。
也不是没有想过找彭兆平,可像他那样多疑的人,告诉他免不了又要被他恶意揣测,白白耗费唇舌,又惹出一番纠缠。再说自从上次删掉了他的号码之后,她已经下决心不再跟他联系了。
最近文惠脑海里总是不自觉地闪过一些从前的情景。记得两人刚交往没多久,她去公司接他下班,不巧写字楼的电闸跳了,电梯停止了运行,两个人不得不走楼梯下楼。在闷热逼仄的楼梯间里,文惠眼前一片混沌,心里就有点发慌,忽然感觉彭兆平那温暖的大手贴过来,不由分说地分开她的五指,与她的手紧紧交握着。一股暖流瞬间从手里注进心里,她突然觉得能被这样牵着往前走,一切都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可现在文惠觉得,自己一直就没从那片混沌里走出来过。
还有一个礼拜菲利普太太就要回来了,瓷像毕竟是在她眼皮底下砸的,怎么也要有个交代才行,文惠忍不住又去了店里。好在那尊订做的瓷像还在,无论是从材质还是从样式来看,它简直跟菲利普太太家的一模一样。文惠看了,心里的纠结立刻就烟消云散了。她一咬牙,从自己的银行卡里刷了两千块。
瓷像那沉甸甸的分量压在文惠手上,她心里反倒松快了不少。她隔着黄色的绒布,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完好无损的陶瓷,感觉仿佛自己也重获了新生似的。
回到菲利普太太的住处时,文惠觉察到家里似乎有些异样,屋子里静得不同寻常,那只黑猫没有像往常那样从某个角落里探出头来看她。
从一楼到二楼,房间的各个角落都被她找遍了,还是没有猫的踪影。文惠急出一头冷汗,她环顾着空荡荡的房间,调整着呼吸,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地板清洁剂的味道在空气中若有若无地飘散着,她猛然意识到刘阿姨刚刚来打扫过了,忙冲到厨房,发现猫砂盆和猫碗也不在那里。
她隐隐猜到发生了什么。
文惠硬着头皮按响了南希家的门铃。门一打开,她就看见那只黑猫慵懒地在南希怀里趴着,紧绷的神经才稍微松弛了一些。
南希不动声色,把黑猫举起来凑到文惠面前问她,你要抱走吗?见文惠略一迟疑,又很快收回了手,冷笑道,到现在还是不敢抱它,你是怎么胜任这份工作的?听见她把“工作”这个词说得很重,文惠没有作声。
南希又拿起一样东西在文惠面前晃了晃,你知道吗,这要是在英国,我们是可以告你虐待动物的。文惠暗暗吃了一惊,那不是自己叠的那张报纸条吗,怎么到她手上了。
事情不是您想的那样,文惠刚解释了一句,南希就摆摆手打断了她,你不好好看猫就罢了,还接二连三地在家里搞事情,听说那尊观音像被你拿走了?是不是跟你那个私自带上门的朋友商量着做的?你别忙着否认,刘阿姨亲口告诉我,那天她去打扫的时候,闻到客厅里好大一股烟味,还看到垃圾桶里扔着烟头。
文惠的耳边轰的一声响,她担心的情况还是发生了,记得彭兆平那晚走后,她累得倒头便睡,第二天中午才起床。刘阿姨已经进来打扫了……也真怪她自己不谨慎!
文惠努力清了清干燥的喉咙,想说点什么,恍惚间又听南希说道,你们也真是打错了主意,那瓷像是菲利普太太拿着照片托我在乐购网上给她淘的,加上邮费也才二百块出头,你们拿去卖了也挣不到什么钱。可这种行径实在让人恶心。说到这个,你反倒怪刘阿姨偷了你的钱,她在我这里哭诉了好几次,说毕竟你这钱是在菲利普太太家丢的,给她回来知道了也不好看,还说要不是你说的数额那么大,她真想索性就赔给你算了……刘阿姨在我家做很久了,她是什么样的人我知道,可是我不了解你,知道你做的这些事后,更不愿意相信你。我给菲利普太太发了邮件,从今天起小墨就在我家了,给你一晚上的时间,收拾好东西,该回哪就回哪去吧。说完,便不由分说地把文惠往门外撵。
门在文惠面前关上的一刹那,她似乎看到那只黑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
文惠不记得是怎么回到楼上的,等她回过神来,发现自己正靠着门坐着,脸颊滚烫,手脚冰凉。她感觉一颗心不断地往下沉,直到把胸腔拉出一个巨大的洞,里面空荡荡的,冷风还在嗖嗖地往里灌。一时间她迫切地想抓住点什么东西在手里,忙爬过去把新买的观音像掏出来。只见观音的脸色温润如玉,正用一副洞若观火的表情看着自己。她摸到雕像底座上还有个圆洞,里面塞着一张纸片,她掏出来一看,原来是用几行小楷写的《普门品》:或飘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文惠读着读着,一股委屈涌上心头,那字迹也变得模糊了。这时天光陡然变暗,远处雷声隐隐传来,看来今晚免不了又要迎来一场雨,就如同那天晚上的一样。
那晚的暴雨一直下到半夜都没停,震耳欲聋的雷声撼动着窗玻璃,闪电把房间照得如同白昼。文惠莫名地从睡梦中惊醒,迷迷糊糊地起床摸到楼下客厅喝水,那黑猫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里去了。在黑暗中,她突然看见主卧门口闪身出现一个提包的人影,蹑手蹑脚摸向门口。文惠吓得睡意全消,惊叫一声。那影子闻声僵了一僵,扔下包便朝着文惠迅速移动了过来,从高大的身形看应该是个男人。男人嘴里对文惠说着什么,可声音被雨声吞噬了大半,她听不清楚。文惠拖着发软的双腿,磕磕绊绊地绕到沙发后面,抓起听筒想要报警,男人一个箭步扑上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腕。
观音像在地板上摔碎的同时,台灯也被拧亮了,灯光下,一个神情窘迫的西方男人坐在地上瞪着文惠,血一滴滴从他按着瓷片的手指缝里流下来。包的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七零八落撒了一地,是好几件看上去价格不菲的女式手表和首饰。文惠觉得这个男人很眼熟,她忽然意识到,他长得跟墙上照片里的菲利普先生一模一样。
两个人谁也没料到会在这样的时间地点遇上彼此。听文惠解释了之后,菲利普先生摇了摇头,轻声咒骂了一句,不知是在怪菲利普太太事先没有跟他交待清楚,还是怪自己最近时运不济,次次搞得全盘皆输,赌场给他下达了今日内还款的最后通牒,是个大数目。可他那几张信用卡都已经刷爆,情急之下只得赶回来,腾挪些保险柜里菲利普太太平时不大用的细软,权当临时救急。
菲利普先生的手指被割了深深一道,恐怕要留下永久的疤痕了,可他此时却无暇顾及,只是胡乱包扎了伤口,就准备动身出门。毕竟时间紧迫,经不起任何耽搁,他得先去银丰典当行兑换现金,再赶去赌场还钱,事情办妥之后,还得连夜回机场坐飞机。
临走前他告诉文惠,这尊瓷像是几年前他们夫妇俩逛森林大厦的时候在一家店里看到的。当时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喜欢,没想到菲利普太太有心买了回来,在他戒赌一周年那天当作礼物送给了他。
你听好了,这瓷像不是我打碎的,也不是你打碎的,它从来就没有被打碎过,你也从来没有见过我,说着,菲利普先生又从保险柜里摸出一叠钞票,随手点了几张装进一个信封递给文惠,这件事情还要麻烦你跑一趟,请一定要按照原样买一个回来,钱大概是这个数,多余的你自己留着吧。
见文惠犹豫着不想接那信封,菲利普先生意味深长地说,你还年轻,在婚姻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为真相刨根问底的。我太太是个要强的女人,你这样做不仅是在帮我,也在帮她,更是在帮你自己,明白吗?
文惠小心翼翼地把那尊新买的观音像摆放在核桃木的长条桌子上,瓷像旁边紧挨着她想用来拨打报警电话的黄铜电话机,电话机的旁边是被菲利普先生拧开的那盏金丝鸟笼灯。这个奇异的组合又重新被摆放在一起了,这一切看上去就跟文惠第一天看见的时候一样。
文惠打开电脑,输入了菲利普太太的邮箱地址,她盯着文本框里闪动的光标发了一阵呆,又把电脑合上了。她起身回到房间,把自己的东西一件件收拾好,一拎行李,发觉居然比来的时候重了不少,这才想起来,那堆旧瓷像的碎片还在里面塞着呢。
文惠回到出租屋楼下的时候已经是半夜,她发现自己房间的灯居然亮着,暖橘色的光朦朦胧胧地从窗户里映出来,把周围的夜色都晕染得温柔了许多。文惠眼眶一热就掏出了手机,虽然他的联系方式被她删掉了,可那串号码早已经烂熟于心。
你在哪里?
一听到那个熟悉的声音从电话那端响起,文惠就忍不住呜咽起来,都是你不好,那天你不该——文惠话说了一半,只听彭兆平讪讪地说道,都是我不好,可那两千块钱我一分也没有动,都给你留着呢。
你说什么?文惠听了心里一紧。
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怎么现在才找我?你非要赶我走,我也是被你气昏了,那晚我看见你口袋里的钱,突然觉得这都你欠我的……你回来吧,我再也不提回家住的事了,好不好?你房租的一半我还会照付的。不过话说你们这个老板可真大方,看几天猫的报酬都快赶上我一个月的工资了,怎么给的还是现金,是为了省银行过户的手续费么?
文惠没有再说什么,她狠狠掐断了电话,转身就朝着离家相反的方向走。雨终于下起来了,豆大的雨点一滴滴砸在她身上,穿过她的皮肤落进她心里,凉丝丝、冷嗖嗖的,她感觉身上的每一个骨缝里都透出一股寒意。
一个礼拜后的星期一,文惠忐忑不安地来上班。到目前为止,菲利普太太没有给她发过一封邮件,打过一个电话,她不知道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可等她到了公司才发现,菲利普太太的位置依然空着。人事部说,菲利普太太家里有点私事要处理,又向公司申请延长了几天假期。文惠听了,一颗心不知道该悬着还是该放下。
又过了几周,菲利普太太仍然没有回来。不仅如此,听说公司批准了菲利普太太的内部平级调动申请,她下个月就要去中国北京的分公司报到了。关于菲利普太太的八卦,公司里传得有鼻子有眼的,有人说菲利普太太从英国度假回来没多久,就跑到公寓楼下的保安室调取了监控录像;又有人说菲利普先生半夜从国外潜回家偷拿东西的证据一到手,她就火速聘请了一位离婚律师,争取到了女儿的抚养权;还有人感叹说真是一次赌徒,一世赌徒啊,菲利普太太这回终于看透了。
这时候文惠从来不参与讨论,她总是在电脑面前假装忙碌着,听觉的雷达却敏锐地接收并消化着房间里碰撞的每一句信息。
接下来的时间,菲利普太太都没有到公司露过面,可公司上下的所有同事都收到了一封来自她的邮件。在那张共享的电子表格里,菲利普太太给公寓里每一件不准备带走的旧物都拍了照片,还在物品旁边明码标价,请同事们看到有中意的,就在价格旁边写下名字,先到先得。同事们一边好奇地浏览着表格上的东西,一边不住地感叹着,真不愧是菲利普太太。
一个月后,季风交替的季节已经过去,天气总算没有那么沉闷燥热了,到了傍晚甚至还能感受到几丝凉风。彭兆平搬出了文惠的出租屋,彻底从文惠的世界中消失了。文惠跟公司签署了正式员工的合同,她的新上司过几天就会来办公室上任。
这一天,一个大纸箱从菲利普太太家寄到了公司,前台通知相关同事过来认领从菲利普太太那里购买的旧物。当有人把一样东西放到文惠桌子上的时候,她觉得很意外,她并没有从菲利普太太那里买任何东西,甚至连那张电子表格都没点开过。可那个缠得密密实实的塑料包裹上面,分明用马克笔写着她的名字。
说不定是她友情赠送的呢?同事冲她眨了眨眼。
随着包装纸越撕越薄,手上那种似曾相识的触感让文惠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她迫不及待地撕开仅剩的那几层包装,那尊被她摩挲过无数遍的观音像赫然出现在她的眼前,还是那温润如玉的脸色,还是那副洞若观火的慈悲神情。
文惠深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一把翻过瓷像的底座。
果然,那个圆洞被填得满满的,原封不动地维持着文惠临走前留下的样子。除了那张用小楷写的《普门品》以外,还有些其他的。
文惠伸出颤抖的手,把那些旧瓷片一个一个从洞里掏了出来。这些瓷片棱角分明,形状各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上面都沾染着菲利普先生斑斑的血迹,它们在公司白炽灯的映照下,正反射出星星点点的寒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