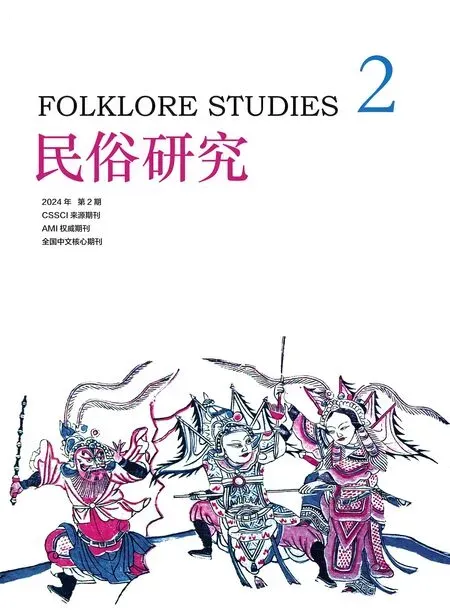文化治理视野下的宗族复兴:甘肃连城铁氏谱庙重修中“历史”叙事的构建、拼装与诠释
2024-06-11赵亚川
赵亚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乡村地区此前被取缔的各类“传统文化”进入复苏状态,在此大背景之下与宗族相关的各类活动得以复兴。这些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宗族文化复兴,或表现为宗祠(或家庙)重建,或表现为家谱重修,一直持续至今。宗祠家庙及谱牒的重修无疑是一次“社会记忆恢复”(1)参见景军:《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吴飞译,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张小军:《再造宗族:福建阳村宗族“复兴”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第167页。的过程,但在现实的政治境况下,却并不一定合法。因此,在民间,这些重修或重建工作往往是在“保护和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话语模式下进行的。能动者主动将自身之实践纳入国家既有的政策话语体系之中,以获得正当性与合法性。毋庸置疑,曾经被视为“封建糟粕”的各类民间文化获得重生,得益于国家“治理术”(governmentality,或译治理性)的调整。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说过,“社会问题起于文化失调”(2)费孝通:《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费孝通:《费孝通全集·第1卷(1924-1936)》,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故而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乡村文化治理问题必然成为重要的议题之一。尤其是在遗产时代的当下以及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完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也必然是国家所强调的“治理有效”的题中之义。何谓文化治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尚未形成一致看法。学者们一般将文化治理的学术源流追溯至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包括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霍尔(Stuart Hall)及本尼特(Tony Bennett)等。文化治理成为一个全球性理论议题与本尼特有着一定的关系。他强调要将政策纳入到文化研究之中,并将其视为特别的治理领域。(3)[英]托尼·本尼特:《文化、治理与社会——托尼·本尼特自选集》,王杰等译,东方出版中心,2016年,第203-225页。就汉语学界来说,王志弘、刘俊裕等最早引入了文化治理的理论概念并加以阐发。(4)参见王志弘:《文化如何治理?一个分析架构的概念性探讨》,《世新人文社会学报》第11期,2010年7月;王志弘:《文化治理是不是关键词?》,《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82期,2011年6月;王志弘:《导言:文化治理、地域发展与空间政治》,王志弘等著:《文化治理与空间政治》,(台北)群学,2011年,第5-24页;刘俊裕:《再东方化:文化政策与文化治理的东亚取径》,(高雄)巨流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胡惠林、吴理财、傅才武等对文化治理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5)参见胡惠林:《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吴理财:《文化治理的三张面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傅才武、秦然然:《中国文化治理: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简单来说,文化治理,即文化的作用或效用,“经由文化来治理,可能以文化本身为对象,但也经常以经济发展或政治秩序稳定为目标”(6)王志弘:《导言:文化治理、地域发展与空间政治》,王志弘等著:《文化治理与空间政治》,(台北)群学,2011年,第7页。。这样一种视角,抛开了人文社会科学界有关文化的繁琐定义,凸显了“文化的作用”。文化的作用即文化治理。吴理财、解胜利在总结中国学界对乡村文化治理的几种路径之余也指出,文化治理就是多元主体以合作共治的方式治理文化,并利用文化的功能来达成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治理目标的过程。(7)吴理财、解胜利:《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因此,我们不难看出,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工具(手段),亦是目标。着眼于官方政策与社会力量之于文化的“战略”(strategy)与“战术”(tactics)(8)关于这一对概念的相关讨论可参见Mich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xiii, xix-xx, 35-37;[英]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61-264页;[澳]卜夏南(Ian Buchanan):《民族志与社会实践导读》,[英]瓦尔德(Graham Ward)主编:《塞杜文选(一)——他种时间/城市/民族》,林心如译,(苗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第127-132页;吴飞:《“空间实践”与诗意的抵抗——解读米歇尔·德塞图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我们可以用文化治理来观察和探讨具体的能动者如何以文化之名义来进行实践、协商和展示。
众所周知,在中国农村,所谓乡村治理,是一个在长期的农耕文明社会中形成的具有闭合性和自洽性的文化能力体系,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乡域性,甚至村域性特征。(9)胡惠林:《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建设:从传统乡村走向现代中国乡村》,《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宗族或家族在这样一个闭合、自洽的村治体系里曾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尽管宗族在20世纪以来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遭到了严重的冲击,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它很快便迎来了“复兴”,重新成为学界关注乡村治理时所考察的重要因素。本文意不在关注宗族复兴所引发的乡村政治权力角逐,而是以具体的家族/宗族复兴过程为个案,观察地方文化精英如何依靠官方的文化政策,利用乡民的记忆、地方社会的历史叙事等,拼装组合完成其“文化复兴”的事业,并考察这些能动者具体的“文化战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文化成为了调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
一、地方脉络中的铁氏家族及其历史记忆
惟我始祖自大清年间卜居于连城铁家台,箕裘以垂其统,耕读以世其家,人丁成立,家道渐昌。惟我祖职司元戎武略,特传于连城,位列长侯,忠贞庶超于河西,声虽未播于四海,而名永传青史也。(道光二十年[1840])
吾始祖翁讳脱脱木尔、脱脱卜化、郑加尔之三翁居住那亥城,光宗耀祖,协力同心,勇耀一世,子孙繁衍。(咸丰七年[1857])
有余亲铁氏者,其先代系出有元陀陀之苗裔也。历有明以来,世居连邑铁家台。卜年而卜世焉。(光绪壬午年[1882])(11)《铁氏族谱》,内部资料,2019年,第7、11、35页。
尽管书面文字与口头传述有所出入,但一些基本的要点大体清晰,即铁氏来连始祖确系居住于连城铁家台(那亥城),或曾在明清时担任过地方某职。后子孙繁衍,枝叶四散,族人迁至连城周边各处为生。
在这些铁氏族人的家族史叙述中,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其先祖是所谓元陀陀(脱脱)者,这一点在铁氏族人后来的记忆和叙事中被不断放大。放大之原因在于其可以与地方统治者鲁土司直接关联起来。据连城鲁土司家谱所载,其始祖名唤“脱欢”,是成吉思汗的后裔。(12)乾隆《鲁氏家谱》曰:“始祖讳脱欢,元世祖之孙也。”参见乾隆《鲁氏家谱》,鲁光祖、鲁璠、鲁纪勋撰,汪受宽等校注整理:《永登鲁氏家谱校注》,三秦出版社,2019年,第217页。对于鲁氏土司始祖“脱欢”之身份学界多有争议,可参见魏文:《元明西北蒙藏汉交融背景中的鲁土司家族政教史事考——以红城感恩寺藏文碑记释读为中心》,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27-465页。铁氏家族乃至一些非铁氏族人传言,铁家始祖(陀陀或脱脱)与脱欢同族、同姓、同宗,是其麾下心腹干将。与这一传言大体相当之内容,笔者曾在铁氏家族于解放初编修的一部家谱之序文中看到过,“鼻祖原籍南京人也,明季时因元陀公行戎西迁,从公而至甘肃省平番县连邑土司所属之地铁家台子,因以安民”(13)《铁氏族谱》,内部资料,2019年,第39页。。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有家谱则直接这般写道:“铁氏宗谱,由来旧[久]矣。特因乱而失之,则某世某翁不得而详。孰昭孰穆,不得而明,据铁氏后裔口叙[述]略知,铁氏先祖是蒙古人民,族别是达达族,当时跟随连城鲁土司而来,定居现连城镇东河沿铁家台。”(14)《铁氏族谱》,内部资料,2019年,第73页。
毋庸置疑,铁氏先祖与鲁土司同宗(始祖系弟兄)同族(皆为蒙古族(15)此处即涉及到鲁土司之民族属性,需稍加注明。对鲁土司之族属,历来多有争议,或称其为“土族土司”,或视其为“蒙古族土司”。然随着史料的发现,鲁氏系“蒙古裔”已基本得到学界认可。鲁氏祖先原为蒙古部落的一支,在元代时“就已是西北望族,拥有一块封地,并掌握了一支武装”(魏文:《元明西北蒙藏汉交融背景中的鲁土司家族政教史事考——以红城感恩寺藏文碑记释读为中心》,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454页),亦崇信藏传佛教。明时,鲁氏归附朝廷,进驻连城地区,并在此建立自己的衙署。故而可以说,“连城鲁氏家族之族属是以蒙古裔族群为主体,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与辖内或周边藏、汉等民族长期交流、交往、交融,形成的一个新的区域性命运共同体”(陶鸿宇、贺卫光:《连城鲁土司家族渊源考辩》,《社科纵横》2021年第1期)。)的关系在铁氏族人当中不断被强调。以至于现如今铁氏家庙的庙管如此说:“可能我们祖上是蒙古人,跟土司一样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后来汉化了么,现在就是汉族么,成吉思汗的汉族名字叫铁木真,我们姓铁可能就是这样(来)的,具体的历史挖不清了。”(16)访谈对象:家庙庙管铁福(化名,本文出现的铁家人之名均为化名);访谈人:赵亚川;访谈时间:2019年9月6日;访谈地点:甘肃连城铁家家庙。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地方历史的脉络中,铁氏家族的叙事越来越多地将他们与土司关联起来。作为地方绝对统治者的兄弟或得力干将,铁氏在地方上的地位可见一斑。不仅如此,铁氏族人说他们是土司之外连城地区唯一同时建有家寺和家庙的家族。铁忠在回忆旧时家寺、家庙盛景的文章中直言了这一点。(17)参见铁忠:《原家佛寺、家神庙面貌陈述》(手稿);修改稿(打印稿)名曰《家寺、家庙变迁记》。后再经修改收入《铁氏族谱》。参见《铁氏族谱》,内部资料,2019年,第378-381页。不仅如此,他还写道,随着铁氏家族不断发展壮大,土司也很是忌惮,还从建筑的风水方位上来进行压制。(18)参见《铁氏族谱》,内部资料,2019年,第379页。作为土司的弟兄或下属,其家族的发展有盖过土司之势头,势必引起土司的嫉妒,这又从侧面凸显了铁家在连城地方的势力与地位。
1932年连城土司改土归流,鲁氏失去了其在地方上的权力。1958年,连城境内众多寺庙被毁,其中土司直系后裔虽绝,土司家寺(妙因寺)却得以幸存,只被毁去了其中的佛像,而铁氏家族的家寺、家庙皆被损毁。1968年省政府决定在连城地区筹建铁合金厂,铁家台被征用,铁氏族人遂迁至今鲁家湾及其北一带,家寺、家庙亦被彻底拆除。据铁氏族人说,现如今的西铁中学所在地正是家寺、家庙之原址。
相较于铁家的寺、庙,土司家寺的命运则是另一番景象。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逐步发展,1981年,妙因寺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紧接着1982年,原先被毁的佛像基本恢复,寺院重新开放。到了1996年,寺院被纳入鲁土司衙门旧址之中,被列为第四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毋庸置疑,重新开放的妙因寺也被政府批准为合法的宗教活动场所。(19)参见杨宪锋、黄雪明编著:《永登民族宗教概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第61页。尽管鲁氏土司并无直系后裔在世,但连城曾是土司旧地的历史命运,以及前述这些文物保护单位的身份认定均为这个西陲小镇戴上了“文化”这颗温润的珍珠,“土司文化”成了小镇发展的重要名片。以土司文化领衔的连城镇自然受到更多关注,1999年它就被甘肃省列为“省级旅游型小镇建设试点镇”,2006年又被评为“甘肃省历史文化名镇”,2007年则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参见赵永生、陈小芹主编:《连城史话》,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6页。
指标含义:10(20)千伏接入的新能源消纳率=规划期内已接入电网或完成接入系统方案评审的用户数/规划期内申请接入的分布式光伏等新能源用户总数。新能源消纳率要求达到100%。
除了仍是小镇的成员外,这一切看起来似乎与铁氏家族关系并不大。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土司文化”为推手,致力于连城的发展与治理,着力将其打造为一个极具特色的西陲边镇。2012年,首届“中国兰州·永登连城土司文化旅游节”在连城土司衙门前的广场上举办,自此之后每年一届,延续至今。以文化为手段,目标在于经济之发展和社会之进步,这一文化治理的要义在连城不可谓不明显。然而,包括铁氏家族在内的众多连城民众,却并未感受到这一“土司文化”所带来的福利。十几年下来,连城并没有因为独特的“土司文化”而声名远播,地方偏远、条件落后似乎一直都是小镇旅游开发难以抹去的标签。抛开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连城镇1949年以来所经历的一系列变化,也使我们更加明晰地看到乡村文化治理本身的变化,即从对文化现代化或乡村文明化的重视,转变到当前以乡村发展(振兴)、经济收益为主要导向。也正是在文化治理体制中的作用及意义如此变化的情况下,地方社会中的主体或能动者方可依据具体形势,在政策、社会价值观、个体(文化)资本及地方社会之传统或惯习的综合影响与作用下,展现其具体的能动性,重建、拼贴和展示各类“传统”文化,铁氏族人制/再造宗族的故事便是其中的例子。
二、制作宗族:铁氏谱、庙中的记忆展示与拼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地区此前被取缔和禁止的各类“传统文化”得以复兴,重新进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一定程度来说亦是国家“治理术”之一环,其目标则非治理本身,主要关乎民众的利益:地方经济之发展,民众物质与精神生活之提升及社会之稳定。如此,一种国家引导、民众主动迎合的文化治理模式便落实、扎根于中国乡村大地,并依据不同的本土情境,呈现出多样化的样态。铁氏家族的故事所凸显的正是文化治理本土实践之一种。
铁氏宗族的诞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可以说这一过程到现在也并未全部完成。而铁氏族人所有的行动与实践皆是在主动迎合国家的文化政策与发展主义愿景下完成的。前文提及的铁忠,是造宗族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在回忆旧时家寺、家庙盛景的手稿中曾写道:“(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面改革开放,寻根祭祖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当时七山乡(连城邻乡)的铁氏后裔铁林主动串乡走户,积极联系,发动铁氏族人重新修建寺庙,得到族人的支持。1994年起,被毁的铁氏寺庙,重新在鲁家湾露出它慈善而灵验的面容。”(21)参见铁忠:《原家佛寺、家神庙面貌陈述》(手稿)。铁氏族人之所以开始联络族众,重建旧时家庙,皆是因为“寻根祭祖”的传统。国人重乡土之情和尊祖敬宗之愿,凸显的是对历史、文化和传承的重视,铁氏家族之举正是如此。
不仅如此,在铁忠等人看来,昔日被毁去的铁氏家寺、家庙乃是连城地区重要的“文化遗产”。老人记忆中的家寺、家庙宏伟秀丽,美轮美奂,甚至可以与鲁土司家寺(妙因寺)相媲美,正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既为“文化遗产”“历史文物”,那么重建它们,并无不妥。1994年底,简陋的小庙在鲁家湾“露出它慈善而灵验的面容”。1995年,铁氏族人开始四处筹款,在上一年所修之简陋小庙基础之上开始了家神庙的重建事宜。除了四处筹款,铁氏家族自己的木匠也发挥自身特长,与雇来的匠人一起肩负起修庙的具体工作。两年后,三间大殿落成。2005年,铁氏家族请连城地区有名的木雕匠人雕刻了始祖“爷爷奶奶”的神像,经装藏、熏沐、开光等仪式后供奉于大殿莲台之上。2006年由家神庙庙会的会长铁国福牵头四处募捐,又得附近厂矿企业的资助,在庙内新修六间厢房,建造了山门,并对大殿及山门进行了彩绘。至此,铁氏家庙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一个具备了独座院落、三间大殿、六间厢房与一座山门规模的家庙就此落成。
历经数年时间,铁氏家族积极行动,重构了他们“遗失”的历史,重建了族人期盼的“慈恩被后代,灵验照四邻”的家庙。2006年家庙架构基本完成时,铁氏族人便在庙中立起了石碑,名曰“铁氏家佛寺庙修建记”,其文写道:
树有根,水有源,人有祖先。
我铁氏先祖原籍南京。元末明初我先祖脱脱木尔、脱脱卜化、郑加尔(未留后)三翁随连城鲁土司始祖脱欢来西北,分别定居于民和史纳、那亥城(铁家台)。后在铁家台分建家佛寺、先祖庙。一九六八年因建西北铁合金厂,根据省委第二四二号文件,铁家台居民全迁居鲁家湾,寺庙先后被拆。一九九七年,由族人发起,捐资出力,在鲁家湾新建大殿三间,寺庙合并,依俗定于农历八月初八为祭奠日。二○○六年又建山门、厢房、围墙。(22)《铁氏家佛寺庙修建记》,2006年,作者录自铁家庙院内之石碑。
石碑以文字的形式向铁氏族人展示了其先祖来连之历史。不难看出,碑文的内容综合了铁氏家族遗留的老家谱、老人们的口述史及连城的地方历史(见前文)。负责庙宇重建的铁忠等文化精英,将一系列元素(迁出地、始祖名字、地方史等)组合拼装在一起,重构了铁氏家族的历史,并将其展示给族人,以为“信史”。毋庸置疑,这一“信史”的重构在铁氏族人当中是成功的,笔者在田野调查过程中问及铁氏家族的相关历史时,他们帮我打电话给庙管,让他直接带我去看庙中的碑文——“历史上面写着了”。家庙不仅是一处供族人祭祀祖先、缅怀祖德的地方,同时也被视为记载、怀想和展示历史的场所。
在社会经济发展、国家文化政策的引导下,铁氏族人以“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重视“寻根问祖”为导向,完成了家庙(家佛寺)的修建,亦开启了铁氏宗族制作的新篇章。虽然家寺、家庙合二为一,昔日雕梁画栋的辉煌盛景不再,但一个供族人拜神祭祖的新场所得以确立,每年农历八月初八的始祖圣诞会也重新在这间小庙中举办。然而,铁忠等人很快又发现了新问题。在《铁氏源流寻访记》中,铁忠不无心痛地写道:
每岁年初,有族人趋向家庙祭祖祀宗,偶聚于斯,却互不相识,互道名讳,而嗣派无法对应,难辨尊晚,不便称呼;知是铁氏一族,其脉何支,其支几许,无法理折;旧时变迁,现时兴衰,无从晓得。祀毕,默然分散,各返原程,一出庙门,视同陌路。此情此景,使人怅然若失,久久为憾,耿耿于怀。(23)铁忠:《铁氏源流寻访记》(打印稿)。
家庙虽已建立,然其却只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拜神”之所,更多展现出的是它“灵验”的面相。铁氏族人赴庙会只是为了求得平安顺遂,对于家族或宗族共同体之建设并不在意。何以会出现这种状况?在铁忠看来,究其根源乃是缺乏“一部完整沿袭的族史资料——家谱”(24)铁忠:《铁氏源流寻访记》(打印稿)。。为改变此种情况,铁忠在每年祭祖庙会上,都组织与会人员积极讨论,希望联络动员铁氏族人共同努力,实现重修家谱的夙愿。2005年庙会时,参加庙会的众族人统一意见,决心对铁氏源流进行一次全面摸底寻访,并确定了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和具体工作:一是以铁家台为中心,对铁氏族人(甘青两省)进行摸底造册;二是搜集现存老家谱,参照序言,理清脉络;三是依据老家谱,排辈列序;四是建立相关的规章制度,组建类似宗亲会的组织。可以看到,包括铁忠在内的铁氏精英意图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同姓联宗行动,且地域范围不限于永登县内(遑论连城镇内)。他们试图进行跨省联宗,将他们想象中可能有关系的铁氏族人全部囊括于内,编修一部“大规模联合型”(25)钱杭:《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40页。的通谱,以此来纠正“源流不一,嗣派紊乱,大小辈分不分”的尴尬窘境,让祀同一始祖神灵之铁氏后裔,不必“视若无睹,互不相识,形同陌路”,进而共筑宗族共同体。
目标确定后,铁忠及家庙庙会负责人国福、铁存、铁剑、铁正等开启了他们的追踪寻访之路。从2005至2010年这五年间,他们先后对甘青两省熟悉的铁姓族人聚居地进行了走访,收集了不少资料。2018年庙会之际,名为“致同宗族人的一封信”的巨幅喷绘在家庙内挂出,向参加庙会的众人阐释了编修家谱的意义,其文称:
欣逢盛世,修史撰谱已成风气。周边家族各支系大多都有谱可读,而我铁氏族内支系,除青海民和所撰一三十辈族谱,尚未有大的行动。应借而今,神州昌盛,社会和谐之机缘,有谱续修,无谱建谱。修谱联宗睦族已成为我铁氏家族生活中的当务之急。兴修家谱,整理排行,势在必行。(26)《致同宗族人的一封信》,2018年,笔者从铁家庙墙之海报原文采录。为不影响阅读,笔者在“尚未”和“大的行动”之间补充“有”字。
整篇文字强调盛世修谱之时机恰当,既是承继历史,亦是继往开来,有意识地将联宗修谱之事“纳入贯穿古今的时间叙事之中,显然是有意迎合国家发展主义愿景”(27)梁永佳:《庙宇重建与共同体道德——以大理Z村空间差异为例》,《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3期。。要言之,祖国富强昌盛,社会和谐,此盛世之际当积极撰修家谱,正是所谓的“盛世修谱”。国兴盛,则家和谐,此时重修家谱是恰逢其时,也势在必行。由铁忠领头的寻访组,组成编辑团队开启了家谱编修,并聘请了西宁市书法协会的成员汪先生作为指导。他们将所收集的各类资料整理归类,增设新的内容,编辑刊印了《铁氏族谱》。2019年农历八月初八的庙会,即名为“铁氏始祖圣诞暨《铁氏族谱》告竣庆典”。庆典当天,参会的人除了永登县境内的铁氏族人,还包括甘肃武威和青海民和的族人代表。就家神庙庙会而言,其在整个连城地区可谓是难得一见的空前盛会。至此,连城铁氏家族修“通谱”“造宗族”之工作可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铁忠等人最初之设想,到最后的成书,《铁氏族谱》均与我们常见的家谱不同,没有世系表,反而多了“户口花名册”“捐款登记表”“庙会活动章程”等内容。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曾说过,族谱乃一套事关起源和关系之宣言,一套组织原则,一幅分布图,一个广泛社会组织架构,更是一个行动之蓝图。(28)Maurice Freedman,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6, p.31.在某种程度上,铁氏文化精英的构想和最终成书的族谱,就是在践行弗氏所说的这些内容。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资料收集、整理和分类,铁忠等人拼贴组装了完整的铁氏家族史叙事。他们根据既存的老家谱,选择了三始祖的名字,而放弃了“元陀陀之苗裔”的叙事。他们完整地梳理出了铁氏家族跟随土司迁徙征战的历史,确立了家族在土司旧地历史中的地位。他们所有行动和实践活动背后的目的和意义自然地呈现了出来——再造一个跨省至少是跨镇的铁氏宗族共同体。2019年庙会时连城镇境内的铁氏族人,以及邻镇大有、民乐、七山等地的铁氏族人皆需缴纳10元的“人头费”,而愿意缴纳此费,则意味着对“一个铁家”(29)笔者参加2019年农历八月初八铁家先祖圣诞庙会时,听到很多人(主要是连城周边的铁家人,而非青海及武威等地的)有“从根上说,我们是一个铁家人”这般的说辞。的认同。与会的成员(亦是连城周边的铁氏成员)都围在铁忠身边,请教他有关家族成员“字辈”的事情,并表示以后的子女当按此字辈来取名,以别长幼尊卑和亲疏远近。借着盛会的氛围,铁氏家族还成立了甘青两省铁氏族人的“族务理事会”(以连城铁氏族人为主),并规定每三年举办一次如2019年般盛大的庙会,尽可能多地邀请甘青两地的铁氏族人赴会,既为祭祀先祖,同时也可联络族人感情,扩大宗族影响力。
2020年,铁氏族人又经捐款捐物,在原大殿右侧建起了始祖殿,正位供奉祖先神像,并于祖先神像两侧的墙上各自设立匾额一帧,上书2019年所修《族谱》中之要文,如“铁氏祖源”“铁氏宗义”和铁氏新拟60字字辈等。如此展示之目的,如始祖殿碑记所言,旨在“供族人进殿即览,警其时刻萦心不忘尔”(30)《重建始祖殿记》,2020年,本文作者录自铁家庙院之石碑。。除此之外,始祖殿的墙壁上还彩绘有二十四孝图,以教育子女践行孝道。庙宇成了文明教化、礼仪教育、价值观培养的场所,族谱也遵从国家规范之语言,满足了国家、地方和族众的共同利益。
三、文化治理与宗族复兴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既已指明,本文所借鉴和引述的文化治理,主要是凸显文化之功能或作用,以此来达成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多重治理目标之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既是工具,又是对象,当然也是目标。与王志弘所研究之中国台湾都市文化治理中的竞争、抵抗等现象不同,本文以铁氏宗族复兴案例所揭示的事实是,乡民主动迎合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大政方针,将其自身的文化实践活动积极纳入到国家认可的治理体系和发展主义愿景之中,呈现出一幅积极配合、共谋未来的画面。正如范可所说,“任何形式的地方‘文化’或‘传统’的振兴和复兴运动在今天已很难说具有任何形式的抵抗意义……整体而言,无论是否受到地方精英的操纵,地方社会对民间传统的振兴,实质上是拥抱全球化的一种理性选择或另类表达”(31)范可:《旧有的关怀、新的课题:全球化时代里的宗族组织》,《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如果说,这场延续至今的复兴运动可以表达出何种的“抵抗”意味的话,那便是在此过程中人们所表达出的“怀旧情愫,以克服因经济多元化和商品化所引起的亲情疏离、社会关系变味乖离的沮丧感”(32)范可:《旧有的关怀、新的课题:全球化时代里的宗族组织》,《开放时代》2006年第2期。。
从开始重建家庙到后来的编修“通谱”,铁忠等人将其具体的实践置于国家政策、社会发展等大的背景之下。譬如说明全社会范围内对追根祭祖的重视,对盛世修谱的强调,以及对重建之物“文化遗产”地位的表述等等,无不展现了这一点。尽管他们对旧时的家寺、家庙满怀眷恋,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孝道的衰落、乡村离婚率的飙升等等,足以淹没破寺毁庙的记忆。故而,当各类曾为“迷信”的“旧”文化可以“去芜存菁”以“优秀”的“传统”文化而重新影响人们的生活时,不管有没有地方精英的操纵规划,一场振兴或复兴运动在广阔的乡村大地上蔓延开来。对包括铁氏家族在内的众多连城人来说,对父母不孝,即便拜再多的神佛都得不到保佑。而求神拜佛,参与各类所谓“迷信”活动,其核心在于劝导人们向善,就像当地民间宝卷里唱的“千万神佛心费尽,借口传言劝人心”。铁氏族人在家神庙中绘制二十四孝图之目的则不言自明。
自宋代以来,续家谱(族谱)和读乡约一直是宗法教育的重要方式,因为族谱不仅排列了人伦位置,其序跋往往也讲述、传达儒家礼法与理念。(33)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增订本),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第211页。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族复兴中亦为人们所重视,甚至成为物质文化极速膨胀时代,人们进行文化“抵抗”的一方阵地。铁氏精英在编修族谱时,在重视人伦次序、礼法观念的同时,也将乡约家训的意义推向了极致,直接与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诸多内容对接、相容,从另一个层面显示了国家乡村文化治理之效用。铁忠等人编修的《铁氏族谱》中单列一节《铁氏品行谆导》(34)参见《铁氏族谱》,内部资料,2019年,第383-387页。下文有关此“谆导”内容之叙述,皆出自族谱,不再一一注明。,对族人“做人、做事”的品行提出了十分细致的要求。族谱要求铁氏子孙须做到“崇仁爱,尚正义,正礼乐,宜明智,讲诚信,首孝顺,须清廉,倡节俭,贵和谐”,要在“继往开来的进程中,始终做到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彰显无愧于时代的正能量”。除此之外,铁氏子孙“作为公民,首先必须要做到爱国、守法”。在此基础之上,言明“光明磊落是处世品格,正己益众是为人根本,勤奋进取是当有精神,敬业奉献是应有作为”。族谱还强调,族人要树立正确的三观,即“大爱无疆、恢宏旷达的世界观,弃恶扬善、明辨荣耻的人生观,切实奉献、利国利民的价值观”。除此之外,族人要唱好人生三部曲——学业、事业与家业:“以博学广识夯实人生基础,以敬业奉献彪其业绩,以正道勤奋隆其家业。”要“远黄,禁毒,拒赌”,“当自强自爱,堂堂正正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在上述大原则之下,对于具体的,如治家(家庭以和为重)、求学(尊敬师长,好学上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务农(吃苦耐劳,淳朴厚道,学习运用先进科技,发展现代农业等)、从商(重德行、重战略,关注自身发展等),以及供职公务(恪尽职守、忠于人民、敬业奉献、公正廉明等)等各个方面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和指导。不难看出,这篇类似“家训”的“品行谆导”在道明儒家礼法和理念的同时,特别融入了新时代的核心价值,通篇内容除了注重修身立德、重视个人事业及家庭和谐等外,特别强调铁氏族人作为国家“公民”,首先要“爱国、守法”。全部“谆导”内容显然是有意迎合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国家这一大共同体之价值导向、精神理念纳入到宗族小共同体的精神文明建设之中,有国才有家的集体主义精神于其中亦是表露不已。
可以看到,连城铁氏家族的个案展现了一个国家引导、地方文化精英积极迎合的文化治理的成功案例。无论宗族复兴或再造背后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其显现在外的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念的主动学习和接纳。反过来讲,也正是借用这些外显的符号与内容,一个跨区域宗族才能够被构建起来。毋庸置疑,铁氏宗族之“制作”离不开铁忠等地方文化精英的努力与操作。铁忠曾是地方小学的老师,参与寻访编修族谱的铁剑是中学老师,铁从是退休职工,铁正是退休的政法干部。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参与寻访、资料整理及最后编修工作的铁氏族人,多数都是有一些“文化”的人。最后,这些“有文化”之人的名字也是写在族谱最前面的(编委名单)。文化精英积极运作,促成了宗族之诞生,同时亦增强了自己在族众中的威望。这些人无疑是国家及地方政府倡导和培育的“新乡贤”。他们凭借自己的德行、威望、名声(当然也应当包括经济实力),在乡村或宗族中起到凝聚乡民或族人的效果。借用杜赞奇的词,这些文化精英或“新乡贤”可谓“保护型经纪人”(35)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他们知道国家政府想要(看到)什么——和谐、有序、“理性”(非“迷信”)及符合主流价值观的乡村文化,同时也知道普通乡民想要什么——保佑平安的祖先神灵。
四、结 语
宗族这个曾经被“污名化”为封建组织,乃至在21世纪仍带有标签的历史文化产物(36)赵增彦:《当前经济欠发达农村乡风文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建议》,《前沿》2010年第13期。,其本身之生存取决于多种因素,尤其是家神庙占重要地位的宗族。与学者在研究庙会时所指出的一样,它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导向联系同样紧密”(37)岳永逸:《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李小云、赵旭东、叶敬忠主编:《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国家大政方针和政策导向在不同时期之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国家“治理术”之一环,只是方式和强调点不同而已。在“迷信与文化两可语境的规训下”(38)岳永逸:《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李小云、赵旭东、叶敬忠主编:《乡村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76页。,连城铁氏族人(不仅仅是精英分子)已然学会了属于自身生存之“战术”,主动地将自身所从事的各类实践活动与国家的主流话语、政策、价值观念等对接、调适乃至融合,以此来赋予自身之实践以正当性与合法性。由此,重建家庙便是恢复“文化遗产”,编修家谱便是在盛世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民众祭拜祖先神灵是怀祖、追祖感情之表达等等。当然,作为主导此次宗族“制作”或再造的文化精英,铁忠等人通过组装、拼贴、诠释和重构铁氏家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历史叙事,亦有其自身的目的,譬如个人之声望地位,乃至可能的经济效益(笔者在田野调查时并未了解到这一点)。他们所进行的“修家谱、造宗族”这件事或这件功劳,也已然成为他们将来被载入族谱之“资本”。
就其本质而言,铁氏家族围绕着其家神庙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除了“制作”出一个所谓“跨区域”(构想中是跨省)的宗族外,其余一切(拜求神灵祖先,赐福保平安等)同过去的“旧”(迷信)文化相比并未有多少差别。然而,在表达和展示形式上,却更加符合国家的文化政策和导向。农历八月初八的庙会不再仅仅只是念嘛呢(39)“嘛呢”是藏语,也就是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也称“六字大明咒”。连城人所念唱的嘛呢(经),地方俗称“平安经”,包括“交灯经”“六字大经”“交钱粮经”“十二洒净水经”“烧香经”。笔者在田野中所见到的经卷都是手抄本(或钢笔或毛笔抄写)。求平安,也被强调为族人在“省祖探亲”,族谱新增了“道德模范、先进个人”的表彰榜,始祖殿里绘制起了二十四孝图,等等。这些社会所倡导的“正能量”的表征无不彰显了新时代乡村宗族文化之“新”特色。宗族“文化”在地方精英的操刀下,融入了主流文化与价值观念,而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地方振兴、乡村移风易俗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对此亦是默许和认可的,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谋”促成了铁氏宗族的形构与发展。官民双方不再是对立冲突,更多是理解及求同存异,文化成了有效调节国家-社会关系之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