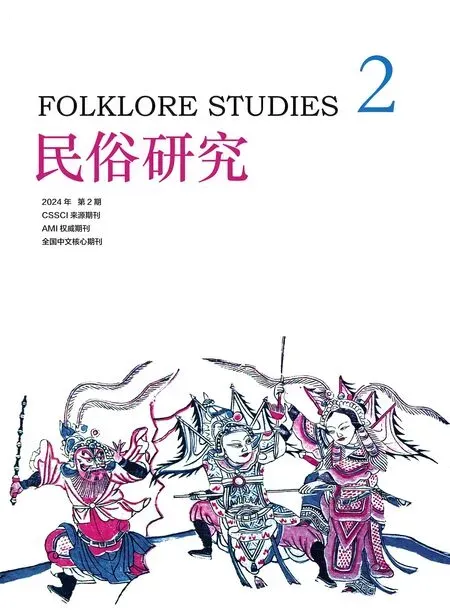公私观念视角下一座乡村祠堂的诞生
——基于对鲁中地区大窎桥村的个案考察
2024-06-11周连华
周连华
“公”与“私”是中国传统社会观念中一对非常重要的范畴。所谓“公”主要是指统治阶层,尤其是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君王,作为“公”的对立面,传统层面上的“私”主要是指地方的家庭。根据“差序格局”理论(1)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家庭,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人的价值主要是通过宗族、群体得以体现,而“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个人,基本上不具有独立的社会意义”(2)刘泽华、张荣明:《公私观念与公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2页。。总之,传统公私观念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治理念,特别是上层统治阶层通过“天下为公”“大公无私”“崇公抑私”等价值标准的建立来强化政权统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公”与“私”的关系不只是反映在政治及道德层面,其在现实经济利益层面同样重要,并成为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视角之一,正如日本知名汉学家沟口雄三在《中国的公与私·公私》(3)[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三联书店,2011年。一书中选取“公”与“私”作为研究的主要线索,来理解中国历史、中国思想乃至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历程,而“公”与“私”的相互交错影响,显现出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脉络。沟口雄三研究的重心聚焦于中国明末清初阶段,此时的儒家学者在“治生为本”观念下肯定了“私”作为“公”的基础性与合理性,并在遵循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谋求个人经济利益,进而维持较好的生存与发展。
实际上,公私观念一直存在于中国社会生活以及政治经济体制之中,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公私问题是中国历史过程中全局性问题之一,它关系着社会关系和结构的整合,关系着国家、君主、社会、个人之间的关系、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关系着社会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社会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核心等重大问题。”(4)张分田:《“公私观念与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综述》,《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基于此,本文对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罗村镇大窎桥村王氏宗族祠堂的当下复建活动展开个案考察,通过开展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搜集到大量民间文献与口述资料,在公私观念的视角下关注王氏宗族祠堂的整个建造过程,进而分析多元参与力量在社会文化心理层面的内在逻辑性与契合性,探寻北方村落多姓杂居的深层社会结构。
一、大窎桥村与王氏宗族
大窎桥村位于山东省中部地区,当前归属于淄博市下辖的淄川区。此地历史悠久,西汉景帝二年(前155)始建般阳县,距今已有两千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淄川区西接济南市章丘区,南邻淄博博山区,东临潍坊青州市,东南与淄博沂源、临朐两县接壤,北与淄博临淄区、张店区、周村区相连。
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淄川区志》记载:“大窎桥,罗村西里许,约建于元代。原以姓氏名杨家庄,明代称吊桥庄,其来历有二:一谓村东有‘吊桥’古迹,一谓该村王姓居官者为其母出殡搭吊桥越门而出,村因故名。清代更称窎桥,1912年以大小改名大窎桥。”(5)淄川区志编纂委员会编修:《淄川区志》,齐鲁书社,1990年,第77页。当前村辖区面积约2.8平方公里,耕地1500多亩,林地300多亩,现有村民1300多户,户籍人口3100多人,人均耕地约0.4亩,符合当地村落人多地少的现实状况。大窎桥村的土地面积和户籍人口比附近其他村落都要多,当前为罗村镇第四大村落。(6)截至2023年底,罗村镇下辖23个村和1个社区,户籍总人口4.4万。镇内户籍人口总数排名前四的村落分别为罗村、千峪村、河东村、大窎桥村。最早居住于大窎桥村的姓氏包括杨氏、闫氏和金氏,明朝初期王氏族人搬迁至此,至明朝中叶,王氏宗族逐渐发迹,且成为享誉一方的名门望族。明中叶之前,关于村落的地方文献记载较少,而在明朝嘉靖年之后,随着王氏族人多有科举入仕的官员涌现,包括世系家谱、诗词文集等在内的文献记载逐渐丰富起来。当前大窎桥村是一个多姓杂居的传统村落,包括王、董、许、孙、李、朱、韩、闫、徐、陈、高等姓氏,其中王氏是村内第一大宗族,人口有1000多人,约占村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大窎桥村王氏是鲁中地区明清时期较为显赫的三大王氏宗族之一,其他两大王氏宗族分别为周村区苏里庄王氏和桓台县新城王氏。三大宗族都以科举闻名于世,大窎桥村王氏明清时期共有146名子弟获得科举功名,包括7名进士和18名举人,多数王氏子弟出仕为官,造福一方,故淄川当地长期流传着“一县科甲、半出王门”的说法,由此可见,大窎桥村王氏宗族科举之盛。此外,借助于宗族实力的不断崛起,明清时期王氏宗族在村中建立起六座祠堂,分为一个合族性质的大祠堂(敦睦堂)以及五个分支小祠堂。
21世纪以来,宗族文化作为村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得到国家认可,续修家谱、祭祀祖先等一系列宗族活动在村落社会不断兴盛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宗族精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那些在乡村社会中占有较多传统资源并在宗族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乡村能人”(7)朱炳祥:《村民自治与宗族关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作为明清时期盛极一时的地方望族,2000-2012年间,在宗族精英的积极运作下,大窎桥村王氏宗族进行了多达5次的家谱续修活动,实际上,这比历史上过往的任何时期都要频繁。(8)大窎桥村王氏宗族世谱由第九世祖王橘肇修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民国六年(1917)前后共续修10次,平均每23.5年编修一次。王氏宗族自2000年完成了第11次宗谱续修之后,又于2004年、2006年和2008年进行了三次增补续修。最终,王氏宗族于2012年完成了合族性的第12次世谱续修,刊印出四卷本的世谱,并分发各地族众。与此同时,自2001年清明节始,祭祖仪式逐渐成为王氏族众每年聚集联谊的重要活动。此外,王氏宗族还集合族之力整理出版了《王氏一家言》《乡园忆旧录》等先辈文集,刊印了8期内部《王氏文化》期刊。随着合族活动的不断开展,王氏族众渴望能够建设一座宗族祠堂,就如本族明清历史上那般,以期通过稳固性的祠堂收宗聚族,展现王氏宗族的当代实力。事实上,复建宗族祠堂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合族活动,在没有适宜宅基地和充足资金的情况下更是很难完成。
二、大公与小公:王氏庄园宅基地归属的博弈
从公私观念来看,“公”与“私”之间是有界线的,而“要形成良性互动的‘公私关系’就需要划定‘公私’的界限”。(9)刘泽华、张荣明:《公私观念与公民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67页。由此,本文将单个家庭视为“小私”,多个家庭所组成的宗族联合体则为“大私”;以村落地缘为基础的聚集区域视作“小公”,而村集体之上的国家政权机构则视为“大公”。大窎桥村王氏宗族在新时代复建祠堂首先经历了“大公”与“小公”的博弈过程。
事实上,在当前村落区域内寻找一块合适的土地用以祠堂建设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国家早已对村域内的宅基地划定了所有权,而祠堂作为单一姓氏宗族的公共空间,时下很难通过村委会申请到宅基地;另一方面,虽然当前村落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在楼房新区的建设布局下,部分老房屋空置出来,这原本可以为王氏祠堂复建提供可能,但相对高昂的宅基地价格以及空心住宅相对分散等客观因素,皆为建设合族性祠堂带来了挑战。所以,纵使王氏一族一直都有复建宗族祠堂的规划和愿望,但并没有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王氏祠堂复建能够获得宅基地的使用权,实则与大窎桥村保存下来的一处清代古建筑群(现为王氏庄园)关系密切。自2012年起,国家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10)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委联合发起了中国传统村落普查活动,而入选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无疑将会为村落在新时代的发展规划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淄川最具文化底蕴的村落之一,历经岁月更替的大窎桥村保存了一处较具规模的清代古建筑群,基于此,大窎桥村委会着手整理申报材料,力求进入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最终,大窎桥村于2016年5月成功入选“山东省第三批传统村落”,之后在2019年6月又进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随后村委会积极推动古建筑群的修复保护工作,而王氏宗族也最终在这一过程中探寻到了复建合族祠堂的可能性。
在大窎桥村入选省级及国家级传统村落保护名录之后,为了进一步提升古建筑群的历史文化内涵,村委会计划重建部分已经消失的村落历史建筑,古建筑群保护方案中明确提出:“王氏主祠堂及五支分祠堂位置可考,保护规划计划恢复其中一座,满足王氏家族文化需求。”(11)淄川区住房与城乡建设局:《传统村落调查登记表(大窎桥村)》,2016年1月。而祠堂一般建于族众聚居的核心位置,是“族权的精神空间,因而它是一种权威的载体,是族权象征性的建筑物,是族人根底所在”(12)杨国安:《空间与秩序:明清以来鄂东南地区的村落、祠堂与家族社会》,常建华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9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页。。王氏宗族作为明清时期享誉淄川当地的科举望族,是当下村落最为重要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而复建王氏祠堂可以充分展现王氏宗族过往的显赫历史,以此增加古建筑群的文化底蕴。由此,村委会充分意识到王氏祠堂复建的必要性,并决定在村集体所有的古建筑群中将其复建。特别是在与大窎桥村直线距离约40公里的桓台县新城镇王士禛纪念馆当中就有祠堂的空间呈现,作为国家2A级旅游景区,王氏祠堂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方位展示了新城镇王氏宗族脉系承传的历史文化,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去参观学习。这也对大窎桥村古建筑群的当下保护产生了直接影响,更加坚定了村委会复建王氏祠堂的决心。
大窎桥村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一处较具规模的清代古建筑群,与王氏宗族的发展历史紧密相关。该建筑群的主人是王氏十六世王怀琪,其生活于民国乱世之中,靠挖煤井发家,不断累积起资本,进而成为当地最富有的民族资本家之一。《王氏世谱》个人传记篇载:“王怀琪,十六世(1868-1924),字竹亭,号筱岩,邑武生,援例入监,考授通判,加四级赏戴花翎,诰授奉政大夫,晋阶中宪大夫,配高氏,子五。”(13)淄川大窎桥《王氏世谱》续修委员会:《王氏世谱》(第12次续修),2012年,第2886页。家境不断丰裕起来的王怀琪在村内建造起了体量极为可观的四合院建筑群,院落东面还配有一座开阔平坦的打谷场。(14)相传王怀琪在大窎桥及附近村庄购置有300亩田地,收获的粮食也多是在打谷场完成晾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建筑群的房屋被适时分配给村中的烈士家属以及贫农居住。
作为国家粮公所的“大公”与作为大窎桥村委会的“小公”,围绕着古建筑的归属问题展开了多次博弈。20世纪50年代,在国家大力支持开采矿产资源发展经济的背景下,大窎桥村所在的罗村镇逐渐建立起了洪山煤矿、洪山铝土矿等国有企业。此时需要固定场域用以收缴农民上交的公粮,并给国有企业工人配发粮食。由此,淄川县政府计划在罗村镇修建一座粮管所,通过实际考察,大窎桥村清代古建筑群很快就成了绝佳备选地点,其原因大致有三点:第一,大窎桥村距离镇驻地罗村直线距离约有1里地,在此设立粮管所进行管辖可谓相当方便;第二,大窎桥村北铺有运输矿产的铁路匝道,借此调入或调出粮食等生活物资也十分便捷;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古建筑群是标准的北方四合院,房屋布局宽大方正,建设质量上乘,稍加改造即可作为储存粮食等货物之用,建设成本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节约。由此,通过直接的行政干预,为村集体所有的部分古建筑群由此被征用改建为“淄川区罗村镇粮管所”。此外,粮管所还在古建筑群东面的打谷场上用红砖砌起了更为宽敞的回字形粮仓,进一步提升了储存空间。
粮管所设立之初所占用的宅基地面积约为7亩,是大窎桥村集体无偿提供,那时土地所有权仍归属大窎桥村集体所有。但据大窎桥村委会成员董志玉讲述,粮管所的土地属性却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992年地方土地确权,确给(淄川区)粮食局了。到了2000年,粮管所就已经不供应粮食了,只用来存储一些粮食,(村委会)就想着把它要回来。然后就去找粮食局,粮食局说确权完已经给他们了,不是你们的了。粮食局找出来了当时的确权书,村里面的领导也都签了字,当时粮食局一共给了2万块钱,就把这个地方买走了。那时候也就是象征性地收了点钱,确权后(粮管所的所在区域)就成了国有土地了。(15)访谈对象:董志玉,男,1962年生,大窎桥村人;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20年7月31日;访谈地点:大窎桥村。
由此可见,通过1992年的土地确权,粮管所辖域的7亩宅基地变更成为国有土地。按照国家规定,国有土地不能进行买卖交易。所以当大窎桥村委会计划收回这一区域的土地所有权时,过程可谓曲折艰难。2000年,大窎桥村委会前后与淄川区粮食局展开了多次沟通与协调,始终无果。直到十余年后的2011年,该区域的土地才最终复归大窎桥村集体所有。而之所以能够重新收回这一区域所有权,一方面是因为1992年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以及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造成粮管所的功能不断弱化,往昔国企工人领取粮食、农民上缴公粮的情景不复存在;另一方面,该区域本就归属大窎桥村集体所有,新中国成立初期淄川区粮食局通过行政干预获得了使用权,且通过之后的土地确权划归国有,但从情理出发,淄川区粮食局应充分考虑大窎桥村集体的无私与贡献。此外,该区域实际处于乡土村落,远离城市中心,其土地价值也相对有限。最终,村委会花费20万元从淄川区粮食局购回了土地所有权。
显然,如果没有以古建筑群为基础的传统村落申报行为,大窎桥村王氏宗族复建祠堂的当代努力依旧很难实现。从古建筑群土地所有权的变动过程中,可以看到作为大窎桥村集体的“小公”与作为淄川区粮食局的“大公”最终都显现出“无私”的观念。一方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大窎桥村能够将作为村集体财产的部分古建筑群房屋无偿提供给县粮食局使用,这充分显现出村集体对于地方政府发展的强力支持,而这种无私行为也为大窎桥村提高在周边村落的重要性与影响力起到了关键作用,且也直接提升了本村村民上交公粮的便捷性;另一方面是淄川区粮食局在通过土地确权实际掌握了古建筑群土地所有权之后,并没有随着土地场域使用率的降低以及价值的抬升,将其售卖进行房地产开发,而是复交给村集体所有,也正是借助古建筑群为主体的房屋建筑,大窎桥村才成功获得了包括国家级传统村落、省级传统村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在内的众多荣誉和扶持政策。
三、小公与大私:王氏祠堂在村落中的合法性的确立
王氏宗族作为众多家庭组成的联合体,其复建祠堂的计划可视作合族性的“大私”,而作为地方基层行政管理的“小公”——村委会以及村落当中的其他姓氏,实际上对王氏祠堂建设的态度有着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2001至2006年期间。2001年初大窎桥王氏宗族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家谱续修活动,作为地方颇具影响力的世家大族,《王氏世谱》最终收录族众近2万人,65个村落参与其中,王氏宗族也在村西广场搭建舞台进行了盛大的谱书发放庆典仪式。家谱续修完成后,王氏族人迫切渴望能够修建一座稳固性的祠堂,方便族众进行祭祀等各类日常活动的开展。受到村落宅基地空间、价格、用途等多方面的限制,2006年起,王氏宗族精英转而将修建始祖碑列入王氏宗族的议事日程。一方面,在村公共墓地当中开辟场域设立王氏始祖碑,不受土地使用权的过多制约。由此,在与村委会反复沟通之后,最终王氏宗族在村西公共墓地偏南的边缘区域获得了建立始祖碑的场所。另一方面,整个工程的耗资也在王氏族众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且外延族众纷纷捐款支持,特别是捐款超过30元即可留名功绩碑,这也极大地调动了族众参与的积极性。
2006年清明节,王氏宗族通过合族力量在村西公共墓地当中修建起坐西南朝东北的始祖碑祭祀空间,这是一个长约6米、宽约6米的正方形场域。此外,场域内的地面还铺砖进行了硬化,其中一边作为出口,其余三边修造起半米多高的花墙,正中间竖起高约2米的王氏始祖碑,碑正面刻有“山东淄川窎桥王氏宗族始祖王公讳贵之墓碑”文字,碑背面刻有族内当前最具威望的十九世王克贵所撰写的《始祖墓碑文》,文末言及:“始祖原葬于窎桥庄北门外老茔,五世而上皆葬于此,六世后支庶殷繁,徙里而居,遂别建茔域。本村又建东茔、西茔和南茔。后即依其居而定。因代远年湮,原茔不复存在,今应族众要求,另卜新阡,重立始祖碑碣于此,供后人瞻扫祭奠永志。”(16)王克贵:《始祖墓碑文》,《王克笔记》(内部资料),2009年,第271页。墓碑前方摆放有石质供桌,左右两边则立起王氏谱系碑和捐款功绩碑。王氏族众不但将立始祖碑的行为视作普族同庆的大事,而且还将其视作合族收宗的重要成果,正如十九世王珍在2006年底出版的第三期族内《王氏文化》刊物中倡议:“通过我们王氏族众的共同努力,现已完成了立碑工程,今后祭祖活动就有了固定去处,希望广大族众把祭扫活动永远进行下去,把传统美德传给后代子孙。”(17)王珍:《始祖立碑记》,《王氏文化》(内部刊物)2006年第3期。
实际上,王氏宗族所修建起来的始祖碑祭祀空间,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飨堂极为类似,飨堂一般设置于陵墓旁,用以祭奠墓主人。王日根等人在研究山东栖霞地区宗族墓祭时,认为飨堂是宗族祭拜以及教化的重要场所,据栖霞《赵氏祖茔建飨堂记》载:“之飨堂非古制也,祭毕而燕,斯有飨堂。古人不墓祭,则何飨堂之有?然报本返始,仁人君子所不忍废,则墓祭不可缺矣!”(18)王日根、张先刚:《从墓地、族谱到祠堂:明清山东栖霞宗族凝聚纽带的变迁》,《历史研究》2008年第2期。显然,墓祭对于祠堂的建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祠本是对祖先的一种祭祀名称,春祭为祠,祠堂则是墓前祭祀所用的建筑。战国时,楚国曾出现过‘公卿祠堂’,民众墓祭也有所见。祠堂墓祭是从西汉时兴盛起来,像富平侯张安世、丞相张禹都在冢茔前修建祠堂”(19)冯尔康、阎爱民:《宗族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14-15页。。另外,济南市长清区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修建于东汉时期,其内壁上至今仍保留着雕刻精美的画像石,当然它也是伫立于墓葬之前的祭祀祠堂。
由此可见,王氏宗族于村落公共墓地建造的始祖碑祭祀空间,虽然与宋明以来士庶化过程中在村落居住空间当中所设立的宗族祠堂有所不同,但从本质而言,王氏宗族已经建构起了一个稳固的祭祀场域,虽然该场域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封闭空间,却与墓地祠堂所承担的功能并无差别。修建完工的始祖碑祭祀空间不仅成为王氏宗族实力的客观见证,更成为宗族精神寄托的象征符号。此后,王氏宗族每年的祭祖活动皆在村西的始祖碑前举行。总之,通过王氏宗族精英的积极运作,作为固定场域的始祖碑祭祀空间被建构起来,纵然其地处公共墓地,规模有限,但王氏宗族修建祠堂的初期努力已颇具成效。
这一阶段王氏宗族在村落公共墓地成功营建起始祖碑祭祀空间,虽然公共墓地属于村集体财产,但无论是村委会还是其他姓氏都没有对这一行为进行阻挠。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村委会成员当中王氏族人不在少数,村委会没有必要对王氏宗族的行为过多干预,因为公共墓地作为闲置土地本身就是供村民使用的,作为村落当中的最大姓氏,王氏宗族只是占用其中一小部分修建始祖碑,是完全可被理解的,村委会最终默许了这一行为;另一方面,村落其他姓氏认为王氏宗族修建始祖碑的过程主要是为本族祭祀使用,特别是公共墓地的使用功能比较单一,始祖碑所占土地较小且没有多少价值,由此其他宗族也就没有太多反对声音。
第二阶段则是2015至2018年期间。2015年大窎桥村成功入选第三批省级传统村落名录之后,就开始制定方案修复古建筑群,规划书中明确提及复建一座王氏祠堂,以此进一步提升古建筑群的功能性与完整性。这显然是作为“公”的村委会主动推进王氏祠堂的复建,而困扰王氏宗族多年的祠堂用地问题也终于得到了解决。但村委会的这一决定很快就招致村内其他姓氏的强烈反对,据王氏宗族第二十世族人王淼讲述:
当时搞祠堂复建的时候,村民意见是非常不统一,特别是村委会就有分歧,有些人说行,有些人说不行,有些人认为如果给王家建祠堂,那其他姓氏应该也建。有些人就是把祠堂复建归结到宗族上了!其实应该归结到村里面的古建筑群,古建筑群是省文保单位的一部分,这是在给村整体修复古建筑群。所以最后也是没办法协商了,许书记也感觉这个事情很难办,统一意见很难!所以就开了村两委和村民小组的大会,投票决定王氏祠堂的复建,一共是四十多人参加,最终同意的有三十多人(20)2018年4月19日,大窎桥村召开村两委(村党委、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会议,无记名投票表决是否复建王氏宗族祠堂,参会人数42人,33票同意,9票反对。,这样形成绝对优势了,就通过了!(21)访谈对象:王淼,男,1950年生,大窎桥村人;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18年9月5日;访谈地点:大窎桥村。
由此可见,在村集体拥有所有权的区域内复建单一姓氏的宗族祠堂,这一行为过程如果只得到村委会核心成员的认可,很难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大窎桥村委会迫于村民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选择更加民主的村民代表大会进行投票表决,最终才确定了复建王氏祠堂的决议。村委会也对村民做出了两点解释:第一,王氏祠堂是古建筑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复建王氏祠堂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提升建筑群功能,更加全面地展现村落历史;第二,村委会明确说明王氏祠堂复建的所有费用都由王氏宗族支撑,祠堂所占宅基地仍然归属村集体所有,王氏宗族仅享有村委会领导下的祠堂使用权。
事实上,王氏祠堂复建过程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合法性的确立,正如高丙中通过对河北一座乡村庙宇复建的考察所见,“造庙本身的困难还不是难中之难,最难的是合法地造庙,最难的是让所造的庙宇具有合法的身份”(22)高丙中:《知识分子、民间与一个寺庙博物馆的诞生——对民俗学的学术实践的新探索》,《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王氏祠堂的建设问题已然成为王氏宗族与村落其他姓氏之间的问题,也就是宗族间“私”与“私”的问题。但“私”与“私”的问题是不能交给其中任何一方进行处理的,必须通过“私”之上的“公”才能沟通与协调。而“‘公’能够解决‘私’无法做的事情,特别是攸关村庄利益和共同体长远发展的集体决策问题”(23)杨华:《家族、公私观念与村庄主体性建构》,《开发研究》2008年第2期。。由此,作为村委会的“公”适时地进行沟通与协调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求”(24)贺雪峰:《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试论中国传统社会农民的行动逻辑》,《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在村委会积极修复古建筑群的背景下,大窎桥村已经成为国家级传统村落,实际上,生活居住在此的各个姓氏都享有这一荣誉,当然也应该支持王氏祠堂的复建,因为王氏祠堂复修的初衷不是为了单个宗族的“私”,而是为了进一步提升古建筑群的规模,促进村落整体“公”的发展。由此,一直困扰着王氏宗族祠堂的合法身份终于找到了强有力的支撑。此后,包括祠堂复建的土地问题以及村落异姓的反对声音,都在村委会的积极干预下得到了圆满解决。因此,王氏祠堂的复建也真正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
四、公私兼顾:王氏祠堂复建实施过程
王氏祠堂复建的宅基地问题,在大窎桥村委会的积极协调下最终得以解决。2017年6月,王氏宗族依托古建筑群的修复方案设计方——淄博齐韵文物保护有限公司,展开了王氏祠堂的规划与设计。该祠堂位于古建筑群的东北方向,计划在拆除原有粮管所仓库的地基之上进行修建。在最初的设计方案中,祠堂正屋为五间仿古建筑,正厅为三开间,东西各配有一间厢房,二进院落,还有十分气派的祠堂大门。祠堂院落整体东西宽约22米,南北长约35米,占地一亩有余。根据设计效果来看,其体量及气势丝毫不逊色于王氏宗族历史上最大的合族祠堂——敦睦堂。
至此,王氏祠堂的宅基地使用问题以及复建规划方案都已完美落实。按照前期协定,此时王氏宗族应该提供充足的资金,推动祠堂进入施工阶段。但王氏宗族筹集建设资金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由于王氏宗族没有公共财产可供利用,所以祠堂建设的全部费用都依赖于族众的募捐。因此2018年1月在大窎桥村委会的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关于募捐王氏祠堂建设资金的动员大会,参会人员共计十余名,除了村委会领导外,其他皆为王氏宗族的核心成员。他们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王氏宗族外延村落中具有一定威望的族贤;另一类则是王氏宗族当中个人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企业家。这两类族人一直以来都十分关心宗族事业的发展,他们也是近年来王氏宗族开展家谱续修、清明祭祖、文集出版等合族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与贡献者。组织此次动员会的初衷,一方面是向宗族精英通报复建祠堂的具体计划和进度,并通过实地参观考察充分调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则是动员宗族精英主动捐助资金支持祠堂复建,特别是参与此次会议的精英还承担着向外延族众积极传递祠堂复建消息,以及组织族众捐款的重要任务。
自2018年3月王氏祠堂进行奠基开工仪式以后,祠堂的建设就一直处于一边发动族众捐款,一边利用到位资金运转施工的状态。奠基仪式半年之后,2018年9月,王氏祠堂复建工程才正式进入施工建设,首先启动了原有粮仓建筑的清除工作,之后又进行了祠堂大殿的地基建造。2018年11月初,祠堂地基顺利完工。2019年5月至7月,五开间的王氏祠堂大殿建设完成。2020年1月至5月,王氏祠堂大门修造完工。2020年10月功绩碑雕刻完成。
2019年12月31日张贴于古建筑群入口大门旁的公告显示,自启动募捐活动以来,王氏族众共捐款63万余元,其中大窎桥村王氏族众捐款13万余元,占比约为20%,外延王氏族众捐款近50万元,占比约为80%。显而易见,王氏外延村落的宗族力量对王氏祠堂的开工复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募集到的资金是否能够支撑王氏祠堂的整体建造呢?显然不能,王氏祠堂的实际施工过程与前期的设计方案存在诸多出入,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募集资金的相对不足。因此,王氏祠堂的建设不得不做出妥协,而这种妥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复建方案,将祠堂复建改为两期工程,一期工程主要完成大殿主体及大门、围墙的施工,建成祠堂的基本格局,东西厢房和相关配套建筑则改为二期工程,暂缓施工;二是在具体施工过程中,王氏宗族通过全权负责此项工作的族人监工,最大限度地将募捐资金用在刀刃上,避免浪费。其中,祠堂大门的修建过程就可以充分证明这点,据大窎桥村委会成员董志玉讲述:
当时就是为了节省资金才自建的(祠堂)大门,村里面以前木匠和瓦匠都很多,所以有能力建出这个大门,但是现在这些人的年龄都大了。王氏祠堂的房梁、房架都是本村的木工自己做出来的,只有祠堂的门窗是在外面订购的,传统门窗是需要雕花的,咱们自己现在雕不了,并且出去雕花的价格也不高,因为都是机器雕刻。其实王长泰(25)王长泰,王氏宗族第二十二世,木工手艺精湛,其祖父、父亲、叔父也皆为木匠。就能够做雕花,他年轻的时候做过。祠堂大门是两个人干的活,一个是王长泰的弟弟,还有一个是姓纪的木匠,主要以姓纪的为主。虽然姓纪的木匠手艺不如王长泰(王长泰之前的手出过事故,后来就不干了),但是别人也干不了,也不愿意干!还是自己干省钱啊!至少省三分之一的钱,这个大门的工艺还是比较好的!王长泰参与了监工,看着哪里不行就会让他们进行修改。(26)访谈对象:董志玉,男,1962年生,大窎桥村人;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20年7月31日;访谈地点:大窎桥村。
王氏祠堂的大殿和大门都是仿古建筑,需要使用大量木材,这些木材原料先后从距离淄川并不远的滨州邹平市和济南章丘区的木材市场自行购得。而为了节省开支,避免外包工程花费过高,王氏祠堂的所有木料加工皆由本村木匠完成,且按天记工结算工资。
王氏宗族之所以能够节省这一部分的开支费用,与本村之前的劳作生产模式有着密切联系。大窎桥村所在的淄博市淄川区,地处鲁中丘陵地带,人口密度较高,人均耕地只有约0.4亩,村民依靠土地营生难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四五十年间,该地区借助丰富的煤炭、铝石等矿产资源的开发吸引了一批农民从业者,他们或直接从事矿产开采的工作,或从事相关附属产业的工作,比如大窎桥村北就有装卸煤炭的铁路平台,村中的装卸工不在少数;洪山各大矿井需要定期建造或翻新厂房,就需要大量的瓦匠与木匠。从20世纪70年代末,大窎桥村就组建起了具有四十多人规模的建筑工程队,队中木匠就有十几人,当时建筑工程的所有门窗都由木匠们纯手工打造而成。所以在王氏祠堂的复建过程中,深谙木工技艺的老木匠们被重新征召,他们再一次运用纯熟的手艺承担起了王氏祠堂的所有木工活。虽然他们大都年事已高,平均年龄已逾七十岁,但他们尽其所能地保证了祠堂木质构件的技艺水准,正如负责监工的王长泰谈及祠堂大门的制作过程时所言:
原木买过来,先去木材厂加工,把木头打开。然后烘干木块,就是用木屑烧起来把木块烤干,要不然木块当中含有水分,后期会开缝。然后用白胶把木块粘合起来,再穿撑固定。这个(祠堂)大门还是烤花工艺,需要用到喷灯。喷灯打上汽油,点燃后把木门表面烤糊,做出仿旧效果,再打磨一下,最后上油漆。(27)访谈对象:王长泰,男,1956年生,大窎桥村人;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20年7月31日;访谈地点:大窎桥村。
可见,祠堂大门的制作技艺比较讲究,且为了达到古朴的视觉效果,老木匠们还特意使用了烤花工艺。虽然在王长泰等木匠行家的眼里,祠堂大门的技艺水平还存在些许的不足及遗憾,但王氏宗族能够通过自身力量修造起这般宏伟的祠堂大门已实属不易。整座大门造价共计5万余元,主要花费集中在木材原料费和木匠工时费两方面。
此外,王氏宗族在祠堂复建过程中,除了动员族众捐款之外,还积极发动村委会成员捐款,王氏宗族二十世王淼认为这一过程也非常重要:
村里(其他姓氏)普通村民捐款很少,通过积极做工作,村两委会成员每人都捐了钱,一个也没少。当时也是考虑捐上钱,就是默认行了,不捐钱,又怕出别的意见,所以想尽一切办法让他们都捐上钱……王家人在村委会的成员占多数,他们(其他姓氏)也怕得罪了王家。(28)访谈对象:王淼,男,1950年生,大窎桥村人;访谈人:周连华;访谈时间:2023年3月29日;访谈地点:大窎桥村。
王氏祠堂复建的村落合法性虽然在2018年初通过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得以确立,但此后村中还是存在少数的反对声音。王氏宗族为了尽可能多地获得村民支持,遂即通过核心人员的引领作用发动村委会全体成员为祠堂复建捐款,比如村书记许立军捐款10000元,负责古建筑群修缮工作的董志玉捐款1000元等。占据人口优势的王氏宗族,在村落政治当中是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此情况下,其他姓氏的村委会成员最终也都全部捐款。众所周知,村委会成员是通过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主要代表村民管理村落日常事务,进而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同时他们也是本宗族在村委会当中的代言人。当所有村委会成员捐款支持王氏祠堂复建,特别是他们的姓名被刻于祠堂功绩碑之上时,那也就意味着作为村委会的“公”与村落各姓氏的“私”之间达成了较为统一的集体认同。
按照前期建设方案,王氏祠堂大门建造完工后,整座祠堂就只剩下院落围墙与土质地面还没有施工。而此时王氏族众所募捐的资金已花费殆尽,宗族精英希望发动新一轮的捐款活动,但实际情况却不尽如人意,祠堂建设不得不陷入停滞不前的窘境之中。为了尽快完成祠堂建设,配套古建筑群,成为可供观览的重要展示区域,在祠堂建设停工一年多后,大窎桥村委会研究决定出资支持王氏祠堂剩余工程的建设,并向村民解释该部分的建设费用为提前垫资,待王氏宗族后期资金宽裕之后,将如数归还村集体。所以在2021年8月至10月,祠堂院落地面与部分围墙在村委会资助下修造完工。至此,大窎桥村王氏祠堂建设前后耗时超过三年半,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
祠堂完工后,王氏宗族转而开始对内部空间进行悉心布置。东耳房设为议事厅,其中摆放有桌椅。西耳房成为藏书屋,其中收藏且展示了部分王氏族众所捐赠的书画作品。至于三开间的祠堂正厅内,按照历史传统应该摆放长桌供奉祖先牌位。在与村委会沟通过后,王氏宗族决定在其中陈设部分祖先的画像以替代牌位,所选人物主要“尊始祖、始迁祖以及与之接近后辈,此外要论德、爵、功,以决定其人在宗祠中的地位”(29)冯尔康:《中国古代的宗族与宗祠》,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98页。。最终,正厅集中展示了包括始祖以及宗族发展历史上最为显赫的2位京官、7位进士,共计10人的画像。其中,始祖画像悬挂于正厅北墙中心位置,画像下摆有一条长几案,其上放置有六卷本的《王氏世谱》与《王氏一家言》文集,几案前是一张八仙桌,桌两侧放有两把太师椅。此外,始祖画像的左右还悬挂有王氏宗族传承谱系以及历史上与淄川其他名门望族关系往来的文字展示板,而西壁和东壁分别悬挂有4幅与5幅先祖画像。值得说明的是,王氏祠堂所展示的10幅先祖画像之中,只有始祖的画像是在祠堂建筑完工之际,由王氏族人邀请族内颇具影响力的画家创作而成。至于其他9幅先祖画像,实际早在2018年王氏祠堂复修之前就已经由村委会出资绘制出来,每幅画像之下都带有较为详尽的有关个人功名、官阶以及著述的文字简介,并在已修复完成的古建筑群当中展示出来。
总之,王氏祠堂在复建过程中,受限于资金压力,工期断续推进,曾一度陷入无法完工的窘境之中。尽管理想的祠堂复建方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得不一次次做出改变,但王氏宗族最终还是在村委会的积极助力下将北方乡土社会的一座家族祠堂建造了起来。
五、结 论
目前,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以及现代观念的传播,村落社会的宗族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已然发生巨大变化。因此,在北方多姓杂居的村落中,建造一座单一姓氏的祠堂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着重做出努力:首先是宗族精英的有效引导与推动;其次是基层政权的认可与支持;再者是调和各宗族之间潜在的矛盾与冲突;最后则是充足的建设资金与保障措施。
“公”与“私”之间实际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公”的众多政策实施与发展规划都内嵌于村落日常生活当中,需要“私”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另一方面,“私”在自身显赫历史文化或者人口优势的加持下,主动贴合“公”的地方权威与影响,以此满足自身发展的需求。大窎桥村王氏宗族仅靠自身能力根本无力建造祠堂,因此作为村落自组织的“私”(王氏宗族),试图借助作为基层政权的“公”(村委会)的力量来参与此事。王氏宗族精英将本族祠堂复建与村落新时代的发展规划密切联系在一起,进而把宗族祠堂凝结成为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获得村委会乃至全体村民的集体认同,从而达到复建本族祠堂的目的。此外,有关王氏祠堂复建的会议以及通知都有村委会成员在场,王氏宗族在不断弱化本族之“私”的同时,进而通过村委会之“公”的权威性充分确立起本族祠堂建设的合法性。最终,明清时期曾为科举望族的大窎桥村王氏宗族,通过“公”“私”合力将祠堂建造起来,这也是北方乡村社会近年来宗族观念以及实践活动复兴发展的一个缩影。
自宋至明中前期,统治阶层逐渐将原本为上层社会所享有的祠堂建筑士庶化,由此众多承担祭祀功能的宗族祠堂在村落社会被建立起来,且形成了群体认同的“祠堂之制”,而稳固性的祠堂也成为国家建构地方社会礼仪与秩序的重要场域。当前中国村落社会展现出新时代的“祠堂之制”,在国家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地方宗族过往的显赫历史已然成为村落历史文化的重要代表,特别是基层政权有将其进行空间呈现、借此促进村落发展的愿景规划;同时地方宗族通过家谱续修、文集出版、期刊编纂等合族活动的开展,也有着将宗族文化进行稳固空间展现的迫切愿望。而王氏宗族祠堂的成功建造,正是“公”“私”通力合作与互利双赢的结果。当然,被复建起来的祠堂已不仅是宗族祭祀的场域,也开始承担起包括旅游参观和教育基地等在内的多种社会功能,逐渐成为建构新时代地方社会礼仪与秩序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