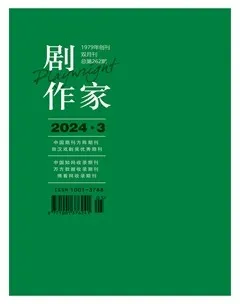《桃花扇·余韵》意涵阐释
2024-06-07李晓嵘
李晓嵘
摘 要:《桃花扇》是清初戏曲家孔尚任创作的一部历史剧,《余韵》一出是全剧内在精神的重要表现,不仅表现了历史兴亡交替之际普遍的情绪和感悟,同时也具有个体生命在不同遭遇中所体味的沧桑与悲怆。对《余韵》意涵的阐释包括探讨《余韵》一出作为结尾所构成的余韵悠长与圆融美满之意,详细分析《余韵》三套组曲【问苍天】【秣陵秋】和【哀江南】在曲调、人物、情感方面对底层百姓、朝代更迭和繁华落尽的独特表达,论述《余韵》出场人物形象及其背后所蕴藏的真幻、渔樵说史和人生如梦的象征意义。
关键词:《桃花扇》;《余韵》;老赞礼;兴亡离合
清初时期由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是一部以南明王朝兴亡为题材的历史剧。剧作“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借秦淮名妓李香君与复社名士侯方域之间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表现了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及由政权更替带给人们的沧桑与感慨。在内容方面,正文第四十出《入道》叙写道士张薇点醒侯方域与李香君,在国破家亡、君死父逝之际,男女之间的花月情恨又有何意义?之后侯、李二人双双入道。从故事情节上看,此出已经是结尾,但作者在正文之外又写了续四十出《余韵》,写前事俱灭、各类风流人物俱往矣,说书人柳敬亭入山做樵夫,戏曲家苏昆生下江作渔翁,两人携手归隐后相聚又恰巧与老赞礼相遇,三人共话当时事,引发一番唏嘘嗟叹,最后以沦落为皂隶的徐青君邀隐逸之人出山作结。《余韵》是《桃花扇》的最后一出,情韵深厚,意味深长,凝结着浓郁的悲剧气氛和伤感情绪,是《桃花扇》中最精彩的片断之一。
一、余韵与圆融
《桃花扇》另加的四出为试一出《先声》,闰二十出《闲话》,加二十一出《孤吟》和续四十出《余韵》。其中《先声》与《孤吟》分别为上本和下本的第一出,以副末老赞礼出场,为“副末开场”;《闲话》与《余韵》为上本和下本的第一出,都以说话笔调悼念王朝覆灭,起着“收煞”的作用。而对于《余韵》,孔尚任尾批中有言:“水外有水,山外有山,《桃花扇》曲完矣,《桃花扇》意不尽也。”[1]P206从命名上来说,就有着“曲尽意无穷”的意味。孔尚任《桃花扇凡例》中有言道:
全本四十出,其上本首试一出,末闰一出,下本首加一出,末续一出,又全体四十出之始终条理也。有始有终,气足神完,脱去离合悲欢之熟径,谓之戏文,不亦可乎?[2]P4
梁庭楠《曲话》卷三也曾指出:
《桃花扇》以《余韵》折作结,曲终人杳,江上峰青,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脱尽团圆俗套。[3]
可见《余韵》一出在结构上与其他三出相互对应,使剧本首尾完整,神气完备,最为重要的是脱去以往戏曲悲欢离合的俗套,别出新意,这是对常规戏曲结构的极大突破,也是孔尚任在戏曲安排上的一大创造。在个人命运上,李香君与侯方域虽最终团圆,但国破家亡之下个人命运也是悲剧一桩;在国家命运上,南明王朝的覆灭标志着整个王朝的最终毁灭,《桃花扇》作为中国古代戏曲的悲剧实至名归。但是,孔尚任安排《余韵》一出,以剧中三年的时间与渔樵闲话的场景极大地冲淡了个人、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悲怆,当剧烈的情感回归平静,怅然若失之感油然而生。理智的回归也使得剧中人与剧外人能够从更高层面思考时代悲剧与个人命运,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使人回味无穷。
梁启超对《桃花扇》评价道:“一部极凄惨极哀艳极忙乱之书,而以极太平起,以极闲静极空旷结,真有华严镜影之观。”[4]P308《余韵》以“极闲静极空旷”的结尾对比衬托全剧的“极凄惨极哀艳极忙乱”,强烈的对比带来巨大的戏剧张力。而“华严”本是佛教用语,“华严镜影”指的就是《桃花扇》中的悲欢离合、朝代兴亡如镜中观影,终为虚幻,因缘而起的华严镜像最后仍然会回归本源,回归“真空”。
《余韵》首尾相接、圆融美满之意还体现在唱词中。《余韵》三副唱词中,第一副【问苍天】由老赞礼起唱,与全剧第一副唱词【蝶恋花】有一一对应之感,老赞礼开篇唱【蝶恋花】:
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老夫不但耳闻,皆曾眼见。更可喜,把老夫衰态也拉上排场,做了一个副末角色。惹的俺哭一回,笑一回,怒一回,骂一回。那满座宾客,怎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2]P1
结尾【问苍天】:
释尽了,胸中愁,欣欣微笑;江自流,云自卷,我又何疑![2]P145
开篇直接点明本剧的内核“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而老赞礼作为贯穿全剧的线索人物,既是《桃花扇》故事的经历者和见证者,同时也游历于故事之外,也是叙述故事的第三人。他在剧中见证侯、李二人的离合与朝代的更迭,是全书的脉络所在。跳出剧外,老赞礼又寄寓了作者对人事与国家命运的无限感慨。并且从情感基调上说,开篇老赞礼是哭、笑、怒、骂,是戏中之人,是时代洪流下被命运捉弄的底层百姓。而结尾时却是释愁、微笑、江流云卷于自身无碍,得以超脱戏剧之外。老赞礼的情感起伏实则也是戏曲本身的情感走向,这种由激烈复归于平静的过程,使整篇戏曲在情感内容上首尾呼应,圆融完美,意蕴上使得《余韵》一出余韵悠长。
二、组曲内蕴
(一)底层百姓的呐喊——【问苍天】
《余韵》一出共三组套曲,分别为【问苍天】【秣陵秋】和【哀江南】。其中【问苍天】由副末老赞礼演唱,属神弦曲。神弦曲本属乐府古题,本义上乃是百姓祭祀神祇时娱神的弦歌,但此曲中老赞礼不为娱神反而是叩问,以底层百姓的身份叩问苍天,为何命运如此悲戚。“问苍天”一语问的是人世沧桑与命运起伏。在个体悲剧命运上,老赞礼暮年之际国破家亡,漂泊流落,曲中以自身的穷困沦落对比财神尊位,自己虽与福德星君同月同日生,在此世间却如同乞儿,这样命运的落差又是由何所致,归结于谁?即使是问神问苍天,也没有答案,只能是归结于命运。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朝代更替中的悲剧性不可避免,命运的无可奈何之感油然而生。而老赞礼不仅仅是作者本人对世事的介入旁观,也是底层百姓的代表,抒发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离乱之苦。“乱离人”甚至不如“太平犬”,明朝覆灭之下是千万百姓逃命奔波的现实,是底层人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是茫茫然不知归去何处的無力。着眼于历史视角,是大厦将倾、明朝灭亡的不可避免,但时代的一粒尘落到个人身上都是生命不可承受之重,百姓的苦难最为真实、最为具象。剧中将【问苍天】与《离骚》《九歌》相提便是着眼于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的联结。正如老赞礼最后一次上场说的第一句词一般:
江山江山,一忙一闲,谁赢谁输,两鬓皆斑。[2]P144
亦是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5]P226
朝代兴亡、战事输赢,到底是百姓苦。情感上的愤懑不平与现实的悲戚无力形成极大的张力。【问苍天】问的就是朝代更迭下真实百姓的穷困与苦难。
(二)朝代更迭的叹息——【秣陵秋】
【秣陵秋】中秣陵指代南京,以弹词形式、采用七言流水句抒发兴亡之感。曲子通篇用典,由隋唐烟月写到乌衣巷口,再到福王建立南明小朝廷。历史变换,朝代更替,帝王将相都已成为尘土,曲词轮转间便是时代兴亡,正是“六代兴亡,几点清弹千古慨”[2]P144。剧中将【秣陵秋】与《汉书》相提,与吴伟业梅村体相较,也是凸显其“诗史”感,以曲词寄寓兴亡,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在人物安排上,以左部间色的丑角柳敬亭演唱。柳敬亭虽为一介说书人,但替侯方域传信左良玉、送檄文至南京的壮举可谓一豪杰之士,参与了数件历史大事。作为历史的亲历者,柳敬亭将南明王朝的覆灭都浓缩在一曲【秣陵秋】中,将剧本前四十出所表现的内容尽收一曲唱词之中,总结南明王朝覆灭的教训。并且柳敬亭并没有采用自己熟悉的说书方式,反而是以盲女弹词的形式演唱。这种“盲”应是有意为之,在于“不忍看,所以盲”——对国破家亡的不忍看,对忠义之士悲壮而死的不忍看。唱词回荡青峰之间,仿佛朝代覆灭前的最后一声叹息。
(三)繁华落尽的超脱——【哀江南】
【哀江南】作为全剧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组曲子,共七支。就命名而言,“哀江南”一词最早出自屈原《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归来兮哀江南。”[6]P202南朝时期庾信《哀江南赋》将朝代灭亡与哀叹个人身世相结合。此后,“哀江南”一语就有了亡国之思、身世飘零的情感基调,在《桃花扇》中亦表现为“黍离之悲”,是国家兴亡之感的独特表达。在声调上,《桃花扇》本身是一个南曲剧本,全剧唱词主要以昆腔演唱,声调婉转柔和,曲词典雅,便于抒情。但至【哀江南】声调为之一变,采用弋阳腔演唱,声音高亢,以鼓铙等打击乐伴奏,表达慷慨激昂的情感,长歌当哭,极叙亡国之悲。在人物安排上也是独具匠心,苏昆生第一次登场为第二出《传歌》,教习李香君唱《牡丹亭》,此时明王朝尚未被攻破,戏曲演唱还在唱着《惊梦》,唱着姹紫嫣红开遍与似水流年。却不想一朝国破,唱曲转为悼亡词【哀江南】,唱帝王飘零、将帅困顿,有商女亦知亡国恨之感。
七支曲子中,第一支【北新水令】写苏昆生重游战后的金陵城,一片萧瑟景象,残军废垒和瘦马空壕昭示着曾经的战争;第二支【驻马听】凭吊明孝陵,守陵太监已逃,无人祭祀,墓碑缺损;第三支【沉醉东风】唱出了明宫室的荒凉冷落,野草丛生,饿殍乞儿居住其中;第四支【折桂林】见往昔秦淮窗寮破败,笙箫音绝,佳人不再,已是物改人散;第五支【沽美酒】回忆当年清溪半里桥,如今只剩一树柳弯腰;第六支【太平令】眼见旧院门已经无人居住,厨灶灰黑,人烟稀少;最后一支【离亭宴带歇指煞】情感到达顶峰: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2]P148
冰看似坚硬光彩实则易碎,日光之下并不长久,以冰消为喻象征往事繁华俱灭,金陵玉殿、秦淮水榭转眼间化为青苔碧瓦堆,兴亡盛衰的巨大反差引起强烈的思想震撼。而楼则象征着国家兴亡,一朝强盛,一夕灭亡,忽喇喇似大厦倾倒。情感上,苏昆生并不愿意相信国家已亡,甚至沉湎于残梦、旧境中,但现实是不管信与不信,舆图都已换稿,国家早已更迭。感情层层叠加,逐步渲染,亡国悲痛之情到达了顶峰。“楼”在此处更上升为万事万物普遍的一种发展与消亡的状态,是世事沧桑、朝代更迭、一切如梦亦如幻的破灭感。此时【哀江南】已经超越了朝代之更替轮转,而寄托了对世事变幻无常、回首皆幻境的人生感悟。
三支组曲在情感宣泄方面有着层层递进的关系,由老赞礼【问苍天】叙个人命运悲哀,悲伤无奈;次由柳敬亭【秣陵秋】述朝代更迭,故地重游,家国兴亡苍凉沉痛;最后由苏昆生【哀江南】超越朝廷之更替,感受时代变迁,一切繁华如过眼云烟,既有“黍离之悲”,更有释然与超脱。感情层层递进,悲痛之情越发深沉,但最后又归于繁华落尽的平静与淡然。
三、人物形象的象征意义
《余韵》中一共出现四个人,分别是隐入山林做樵夫的戏曲家苏昆生,闲作渔翁的说书人柳敬亭,贯穿全文的老赞礼,以及沦落为皂隶的徐青君。四个人都有着自身独特的象征意义。
(一)老赞礼——真与幻
老赞礼是“全书之脉络也”,出乎其外,又入乎其中,他既是《桃花扇》故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同时又以说戏的方式脱离故事,使文本具有“戏中戏”的结构,真幻相互交织。不仅如此,老赞礼是经历过明王朝灭亡历史的人物,但作家孔尚任又常借老赞礼之口抒发情怀和内心,表达现实的感受,从而塑造了老赞礼游离于真实与虚幻、现实与历史的特殊性,以“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的语调讲述故国遗事,带给观众一种亦真亦幻的审美感受[7]P39。
孔尚任将老赞礼定义为“纬星”,细参离合之场。在之前的四十出中,老赞礼作为剧中人物主持过文庙丁祭与崇祯皇帝祭日,在中元节超度故明亡魂,可以说与祭祀相关之事都由老赞礼完成,符合其赞礼的官职。《余韵》中将前事做个总结的也是老赞礼——“后来约了许多忠义之士,齐聚梅花岭,招魂埋葬,倒也算千秋盛事……也是我老汉同些村中父老,捡骨殡殓,起了一座大大的坟茔,好不体面”[2]P148——埋葬史可法和黄虎山,完成众豪杰的身后之事。由此老赞礼既是开场之人,同时又是收结之人,以亲身经历参与王朝覆灭的全部过程,由戏中之人叙述整场剧目,具有引人入胜之感,提高了剧目的真实可感性。并且老赞礼在剧中是乱世下百姓的代表,在《余韵》中以【问苍天】一曲表达芸芸众生在战争离乱、国破家亡时的辛酸与苦涩,是时代的见证者,具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爱国情怀。但同时出乎剧外,老赞礼是作者孔尚任的寄托,梁启超曾评价道:“《桃花扇》之老赞礼,云亭自謂也,处处点缀入场寄无限感慨”[8]P551,《余韵》中一句“避祸今何晚,入山惜未深”,道出功名利禄皆尘土的真谛,借老赞礼之口,抒发一己之情怀。“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两度旁观者,天留冷眼人。”[2]P71戏目与历史交织,老赞礼就游走在真与幻之间。
(二)柳敬亭与苏昆生——渔樵共话前朝事
柳敬亭替侯方域送信给左良玉,后送檄文,可称为豪杰;苏昆生在侯方域被捕后替他奔走相救,左良玉身亡时独自守尸身,设案祭奠,也是一位义士。明朝覆灭之后,二人归隐山林,柳敬亭做了一渔翁,苏昆生上山为樵夫。《桃花扇》是我国戏曲史上难得的悲剧,剧终之时,无论是史可法、左良玉、黄得功等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如马士英、阮大铖等人,都已化作尘土,抑或是男女主人公侯方域、李香君也出家为僧为尼,最终为全剧做结的却是柳、苏这样非政治化、非中心化的角色化重大为寻常。柳敬亭、苏昆生以说书、唱戏之人的口吻道尽前代兴亡缘由,将国家大事借由市井之人之口言说,崇高与平凡,身份和事件的落差带来极大的张力,发人深省。
而柳敬亭做渔翁的结局从其第一次上场时就已暗示,他唱道:“门掩青苔长,话旧渔樵来道房……俺们一叶扁舟桃源路,这才是江湖满地,几个渔翁……重来访,但是桃花误处,问俺渔郎。”[2]P4数次提到渔翁一词。戏曲家苏昆生在第三十九出时亦有“俺要到岭头涧底,取些松柴,供早晚炊饭之用,不强如坐吃山空么?”[2]P136也暗示了樵夫的归宿。《余韵》中两人归隐后为樵夫渔翁,共话朝代兴亡事。渔樵的组合本身就具有历史兴亡的特殊意义,人们熟知的“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9]P1就是借助了这一形象的特殊意义。渔樵闲话历史关注的并不是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是非曲直,而是作为命运的历史性,或者说个人与国家在命运中的必然性,即明王朝国运的灭亡是必然的,侯、李二人的入道是必然的,底层群众的悲苦也是必然。渔樵的深层意识是对山水的寄情,而山水的意识是超脱、脱俗。渔樵凭借青山而论青史的谈论方式是一种超越功利和私我的谈论方式,山与水是一切兴衰成败的无言旁观者[10]P57,“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11]P163,渔樵为山水代言,由此古今之事成为了超越是非的笑谈。
(三)徐青君——人生如梦
人物徐青君的出现也颇具深意。徐青君原为国公之子,其祖先更是明代的开国功臣徐达。在《桃花扇》中,他一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出场仅是在全剧第一处《听稗》的宾白中,复社文友相约去冶城道院赏梅,却被徐青君的家僮阻拦,“魏府徐公子要请客看花,一座大道院,早已占满了”[2]P3。人物并未露面,仅是由家僮一笔带过,却足见其豪奢。此时其象征着王朝落幕前不问世事的权贵。宾白“中原无人,大事已不可问,我辈且看春光”[2]P3一语便已点出,国家兴亡于他而言是事不关己,只顾享乐。第二次出场则是在《余韵》中,徐青君以身穿清朝官服的上元县皂隶自述道:“生来富贵,享尽繁华。不料国破家亡,剩了区区一口。”[2]P148前后反差极大。由“徐公子”到“徐皂隶”,由家仆告知众人一声“鼎鼎大名”到身为小衙役自报家门,由请客看花占满院到奉上司之命访拿山林隐逸,“富贵繁华”到“区区一口”皆因“国破家亡”,凸显出祸乱之惨烈。徐青君首尾的两次出现不仅前后照应,完善了戏曲结构,同时以其个人经历,突出了怀旧悼亡、人生如梦、繁华落尽的戏剧主题。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言道:“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12]P159徐青君的人生就是真实的写照。
并且,徐青君隐隐与老赞礼、苏昆生、柳敬亭等人对比。徐青君作为开国功臣的后人,作为享受前朝繁华的权贵,却毫无气节,为了薄禄度日,甘愿做清朝的一介衙役。老赞礼和苏、柳等人是寂寂无名之士,却宁愿隐居山林,面对巡查隐逸之人,忙逃走无踪。“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具已出山了”[2]P149,可见,徐青君亦是自己口中所谓识时务的俊杰,出仕清朝者不乏其人。但三年已过,布政司行文过了数月却并不见一个人来报名,当初未曾出仕清朝之人,现如今依旧坚守自我的气节,仍然有老赞礼、柳敬亭、苏昆生这些不识时务的隐逸之人,即使是面对官吏寻访,出于对故国的坚守和对名利的看破,也连忙走开。这样鲜明的对比,更表现出小人物的崇高和曾经权贵的没落,人生如梦一语在此得到印证。
四、结语
《桃花扇·余韵》一曲作为全剧的最后一出,从结构、唱词到出场人物都是孔尚任苦心孤诣的结果,使得剧本在结构上圆融美满,在意蕴上余味无穷。而三套组曲及出场人物象征意义的设置,让《桃花扇》这部戏曲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深沉与厚重,远超一般历史剧述一朝代之兴亡,而具有对历史必然性的思考,对人生命运的超脱,极富哲学意味。《余韵》在情感方面除单纯的遗民悲戚之外,还具有一种人生的感伤。这种感伤与平静,使其超越时代,即使是在四百余年后的当代社会,依旧拥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陈竹:《明清言情剧作学史稿》,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2]孔尚任:《桃花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
[3]梁廷楠:《曲話》,《藤花亭十种》卷三,清道光十年刻本
[4]梁启超:《小说丛话》,《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5]刘兰英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学词典(第五卷)》,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89年
[6]王逸撰,黄灵庚点校:《楚辞章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7]车振华:《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桃花扇〉戏剧结构简论》,《人文天下》,2022年第2期
[8]程炳达,王卫民:《中国历代曲论释评》,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
[9]罗贯中:《三国演义》,西安:三秦出版社,2013年
[10]赵汀阳:《历史、山水及渔樵》,《哲学研究》,2018年第1期
[11]衡塘退士等:《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元曲三百首》,北京:华文出版社,2009年
[12]张岱著,云告点校:《琅嬛文集》,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责任编辑 岳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