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味悠悠
2024-05-31方华
方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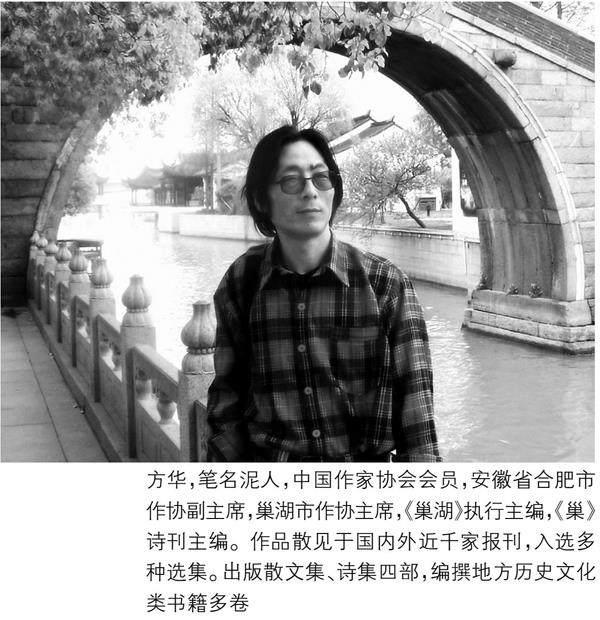
芦蒿
苏轼在《惠崇春江晚景》一诗中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我们大都熟记和欣赏前两句的春景,却忽略了后两句提到的春味。
诗句中说到的蒌蒿即芦蒿,又有藜蒿、水艾、水蒿、泥蒿、蒿苔等多种别称。在我生活的长江北岸环巢湖一带,人们称之“鱼蒿”,臆断是其大都生长在水湄的缘故吧!
幼时生活在巢湖北岸的丘陵地带,缺水多旱地,难得见到芦蒿。春天里,在田间劳作的母亲偶尔从渠塘边带回一把野生的芦蒿,也懒得伸一筷子。因为那股浓郁的艾草味,让喜甜乐香的少年退避三舍。
可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也在改变,及至中年以后,却越来越喜欢一些异香之蔬,如水芹、茼蒿、芫荽之类,对芦蒿更是喜爱有加。顾及四周,发现与我同好之人甚多,或许是生活越来越好,人们越来越需要那一口清蔬来“刷一刷”满腹的油水吧。
“正月芦,二月蒿,三月当柴烧。”除了其特别的香味,芦蒿吃的就是那一把嫩。一把芦蒿,摘叶去根茎,留下其间的嫩杆,洗净切段,即便像我年少时母亲那般一勺菜籽油清炒,那唇齿间的脆嫩、味蕾上的清香,也让人回味难舍。
江南水乡,芦蒿遍生,人尤喜食。比如在南京一带就有“荤有板鸭,素有芦蒿”之说。江南人吃芦蒿,夸张点的比喻,说一斤要掐掉八两,单剩下一段青青翠翠的芦蒿秆尖儿,精细如一茎温润的美玉,无论是盛放在竹篾的篮中,或是铺呈在青瓷碟盘,都让人心生怜爱与欢喜。
芦蒿炒香干是南方人家一道极普通却精致的菜肴。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第二十二回,就写到“芦蒿炒豆腐干”。将择取的芦蒿嫩茎洗净,切成小段,香干切成细条,除了盐和烹饪油,基本不加任何的佐料,一份春天的脆嫩与清香,就在我们的舌尖上跳跃。
最喜欢母亲的臭干炒芦蒿。被大火烧“辣”的油,激发出臭干和芦蒿各自特别的气味,两种奇味在热锅中相互交融、汲取,又衬托、凸显出各自的异香,让人难以止箸,回味悠长。
冬去春来,南方人家多存有腊肉。腊肉炒芦蒿,也是别有风味。将腊肉切成丝或薄片,芦蒿切成段,热油锅中将腊肉炒出油,倒入芦蒿段和红椒丝快速翻炒,出锅装盘。不说其味脆嫩清新,唇齿留香,单是那青瓷盘中腊肉的黄、芦蒿的青、辣丝的红配成的清鲜之色,已是令人未食先陶了。
春日,竹笋破土,与芦蒿拌食,两嫩相配,笋白蒿青,也极美鲜。此味早在明代即有记述:“多生江边湖滨,金陵人春初,与笋同拌食之,最为美味,碧如玉针,嫩不须嚼,良于他方所出。”
《红楼梦》第六十—回中写道:“……前儿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小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虽没有尝过这道“芦蒿炒面筋”,想曹雪芹既将之写进红楼,定是味道不错。
作家、美食家汪曾祺曾这样形容品味芦蒿:“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初读时虽觉其美,却不入其味。及至某个春日,在无为的一处江畔看见一群女子采蒿,看那一把把青绿的芦蒿握在少女嫩白的手中,春风吹拂,江水清新的气息入鼻,才真正领略老先生笔下的美妙。于是,在日后的每一次品味中,眼前总是晃动着江滩上那一丛丛的青绿和婀娜窈窕的身影。
草叶入食,也是勇敢的美食者不断探索和发掘的过程。据文字记录,芦蒿的美味是在北魏时期被发现的,这在北魏《齐民要术》和明代《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载。而在其前,鲜见食蒿之说。虽然三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即写到芦蒿,但也只是把它当成野草的一种。
“翘翘错薪,言刈其蒌。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此诗中的“蒌”即芦蒿。大致的意思是割草要先割芦蒿,旁边的姑娘长大了,我却不敢表露爱意,只能喂饱她的马看着她出嫁。诗中可以看出,那时还没有把芦蒿作蔬,只是用来喂马或者当柴火。被少年用来寄托情思,上升到了精神层面。
清香宜人,外脆里嫩,风味独特的芦蒿,越来越受到当代人的喜爱,于是就有了人工的种植。只是那杆茎越来越长越来越粗壮的芦蒿,少了阳光雨露的滋润、自然的率性,味道也越来越淡。
于是,在踏青时,我总喜欢在水湄草滩处寻觅那修长窈窕的身影,回味“新涨的春水的气味”,品味那一份虽清苦却幽香难忘的乡愁。
马兰
“原上草薰春盎盎,心中人隔路漫漫。疏风小圃宜莺粟,细雨新蔬采马兰。”读清人吴宗爱的这首诗,眼前便浮现出孩童时在原野上采马兰的情景。只是经年以后,不知少时同采马兰的小伙伴们散落在何方。
马兰是一种山野常见、非常普通的“草根”植物,春日初發时,人们采其嫩头入食,称之为马兰头。又有状其形色,称红梗菜、泥鳅菜等。因为马兰在田头、路边随处可见,入夏开淡紫的形似雏菊的花,又有人叫它田边菊、路边菊的。这些随性的称呼,像极我乡村童年中那些小伙伴们被父辈随口起出的土得掉渣的名字。
物资匮乏的年代,春日正是青黄不接,窘困人家都会在田野上采荠菜、马齿苋、野葱等野菜,用它来填补日子中那段空白的滋味。遍生的马兰自是人们掐取的欢喜。
及至当下生活小康,那些填补穷困的马兰头等野菜,竟成了餐桌上的宠爱。寓居城市中的人们或是要在油腻之中寻一份清淡,或是要在灯红酒绿中寻觅那一份难得的春天的味道吧。
其实,马兰的美味古人早已知之。
“离离幽草自成丛,过眼儿童采撷空。不知马兰入晨俎,何似燕麦摇春风。”陆游之诗即生动描述了宋时儿童采摘马兰头去做早餐的情景。
明人赵楷在其著《百草镜》中说:“马兰气香,可作蔬。”清人王士雄在《随息居饮食谱》中也称马兰为“蔬中佳品,诸病可餐”。
明代有一首《马兰歌》则这样写道:“马兰不择地,丛生遍原麓。碧叶绿紫茎,三月春雨足。呼儿争采撷,盈筐更盈掬。微汤涌蟹眼,辛去甘自复。吴盐点轻膏,异器共衅熟。物俭人不争,因得骋所欲。不闻胶西守,饱餐赋杞菊。洵美草不滋,可以废粱肉。”诗中不但生动地描摹了马兰头碧叶紫茎的形态、采撷的景况,还记述了吃法,甚至夸赞其美味胜“粱肉”。
马兰头简单普遍的吃法是拌香干。新鲜的马兰头在开水里焯烫十几秒,用手挤干水分切成细末,再将香干剁成黄豆大小加入切好的马兰头中,添入盐、糖、香油拌匀即可。清香、清爽、开胃,是配餐佐酒之佳品。
而我记忆中母亲的酱炒马兰更是简单。油锅烧热,投入拍碎的蒜头煸香,将焯水变绿的细长马兰头入锅,加一勺蚕豆辣酱稍翻炒,即盛盘上桌。母亲的味道、春野的味道皆让我久久难忘。
春日鲜嫩的马兰头,在母亲的手中还有多样的滋味。马兰头炒鸡蛋、马兰头包饺子、马兰头下豆腐汤,马兰头炒草虾……每一味都是母亲给我留下的春天的记忆、亲情的记忆。
马兰之美味,一直受到美食家的青睐。清人袁枚将其记入《随园食单》,写道:“马兰头,摘取嫩者,醋合笋拌食,油腻后食之,可以醒脾。”汪曾祺则描写他的祖母“每于夏天摘肥嫩的马兰头晾干,过年时作馅包包子。她是吃长斋的,这种包子只有她一个人吃。我有时从她的盘子里拿一个,蘸了香油吃,挺香。”
清代李渔在其《闲情偶寄·饮馔部》中这样评述:“吾谓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自古及今,这些喜好马兰等野蔬之人,首要之因,就是这些草叶之中深蕴了自然之清香吧。
明人王磐在《野菜谱》中记录了一首马兰头的歌谣:“马拦(兰)头,拦路生,我为拔之容马行。只恐救荒人出城,骑马可到破柴荆。”歌词道出了马兰生长的旺盛快速。所谓“莫待无花空折枝”,趁大好春光,马兰正嫩,且啖一口来自原野的美味,也让我们倍加珍惜过隙白驹般的韶华。
于是我又想起儿时的一首《马兰开花》童谣:“一二三四五六七,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歌声中,母亲臂挎竹篮,领着我一起在芳草萋萋的山冈上采撷马兰头的情景,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马齿苋
红茎绿叶的马齿苋贴地生长,这些委伏土地的野草,如同故乡大地上那些世族的繁衍,卑微却生命旺盛。
在秋冬匿迹的马齿苋,它们将针眼般细小的籽粒委于身下的泥土,或随风安身于另一片泥土,只需一场细雨和风,它们就再次生根发芽。
春天里,它们开始呈献鲜嫩,却隐含一份酸涩,仿佛提醒那些逐渐淡薄的记忆,不要忘却那曾经的酸辛。
即便酸涩,也是旧日乡下人家春日的难舍。一只小篾篮、一把小铁铲,我也曾随着村里的小伙伴们,在草长莺飞的田野上寻觅它们匍匐于地、隐身草叶的身影。
“嗬,这有好多马儿汗啊。”“苋”在我们的方言中读“汗”,马儿汗就是马齿苋,祖祖辈辈这么叫。当大丛的马儿汗出现在眼前,总是引起欢喜的惊叫,仿佛面对一田的丰收。
春天的马齿苋适合凉拌、清炒。凉拌的做法非常简单,将洗净的马齿苋放入沸水焯至马齿状的叶片变成碧绿,捞出用清水过凉并冲洗黏液,沥干水分后切碎,依口味喜好放入盐、辣油、香油,拌匀即可食用。马齿苋本身具有的那种酸酸滑滑的味道,让口腔里充盈着鲜爽。
乡下人家通常都是将马齿苋配以蒜瓣、大葱等清炒,一勺菜籽油、一撮盐,不做任何调味,保持着野菜本身源自自然的味道。
如果家中有富余的面粉,或是老母鸡多下了几个蛋,母亲会包顿马儿汗饺子,或是煎个鸡蛋马儿汗薄饼,那份享受,是那个春日久久难忘的回味。偶尔家里有肉,桌上有盘马儿汗炒肉丝,对于我,就是过年一般的快乐了。马齿苋的酸很入味,它被肉吸收,让肉丝显得嫩滑,而其茎叶又汲取了肉香,鲜美异常。
窘困的年代,缺米少油,鄉下人的口水都是寡酸的,于是,马齿苋的酸味自是难以得人欢喜。为了既能果腹糊口,又不至于酸涩刺嗓,乡人不知何时发明了用草木灰揉搓的方法,来祛除马齿苋的酸味。
最需去酸的,是春末夏初的马齿苋。这时节,马齿苋丰厚茁壮,将要开花,酸味最重,随后即茎变柴叶变老,不宜食用。此时,外婆会将地间田头采回的一篮篮肥大的马齿苋,用灶膛里的草木灰掺拌,一遍遍地揉搓,直至将茎叶的汁揉出,将草木灰濡湿,然后铺陈在阳光下暴晒。晒干成褐色的马齿苋盘缠在一起,抖去草木灰,外婆便将它收存起来,等待日后食用。
春日,我在城市里的许多酒店都尝到过新鲜的马齿苋,因为寓居在钢筋水泥城堡中的人们越来越喜欢那一把野味,而马齿苋的那份酸辛,也改善着小康生活里油腻的口味,反倒是让人喜爱的一味鲜新了。
但用干马齿苋烹制的美味,我一直未在饭馆里见到。
与新鲜的马齿苋相比,晒干后的马齿苋吃起来软韧富有嚼劲,那种独有的干香味,绵厚浓郁,余味盈口。干马齿苋无论是炖鱼、烧鸡还是焖肉,都是佳配。尤其喜欢外婆的干马儿汗烧肉,慢火煨炖,时间在微蓝的火焰上曼舞,马齿苋的干香渐渐沁入糯软的五花肉,肥美的油汁也慢慢浸入马齿苋的茎叶,时光和亲情为我们保留的山野的味道、春天的味道和故乡的味道,重新在我们的舌尖上弥漫。
马齿苋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耐旱,即便是在炎炎的夏日下,它也叶展花开,生长旺盛。传说后羿射日时,一连射落了九颗,其中一颗就是躲到了马齿苋的叶子下面,才没被后羿找到而幸存。为报答马齿苋的恩情,太阳就赋予了马齿苋一种特异功能,不怕阳光的暴晒。当然,这是追求美好的乡人根据马齿苋耐高温的生长特点编造的神话,其实马齿苋在夏季不会被晒死,是因其叶茎饱含那酸涩之水的缘故啊。如同我那故乡中的人儿,饱经尘世的荣辱与辛酸,依然烟火不熄,立于天地。
因马齿苋叶青、梗赤、花黄、根白、子黑,故又称五行草。五行者,万事万物之取象,阴阳演变之道。将乡里乡气的马儿汗起名五行草,有点高大上,定非乡人所为。多种称呼中,还是方言的“马儿汗”最为亲切、温馨,它让我想起记忆里的童年、远去的母亲和外婆、淳朴的家常味道、充满春天之味的酸涩的乡愁。
春螺
春到中段,不但时令蔬菜争“鲜”恐后,各种河鲜、湖鲜也正是肥美之时。其中,螺蛳是此时节很受青睐的水鲜。
食螺,据说在两个时段最美。一是清明前后,一是中秋以后。清明时节,已从冬眠中醒来的螺蛳,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滋养,尚未怀子,肉质丰满且富弹性,甚为鲜美。及至春末夏初,螺蛳开始繁殖,不但多子碜牙,且营养多输与满腹的幼仔,味道寡淡。至中秋,产子后的螺蛳又渐渐恢复“身子”,重又丰腴。
在江南水乡,人喜食春螺。有“清明螺,赛肥鹅”之说。一重意思自然是说此时节螺蛳之美,另一重意思则表明,那清贫人家因为有了春螺的“开荤”,其味在寡淡的日子里自是胜过一只鹅的肥美。
曾经的日子,吃不起鹅的人家,在回暖的春水里摸盆螺蛳,用清水养两天,滴上几滴菜籽油,等螺蛳吐尽泥沙,用刷子刷干净,然后夹去尾端,放点葱姜辣椒煮熟,即是一盆久违的“肥”美。简单的,掏一把过冬的腌菜合煮,其味咸鲜爽口,也是美甚。
在渠边塘畔摸螺蛳,也是乐趣。三四月天,塘坝里的水还带有一丝凉意,浅水处,可以看到一只只螺蛳或吸附碎石或缓缓移动。卷起裤脚,脱掉鞋袜,站到水中,一边感觉春泥的酥软,一边在水中沿堤摸索,不消一个时辰,就可收获满满。
春天,韭菜正嫩,韭菜炒螺丝是寻常人家案上的佳肴。将新鲜的螺蛳肉从壳中挑出洗净,青嫩的韭菜切段,配入红椒爆炒。鲜韭去腥增香,螺肉汲取韭香提鲜,两者搭配,清新鲜美到难以想象。
秋螺以大为美,春螺则以小为鲜,春日里市场上有“小螺比大螺贵”之说。春天的小螺蛳,肉质更加细腻软嫩,鲜美爽口。
烹饪螺蛳肉的方式多种多样,适合清炒,也可以烧、煮,烩成蒜香、麻辣等多种口味。如红烧螺蛳、酱爆螺蛳、香辣螺蛳等。春食螺,有“一味螺蛳千般趣,美味佳肴均不及”之誉。
先民食螺历史悠久。食螺最早见载于《魏书》:三国纷争,袁术驻兵江淮,粮草不丰,袁术便令士兵拾螺为食。南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也在其著述中记叙了食螺。元代《荆钗记》提到了当时人们已经买卖螺蛳。明朝《运甓记》则记载了炒田螺这道美食。
民间有“啄螺蛳过酒,强盗赶来勿肯走”的俗语,喻螺蛳之味美,到了即便冒生命之险,也不肯舍弃的地步。
民国时,李宗仁曾邀白崇禧一起吃螺蛳,感叹:如果没有战事,美酒配田螺,也是一大乐事。
螺蛳之魅力,即便是尝尽了人世间各种山珍海味的帝王也无法抵挡。南宋高宗赵构,某日去臣子家吃饭,这位大臣知皇上喜好,准备的珍馐中就有“姜醋生螺”“香螺炸肚”两道以螺蛳为原料的佳肴。
童年的时候就听过螺蛳姑娘的故事,各地版本很多,大同小异。这在陶渊明的《搜神后记》、晋朝人束皙的《发蒙记》、南朝梁任昉撰写的《述异记》、唐代徐坚编撰的《初学记》等诸多文集中皆有记述。
就像螺蛳姑娘的故事属于民间,螺蛳也是最平民的食材,它寻常易得,是普通人家春日之爱。即便以其美味上得贵席,也若偶入灯红酒绿的乡下女子,难脱其乡野的淳朴。
南方人喜食带壳的春螺,剪去尖尾的螺蛳,投入姜、椒、蒜等调料先炒后煮,鲜辣异常,是街边排挡的必备。会吃的,将螺蛳用筷子夹住放入嘴边一嘬,鲜嫩的螺肉和汤汁就轻松入口。有嘴笨的,只好用牙签将螺蛳肉挑出,只是少了“嘬”的乐趣。嘬螺蛳是容易上瘾的,鲜美的螺蛳仿佛就是唇舌上不能割舍的春日之吻,让人沉迷。
一边食螺佐酒,一边品味螺蛳姑娘等佳话,春天的滋味,生活的美好,悠长。
地丹
乡人送来一小篮地丹,洗净盛入盘中,宛如一片片温润的美玉,让人怜爱。
春回人间,第一聲春雷过后,山坡上、草丛中、乱石间便冒出一片片形似小木耳的地丹,于是有人称之雷耳、雷公菌。
也有叫地皮菜、地衣、天菜、地软儿的。比如我的外婆便称之为地耳,说木头的耳朵叫木耳,土地的耳朵叫地耳。这些地耳,是土地公公贴着地面在聆听春天回来的脚步和万物生长的声音呢。
在我的家乡,乡人大都称地丹为“自达”(音),窃以为是方言口音差异。后来在文字中知道,地丹又称地踏菜,地踏与“自达”在乡言中发音很是接近了。
明代的王磐在其《野菜谱》中记录了一首“地踏菜”的歌谣:“地踏菜,生雨中,晴日一照郊原空。庄前阿婆呼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饱食忘岁凶,东家懒妇睡正浓。”
歌谣中描绘出地丹的特殊生长环境,就是雨后旺盛,久晴却无。连续两三天的春雨后,最适宜捡拾。这时,提个小篮,在湿润的山冈和林丛中寻觅,总会有“青满笼”的收获。
地丹实际是真菌与藻类结合,一种非常奇妙的共生体,它无枝无叶、无花无果,菌类吸收水分及无机盐供给藻类,藻类则通过光合作用将营养供给菌类,相互依存,分不出根茎。地丹遇水滋润铺展开成深绿色,遇阳光暴晒风干时卷缩为灰褐色,久晴之日则难觅,所以说“晴日一照郊原空”。
明代的官员学者庄昶在退隐山野时,写过一首《拾地耳》的诗:“野老贫无分外求,每将地耳作珍馐。山晴老仆还堪拾,客到明朝更可留。人世百年闲自乐,山斋一饭饱还休。曲肱偶得同疏食,不是乾坤又孔丘。”
野生的地丹在富足闲适的生活里成为“珍馐”,在“贫无”人家却是同荠菜、马齿苋、榆钱等野菜一样,成为度过“岁凶”的恩宠。
王磐之所以记录下“地踏菜”等歌谣,是因其生活的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江淮一带水旱之灾频发,灾民靠采食野菜苟活。王磐深恐灾民误食有毒的野菜危及生命,便精心编著了一本图文并茂的《野菜谱》行世。
回想拮据的童年,在山野中捡拾地丹等野味,也不过是在青黄不接的时日为饥腹做些填补,真的鲜有“闲自乐”的情趣。
从第一声春雷开始,在雨后,地丹可以一直捡拾到秋天。据说地丹也可以晒干备食,但在我家乡一带未见晾晒收藏者,毕竟野生的地丹难有多少收获吧。
从野外捡回的地丹,需要细心地拣除枯叶杂草,用清水一遍遍地浸泡、漂洗,去除黏附的沙土。清洗干净的地丹,墨绿的似宝石,青翠的如翡翠,可以烹制出多种美味菜肴。
记忆中,乡下人家捡回地丹,大都与新鲜的蔬菜搭配炒食,如地丹炒韭菜、炒大蒜、炒辣椒。若是母亲在鸡窝里取两三只鸡蛋来炒地丹,或是在集镇上割回几两肉切丝配炒,那真是人间至甚的美味。
将洗净的地丹入沸水焯一下,沥水装盘,加入盐、酱油、辣子、葱花等,再淋上麻油凉拌,是村中好酒之人的佳品。一口嫩滑爽口的地丹,一口苦辣的“老白干”,辛苦的日子也被品咂得有滋有味。
外婆则喜欢用地丹做羹汤。清凛的井水烧开,加入洗净的地丹和切碎的豆腐丁,汤滚后勾芡,只需撒上几粒盐、滴上几滴麻油,一盆素淡清新的地耳豆腐羹就呈现在家人面前。那种隽雅清淡又不失丰腴柔美的羹肴,让我回味至今。
将地丹切碎,与豆腐丁、姜米、葱花,以及花椒粉、盐等调料混合拌成馅,做饺子或包包子,在那窘困的年代,是富裕人家的奢侈。我的童年时代是没有这样的情景回忆的。
春日里,也在菜市场里偶遇提篮兜售的,那堆陈的来自乡野的地丹,仿佛就是外婆所称的一只只土地的耳朵,等待着我用乡音叫出它们土味浓郁的名字。
水芹
据《吕氏春秋·本味》中记载,商汤曾问他的宰相、被后人尊崇为“中华厨祖”的伊尹:什么菜好吃?伊尹回答说:“菜之美者,有云梦之芹。”云梦,现有人牵强考证为某地,而我却坚信伊尹描述的当是烟雨蒙蒙的山野。想象春水之湄,那簇簇蓬蓬清灵翠秀的水芹被云梦般的雾气浸润之景境,真是曼妙。
春日,水芹生发,青嫩幽香,是啖芹的好时节。于是隔三岔五从农人的箩筐里买回一把水芹,或切段焯水凉拌,或加干丝爆炒,或与腊肉配炒,满口脆嫩清香,余味悠长。
水芹也可做汤羹。比如杜甫就写过“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的诗句。宋人林洪在其《山家清供》中描述“碧涧羹”的味道是“既清而馨,犹碧涧然。”一碗芹菜汤,汤色澄碧,清香氤氲,让人仿佛置身于高山幽谷间碧绿的小溪一般,只此青绿,怎不令人心生欢喜?
水芹之美味,自古得人识,也深得文人墨客的喜爱和赞美。如《诗经》中的“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朱翌的“并堤有芹秀晚春,采掇归来待朝膳”。苏轼的“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对美食颇多讲究的苏轼,对水芹颇为钟情,他还写道:“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脍。”在此诗的后面,他还作了自注:“蜀八贵芹芽脍,杂鸠肉为之。” 于是这道传承千年的名菜,有了一个颇诗意的名字——雪底芹芽。此菜是用斑鸠和水芹同炒,荤素二嫩相搭,衬以蛋清制成的“雪底”,三色分明,色、香、味、形俱佳。斑鸠是一种体型似鸽的飞鸟,栖于山野林间,其肉鲜嫩。因为现代的野生动物保护,美食者用鸡、鸽等家禽替代斑鸠,依旧可得苏东坡笔下美味之享受。
荤素之好,也如人之群分。北宋的黄庭坚有诗云:“黄华虽众笑,白雪不同腔。野人甘芹味,敢馈厌羊羫。”黄庭坚还有一个与芹菜有关的奇幻故事。据其家乡《修水县志》记述,黄庭坚有一次梦中进了一个村子,看见一户人家供桌上有碗芹菜面,他端起来就吃了。第二天醒来到衙门,嘴里还有芹菜味。当天晚上,他又在梦中到了那个村子那户人家,屋内一位妇人告诉他,她有个女儿26岁去世了,生前爱吃芹菜面,故此用芹菜面祭祀。黄庭坚刚好26岁,他看到这个女孩子写的文章,竟和他写的一字不差。醒来后,黄庭坚觉得这两场连续的梦甚是蹊跷,写下“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之感悟。
“青青绿绿的叶,脆脆嫩嫩的茎;清清雅雅的态,亭亭玉立的女。”后来读到徐志摩这首写水芹的诗句,感同身受。
芹是本土多年生草本植物,到明代,有“西芹”从西方引入,人们为了区分,分别称之为水芹和旱芹,或本芹和洋芹。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即记:“芹有水芹和旱芹,水芹生于江湖陂泽之涯,旱芹生平地。”
人有气质,草木也然,水芹在我看来也比旱芹具气质。如气息,旱芹之味,要贴近才能“感觉”,水芹则香远益清,回味无穷;如本质,旱芹茎干扁宽,内外含纤维质,若皮糙之女,而水芹青白通透圆润,当是“豆蔻年华”;再说身姿,旱芹粗壮,若比作女汉子,水芹清秀窈窕,则是如兰的淑女了。
每每从菜市场买回水芹,盈盈一握在手,总觉得它清灵飘逸,有“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清贵之相,真是未食先爱了。
正是水芹中通有节、清灵俊秀、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古人把读书人比作“采芹人”,以此借喻读书人的性情高雅、清高脱俗。如杜甫诗云:“炙背可以见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陆游诗云:“大官荐玉食,野人徒美芹。”邓文原诗云:“寒士简编穷皓首,野人芹曝抱丹心。”黄遵宪诗云:“闻道铜山东向倾,愿以区区当芹献。”
水芹之美味,也有人不以为然。如《列子·杨朱》中所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蛰于口,惨于腹。”春秋战国,诸雄纷争,饿殍遍野,食物匮乏,乡豪们或只以鱼肉为美,哪里食得庶民们的“草根”,尝得出水芹之类的美味?也就更体味不到水芹之诗意了。
“深渚芹生密,浅渚芹生稀。采稀不濡足,采密畏沾衣。凌晨携筐去,及午行歌归。道逢李将军,驰兽春乘肥。”千百年来,水芹生生不息,幽香依然,何不趁着春肥芹嫩,去那片山野中采芹?
(责任编辑 蒋茜 740502150@qq.com)
方華,笔名泥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合肥市作协副主席,巢湖市作协主席,《巢湖》执行主编,《巢》诗刊主编。作品散见于国内外近千家报刊,入选多种选集。出版散文集、诗集四部,编撰地方历史文化类书籍多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