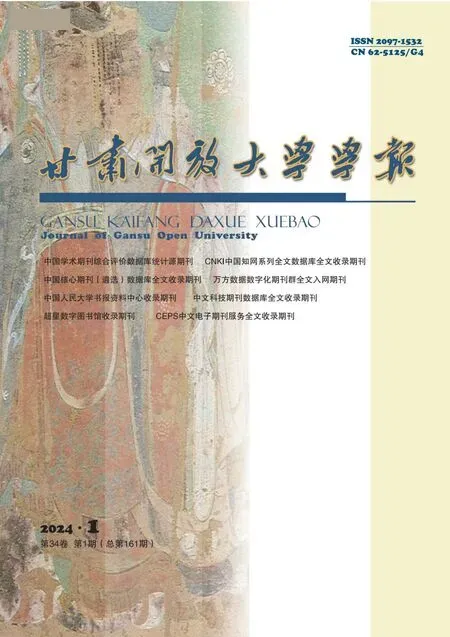丝路物质文化的历史记忆与话语建构
——对“马踏飞燕”的物质性诠释学考察
2024-05-27缐会胜
缐会胜
(西北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7)
2022 年6 月,甘肃省博物馆推出文创产品——“马踏飞燕”玩偶以及“神马头套”等“神马来了” IP 系列,掀起了大众的讨论热潮,类似的有川博“三星堆考古盲盒”,陕博陶俑手办等,这一系列物质性的文创产品背后承载着文化、历史以及记忆。“马踏飞燕”①是1969 年出土于甘肃武威雷台墓的青铜质料的“历史流传物”,为西汉灵帝时期的人工制品。其主体是奔马踩在飞鸟上,是古代中国与其他丝路沿线国家在长期双向交流过程中熔铸生成的产物。揆诸“马踏飞燕”的学术史研究,以往学界对“马踏飞燕”的研究大多囿于内部考量,或根据“马”与“鸟”两元素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探讨如何命名,或从美学角度探究其平衡美学与铸造工艺,或探讨“马踏飞燕”的宗教学意义②。然而外部视角却较少被人关注,“马踏飞燕”作为丝绸之路上见证文明交流与文化熔铸之物,从发现到发明、从寻常物成为表征中国文化的符号物,除器物自身的审美因素外,还有权力、历史以及资本等外在因素的参与或介入。本文通过对前人研究进行反思与重构,运用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从“物质性诠释学”(Material Hermeueutics)③视域探讨“马踏飞燕”这一丝路之物的民族与国家神话是如何被历史、政治与资本建构的。
一、物的历史性:“马踏飞燕”中的丝路记忆
在符号学看来,物是具有指称意义的符号而不是物本身,物自身充当意义载体与媒介,物是“记忆、时间、生命意味的负荷者”[1]。“马踏飞燕”作为物属于一种记忆媒介,即记忆的储存器,这种记忆的储存通过外形特征表现出来,正如扬·阿斯曼所说:“人总是被或日常或更具私人意义的物所包围……这些物反映了人自身,让他回忆起自己、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先辈等等,人所生活的这个物的世界拥有一个时间索引,这个时间索引和‘当下’一起指向过去的各个层面。”[2]马踏飞燕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过去与历史文化,勾起关于传统文化各个层面的文化记忆。另外,“马踏飞燕”中关于“马”与“鸟”这两个基本符号元素的定性以及对物的命名权的协商与争夺说明意义阐释的丰富性,所以对“马踏飞燕”具体为何物的阐释的多重性蕴含着多重文化记忆,对“马”与“鸟”基本构件的每一次定性对应着一种文化传统与文化记忆,每一种命名代表着一种文化记忆,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情感、身份、价值与审美认同。故而“马踏飞燕”作为文化记忆的储存物,携带着多重文化记忆。
(一)墓葬记忆与交流记忆
“马踏飞燕”是中国古代墓葬文化记忆的象征符号。“马踏飞燕”与铜车马仪仗队以及各种器物等均为墓中之物,在墓穴语境中以随葬品的身份出现,所以对马踏飞燕这一器物的意义与价值的定位,需要在汉代墓葬文化中来阐发解读。殉葬铜马属于一种殉葬习俗。车马在古代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是人的社会地位的象征。车马殉葬在古代极其常见,先秦时代的车马坑、秦始皇陵墓的兵马俑、汉代墓葬中的车马壁画以及画像砖等都验证了这一点,说明中国古代就有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灵魂不灭观念,人的死亡仅仅是肉体的消亡,灵魂脱离身体去往另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的空间,车马殉葬说明灵魂的空间依旧如现实世界一样需要各种日常生活之物。所以“马踏飞燕”作为随葬品,在墓葬中具有三重作用:其一,将死者的灵魂牵引到彼岸世界,马踏飞燕是灵魂从一个现实空间转移到想象空间的媒介。其二,马在彼岸世界生活中供灵魂日常使用,再次在两个世界都作为墓主身份的象征符号,“铜奔马造型的塑造本就是一种宗教行为,它的塑造重点在于表现墓主希望其亡灵可以顺利升天”[3]。其三,“鸟”是中国古代墓葬中的重要元素,青鸟、金乌、朱雀、玄乌等在西王母神话中都是具有神性的物。鸟凭借翅膀可以自由飞翔于天地间,可以沟通两个空间,鸟成为西王母所在神仙世界的物质象征符号。“鸟”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和“马”元素一样沟通天地。引导灵魂去往彼岸世界,是升仙的媒介与工具,另一方面“鸟”自身成为神仙世界的象征。“马”符号与“鸟”元素熔铸生成的“马踏飞燕”,是关于中国古代墓葬文化记忆的一个储存器。
中外丝路文化交流记忆也是“马踏飞燕”所携带的一种文化记忆。“马踏飞燕”所呈现的是当时中原与西域大宛、大月氏、突厥、匈奴等各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图景。“马踏飞燕”是东汉时武威地区的一个将军墓葬中的文物,“物为过去及个人的人生记忆的集体表征”[4],代表将军生前的戎马生涯、高贵的社会地位、情感、审美理念和个人价值取向,此物携带着墓主个人的生命记忆。另外武威属于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重镇,整个河西走廊是帝国重要的养马基地,殉马说明当地人民对马的崇拜与对其价值意义的重视。马在武威地区被广泛地用于交通驿站、长城防御、军事行动、民族和亲等方面,马踏飞燕承载武威地区的地方性记忆。又整个墓穴空间属于汉代礼仪社会缩影,整个仪仗队有领头的马踏飞燕佣、车马华盖、武士佣、婢女佣等按照一定的秩序整齐排列,反映严格的礼仪文化,汉武帝作《太一之歌》:“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5]1178又《西极天马歌》:“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6]1060-1061天马仪仗队以及天马歌成为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奔马踩着飞鸟,正是天马之形象,天马歌与马踏飞燕铜雕以及铜车马仪仗队是当时社会中礼乐文化的表征。同样马踏飞燕是在整个丝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流的语境中被创造出来,是文化交流融合的见证。“马踏飞燕”中马的原型是西域的汗血宝马。自张骞凿空西域,中原汉帝国与西域诸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等展开一系列的交流,汗血宝马开始传入中原地区。
天子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宛,……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语在《张骞传》……宛王蝉封与汉,岁献天马二匹。[6]3895
敦煌悬泉置汉简记载“□守府卒人,安远侯谴比胥健康……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命籍畜财财务。(A)[7]
在汉帝国军事权力的刺激下,不仅西域诸国纷纷献马,随马而来的使者和外国人也开始逐渐增多,这些天马的传入使得马踏飞燕的创造具有了可能性。马踏飞燕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承载着丝路上天马的物质旅行记忆。
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葡萄,苜蓿极望。[5]3173-3174
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5]3170
天马作为物,通过战争掠夺、商品贸易、政治呈献等方式开始进入中原,被赋予了一种神性,逐渐形成中国的天马文化。
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5]3170
应劭注“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曰“言天马者乃神龙之类,今天马已来,此龙必至之效也”。[6]1061
从寻常的外来物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象征,与中国的龙图腾崇拜文化一起,延续曾断裂的龙马文化。《周礼·夏官司马·廋人》:“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8]根据林梅村的阐述:“中原新石器遗址中普遍不见家马骨骼出土,八尺以上的高头大马可能是月氏人最先驯养出来的,所以这个民族有‘龙部落’之称。那么原始汉藏语‘龙’的读音可能借自吐火罗语nage(龙)或nakte(神),实为月氏人对马或神的称谓。大月氏西迁不单是民族的迁移,还带走了‘豢龙术’。由于龙在中原销声匿迹,中原人士不知龙为何物,于是将古史传说中的龙神化为神灵。直到汉武帝伐大宛从中亚带回汗血马,中原才终于再次见到龙,汉武帝称其为‘天马’而不是龙,这表明汉代人已不清楚这些高头大马其实就是古史传说中的龙。”[9]说明中国龙文化以马为原型,在张骞之前的丝路史前时代早已存在,随天马的消失“龙”成为一个漂浮的能指,天马的重新发现又重新构建起断裂的回忆,“飞龙在天”,龙马即天马,马踏飞燕中的鸟是被称作飞廉的神鸟,用来衬托天马的神性或龙性,“马踏飞燕”是龙马文化记忆的一种表征。所以“马踏飞燕”作为记忆的媒介,不仅体现墓主个人的生命记忆、武威地区的地方性记忆,更彰显国家记忆、礼乐文化记忆与丝路文化交流的记忆。
(二)神话记忆与祭祀记忆
“马踏飞燕”还储存了早期马神与金乌——太阳神的神话记忆。西汉时天马、马神祭祀以及金乌、西王母神话熔铸生成了当时的马踏飞燕铜雕。关于金乌——太阳神的记忆,《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有:“汤谷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山海经·海内经》“羿射十日,中其九乌,皆死,坠羽翼”。《淮南子》:“日中有踆乌。汉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10]张衡《灵宪》曰:“日阳精之宗,积而成乌。乌有三趾,阳之类数也。”乌鸦与太阳之间是互为隐喻,“马踏飞燕”“所踏之鸟,实为乌,即乌鸦,它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乌鸦,而是神话、传说中的乌鸦即太阳。”[11]乌鸦是太阳神的象征符号,在汉代以前三足乌仅仅属于太阳神谱系;而在西王母神话谱系中,金乌与西王母之间毫无关系,青鸟被视作是西王母的使者,“青鸟和乌鸦本应为两种不同的禽类,各自有不同的故事体系。然从西汉开始,西王母旁的青鸟时常以三足乌代之,或三足乌与青鸟同时出现在西王母故事中”[12]。金乌太阳神话与西王母神话开始不断融合,《河图括地图》有“昆仑在若水中,非乘龙不能至。有三足神鸟,为西王母取食”,龙即龙马(天马),青鸟与金乌之间的差异被抹掉,金乌开始充当西王母连接西方与东方、天上与地下的媒介与使者,这一过程形成的背景是西汉董仲舒倡导天人合一与汉武帝追求长生不老等,神话体系开始融合。
从周朝开始的马神崇拜与祀马是古代重要的祭祀活动,马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周礼·夏官》曰:“春祭马祖,执驹;夏祭先牧,颁马攻特;秋祭马社,减仆;冬祭马步,献马。”[13]不同的季节用不同的祭祀,春天祭祀马祖,夏天祭祀先牧,秋天马社,冬天则属于马步,凡养马者均可以祭祀马祖。郑玄注:马祖,天驷也。又《孝经》曰:“房为龙马。”贾公彦疏:“马与人异,无先祖可寻,故取《孝经》说房为龙马,是马之祖。”[14]龙马即天马。在整个雷台汉墓语境中,马踏飞燕以及后边的铜车马仪仗队属于一个礼仪队伍,与墓主人所进行的祭祀活动有关,最前边突出的“马踏飞燕”属于祭祀对象,与普通的骑士佣所骑之马有很大不同。在《史记·乐书》中司马迁提到“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5]1400,祭祀最高神灵“太一”。“正月”属于“春祭”,与古代春天祭祀“马祖神”时间一致,汉武帝得到天马之后,“复次以为太一之歌”,“太一贡兮天马下”[5]1178。汉武帝将天马与太一视为统一过程,马神的祭祀与对主神太一的祭祀同时进行,将天马作为极其重要的存在。汉武帝在改革国家礼乐祭祀体制中将马祖的祭祀与太一的祭祀看得同样重要,在祭祀中将天马进一步神化,成为天地或东西两个空间交流的媒介。《汉书·礼乐志》所记载《天马歌》“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文颖注:“言武帝好仙,常庶几天马来,当乘之往昆仑也。”[6]1061昆仑是西王母所在空间,在汉代壁画墓葬中经常有天马驾车奔驰,西王母漂浮在云端的图像。因为天马与西王母同样来自西方,在神话融合中天马开始和西王母建立起联系,成为西王母中神话场域中的一个符号,同时也是汉武帝期待成仙过程中与西王母或神仙世界建立联系的媒介。在太阳神话与西王母神话融合中,金乌已经成为西王母与东方、人间交流的媒介。而马神祭祀、天马西来与太一、西王母等神话融合的时候,神性的天马就成为世间之人与天上、西方交流互动的媒介。“马踏飞燕”就是天马与金乌等神话在丝绸之路上相互融合的产物,“马踏飞燕”意味着将天地与东西之间两种交流媒介进行整合的结果,是汉代各种神话系统开始相互影响并最终形成一个更大神话谱系的见证。另外,在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中有“逮乌鸦”与“袭乌”的材料作为佐证,又浙江龙游石窟石刻上“天马行空图”,由四个符号元素构成:右上角圆圈内一“月”字,右下角为鱼的残影,左上角为一马,左下角为一鸟,此图马当为天马,马头向西,鸟为金乌,与月相对,四物构成“天地日月”,与“马踏飞燕”所表征的一样,是太阳——金乌神话、天马神话、西王母神话等高度融合的表现,承载着丝绸之路上的许多神话记忆,还携带有图腾崇拜的残影。
二、物的政治性:“马踏飞燕”中的权力话语
(一)物的象征性与“命名权”争夺
物具有政治性,象征权力与身份。“马踏飞燕”是武威雷台墓葬中的随葬物,墓主人是张姓将军与其妻子,在前室摆放着马踏飞燕与铜车马仪仗队,包括青铜武士俑、奴婢俑、铜车马牛等。另墓中随葬有“设计精美、造型独特的铜莲枝灯以及铜壶、铜尊、铜熏炉灯”,还有许多陶器物品与四枚“⬆⬆将军”龟钮印[15]。随葬器物以及精致的墓穴结构共同构建了张姓将军与妻子的地下私人空间,此空间既封闭又开放,对内仅属于墓主,物具有实用性与审美性价值。同时此空间在对外开放性中确立具体的社会位置,物与空间言说一种社会关系,包括马踏飞燕在内的各种随葬物都是墓主的“身份资本”[16]14。
即使小物品,都是个人符号资本。如衣服、交通工具、装饰物、生活用具等,可以帮助完成严肃的意识形态工作。物作为身份的标记,可建构人的身份,“马踏飞燕”作为随葬物,是张姓将军作为社会上层权力的象征,对物的占有关系就建构了将军的身份,同时马踏飞燕也是被社会关系表征了的物。对“马踏飞燕”与墓主关系的分析中可知,物与权力之间呈现出一种辩证关系,“物是由特定的权力关系建构的,反过来又积极的构建权力关系”[16]14。一方面物参与个体权力、身份地位的建构,物自身就是代表价值、观念的文化符号,物的呈现就是权力的展演,如秦代的虎符,见物如见人,以物行事。另一方面,权力的参与可以赋予物以新的价值与意义,通过权力利用各种手段对物进行建构,使其成为象征权力与集体利益的象征。同时“物和人一样都是社会网络中的‘行动元’,不但和人之间有着‘交互性和互补性’,而且物存在于关系网络之中,和人共同构建关系网络的意义,反之也是在关系网络中意义才得以构建”[17]。“马踏飞燕”表征了东汉武威那个时空语境中墓主人的权力、身份、社会地位以及当时上层阶级所具有的依仗礼乐文化,表征了个人价值的同时也表征了整个上层社会群体。
“马踏飞燕”作为物质符号,象征人的权力与身份的同时,也成为知识权力话语相互争夺的场域,就命名权进行协商与争夺。当物被发现或发明,首先面临命名问题,因为命名的成功意味着表征的开始,物被命名后才能够被言说、被讨论,才有了被话语言说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即对物而言如何命名、如何表征成为一个问题。正如布迪厄所说,“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无法命名之物的权力,是一种不可小看的权力”“命名一个事物,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这一事物存在的权力”[18]。“马踏飞燕”恰好就是一个无法命名之物。“马踏飞燕”作为物,是由腾空的“马”与底座的“鸟”两个符号元素构成,马元素确定,但具体为何马不确定。同样底座上的鸟是确定的,但具体为何鸟是不确定与模糊的。这种模糊性与确定性的悖论式存在使得这件青铜器具有双重性,确定性中潜藏了不确定性。青铜器的这一特性使得对其的命名成为难题,似乎马踏飞燕是无法命名之物。拥有知识阐释权的知识分子都在争夺对这一物品的命名权,因为命名权的存在意味着权力的力量、场域等的划定,同样正是因为这一确定中的不确定的存在,对其的命名就成了知识分子争夺的场域,“马踏飞燕”成为权力场。
命名是对物的基本定性。“对象可能以实指的方式来命名,或者这个名称的指称也可以通过某个摹状词来确定”[19],对于“马踏飞燕”的命名不能凭空捏造,必须依靠物的形状与两个基本符号元素。郭沫若将其称作“马踏飞燕”,采取一种文学浪漫化的命名,并将其“鸟”确定为燕子,用燕子衬托马的轻盈[20],命名体现郭沫若文学家的性格;初世宾将其命名为“铜奔马”,“在不知文物的原名、真名时,文物、考古学一般是按学科规范习俗给予定名,即简明地按其质地(铜)、形态(奔)、性质用途(马)等要素给予概括”[21],命名体现初世宾文物学家的性格特征;牛龙菲命名为“天马”,通过考据张衡《东京赋》“龙雀蟠蜿,天马半汉”,认为铜奔马、马踏飞燕等名称并没有能够揭示这件文物的深邃精神内涵,其命名符合历史学家的考据性格,后《人民日报》依据牛氏“超越龙神飞雀的天马行空”简化为“马超龙雀”[22];张崇宁认为应称作“紫燕骝”或“飞燕骝”,张协《七命》将飞燕与良马并称唐昭陵六骏,李世民《赞》之首句即“紫燕超跃”,尤其是谢灵运《会吟行》诗李善注引:《西京杂记》曰:文帝自代还,有良马九匹,一名飞燕骝[23],命名带有考古学家的气质;马斗全认为将铜奔马命名为马踏飞燕、马超龙雀、飞马奔雀都不准确,《后汉书》:“明帝至长安,迎娶飞廉并铜马”,命名为“飞廉铜马”,无须后人为它重定什么名[24],同样带有明显的历史考古韵味;伍德煦、陈守忠将其命名为“马神—天驷”,二十八宿的东方苍龙七宿——角元氏房心尾箕的第四位房星,又称为“天驯”,此即古人信仰的马祖神,意味着对马的祭祀崇拜[25],有很明显的宗教学特征;而曹定云认为武威雷台墓出土的马是天马,底座下的鸟是乌鸦,乌鸦代表太阳,故将其命名为“天马逮乌”,属于一种原始神话[26],带有神话学色彩。除上述七种命名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命名,如“马踏胡燕”“马踏飞隼”“马踏飞鹰”“相马法式”,等等。依据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马踏飞燕”这个物作为能指,所指是不确定、漂浮、滑动的,一个能指对应着许多个所指,马踏飞燕、铜奔马、马超龙雀等“都是作为漂浮的能指和命名的工具起作用的,他们依附于和服务于意指特定类型的各种文化实践”[27]161。每一个所指或命名背后都是不同知识分子的情感诉求与价值、身份与审美认同,知识即权力,为了夺取或协商命名权,导致权力在其场域中众声喧哗,反复的话语言说与争论,使得这一器物成为话语焦点,命名权或表征话语权的争夺使得寻常物变得突出,话语权的斗争成为标志性事件,成功缔造铜奔马的经典化。从命名权的协商与争夺中可知,“马踏飞燕”能为人们所熟知,除自身力量美、平衡美以及形体等原因外,其名声与价值是物自身的不确定和确定性的矛盾与多种权力合谋的产物,权力话语的参与使其成为中国文化象征符号。
(二)权力介入与语境重构
除命名权争夺外,探讨“马踏飞燕”另一权力话语层面,需要将其置入具体历史国际语境中,“马踏飞燕”是在20 世纪70 年代中国外交背景下中国与国际权力合谋建构的神话。将马踏飞燕作为中国形象的表征,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一个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中国外交形象的重塑,类似“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马踏飞燕的神话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被建构。20 世纪70 年代初中国开始谋求建立新外交关系,“人文外交开始受到国家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外交权力进入非外交领域的人文交流”“公共权力一旦进入国际人文交流领域,人文外交开始具有了外交意义与价值。”[28]1971北京故宫举办文物展,马踏飞燕被选为故宫文物展文物。1973年郭沫若主持“文革”第一次对外大型历史文物展览。对外大型文物展览是文化宣传,“具有意识形态性,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往往也被称之为政治宣传”[29],英法等国将马踏飞燕作为中国象征符号。政府开始将马踏飞燕作为一种外交手段,不仅将马踏飞燕作为“文革”期间第一次大型对外文物展览的文物,还派遣宿白等人组织撰写文章在英国发表,为马踏飞燕等编写物的传记,旨在将马踏飞燕作为中国的文化符号或文化资本,将马踏飞燕推向世界。“马踏飞燕”在大英博物馆展出中,中国政府公共知识分子与英国大使,进一步缔造马踏飞燕神话,此时马踏飞燕成了中国的标识,它不再是物,而是国家,其神话是在微观权力、宏观国家政治权力的参与下与世界的合谋。相对于世界而言,马踏飞燕即中国,神话的意义是漂浮的所指,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够把握其价值与意义,马踏飞燕不再是墓葬中象征墓主人身份的物,而是象征国家身份的物,带有强烈的政治诉求——打造中国形象,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
对马踏飞燕的“空间语境化重置”是物与权力话语纠缠的另一重表征。如果将“马踏飞燕”进行还原,它仅是张姓将军身份权力的象征物,在墓葬空间中墓葬棺椁是整个空间的中心,位于前室的马踏飞燕与铜车马仪仗队、铜莲枝灯以及铜壶、铜尊、铜熏炉灯、印章、铜钱等物等位于中心的边缘,但经过空间语境重置后,从私人墓葬空间转移到公共博物馆空间,将马踏飞燕剥离原来空间语境,去掉墓葬中的铜钱、陶器、金银器等物,放入到全新的语境中,在解码的同时进行编码。经过“语境重置”,在博物馆空间内墓主人所在的后室仅仅是象征性的图形结构,马踏飞燕与铜车马依仗佣成为整个“开拓”展区的中心,从墓葬中的边缘附属位置成为中心位置,把马踏飞燕放入玻璃柜进行“去序化”与语境重置,并在周围布置汉代同时期的各种文物,建构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真实性”——虚构的真实,这些虚构的表象直接意指“马踏飞燕”所在“环境的‘真实性’并进而含蓄意指展出技术的‘自然性’”[27]173。博物馆完成对马踏飞燕的“中心化”表征后,再将马踏飞燕所在的“开拓展区”作为整个“丝绸之路文明展”的中心,完成双重中心化的表征,马踏飞燕展区与其他展区构成关于丝路的文化记忆,整个“丝路文明展”展示了古丝路甘肃段的精美文物,包括北方草原文化青铜器、“马踏飞燕”及仪仗队、汉唐丝织品、佛教造像、金银器、唐三彩、元青花等丰富多彩的丝路审美文化遗产。通过博物馆化与展览的诗学,把墓主私人空间表征为丝路文明交流空间,空间重置后马踏飞燕等物在具体语境中创设出新意义,马踏飞燕不再象征墓主政治身份,而意味着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交流的表征,建构成一个诗意的场所,呈现古代丝绸之路的开拓与发展,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表征个人身份地位的物被赋予了人类意义,成为人类交流的见证,物被政治、权力以及美学重塑。
三、物的复制性与符号性:“马踏飞燕”的跨媒介生产与重塑
经过权力话语建构与语境化重置,“马踏飞燕”不仅是墓葬空间内象征等级身份的私人物品,而且已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资本,具有很强的文化再生产功能。“马踏飞燕”开始与现代科学技术、新艺术形式与新媒介等合谋,不断进行意义的重构与审美变形,获得新表达形式,经过变形的“马踏飞燕”形象在社会功能、审美认同、情感表达以及意义等方面均体现出后现代社会文化多元性特点,在雕塑、图像、邮票、音乐、戏剧以及文创等艺术层面经过“机械性复制”,重新被建构、被表征的“马踏飞燕”成为“表征群”,变形符号的意义是不固定的、流动的、漂浮的所指,在遮蔽原始意义的同时生成新意义,马踏飞燕成为具有多元意义的文化符号,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
(一)图像/影像中对“马踏飞燕”的生产
在视觉图像领域,关于“马踏飞燕”的重构与变形首先表现在图画艺术形式中。国家将其为中国旅游的标志,经过20世纪70年代对外大型展览过程中权力话语建构,此时“马踏飞燕”已成为中国的标志符码,用这样已经被符号化的物来作为旅游标志,能很快被人们被熟识与认同。保留符号的能指外形,赋予新的所指,将其命名为“马超龙雀”,这种命名其实也是意义的生产过程,使其有别于马踏飞燕与铜奔马,建构出区别性特征,形成一个新的旅游神话:“一、天马行空,逸兴腾飞,无所羁缚,象征前程似锦的中国旅游业。二、马是古今旅游的重要工具,奋进的象征,旅游者可在中国尽兴旅游。三、马踏飞燕的表铜制品,象征着中国数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显示文明古国的伟大形象,吸引全世界的旅游者。”[30]通过新媒介、新图画艺术形式将其表征出来,马踏飞燕作为一个能指符号,拥有不一样的所指。图像与文字的融构使旧的符号与新的符号组合,这就赋予马踏飞燕这样一个象征中国传统政治、宗教、历史、文化交流等丝路文化记忆的符号一个新的所指,在符号组构的过程中,意义或所指是滑动的,马踏飞燕这样一个符号从指正过去历史的封闭系统转变成对未来的开放,通过人类有意识的在再生产活动,历史中的符号又变成了新中国旅游业的神话,是中国的旅游“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31]。
除视觉图画层面的再生产与变形,视觉雕像也是“马踏飞燕”符号占据的重要场域。将“马踏飞燕”按比例放大,做成占据着一定的空间的雕塑,再次被符号化、空间化,马踏飞燕的空间化存在意味着对某一城市空间的定性,即马踏飞燕所在的城市空间属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它是对雕像所在城市空间旅游价值的确认,马踏飞燕雕塑作为空间符号其存在给城市的人文与自然价值提供合法性。正如罗兰·巴特所认为的,模仿性艺术携带有两种讯息,“一种是外延的,即相似物本身;另一种是内涵的,它是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借以让人解读它所想象事物的方式。”[32]当其作为雕塑再生产出来,马踏飞燕及其红色底座、金色烽火台,圆形地球仪三个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雕塑空间。铜质镀金长城烽火台,表明中国的旅游业历史源远流长和城市旅游业在中国旅游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基础地位。中部铜铸镀金浮雕地球,象征中国旅游业是对外开放的先导产业,也表明了中国的旅游城市要面向世界,向现代化、国际化的目标奋进。顶部的铜铸“马踏飞燕”,意味着马踏飞燕环顾四宇,潇洒奋蹄于地球之上,象征中国旅游业蓬勃崛起的形象和光辉灿烂的前景,也表明中国旅游业已昂首屹立于世界。“马踏飞燕”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象征,马踏飞燕借助于图画与雕塑媒介与艺术形式,参与建构了中国旅游神话。
马踏飞燕和陇剧都是有鲜明甘肃地方性色彩的文化符号,大型神话陇剧《马踏飞燕》对马踏飞燕进行了新的表征。它利用戏剧形式将静态视觉形象“马踏飞燕”与活态视听陇剧熔铸在一起,将马踏飞燕塑造成一个爱情与救赎为主题的悲剧。借助传统神话原型,进行生活化的改造,把“马踏飞燕”人格化,“马”代表房府星君,“飞燕”即天女龙雀,马与飞燕成了正义与善良的化身,对抗太岁——象征邪恶的自然力量,如沙尘暴、雾霾等。全剧利用《祸起天土》《太岁逞凶》《龙雀思凡》《天神助阵》《情定人间》《马踏飞燕》六个情景动态呈现房府星君与天女龙雀为救赎人类在与太岁的斗争中,将对人类的救赎与二者之间的爱情定格为马踏飞燕的瞬间。在此剧中,“马踏飞燕”不再是物质性的物,完全摆脱了墓葬语境,被放入到明清才成熟的神话语境中,在对马踏飞燕进行解码的同时进行编码,消解其物质性,成为一种救赎与爱情的观念,在丝绸之路的生成中马与飞燕都是重要的存在。将“马踏飞燕”、中国神话、丝绸之路、人类救赎、爱情等糅合在一起,再生产出全新的文化意义,“采用神话剧的形式赋予剧目民生的主题、爱情的线索、飞翔的思维、牺牲的精神。其巧妙地把天上人间、丝路悠长、河西走廊、黄土高原、飞沙走石、环境污染、民俗文化等完美结合,既解释了马为什么踏了燕,又诠释了陇剧的戏曲韵味之美。”[33]被戏剧化表征的马踏飞燕重构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同时也意味着马踏飞燕从一个单一的视觉物质符号变成视听兼具的审美艺术符号。
(二)邮票与文创中对“马踏飞燕”的重塑、复制
马踏飞燕的邮票化表征是其意义在生产过程中重要的一个文化机制。自1973 年马踏飞燕进入邮票,截至时间共有九次被纳入邮票,中国七次,联合国一次,2014年保加利亚发行中国与保加利亚建交纪念邮票一次[30],但中国、联合国与保加利亚对马踏飞燕的表征存在很大差异。这三种不同表征背后蕴含丰富的意义,被差异化表征的马踏飞燕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表征体现出对政治、文化等话语权的争夺。马踏飞燕作为物,是张姓将军的社会地位的象征物,表明个人生前的一种审美兴趣,马踏飞燕的价值意义具有语境性特征,不具普遍性,但在邮票中“马踏飞燕”具有一种普遍性价值与意义,获得普遍性的表征,马踏飞燕即中国。
中国邮票中马踏飞燕形象基本统一。古铜色代表中国青铜文明颜色,马踏飞燕与长城、大漠雄关等符号元素组合代表中国在世界上的基本形象,它们表征了中华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马踏飞燕即中国。另头向左尾向右的侧影表征“马自西来”的文化含义。《史记·乐书·天马歌》:“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马自西来”象征古代四夷来服,外国归降及中国为天下之中心的观念,所有优秀旅游城市中的马踏飞燕雕塑均头向东尾朝西,东方是中国的空间符号。联合国在表征时,马踏飞燕作为物表征整个中国,马踏飞燕/中国踩在“UNITIONS UNIES”之上,此时联合国成了世界的中心,头向左尾向右的马踏飞燕侧影奔向联合国徽标,若中国传统从左到右的侧影象征“马自西来”的万国归服,那么从左向右仰望联合国徽标的侧影意味着联合国将其作为政治核心权力所在,期待中国成为联合国拥护者。而保加利亚邮票是中国元素与保加利亚元素的有机组合,五星红旗与马踏飞燕以及“中国农历马年”等字样象征中国,马达尔骑士与保加利亚国旗象征保加利亚,并配有两国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保加利亚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65周年”。这枚邮票是外交政治的产物,是一种政治交往的媒介,马踏飞燕与马达尔骑士的结合,“突出两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象征保中友谊源远流长;另一方面体现了今年是中国农历马年,寓意吉祥和奋发向上”[34]。另外保加利亚马达尔骑士的马头是联合国所表征的“自东向西”的符号,而马踏飞燕是“自西向东”,呈现出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并非一方向另一方的臣服,任何一方都不处于中心地位,中保双方平等的外交关系。对马踏飞燕物质符号在邮票这一媒介中的不同表征都是从表征主体的政治目的出发,在消解掉原有价值意义的基础上,重构与生产符合主体目的的政治意义。中国、联合国以及保加利亚都在争夺一种表征权,试图在对原有的物质符号的变形解构中摆脱被动的意义接受,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表达表征者不同的政治诉求。
另外,在这样一个机械复制与数字超复制时代,不仅作为图像与影像的“马踏飞燕”可跨媒介生产与无限复制,作为“历史流传物”的马踏飞燕亦可被无限复制,即从“图像的复制生产”转向“物的复制生产”。作为历史传承物的马踏飞燕具有唯一性与原真性的特点,拥有本雅明所说的膜拜价值,遵循历史逻辑与文化逻辑,最根本而言是人类文明交流的见证物。而作为文创存在的”马踏飞燕”人工制品——玩偶、头套以及关于马踏飞燕的系列IP 产品,作为可无限生产与复制的物,遵循的是经济社会的资本逻辑与审美逻辑,体现为一种展示价值与交易价值。在作为物的“马踏飞燕”的复制性生产中暗示出三重含义:其一,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物的堆积成为一种社会景观,物可满足人的恋物癖,对马踏飞燕文创物的竞相购买与消费是主体自身欲望与需求满足的一种表征,进而在物中找寻到疏离社会中的亲密感,同时可以从复制物中感受到历史感与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其二,复制的文创物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丑萌”,原物所呈现出的平衡之美与精湛的铸造技艺给人的审美感与震惊感被娱乐时代的大众狂欢化与审丑所取代,对马踏飞燕的文创化复制是对经典之物的解构与颠覆,历史感与传统被肤浅的遮蔽,从审美到审丑的内在转变是马踏飞燕广受欢迎的内在审美逻辑与情感结构。其三,马踏飞燕的成功复制还在于物象征自由。一方面鉴于马踏飞燕自身的铜绿色与疫情中的技术装置二维码“绿码”之间的谐音,对马踏飞燕这一物的拥有就意味着拥有健康与自由,可自由出入任何场所。另一方面马踏飞燕与“马踏肺炎”之间的谐音,使得这一复制物拥有了战胜疾病的神秘力量,马踏飞燕自身带有了战胜疾病的隐喻维度。
四、结语:“马踏飞燕”的物质性诠释学意义
“马踏飞燕”不仅作为物质符号在图像、声像、戏剧、邮票、文创等中重新被生产表征,获得新的意义,而且“马踏飞燕”这几个文字建构出一种概念,不仅符号中的能指成为一种文化资本,而且概念或所指本身就是价值。商品生产者把“马踏飞燕”这样一个名称当做商品来吸引消费者,与马踏飞燕模型商品化不同,这是名称商品化的过程,吸引消费者消费的不再是作为物的“马踏飞燕”,而是一种符号概念,就如同马可·波罗瓷砖一样,“马踏飞燕”这个名称在长期的表征过程中,自身成为一个有价值意义、象征身份的文化符号。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所进行的不再是物质的消费,而是一种理念的消费,这种理念彰显的是消费者个人的审美品位与社会地位。总体而言,在关于丝绸之路上“历史流传物”的文化传记的书写中,通过物质性诠释学让“事物”说话,让物“活起来”,让“物”自身言说人类文明交流的历史与记忆。藉由对“马踏飞燕”这一事物神话的建构机制进行深层挖掘,打破以往研究者单一的美学与历史视角,揭示隐藏在背后的权力话语、文化记忆以及跨媒介重构等外部因素对物的建构的重要价值与意义。马踏飞燕作为一个单纯的历史流传物,通过命名、阐释、重置以及重塑等人类的一系列活动,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象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资本。此外,将“马踏飞燕”作为丝绸之路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进行物质性诠释学的考察与分析,可以为丝路物质文化的研究提供理论资源与有效的方法路径。
注释:
①为便于论述,全文将出土铜马称为“马踏飞燕”,具体应如何命名,学界尚无定论。
②对“马踏飞燕”物本身的界定以及命名争论参见胡幸福《铜马非马——中国旅游图形标志“马踏飞燕”新解》,载《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对平衡美学与铸造工艺的研究有李闻茹《东汉“马踏飞燕”式奔马形象的程式化造型分析》,载《美术大观》2015 年第8 期,徐承泰、倪婉《从漆画到铜雕──东汉“马踏飞燕”铜雕艺术构思的渊源》,载《江汉考古》1999 年第3 期,马凯臻《从汉画像石“鸟”图像到“铜奔马”的时空隐喻——以跨文化视域下“物像倒置表现”的视觉诠释为逻辑起点》,载《国际比较文学》,2020年第3期;对马踏飞燕宗教学意义的探究有张翼《马踏飞燕折射出的马神崇拜研究》,载《兰州学刊》2017年第9 期,张晋峰、牛宏《“马踏飞燕”当为“天马伴金乌”——雷台汉墓铜奔马的宗教学解读》,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等。
③“物质性诠释学”由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提出,有别于立足于语言符号的文本阐释学,唐·伊德在2022年的新作《物质性诠释学:扭转语言转向》中直接对语言论诠释学进行批判,并延续《让“事物”说话》一书中对非语言文本的关注,譬如自然物、非语言的历史传承物(譬如动植物化石、绘画或图像、考古文物等)以及语言文本的物质性(譬如颜料、纸张等)维度,通过对这些事物与物质性存在的阐释与解读,让“事物”说话,赋予其一种意义与价值,进而打开一个新的人类生活世界,唐·伊德的理论可以有效的解释丝绸之路上非文字的历史流传物等非语言文本。陈玉林、吴畏的“历史的物质性诠释学——伊德技术哲学的历史意识及其对唯物史观的意义”[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8(4):29-33,100已对物质性诠释学做了详细介绍,具体参见Don Ihde,Material Hermeueutics:Reversing the Liuguistic Tur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22,p: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