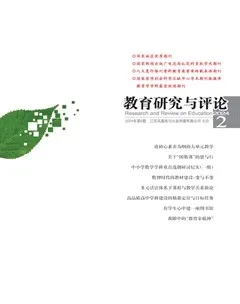我眼中的“教育家精神”
2024-05-26郑朝晖
现在大家都在谈“教育家精神”。什么是教育家精神呢?一下子也说不清,但是一说到“教育家”,似乎总有几幅画面在心里挥之不去。
一幅画面是陶行知先生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陶行知先生低眉顺目望着孩子们,那种慈爱的神情,让人动容。在中国要说起“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大概是公认的了。但是陶行知先生作为教育家的精神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对儿童的爱。爱,不是宠溺,不是纵容,爱是赤心待人,成人渡人。
我们对陶行知先生常常有一种断章取义的理解,似乎陶行知先生只是一个宗教徒式的奉献主义者:“捧著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实际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首先是致力于解放儿童的教育,是为每一个生命求真争自由的教育。
他说:“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他的嘴巴,使他能说;解放他的时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去取得更丰富的学问;解放他的空间,不把他的功课排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给他一些空闲的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学的学问,干一点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他说:“儿童的生活,是一面社会的镜子。”如果我们现在也用这样的镜子去看我们的社会现实,难道不会让我们这些后来者赧颜吗?教育不应该用来淘汰人,而应该造就人;教育不应该让人厌恶这个世界,而应该让人热爱这个世界;教育更不应该让人有死的决心,而应该让人有生的热望。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陶行知先生的“爱”,或许才是真正地理解一个教育家的伟大。
说到陶行知先生,很多人都会以为他是一个“泥腿子”教育家。事实上,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是大哲学家、大教育家杜威的及门弟子。他的教育著作最大的特点,就是将精深的理论转化为最平实的人人能懂的语言,而不是相反。如果说当今需要培植教育家精神,那么不以莫名其妙的概念来唬人,说人人能听懂的话,大概应该是第一步。这是关于陶行知先生的题外话。
第二幅画面和梁漱溟先生有关。当时,他正在山东邹平搞乡村教育运动,目光炯炯,望之肃然。他在乡村的教育是伴随着乡村的改造一起的,这一点十分重要,也是我以为的教育家精神的第二个重要内涵,那就是致力于社会改造的教育变革。教育不应该单纯地为了顺应社会,更不应该在不好的社会里助纣为虐,而应该是指向更好的社会的。
梁漱溟先生说:“今后要设施(设法实施——引者注)教育,必先体认得社会的出路所在,而把握之以为设施教育的指针,不要再盲目地办教育。——这是更要紧的一层。”我以为这是十分剀切的观点。现在有些人办教育是缺乏观照人类发展的眼光与勇气的,一味以迎合社会为目的,甚至因为利益和认识的问题,误导社会,从中干名渔利。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被社会捧得再高,离教育家的名号其实还是很远。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他的作品里用了一个词“Kitsch”,我们翻译成“媚俗”。我以为,“Kitsch”所指何止媚俗,还有谀权和逐利,所以“媚俗”这个词语似乎还不足以表达这种行为的可恶。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陷入“Kitsch”的行为中,并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对于社会非但无益,还是大有害的。不把教育作为社会的附庸,而看作一种引领社会发展的力量,看准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就以移山填海的勇气去做,这才是教育家应有的追求。一个社会的教育工作者应该眼中有道,手中有术,心中有爱,唯有如此,方能配得上“教育家”的称号。
说到梁漱溟先生,我们很多人都会以为他的教育追求就是复兴儒学,其实这是大大的误解。梁漱溟先生不仅精通儒学,而且对于佛学和西方文化都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他的教育思想与其说是东方视角,毋宁说是人类眼光。以人类视角看待教育(如果可能,还可以天下视角看待教育),才能够真正把握教育发展的方向。
第三幅画面是胡适先生的。彼时他和蒋介石并排而坐,谈笑自若,倜傥潇洒。相比较而言,作为当时的政治首脑,蒋介石反倒显得拘谨局促。胡适先生说:“只有在自由独立的原则下,才能有高价值的创造,而这既是我的希望,也是后世教育者所要努力的方向。”他还说:“我们当时曾引杜威先生的话,指出个人主义有两种:(1) 假的个人主义就是为我主义(egoism),它的性质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管群众的利益。(2) 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它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这后一种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教育既然是指向未来的,那么因循守旧、缺乏批判精神的教育,就不足以开创我们的明天。所以,我们的教育就需要培养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现代人,也因乎此,教育者自己就首先必须是这样的人。
当然,我之所以专门提到胡适先生,也是因为他和陶行知、梁漱溟这些教育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埋头苦干”。站在岸边指手画脚的人不少,真正愿意挽起裤腿躬身拉纤的苦力不多。但要想成就中国的教育,成为中国的“教育家”,恐怕就非得要有这样的“苦力”精神不可的。
今天我们倡导教育家办学,还应该清楚的一点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中国的”教育家,要办的也是中国的教育,中国有很悠久的教育传统,也有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我所列举的三位,或者放眼整个中国近现代教育发展中有所建树的大家,无不是中西融通,推陈出新的,但关键在于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颟顸自大,而是真正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去思考教育,去从事教育实践。
能以爱心对待每一个学生,能以改造社会的勇气和决心去改革教育,能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有学识,有追求,肯担当,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这大概就是教育家应该有的精神了。以这样的精神去办学,我们国家教育之强盛当可期待。
现在国家强调“教育强国”,将教育放到了民族复兴的高度去认识,这是教育发展的机遇,也是教育界同仁当仁不让的责任。以“教育家精神”来办学,也自然应该是题中之意。然而“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教育家也不是完全靠培训来培养的,更不能靠名额分配去选拔出来。教育家之形成,一定是依赖良好的教育文化环境的。
这种文化氛围中的第一点就是尊重差异、鼓励发展。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每个生命也都是在成长中的,那种从一出生就让孩子进入拼杀的“战场”的文化是培养不出教育家的。
第二,这种文化还应该有对儿童成长规律和教育科学的敬畏。全社会应该有一个共识,就是将教育交给真正懂教育的人去办。
第三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宽容,要为教育家的形成准备宽松的思考、研究、实践的环境。如果先入为主,将教育工作者的手脚都束缚住了,教育家就很难形成。当然,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看,我们要做的是对生命自由发展的尊重,对生命成长规律的尊重,还要如鲁迅先生所说的“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唯其如此,教育才能成为新教育,教育培养出的人才能成为新人。培养教育家的目的并不在名号,而在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在于我们的未来。
(郑朝晖,上海市建平中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