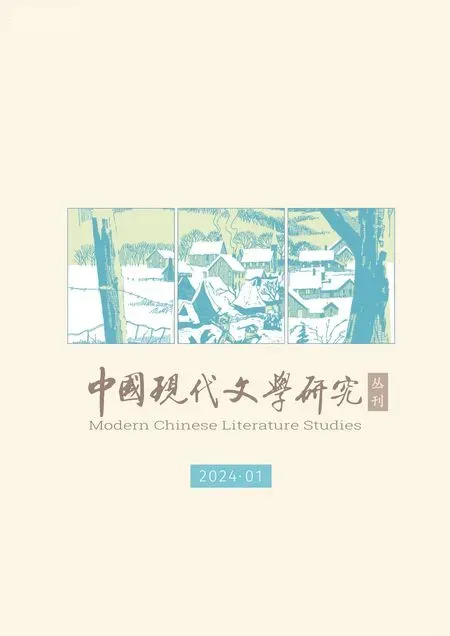“硬性电影”“软性电影”论争与新感觉派作家“转向”※
2024-05-18吴述桥
吴述桥
内容提要:虽然与电影史常见的“围剿”叙述有所不同,以新感觉派主要作家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软性电影”论者,的确“转向”国民党立场。电影需要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为基础,在左翼电影的蓬勃发展遭到国民党政府残酷打压之际,“软性电影”论者迅速填补、争夺左翼电影人被迫收缩的活动空间,从而与左翼发生“硬性电影”“软性电影”论争。这次论争显示在南京政治打压下电影发展路线发生重要调整,而“软性电影”提供了一种建立在承认南京“合法”基础上的替代选择,反映出大革命失败后部分受过左翼影响的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回归。通过对电影论争的重新梳理和考察可以发现,新感觉派在左翼和民族主义政治等之间存在交涉协商。
1930年代被称为“左翼文学的时代”,作家“左”转现象比较普遍,却也不乏脱离左翼乃至于转向右翼的例子。其中新感觉派作家群体比较特别,他们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治身份,只是与左翼关系一度密切,而且最终选择了分道扬镳,部分新感觉派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等还成了“软性电影”论者,与左翼发生“硬性电影”“软性电影”论争。研究者多将新感觉派以上动向看成是“趋新”的表现。而从后来人角度来说,前人思想倾向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被理解为某种“本性”使然,“趋新”很显然就是这样一种带有事后定性意味的解释。“趋新”的说法赋予了新感觉派以前卫、先锋等现代性内涵,这对描述中国现代主义的艺术追求和坚持而言十分重要,与此同时,它将新感觉派和左翼还有民族主义政治给有效区隔了开来,非常符合“去政治化”的愿景,但难免会遮蔽他们思想倾向的前后变化及其潜藏的思想史和文学史可能。
新感觉派是一个公认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这并不妨碍他们和政治思想发生关联。实际上施蛰存曾明确表示自己当年“左”倾过,最终因对文艺存在不同理解而又选择离开。1施蛰存晚年回忆说:“我明白过来,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的政治思想可以倾向或接受马克思主义,但这种思想还不够作为他创作无产阶级文艺的基础。”见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北山散文集》(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在一次访谈中他表示,“在政治立场上,我们是Left Wing。我们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可是文艺上,我们不跟他们走”2施蛰存:《为中国文坛擦亮“现代”的火花——答新加坡作家刘慧娟问》,《沙上的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施蛰存还为自己不再恢复组织关系作出解释:“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3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沙上的脚迹》,第129页。从施蛰存有关表述可见他们不可避免地与左翼政治发生交涉,与传宗接代等传统伦理相交涉,他们需要在政治、审美以及日常伦理之间辗转腾挪,从而选择坚持相对独立的艺术追求。
作家思想倾向先后有重要变化,应该可以被称为“转向”。施蛰存就用“转向”一词来描述自己的“左”倾:“为了实践文艺思想的‘转向’,我发表了《凤阳女》……”4施蛰存:《我们经营过三个书店》,《北山散文集》(一),第317页。由于日本曾用“转向”来指称在反动政权压迫下左翼分子“放弃其思想立场,甚至向右转变”5仓重拓:《试论鲁迅对转向的看法——以日本友人访谈录中的相关记载为主》,《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的现象,现在沿用“转向”一词来讨论新感觉派的确显得贬义色彩有些过重。如果能客观中立地来看“转向”,恢复其思想倾向转换的基本意涵,则能清晰地感受到新感觉派对此拥有清醒的认识,能更好地辨识现代主义在革命和日常之间的折冲。笔者此前论述过新感觉派从左翼转向现代主义以及部分作家转向民族主义政治的内在逻辑,其中涉及他们与左翼电影论争的一些文字,尚未论及电影论争事件对考察其“转向”的重要性,本文尝试从1930年代电影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去重新梳理、探讨和评价。
一 新感觉派作家的“政治选择”和左翼的“围剿”叙事
新时期以来已很少会简单地判定“软性电影”论者是所谓国民党“御用文人”。虽然“围剿”叙事存在“左”的痕迹1以《晨报》副刊《每日电影》为例,这份刊物是“硬性电影”“软性电影”论争的重要起点和阵地,有学者认为,“《每日电影》由一个极具左翼色彩的‘先进’影刊一转而为‘软性论者’的阵地,是主编姚苏凤的电影观念不断调整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直接结果”,“从‘软硬之争’到‘凤鹤之争’,众声喧哗中不乏组织力量介入,也有与利益相关的个人恩怨参杂其间”。参见张华《姚苏凤和1930年代中国影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4页。,但是刘呐鸥和穆时英等的确呈现出接近国民党权力的政治选择,即发生了“转向”。据过去的电影史叙述,“软性电影”论者的进攻在1933年3月办《现代电影》杂志时就开始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刘呐鸥、黄嘉谟之流,配合反动派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围剿’,办起了他们的《现代电影》杂志”2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396页。。但《现代电影》几位编辑当时只有黄天始与国民党存在间接关系3黄天始的弟弟黄天佐在北伐期间担任国民党中宣会文艺科艺术股股长黄英的助手,1933年为黄英在南京创办的东方影片公司拍摄电影《儿童之光》,1934年担任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技术专员兼剧务组组长,刘呐鸥与“中央电影摄影场”发生关系主要得力于黄氏兄弟的介绍。见秦贤次《刘呐鸥的上海文学电影历程》,《刘呐鸥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学馆2005年版,第294页。,舒諲参与过该刊早期活动,他也表示“没有发现有国民党分子掺杂其间,更不是潘公展在牵线”4舒諲:《微生断梦:舒諲和冒氏家族》,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页。。另外,将“围剿”叙事全归因于“左”的做法也有些简化,正如日本学者三泽真美惠所述,无论刘呐鸥等的主观意愿如何,他们的确都做出了“政治选择”:
原本艺华有左翼电影人田汉与阳翰笙协助,但在他们两个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逮捕后,艺华在1935年下半年找来刘呐鸥、黄嘉谟、黄天始等“软性”电影论者,并在原本公司内的左翼电影人陆续退出后,将制作方针由原本的“重视思想性”变更为大众娱乐路线。亦即,刘呐鸥之所以被民间大型电影公司招揽,其背景包括来自国民党对各电影公司取缔左翼电影人的压力。这也使得在电影理论中选择“非政治性”路线、保持沉默的刘呐鸥,得以在这股国民党暴力式排除左翼分子的过程中获得一席空位——就前后文脉而言,的确呈现出接近国民党权力的“政治选择”。1三泽真美惠:《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李文卿、许时嘉译,台大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91~192页。
因时代久远,回忆有些错误在所难免,需要研究者考证和辨析史料细节的真实性,然而也很少有人细究左翼电影人为何如此言之凿凿。
“软性电影”论者最为左翼电影人所不齿并被认为是暴露本来面目的是黄嘉谟说过的一段话:“如果目前有人摄制一部以东北血战为背景的反帝片,包你大吃剪刀。”2嘉谟:《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二)》,《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6月29日。这段常用来引证的话有些断章取义之嫌,因为黄嘉谟后半句话是在解释“包你大吃剪刀”:“因为中国早已成为半殖民地,列强是随处都可以干涉我们的。”3嘉谟:《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二)》,《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6月29日。当时电影检查十分普遍,包括苏联、德国和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都有电影检查制度。上海租界当局也对租界电影放映活动实行检查。国民党“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主要职能是检查威胁南京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影片,其中包括阶级斗争影片,还有抗日题材电影。反映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的电影为日本侵略者所不乐见,他们也会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国民党图书审查制度对左翼文化人造成了极大压迫,却由于检察官马虎造成“《新生》事件”,这遭到日本抗议,从而导致这个庞大的检察制度很快销声匿迹。4此处主要参考姚辛《左联史》第三章第六节相关叙述。见姚辛《左联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所以黄嘉谟说“列强随处都可以干涉我们”是有时代背景的。当然,禁止抗日电影主要还是由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所决定,并不能全部归结于外交压力。因此不难理解黄嘉谟说摄制东北血战的反帝片会“吃剪刀”,问题是他说这句话的时间是在国民党刚刚捣毁艺华影片公司并威胁电影行业不久。
国民党刚刚捣毁“艺华”,“软性电影”论者就接盘左翼被打压所留活动空间,不可能不影响到左翼对其政治态度的主观感受。不少新感觉派作家对电影饶有兴趣,但正式进入电影行业要比左翼稍晚一些。刘呐鸥对电影有深入研究,他在日本期间接触到了世界主要电影生产国家的一些影片和电影理论,在正式进入电影行业前写过一些电影文章,直到1933年3月和黄嘉谟等创办第一个电影刊物《现代电影》。这个刊物一开始就有批评左翼电影的言论,可电影史家认为“在1933年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根本没有能对电影界发生任何作用与影响”1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396、397页。。左翼这段时间已经在电影界基本占据了话语权并站稳了脚跟。而到左翼遭到国民党打压被迫收缩之际,黄嘉谟公开发表《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提出“软性电影”概念,刘呐鸥和穆时英等进入艺华等影片公司,穆时英掌握了左翼阵地《晨报》电影副刊《每日电影》,等等,诸如此类动作给左翼留下了“趁虚而入”的印象,毕竟“软性电影”论者的“进攻”“恰恰是发生在反动派对左翼电影加紧‘围剿’、对影片公司加剧白色恐怖、一部分曾与左翼电影工作者合作的创作人员特别是各公司老板呈现动摇的紧要关头”2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396、397页。。
这些以新感觉派作家为主的“软性电影”论者3张煊认为“软性电影”主要成员有刘呐鸥、黄嘉谟、穆时英、江兼霞(即叶灵凤)等,而黄天始、柳絮、高明等文章不多,不具有代表性,舒諲、秋士(即姚苏凤)乃后期加入,角色很难界定。陈犀禾、金舒莺也认为“软性电影”论者以“‘新感觉派’文人刘呐鸥、穆时英、黄嘉谟和江兼霞等为主将”。笔者认为黄嘉谟虽和刘呐鸥、穆时英、叶灵凤等有交集,但主要还是电影从业人员。参见张煊《吴村创作个案分析及“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论争再评价》,《电影艺术》2012年第4期;陈犀禾、金舒莺《现代电影理论的建构——重新评价“新感觉派”电影论的理论遗产》,《上海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还主动与左翼电影人展开激烈竞争。鲁思晚年回忆这场论争时给“软性电影”论者总结出“四大战术”4鲁思:《影评忆旧》,陈播主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954~955页。。这个总结或许有意气情绪,也并非完全杜撰。黄嘉谟等提出“冰淇淋”路线时十分露骨地表达出了争夺话语权的意图。黄嘉谟发明“软性电影”“硬性电影”一组对立词语,肯定“电影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是给心灵坐的沙发椅”5嘉谟:《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现代电影》第1卷第6期,1933年12月1日。。这种观点如今已被上升到了消费文化“高度”,可也忽略了其具体历史背景与所指。黄嘉谟自以为“在中国电影言论纷乱而芜杂的年头”,“软性电影”“无疑是针砭目前中国电影病态的一种有价值的主张”,他声称“她的旗帜是鲜明的,她的理论是有根据的,切中时病的”,认为“软性电影”不会导致中国电影业“误入左倾的径路”,而且可使每部影片“利市三倍”。6嘉谟:《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三)》,《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7月2日。此处所说“中国电影病态”针对的正是左翼所提出的“意识”:“一般无聊的影评刊物,动辄侈谈意识,而所谓意识云者,简直都有着很浓厚的左倾色彩。”1嘉谟:《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现代电影》第1卷第6期,1933年12月1日。黄嘉谟提出“冰淇淋”理论并不是要反对所有“意识”,他也承认“电影之中有喜剧、悲剧,也有教育片、宣传片,可以说各有其使命”2嘉谟:《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6月28日。。也就是说,“软性电影”正是为了对抗左翼电影而提出,而左翼电影人相应地“展开了对‘软性电影’分子有组织的反击”3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398页。,“围剿”叙事也由此得以产生。
二 电影文化工业特性和电影论争的发生
时至今日,那场“纸上硝烟”已烟消云散,“软性电影”也在审美/消费/本体话语中获得认可,隐隐与“硬性电影”构成奇异并置,但当前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各自观点,一旦涉及比较就成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一度和“左”倾密切的新感觉派作家为何会如三泽真美惠所说,在“国民党暴力式排除左翼分子的过程中”作出“接近国民党权力的‘政治选择’”呢?毕竟该选择意味着免不了与左翼发生冲突。笔者论述过新感觉派脱离左翼文艺运动的两个原因:穆时英等思想认识与左翼不同4吴述桥:《民族主义与新感觉派的“转向”》,《文学评论》2019年第2期。;1931年前后“左联”检讨新感觉派作家的“阶级意识”,让他们疏远左翼文坛5吴述桥:《新感觉派和左翼文学关系再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期。。然则思想观点和文艺路线并不必然导致部分新感觉派作家接近国民党,如施蛰存也没有如此选择,当他看到杜衡与韩侍桁等“隐然有结合‘第三种人’帮派之意”,他“连朋友交情也从此冷淡了”。6施蛰存:《〈现代〉杂忆》,《沙上的脚迹》,第29页。其实刘呐鸥、穆时英等和左翼在电影领域的冲突还与电影的文化工业特性有关。
电影和戏剧一样是无须观众有识字能力的大众媒体,比文字作品更具有大众传播效力,左翼知识分子很早就注意到了它们对社会的巨大影响,电影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识字率极低的工农大众而言,具有极好社会宣传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电影总是用它的内容教育观众,促使观众直接用它去衡量现实”1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列宁比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更早认识到了电影的社会价值,他确信,“只要管理得法,这个事业会有很大收入”,列宁对苏俄人民教育委员卢那察尔斯基表示,“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于我们是最重要的”。2《列宁关于电影问题的谈话——卢那察尔斯基的回忆》,《电影艺术译丛》1978年第1期。苏联电影的兴起和苏联共产党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刘呐鸥、穆时英等为电影史所关注的往往是其理论批评,不能否认其对中国电影乃至文艺理论的贡献,而就当时电影行业而言,更现实的是他们与左翼电影人构成理论竞争。左翼文化人在“左联”“剧联”成立之初已经关注到电影,1931年9月“剧联”提出“为争取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学生群众与小市民”“去发动、组织,并领导其戏剧运动”,同时“对于中国电影运动实有兼顾的必要”。3《中国左翼剧作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文学导报》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夏衍等向瞿秋白汇报时,后者也说,“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电影是最富群众性的艺术,将来我们‘取得了天下’之后,一定要大力发展电影事业”4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53页。。在左翼电影人的努力之下,左翼理论与实践获得了电影行业广泛认可,初步掌握了电影领域的话语权。问题是在左翼遭受国民党打压之际,如王尘无所认为的那样,刘呐鸥“杂拌着机械的唯物主义,神秘的观念论的破铜烂铁装点着他的‘艺术即手法’的‘形式主义’而到处招摇”,“掀动了一部分落后的电影从业人员”,刘呐鸥“更亲自编写剧本导演影片,把他的理论实践起来”,“在中国电影界形成一个势力并不是不可能的”,故而有必要“清算刘呐鸥的理论”。5王尘无:《清算刘呐鸥的理论》,《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8月21日。
这种竞争不仅是理论上的,更是涉及文化工业的实际。电影与小说、诗歌和散文等文学体裁完全不同,文学家只要有一副笔墨就能创作,而电影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据有关统计,仅仅以电影制作成本而言,1930年代中期“一部片就需要2至4万元。当时百货公司小姐一个月收入约20元,新闻记者一个月收入约40至210元”1三泽真美惠:《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李文卿、许时嘉译,第193页。。一部电影被拍摄出来,摄影场等物质设备、导演、演员、剧本等缺一不可,到上映阶段还需要有电影宣传和院线,也就是说需要完整的电影文化工业体系作为支撑。电影行业的特性让国家机器在电影发展过程中占据先天优势,国民党方面让银行停止给影片公司贷款,不准电影院上映宣传阶级对立影片,就让艺华、明星等公司不得不屈服。2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77、153、163页。瞿秋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左翼电影人在当时不可能像苏俄电影人那样能够享有国家政权提供的各种保障,当“文委”讨论周剑云邀请左翼文化人加入明星影片公司事宜时,他告诫夏衍等人“你们特别要当心”“现在只是试一下,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更不要幻想资本家会让你们拍无产阶级的电影”。3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77、153、163页。夏衍自己也说,“当时我们是寄人篱下,国民党反动派掌握政权,所有的电影制片厂又都是资本家办的。我们参加电影工作,一方面国民党、租界工部局把住了思想政治关,另一方面,资本家掌握了经济关,你的剧本不卖座就不让开拍”4夏衍:《新的跋涉》,陈播主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第11页。。左翼背后有组织力量支持,也只能是抱着尝试的态度,个人就更负担不起这个庞大产业,即便是“资产家刘呐鸥,面对制作一部片需要动辄以数万元为单位的资本额,且初期没有卖座片的情况下,这不是单凭己力就可以继续支撑下去的事业”,也不能不抓住了“大型民间电影公司有充分资金可以起用大明星制作电影的机会”,“即使明知此举代表着向国民党的政治权力靠近,对他还是充满着无法抗拒的魅力”。5三泽真美惠:《在“帝国”与“祖国”的夹缝间——日治时期台湾电影人的交涉与跨境》,李文卿、许时嘉译,第193页。
刘呐鸥、穆时英等“软性电影”论者迅速填充和挤占了左翼过去占据优势的电影生产领域。1933年五六月,周剑云再次找到夏衍,告知他已经遭到潘公展警告,并把姚苏凤推荐到了明星影片公司6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77、153、163页。;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成立“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11月12日,国民党特务捣毁艺华电影公司,散发“上海电影界铲共同志会”署名传单;12月1日,刘呐鸥主编《现代电影》发表黄嘉谟提出“软性电影”论的文章,宣称“这多无常识的制片家终于被这多‘意识先生’强奸了”7嘉谟:《硬性影片与软性影片》,《现代电影》第1卷第6期,1933年12月1日。。1934年1月,“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发表“铲除电影赤化宣言”;2月,陈立夫讲话不准放映“普罗意识作品”1《陈立夫先生谈电影:要以民族主义为艺术中心》,《晨报》1934年2月9日。;3月,“电影检查委员会”在“中央宣传委员会”召集电影公司老板、经理等人员开谈话会的同时发表“告诫电影界书”;2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304、309页。10月,夏衍等被迫离开明星,他们主导的编剧委员会也于11月撤销3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304、309页。;12月,左翼基本退出《晨报》电影副刊《每日电影》,取而代之的是刘呐鸥、穆时英、周楞伽等新感觉派作家。4盘剑:《上海〈晨报〉副刊〈每日电影〉的公共领域分析》,《文艺研究》2008年第6期。1935年2—3月,穆时英在《每日电影》发表批评左翼电影理论的长文《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1936年,刘呐鸥担任官营的南京“中央”电影摄影场实际制作负责人。
新感觉派等“软性电影”论者虽趁左翼被打击之际顺利进入电影生产领域,也使自己成为左翼猛烈攻击的对象。他们一方面向资本家寻求支持,如黄嘉谟在鼓吹“软性电影”的同时还“保证”使电影公司“利市三倍”,而左翼电影只会大“吃剪刀”而导致公司蚀本;另一方面则向国民党靠拢,如穆时英1935年2月与潘公展搭上线,担任《晨报》副刊《晨曦》主编,很快发表《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根据夏衍等回忆,尽管左翼电影人受到了国民党威胁,也给电影公司造成经济损失,不过管理层仍以各种名义和方法挽留了“左”倾导演、编剧和演员,明星、联华等依旧采用左翼剧本,大量电影刊物还掌握在左翼电影人手中,另外还新建了“电通影业公司”。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81页。足见左翼电影力量尽管遭受了挫折和更大的压力,在电影行业仍拥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此情势之下,双方的论争很难避免。在黄嘉谟发表“软性电影”论大约半年之后,即到1934年6月左右,左翼电影人“重整队伍,组织文章给这些攻击左翼电影的论客以强有力的反攻”6凌鹤:《左翼剧联的影评小组及其他》,陈播主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第940页。。
三 回归日常抑或走向革命?
从以上对电影话语权和生产领域竞争有关史实的梳理可见,作为“软性电影”论者核心成员,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他们由靠近左翼到“转向”国民党,不是遭受残酷政治迫害,个中原因有话语分歧,更有他们对电影生产关系的权衡与选择,揭示出大革命失败后“左”倾知识分子文化思想分化的一种历史向度。
1932年日寇入侵上海,对上海造成巨大破坏,工商业亦蒙受严重损失,仅以电影行业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战后有三十家左右电影公司停业,而中国人经营的电影院全部被毁。1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第182页。“一·二八”淞沪抗战激发了工商业界的民族意识,电影行业资本家也主动找左翼人士寻求合作,如明星影片公司负责人周剑云委托钱杏邨找人做“编剧顾问”,此事成为左翼进入电影界的起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和制作十分落后,左翼除了提供“反帝反封建”的“意识”,他们还提供了更为科学的电影理论和制作技术,推动了电影行业专业化发展。左翼电影人输入了苏联蒙太奇电影学派一些理论和技术,如夏衍与程步高合作编写《狂流》为中国电影界引进了苏联的分场分镜头剧本,这让明星公司与左翼电影人“一拍即合,各取所需”2舒諲:《微生断梦:舒諲和冒氏家族》,第196页。,于伶也回忆说自此以后“联华公司、天一公司等也纷纷向我们左翼要剧本了”3于伶:《党在解放前对中国电影的领导与斗争》,陈播主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第893页。。左翼电影人获得电影行业广泛认同和接受,一度几乎占据了所有电影舆论阵地,电影公司纷纷延请,许多电影从业人员发生“左转”,《狂流》《春蚕》等左翼电影大量涌现。4秦翼:《对电影“软硬之争”的再认识》,《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13年第3期。
但左翼电影的蓬勃发展遭到南京政府空前政治打压,给电影行业带来极大政治风险,捣毁艺华即为一例,而“适时”出现的“软性电影”则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合法”的替代选择。“软性电影”集“本体”“审美”“消费”话语于一体,具有较强理论性和市场导向性,给了电影行业很大安慰,是新时期以来获得“专业”认可的重要原因,然而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论述文化工业时代消遣娱乐时说,“商业与娱乐活动原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了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欢乐意味着满意”5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洪佩郁、蔺月峰译,第135页。,在他们看来,“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抗”1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威·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洪佩郁、蔺月峰译,第136页。,“软性电影”对“本体”、“审美”和“消费”的专注倾心,特别是他们所提倡的“冰淇淋”路线,从上述观点看来,就算不是为南京统治合法性进行辩护,至少也是逃避了对现实政治的反抗。
“软性电影”论者不是不懂政治的天真“理论家”,他们还发表过不少“去政治化”言论。舒諲认为穆时英“起初是从唯美主义的资产阶级观点批判电影,后来才被迫投靠国民党的”“原可以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摆事实、讲道理批驳他”2舒諲:《微生断梦:舒諲和冒氏家族》,第213页。。舒諲的看法显得有些书生气,实际上“吃剪刀”论正是黄嘉谟对电影公司拍摄左翼电影的提醒甚至警告。黄嘉谟还从正面“劝说”电影行业放弃“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诉求:
中国影业对于反帝反封建的工作,至多是和中国政府当局一般社会运动并行合作地进行。不应做不自量力的争先而致扰乱了共同的阵线。作冒险而无谋的激烈行动,以致使中国仅存的影业同归于尽,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壁垒,绝不是微弱新生的中国影业所能单独打倒消灭的,必是联合一切被压迫的展现进攻,各人做各人一部分的工作,而且这艰巨的工作是需要长时期的抗战,而不是短期间所能完成的,而同时影业从业员所应做的工作还多着呢,不要愤激爆进,因噎废食。3嘉谟:《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三)》,《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7月2日。
黄嘉谟看到了新生的电影行业的生存状况,可是这种有似于“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的论述,无异于接受“政府当局”的说辞。
“软性电影”论者的“合法”言行反映了部分文化人经历大革命风暴之后又逐渐恢复日常生活的心态。苏汶和刘呐鸥、穆时英等相熟,他晚年回忆说左翼误以为自己做了图书杂志检查官,不过他认为这也是一种职业,虽然做这官并不合适。4参见戴杜衡《一个被迫害的纪录》,《鲁迅研究动态》1989年第2期。韩侍桁还为苏汶脱离“左联”补充了一个理由:苏汶夫人一再要求过小资产阶级舒适生活。1韩侍桁:《我的经历与交往》,《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施蛰存也回忆和戴望舒、苏汶三人都是独子,受到封建家庭影响,不再参与政治活动。2施蛰存:《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北山散文集》(一),第290页。如果把“日常生活”定义为与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和公共事务等“非日常的社会生活领域”区隔开的,“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3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自身现代化的文化透视》,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1页。以上关于职业、传宗接代和物质生活等事例说明,1930年代的确存在从革命氛围中逐渐回归“日常生活”的各种因素。选择回归日常还是继续抗争各有复杂因缘,但既然选择回归,那也就意味着脱离左翼运动,转而接受南京统治。
“硬性电影”本身也存在革命与日常生活的交涉协商。职业革命家以革命为业,偏偏生活在上海这个“东方魔都”,如何处理和日常的关系,一样是他们要面对的“琐碎”。左翼进入电影行业,首先意识到“要发表影评,非在公开合法的大报上争取版面不可”4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58、159页。。在“初战告捷”后“文委同意了‘剧联’成员打入各电影公司和各报副刊,不少党员走出‘地下’”5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第158、159页。。走出“地下”非“暴露身份”,左翼电影人是以“化名”加入电影界,这给他们的活动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即便如此,他们仍然遭遇了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质疑。如舒諲提出,他被左翼影评人围剿,是因为他批评左翼影评人“靠稿费吃饭”6契夫(舒諲):《契夫来信》,《晨报·每日电影》1934年10月31日。。夏衍也坦承要与电影行业搞好关系,“就不能完全违背他们的生活规律。我一辈子不会跳舞,但为了工作需要,也得和导演一起进跳舞场,不跳舞就在旁边坐着”7夏衍:《从事左翼电影工作的一些回忆》,会林、陈坚、绍武编:《夏衍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1页。。针对与资本家“合作”的指责,夏衍借用瞿秋白的话为自己辩护,“假如我们的剧本不卖钱,或在审查时通不过,那么资本家就不会采用我们的剧本,所以要学会和资本家合作,这在白色恐怖严重和我们的创作主动权很少的情况下,便不能不这样做的”1夏衍:《新的跋涉》,陈播主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第11页。。
左翼作家不是没有日常生活,只不过与选择回归日常的新感觉派作家存在根本不同,他们主要还是采取革命立场的言说和应对。1935年,穆时英公开指认“硬性电影”论者的隐秘政治身份:“他们向演员和导演提出充实生活的口号;所谓充实生活就是要求演员和导演不但是胶片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实生活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一期的代表人很多,以尘无、鲁思、唐纳为领导者。”2穆时英:《当今电影批评检讨》,《妇人画报》第31期,1935年8月。穆时英应该清楚自己的指认已经从法律层面打破了左翼和电影行业合作的脆弱基础,无异于向对手发出政治乃至死亡威胁。鲁思随后向法院提请刑事诉讼,假托自己是三民主义信徒,借此拖延时机逃往海外。3舒諲:《微生断梦:舒諲和冒氏家族》,第218页。他的逃亡说明,尽管电影行业和左翼存在一定程度的合作,即便部分左翼电影人被“软性电影”论者揭穿真实身份后双方仍保持私下友谊,然而这无法改变电影行业接受南京“合法”统治的基本现实。电影行业应该走“反帝反封建”还是“冰淇淋”路线呢?双方最终诉诸和应对“法律”的方式将1930年代日常生活的政治根基给赤裸裸暴露了出来。“硬性电影”“软性电影”之争最终给出的答案不言而喻。
结 语
刘呐鸥、穆时英等曾长期被左翼电影史叙述为反动势力,自1980年代被重新发掘以来一直对其现代主义给予许多肯定,文学史研究至今仍主要持续对其小说和电影的先锋实验、审美自治以及都市文化精神等进行现代性阐述。新感觉派诚如史书美所说,“现代中国整个的现代主义事业关注的是形式、技巧和语言”4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17页。,但詹姆逊却提出要对现代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反思,他认为“人们对现代主义所持的惯常看法……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特点都不再充分和具有说服力了……即便仅仅是为了更有力地展示开始于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原型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即文学外的因素的预示性在场的话,在当下的语境中也仍有需要说明的东西”1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陈永国译,王逢振主编:《论现代主义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7页。。对新感觉派的现代主义也需要回到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当中加以重新审视。
研究者不是没有关注到新感觉派曾经“左”倾,而是将其理解为“趋新”表现,并且赋予其现代性内涵,不过“趋新”不只是先锋、前卫、时尚和审美的代名词,同时暗含缺乏“诚心”之意。“趋新”似乎印证了左翼理论家所批评的“阶级意识”不正确,加强了对新感觉派的现代性论述,不出所料也抹平了新感觉派思想倾向前后变化。可即便加入某个政党也不代表就一定具备相应思想觉悟,不能通过是否有“诚意”来判断思想“合格”与否。通过对“硬性电影”“软性电影”论争前后有关史实的考述,我们看到新感觉派不但“左”倾过,而且其主要核心成员还转而接近民族主义政治,这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思潮起伏变化密切相关,不能简单地用“趋新”一词来加以概括。
新感觉派主要作家的“转向”折射出时代风潮对中国现代主义发展的巨大影响力。史书美曾阐述过现代主义产生的半殖民语境,在此基础上提出新感觉派并没有明确政治倾向性的观点,她认为刘呐鸥大部分小说“不含任何明确的政治倾向,相反,却充斥着意识形态的暧昧”;穆时英“随心所欲地选择着自己的立场”;而施蛰存的心理分析小说“明显经过了去政治化的处理”。2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第323、378、409页。这和“趋新”论看似有些接近,都将“转向”看成是某种本质使然,但史书美揭示出了政治策略性一面。而笔者进一步发现新感觉派在左翼和民族主义政治等之间存在交涉协商。电影文化工业特性决定了以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为代表的“软性电影”论者并不能以一己之力左右电影事业,他们对电影艺术性的强调与他们和左翼争夺电影领域话语权的竞争存在内在关联,而电影产业依赖、话语权争夺、政治风险规避等都成为他们“转向”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