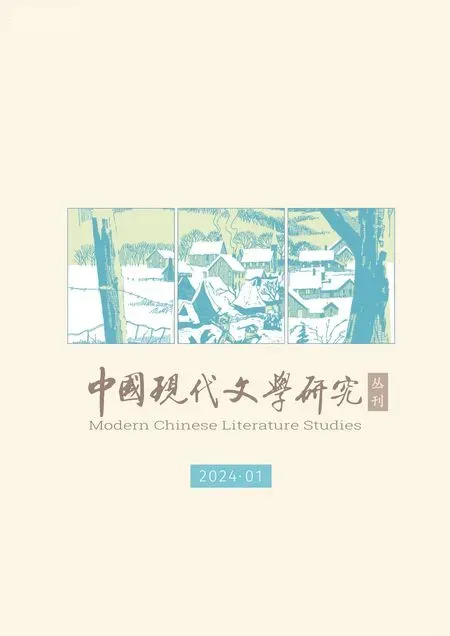琴师的复活与隐遁
——1950至1970年代“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探析
2024-05-18于慈江
于慈江
内容提要:“新意境诗”是学者谢冕对“西南边疆诗群”诗风的命名。而所谓“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只是加大其涵容量,以便涵盖共和国前30年相类的诗歌倾向。虽作为一个诗歌群落、一场诗歌运动或一种诗歌现象,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自有其优长与缺欠,它的生成、发展与式微,或者说它所象征的琴师的复活与隐遁,都有其内在必然性,但它毕竟作为与写实倾向相对的不可多得的抒情倾向、与政治抒情诗的豪情意向相对的不可或缺的柔情意向,为当代中国新诗的发展铺垫了基石。因此,不管新诗的观念已经或将要有怎样的深化,不管抒情诗的抒情意向已经或将要出现怎样不同的变延,以公刘和李瑛等为代表诗人的新意境生活抒情诗那清越的琴韵,都将作为中国新诗史的保留曲目长久回响。
一
翻开百余年中国新诗史,在细细咂摸各个篇章记载的不同时期新诗呈现的迥异格调与情韵并进而剀切评判其各自的功过与优劣时,任谁也不能不着意注目甚或忘情流连于共和国之初,那主要由一群战火洗礼过的、生活在西南边疆的青年军旅诗人谱写的独特篇章。不绝如缕地,人们为之题写下“新山水诗”、“新意境诗”1谢冕教授在北京大学主讲“当代诗群研究”时用语。、“青春颂歌”2详见骆寒超《新诗的来路与去向》,湖南《中外诗坛报》1985年第1期。、“西南边疆诗(群)”之类篇名。
一时间,这些缤纷呈现的清纯的诗与诗的清纯宛若清凉和风,润泽和舒爽着人们久被战火硝烟熏灼得异常浑浊干涩的双眸。人们迫不及待地为这共和国诗坛的新生儿及其清越啼哭额手称庆,不知不觉中已是欣然见证了新诗诗坛上复活的琴师与琴师的复活。无疑,这一隐含的内容要意味深长得多。
近代以来,中国连年战乱频仍,阶级与民族的争斗无时不在排斥着闲适诗情与淡雅画意。在民族安危所系的抗战时期,诗人闻一多曾这样强调:“这是一个需要鼓手的时代,让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至于琴师,乃是第二步的需要,而且目前我们有的是绝妙的琴师。”3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闻一多全集》第2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原载《〈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3年11月13日。这一由对比至阳与至阴两类音乐演奏者而生发开来的呼吁,道出了文学艺术受政治与社会历史因素制约的严峻事实,以及阳刚文艺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不可或缺的时代价值。
诗人们也正是意识到了自身的历史使命,用诗句自觉不自觉地应和着民族觉醒的时代鼓点,在阶级与民族的解放运动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无论是郭沫若、艾青,还是田间、臧克家,甚至1949年之后的贺敬之、郭小川等,莫不在前赴后继地担当时代的鼓手。
与此几乎同时,快板、唢呐式的叙事写实诗以其平易晓畅、极接地气的优长,在此基础上大为发展,共同汇成解放区文艺特别是诗歌创作特有的两大传统,进而予国统区文学以深远影响——如之于“九叶”派诗人后来的诗。持续到1950年代初,闻一多所暗示的第一步“需要”终于得到极大的甚至膨胀了的满足。
不过,与这一历史状况相伴随,闻一多所谓“有的是”的琴师不知何时,却早已寥寥不知所终,更不消说那“绝妙的琴师”。《雨巷》(戴望舒)里的惆怅与哀怨,《湖畔》(汪静之等)边的绻缱与情爱,《流云》(宗白华)迎送的飘逸与精灵,《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的《雪花的快乐》(徐志摩)一概难觅影踪。或者说,杂树生花般优美而轻灵的琴韵不知何时开始,已成为人们永久期待填补的心灵与历史空白。这一心理期待在社会历史变更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时段时,呈现得尤为突出与强烈。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那仿佛久违了的、事实上又绝对是崭新的柔美而清健的“一朵云”“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1公刘诗《西盟的早晨》句,参见公刘《黎明的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19页。升起在刚刚矗立于废墟之上的《黎明的城》2《黎明的城》系公刘诗集名,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时,才那般亲切醒目、清雅动人,激起人们难以止歇的强烈共鸣。相比之下,琴师已非旧时人、琴声已非昔日韵的事实则显非重要。
然而,也正因了如此深刻的历史矛盾与文化纠结,共和国春天的琴师从其复活的几乎第一天起,便无法逃避加诸其身的各式要求和制约。
不妨回望一下“爱情歌手”闻捷的爱情诗代表作《吐鲁番情歌·舞会结束以后》3闻捷:《舞会结束以后》(组诗《吐鲁番情歌》含《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成熟了》《舞会结束以后》《种瓜姑娘》),《人民文学》1955年第3期。后收入诗人第一本诗集《天山牧歌》,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第30~32页。:
深夜,舞会结束以后,
忙坏年轻的琴师和鼓手,
他们伴送吐尔地汗回家,
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你心里千万不必为难,
三弦琴和手鼓由你挑选……”
“你爱听我敲一敲手鼓?”
“还是爱听我拨动琴弦?”
……
“去年的今天我就做了比较,
我的幸福也在那天决定了,
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
带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去了。”
这首背景是深夜舞会、主角是男女青年且大部分由对话组成的诗生活气息浓郁,颇具边疆色彩与民族风情,读来生动可感。无非是写“琴师”与“鼓手”各凭实力,竞争同一位姑娘吐尔地汗的青睐,却绝未料到结局竟出人意表:另一位没工夫露面、正忙于边疆工业建设的年轻人阿西尔早已赢得姑娘的心!
暂时撇开这首诗对百爪挠心般的爱情心理的生动描摹,以及别致情致和幽微内涵不谈,人们会发现,无巧不巧,它刚好是共和国前30年诗坛一个不可多得的绝妙象征:琴师与鼓手(借用前举闻一多的妙喻)的诗创作虽仍存在,但规模、实力及可接受性远不如直接介入生活、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俘获女青年吐尔地汗芳心的阿西尔所喻);琴师与鼓手也受到了写实倾向诗的极大熏染,而具有了程度不同的写实倾向;换一个角度看,非均衡三足鼎立的景观也多少见出了共和国开初,诗坛一定程度上的红火兴旺。
但更为精准的概括或许是,这种哪怕是隐约的三足鼎立也极端不均衡:它不仅表现为如上面这首诗所描写的琴师与鼓手同那位隐在的年轻人阿西尔(喻写实倾向)之间的前者弱而后者强的悬殊反差,而且也表现为琴师境遇相对于鼓手的不可同日而语。事实上,鼓手擂动的强劲鼓点曾响彻于1930—1940年代之交。1940—1950年代之交虽一度沉寂,让位于具写实倾向的民歌叙事体,但从1950年代末直到整个1970年代乃至1980年代之初,一直与写实倾向的诗并驾齐驱,甚至时居最前列,成为时代的诗美风尚,被盛誉为“政治抒情诗”,涌现出郭小川、贺敬之一类标杆诗人。而琴师清幽涓细的琴韵客观说来,则始终是被铿锵豪壮的鼓点与直白明快的快板、唢呐声遮蔽挤压得气若游丝,一度复又沉寂。
这里所谓的“遮蔽挤压”,其一是指,琴师的琴韵被后二者程度不一地同化乃至边缘化,且始终摆不脱这一尴尬的命运与危机;其二是指,新诗理论批评界甚至相当一部分读者群几乎先天地认定,琴师及其琴韵的致命缺陷不可救药,包括所谓无病呻吟与小资情调,始终试图排斥或矫正之。譬如,历年的《诗选》序言(由《诗刊》主编臧克家执笔),连同沙鸥、安旗、沈仁康等诗评家在“抒人民之情”这一名义下,对诗人公刘,如其诗《姑娘在沙滩上逗留》(1956)1公刘:《姑娘在沙滩上逗留》,《离离原上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1~142页。等不断点醒和批评2详见沙鸥《谈诗》,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沙鸥《谈诗第二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沙鸥《谈诗第三集》,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安旗《论抒人民之情》,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沈仁康《抒情诗的构思》,湖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等等。,均可见出这一痕迹。
姑娘,你为什么为什么
在夜的沙滩上逗留?
听任清凉的风、清凉的星光
灌满你的衣袖?
……
我不觉得有什么灌满了衣袖,
灌满了我的心的
是甜蜜的忧愁,
我的人,今夜在海上住宿。
我的人,此刻正驾着一叶扁舟,
系着我的心儿浮游……
(公刘《姑娘在沙滩上逗留》节选)
公刘这首诗一问一答,颂扬了健康的你牵我挂、人间情爱,回应了人们对深夜一位妙龄少女在海滩上孤身鹄望、久久不去的好奇或质疑:她不是无所事事,更非感情受伤,而是心中牵挂着驾船出海、竟夜捕鱼的爱人。姑娘的鹄立中宵虽不免让人生疑,其回答亦非豪言壮语,但毕竟代表了人民一分子的朴素情爱,本不应妄加挞伐。
当然,纯从技术层面如押韵考虑,倒数第二段最后一句诗“我的人,今夜在海上住宿”似应改为“我的人,今夜(会)在海上住一宿”。因为动词“住宿”的“宿”读“素”音,名词“一宿”的“宿”才读“朽”音、胜任韵脚。
或许唯因如上所描画的奇特历史格局,才使得我们对共和国特定的30年“琴韵”在视听觉上的重新“咀嚼”,有如品味一枚隐有回甘的橄榄般饶有兴味。
二
为了整体把握,笔者把上面已得到形象化界定的所谓“琴韵”,定名为“新意境生活抒情诗”。
“新意境诗”是学者谢冕对“西南边疆诗群”创作一个十分精当的命名。这里只是把这一称谓的涵容量稍予扩大,以便涵盖共和国前30年具有类似倾向的新诗。以此为规范,我们会发觉,“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呈现方式十分像一个不尽规则的同心圆:圆心自然是我们已经以及下面仍要多方意会的,使我们得以用“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概念来总括这一纷繁现象的、那个很难三言两语言传的核心意念,也即本文试图达到的最终目的;而最里面的一个圆圈理所当然是西南边疆诗群,以军旅诗人公刘、白桦等为代表;接下来一个稍大的圆圈,是几乎整个军旅诗,由诗人李瑛为杰出代表,直到1970年代末;再外面一个圆圈,是以诗人陆棨、严阵等为代表的,主要体现农村风光与生活的诗歌;最外面一个圆圈,是以诗人蔡其矫等为代表的倾向于个人情怀的一类小众诗歌,以及那些以小花小草为指征的所谓山水意境诗等。
之所以看起来像一个类同心圆,是因为圈子与圈子之间往往有着很大复合面。譬如青年军旅诗人与边疆地域,便几乎是它们共有的贯穿性标识。而这也便自然地导出了它另一个特点,即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每一个圆圈或种类相对而言,都可说“五脏俱全”,其基本内涵从而可相互替代与置换。这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举一反三的便利。而无论就其集成性还是实际影响而言,最适于解剖和聚焦的都要首推作为发轫点的西南边疆诗群。
可以说,“云”的缥缈清新、“炊烟”的亲切暖心、“叶笛”的悠扬清亮所融成的一幅意境画卷,暗示性地包容了以公刘和白桦等为代表的西南边疆诗人全部的卫国与建设热情,更可代表其诗作的主体特色,也即整个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基调。诗人蓝曼曾把自己的一部诗集特地命名为《绿野短笛》1蓝曼:《绿野短笛》,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而自谦平生只做了新诗诗评一件事的诗评家谢冕,也曾锐敏而精譬地比较过公刘、白桦与李瑛等诗人笔下各个不同的“云”的奇幻与清新——1详见谢冕《和新中国一起歌唱·天边涌出灿烂的星群》,《共和国的星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7~49页。
我推开窗子,
一朵云飞进来——
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
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
(公刘《西盟的早晨》2公刘:《佧佤山组诗·西盟的早晨》,《黎明的城》,第19页。)
一朵云,
拧下一阵雨,
匆匆地掠过车篷。
(李瑛《雨中》3李瑛:《雨中》(1961),《红柳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51~52页。)
在“云”之外或之下,或可先感受一下诗人公刘一首曾被质疑的超短诗,感受一下海滩和心间,以及爱情的幽微与辗转:
海把贝壳失落在沙滩,
我把爱情失落在人间;
凡属我的,我必追寻,
而且我知道,此刻,正是此刻,
它藏在某一个幽闭的心坎……
(公刘《海把贝壳失落在沙滩》4公刘:《海把贝壳失落在沙滩》,《离离原上草》,第144页。)
公刘的这首《海把贝壳失落在沙滩》(1956年)仅有五行,却能巧用既兴又比、相互映衬的比兴与镜像,以退潮的海自况失恋的“我”,让搁浅的贝壳和失落的爱彼此寄托、遥相互寓或互喻,进而衬托“我”对爱情的不甘,以及对又一场尚无法定位的心心相印的期许……这虽缺乏边塞风情因子,也是典型的“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抒发的是一己心境,带着鲜明的小我印记和生活实感。
接下来,不妨再以代表人间烟火气的意象“炊烟”为视点,具体比较一下梁上泉的《雪地炊烟》(1955年)1梁上泉:《雪地炊烟》,《喧腾的高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24~25页。和公刘的《炊烟》2公刘:《佧佤山组诗·炊烟》,《黎明的城》,第14~15页。亦可参见公刘《离离原上草》,第66~67页。——各以近结尾的两诗段为样例。这两首诗在自我之外,感怀时事、珍惜和平与安宁。
前者把炊烟比喻为象征和平、安宁与温暖的“报信白鸽”:“住在草原上的牧人,/放声对炊烟欢笑;/住在雪山上的猎手,/伸手把炊烟拥抱。//炊烟呵炊烟,/愿你升得更高,/带着我们建筑的热情,/把万里冰雪一概融消!”后者则这般描述军旅儿子与母亲温馨的对话:“母亲,我告诉你,/我喜欢瞭望祖国的炊烟,/炊烟,就是平安。//不错,炊烟报平安。/唯愿它长飘在你头上,长记在你心间,/不要再有炮火,再有硝烟。”
同样是聚焦炊烟这一温暖意象,一个是描写筑路大军在雪野上,像放飞信鸽那样,用炊烟升起温暖信号;一个是凸显在与母亲的对话里,诗人内心深处对祖国不再有炮火硝烟的深深祈愿。二者无疑具有情致上的一体性,温馨而向上。这种比较单纯而明朗的情绪在当时说来非常真实而感人,现在读来仍觉亲切。
应该说,共和国最初的十年极特殊——战争硝烟刚熄,边疆秀色便一下子袒露在那些平时被战火所烤炙着的战士面前,与之相伴随的贫瘠一面反而不被注意。而那些神奇瑰丽的云雾、山脉与河流对他们来说,无疑还有着更特殊的意味——毕竟都是他们及其先驱用鲜血换来的。于是,他们之中的文艺“细胞”被迅速地激活,进而被眼前的美好景致深深陶醉。随着其诗情山泉般涌出,极具抒情意味的边疆诗便自然而然降生。
这不仅仅发生在西南,也发生在整个边疆,如西北边疆以写《果子沟山谣》1闻捷:《果子沟山谣》(组诗九首),《天山牧歌》,第43~63页。著称的闻捷、东南边疆以写大海闻名的韩笑,以及东北边疆写出《金黄金黄的婆婆丁呵》2万忆萱:《金黄金黄的婆婆丁呵》,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一类作品的万忆萱均属此列。
无论是参较中国新诗史任何一个阶段,还是远溯古代特定的“边塞诗”,新中国边疆诗的崭新性和独特性都十分突出。中国古代边塞诗描画的多是中国北部边塞的雄浑苍凉、艰难时世,以及诗人投射其上的或悲凉或豪壮的心境。而近现代的中国边疆大多兵荒马乱、连年征战、穷困闭塞,尤以1930—1940年代为甚,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况乎诗神,诗情自是极其淡漠。
与古代边塞诗相比,以闻捷等为代表的西北边疆诗虽诙谐轻松、气魄较大,染带着西北特别是新疆各民族的浑朴与豪气,却已称得上弥足“秀丽”了。但秀丽清奇得让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则还要算以公刘等为代表的西南边疆诗。
自古至今,中国诗里所谓边疆或边塞大都指北部,赖以御辱于外。南方,哪怕是西南,皆被忽略。因而,共和国之初西南边疆诗群的崛起,实在是一个新的诗现象,是抗击内敌(包括打击残匪)后的簇新发现。灵山秀水的西南边疆同到处是沙漠、雪山和草原的北部边疆一清奇一粗犷,注定了西南边疆诗与西北边疆诗的一清丽一阔达。当然,不排除二者的临界面融合,如虽同属西南界域,川藏间梁上泉诗中的“高原”“红日”与滇边公刘诗中的“云”“雨”便明显一酷烈一温润。走笔至此,实际上已涉及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一个基本成因。
其次一个成因是,对民歌与古典诗相结合的实际提倡(虽然作为口号,尚要更晚一些)。或者说,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是这一“结合”真正意义上的产儿。就此前的解放区诗歌而言,对民歌与古典诗歌多半还只停留在外在形式的简单模仿或粗糙借用——如李季某些诗。与其相对照,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则是在二者基础上,真正“化”了出来。我们当然因此也可以说,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是现代新诗于理想状态下,正常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复活”形式,一如本文开篇所强调的那样。这是因为,尽管事实上或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一诗现象是无知或紊乱的结果(相对于正常发展的诸环节),但更准确地说,却是无知基础上不尽平衡的全方位“有知”的结果。
这一化用的痕迹虽大都比较模糊,但的的确确化用自民歌,主要体现在风格和形式,如句式与韵脚上。而骨子里,则是古典诗歌的“练”字与造“境”。但整体上毕竟仍属极自由蓬松的体式,显非凭空而来,至少得到过现代新诗优秀遗产一定程度的浸润。不过,若更进一步推敲便可发现,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对各方面影响的接受与化用具有相当程度的不自觉性与难于自我把握性。这直接导致这一诗群内部水平的参差不齐(包括一个作者自身创作系统内部的忽强忽弱)。
除了因当时文化承续上的失序与限制而导致的混乱,造成这一不自觉性的显在因由还有一个,那便是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创作主体普遍文化水准不高,多半出自当时部队文化生活活跃分子。加之部队纪律又比较严明,思想相对单纯。因而他们在心态正向之余,各方面素养不免略显贫血。但恰恰是在无知与有知、多杂与不足之间,诞生了一个新生命。这实在是造物的神奇与不可捉摸处。伴随创作主体所产生的这一状态,可说是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一个基本特色。
它的第二个基本特色是“宣叙”性。这是为了与写实倾向诗的叙事性相区别而借自歌剧(与笔者另一篇文章《新诗的一种“宣叙调”》1于慈江:《新诗的一种“宣叙调”》,《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第4期。借用的角度不尽相同):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同写实倾向诗相比,可以说没有什么写实性;但若比之纯粹意义的抒情诗,则又有一定的叙事性。它毕竟无法逃避诗歌发展整体框架的限制。
与此相关联的第三个基本特色,是实(开头铺叙)→虚(结尾升华)互补与递进的造境谋篇方式,如下面这首短诗所示:
三月、四月、五月,
雨淋湿了海和它的贝壳。
一只贝壳,一片大海,
无数贝壳向我诉说。
贝壳说:告诉我吧,
告诉我今天欢乐的生活;
我虽然死了,却留下
一只金色的耳朵,
为了倾听,倾听这时代的歌!
(李瑛《贝壳》1李瑛:《贝壳》(1956),《红柳集》,第79页。)
李瑛这首两段九行(原诗排列为八行,倒数第二、三行为一行)的《贝壳》(1956年)一诗上四下五:上段写春夏之交的雨和雨中的大海、贝壳,是有一定写实性的状物与写景、铺叙与铺垫;下段则借自拟为“(被留下的)一只金色的耳朵”的“贝壳”之口,表达主动倾听“时代的歌”的心意,进而衬托和强调“今天欢乐的生活”的现实存在,是为点题和升华。
这种立意造境方式因小而大,依形赋神,举一反三,见微知著,实际引发的是由时空距离与情境反差蕴蓄的内在张力。很多优秀的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也恰恰好在这一点。
总之,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把握世界的方式既不同于一般写实倾向诗的叙说和讲故事,更非政治抒情诗的呐喊,而是趋向于凸显某种内在意蕴的视画与谛听。或者说,它不仅很大程度上超越了过去那种陈旧的叙事模式,也初步超越了一度流行的情感-想象抒情模式,接近了体验-感受的现代抒情模式。由“在敦煌,/风沙很早就醒了,/像群蛇贴紧地面,/一边滑动,一边嘶叫”(李瑛《敦煌的早晨》2李瑛:《敦煌的早晨》(1961),《红柳集》,第122页。)等诗句可略窥一斑。
这或许可说是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较之写实倾向诗与政治抒情诗更富持久魅力的内在缘由。当然,由于历史与时代限制,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不可避免地仍大量保留一些单一而浮夸的想象因素。或在想象的基础上练意,基本趋势是由坏想象好,由好想象更好。这是本文后面将提及的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整体上有单一雷同感的一个基本成因。而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排斥想象与情感的那些意向多半也只是被动的,虽摒弃了过去狂妄超越客体的模式,却又不自觉地堕入对客体特别是大自然的局部膜拜,本质上并非源于后来那种对于主体能力的客观评价与认可。
三
诚如前文所提及,作为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前期或最里面一个圆圈的西南边疆诗群最富集成爆发性——在1950年代早中期短短几年间,便涌现出了公刘、白桦、周良沛、杨星火、高平、顾工、雁翼、梁上泉、饶阶巴桑、高缨和傅仇等声名大振的青年诗人。相信李瑛、公刘和顾工如下三段话,十足地代表了这批军旅诗人当年共同的心声与自我定位:“一个诗人的任务就是一个战士的任务,诗人的声音应该是时代的声音。”1李瑛:《自序》,《李瑛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因为我是兵士,/我才写诗;/因为我写诗,/我才被称作兵士。”2公刘:《因为我是兵士》(1956),《离离原上草》,第53页。“一个辉煌的胜利,接着一个更辉煌的胜利;一个欢腾的节日,接着一个更欢腾的节日……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主题……诗歌的主题……”3顾工:《后记》(1957),《军歌·礼炮·长虹》,重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6页。
下面这两段诗分别来自白桦和藏族诗人饶阶巴桑,虽然写作的时间跨度几近25年,却刚好都是以军人的身份写巡卫边疆的巡逻兵(也刚好都有用破折号习性),写他们如何以苦为乐、如何因保家卫国而自豪:
淡蓝色的天空、河流和森林,
淡蓝色的轻雾和浮云,
透明的淡蓝色啊!
——红河浸沉在淡蓝色的黄昏。
我的刺刀闪着淡蓝色的光芒,
我大睁着一对警觉的眼睛,
祖国最前面的一寸土地上,
刻下我的脚印。
(白桦《淡蓝色的黄昏》首两段)4白桦:《淡蓝色的黄昏》,《金沙江的怀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1页。
细细的风牵我缰绳走栈道,
——翻一山,尝一山野果;
浅浅的浪送我马蹄过沼泽,
——走一路,拾一路牧歌。
甜的山果,甜的牧歌,
巡逻兵再不能贪得更多:
让剩下的一切酸酸甜甜的滋味,
悄悄流入亲人的生活。
(饶阶巴桑《牧歌》)1饶阶巴桑:《棘叶集·牧歌》,《爱的花瓣》,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7~168页在饶阶巴桑诗集《石烛》(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3页)的《棘叶集·牧歌》里,最后两句的版本略有不同,是“让剩下的一切甜的滋味,/悄悄流入他人的生活”。
白桦的《淡蓝色的黄昏》写于1950年代初,其首两段诗不厌其烦地连着用了五个“淡蓝色”,把一个黄昏时分的奇幻河畔边塞烘托了出来——这既是“我”这个巡逻士兵巡哨和保卫的内容,更是“我”赖以依托的强大背景。这两段诗的可贵之处在于,它首先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了唯美的氛围——无论是“淡蓝色的天空、河流和森林”,还是“淡蓝色的轻雾和浮云”,都是美得“透明的淡蓝色”,而不是日复一日巡哨的那一份固有的单调和无聊。尤其是,透过最后一个淡蓝色——“闪着淡蓝色的光芒”的枪刺,与“我”大睁着的“一对警觉的眼睛”互衬,让人们看到了在岗边疆卫士的英武剪影。
与此相仿佛,饶阶巴桑的《牧歌》虽然写于20余年之后的1979年,表现的却也是边疆卫士一路巡逻时的苦中作乐:无论是牵着缰绳顺风走栈道,还是骑着骏马踏浪跨沼泽,边塞巡逻兵“我”都能恬然以对,或在翻山越岭过程中顺手采几枚野果一尝,或一路涉水时顺耳听一嗓牧歌。与白桦的诗一口气连用五个“淡蓝色”相类,饶阶巴桑这首诗连用四个“甜”,强调“我”作为巡逻兵的知足常乐——一路的野果吃起来甜,一路的牧歌听起来亦甜,足矣,其他的甜美由别人(“我”所卫护的人,亲人)来享用好了。
不过,最能代表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前期水平的还得说是诗人公刘。
在其前期创作中,公刘接连出版了《边地短歌》(1954年)1公刘:《边地短歌》,湖北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和《黎明的城》(1956年)等几部诗集,以其活跃的创作姿态,显示出了雄厚实力。他颇擅短诗,或由几首短诗构成的组诗,偏重抒情性和哲理性,主体诗风与特色在于工巧凝练、细腻自然、意蕴隽永而又变动不居,如其《山间小路》2公刘:《佧佤山组诗·山间小路》,《黎明的城》,第16页。一诗首段:
一条小路在山间蜿蜒,
每天我沿着它爬上山巅;
这座山是边防阵地的制高点,
而我的刺刀则是真正的山尖。
而更主要的则在于“自我”意念较强,从他时不时会冒出《迟开的蔷薇》(1956年)3公刘:《迟开的蔷薇》,《离离原上草》,第149页。之类的一些作品便可略见一斑:
盛夏已经逝去,
在荒芜的花园里,
只剩下一朵迟开的蔷薇;
摘了它去吧,姑娘,
别在襟前,让它
贴近你的胸膛枯萎……
这一类类乎小花小草小资,带着淡淡一丝幽婉、哀戚与不甘气息的作品在当时,曾遭到严厉批判。然而,也恰恰是这类作品体现了一定的“超前性”,从而提供了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较之左近的其他诗现象具有更接近纯诗的本质、艺术上也更为成熟的可能性——尽管悖论在于:这一可能性的实现说到底,要以突破新意境抒情诗最初一套艺术方式为前提。
当然,若论谁在整体上最能代表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以及谁创作成果最为丰富、气脉和后劲最为悠长,则再没有比北大出身的诗人李瑛更当之无愧的了。
首先,虽然他仅仅是到过大西南,但恰恰是他,把西南边疆诗群有关诗歌的初具规模的、哪怕尚只是萌芽状态的艺术方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经过他的光大改善之后,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才真正名副其实起来,甚至说它是“李瑛体”亦不算过分。在李瑛诗集《红花满山》(1973年)1李瑛:《红花满山》,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版权页后一页上,有两句乍看毫不起眼的“题记”:“看那满山满谷的红花,是战士的生命和青春。”这堪称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质地的绝妙界定和写照,与诗人白桦后来在编自选诗集《白桦的诗》2白桦:《白桦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时,把总共两辑的第一辑诗命名为《我的青春在边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我(“战士”及其生命)、青春和边疆(李瑛所谓到处是红花的山谷)作为三大关键词或要素,正是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主体构件。
其次,虽然任何诗人诗艺的趋于成熟都是逐渐演进的,但在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诗人群里,要以李瑛最具艺术恒定性(特别是与公刘相比)。他从1950年代初起,一直到1970年代末,持久地坚持写诗,先后出版了20多本诗集,如《野战诗集》3李瑛:《野战诗集》,上杂出版社1951年版。、《静静的哨所》4李瑛:《静静的哨所》,解放军文艺社1963年版。、《枣林村集》5李瑛:《枣林村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红花满山》等。特别是后两部诗集,均出版于1970年代,成为当时荒芜的诗坛上绝无仅有的富于可读性的作品。而它们也恰恰延伸了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两个最主要场域,即乡村与军旅。前者原是以写《江南曲》6严阵:《江南曲》,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版。驰名于一时的严阵和以写《灯的河》7陆棨:《灯的河》,重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引人注目的陆棨为代表。后者原是以西南边疆诗群诸诗人如公刘为代表。
这两大场域之所以为世人尤其是诗人所瞩目,是因为两者至少都与大自然有关,都足具朴野淳厚气息,也都有生发出诗心、诗情与诗意的纵深、空间和可能性。而和平年代的军旅生活场域又往往以边疆为主,所谓金戈铁马、戍边卫国。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主要诗艺方式和诗意张力既经由它们涵养,又反过来用于呈现之。但就事论事,李瑛表现得最多也最成功的还是军旅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李瑛,带动了整整一代军旅诗人的成长,从而使得20世纪60—70年代成为军旅诗纵横驰骋的天下,陆续涌现了受他很大影响、令人瞩目的众多军旅诗人,诸如叶文福、时永福、徐刚、韩作荣、李松涛和雷抒雁等。
李瑛的诗很多较为短小,是对大自然与心灵秘奥的细部谛听与凝视。虽然这一谛听与凝视受限于时代与社会因素,大多比较单一,仅只朝着向上的正方向着眼,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向下的负方向,从而显得深度不够,但无碍于其丰富性的呈现。月夜潜听、站岗、巡逻、放哨、军营熄灯,以及山、水、路、小树、贝壳等,无不成为李瑛诗思涌流和过滤的内容和视点。诗集《红花满山》中的《深山春早》1李瑛:《红花满山》,第17~18、39~41页。、《山间小路》2李瑛:《红花满山》,第17~18、39~41页。等篇什都是这方面典型的作品:
绿水一半,
浮冰一半;
山里的积雪化了,
每条溪水都是它闪光的弦。
条条溪谷,
层层梯田;
社员正出动,多忙碌,
挑沟,送粪,春翻。
(李瑛《深山春早》首两段)
像李瑛《深山春早》这两段诗画意盎然,一幅红绿相间的山中早春农忙图景伴着耀眼的声光色跃然纸上:首段聚焦大自然景观,刻画浮冰半泛的一条条澄碧溪水,有如漫山积雪背景下闪着光的弦儿——冰消雪融、四处辐射的动态景象仿若大自然在奏响天籁,有关“弦”的比喻便尽显自然(这“弦”首先是色,泛着光影,然后才是声,隐约着大自然的喧嚣与律动);次段着眼于人间安恬,写一条条溪谷和一层层梯田纵横交错,置身其间的公社社员忙于准备春种。
而他另一首诗《边寨夜歌》1李瑛:《红花满山》,第61~62页。起首一段,仅寥寥数语,却十分生动地勾画出了一幅战士上岗夜巡的静谧剪影:山高月渺,万籁俱寂,边疆大地之上,包括山、月在内的一切都在安眠,唯有巡岗战士警醒;尤其是,月倚大山、山倚卫士的两句拟人堪称神来之笔,一下子衬托出卫疆战士大山般伟岸英武、稳重可依的形象和气质。不唯用语自然妥帖、毫不造作,造境和立意也巧妙新颖。
边疆的夜,静悄悄,
山显得太高,月显得太小,
月,在山的肩头睡着,
山,在战士肩头睡着。
(李瑛《边寨夜歌》首段)
一如李瑛上面这两首样诗及其片段所示,他运用得最成功也最典型的艺术手段,就是情景交融的立意造境方式,所谓寓情于景、“以画写情”。对这一点,很多人都作过深入探讨。2如于丛杨、周岩、吴开晋《“以画写情”的抒情方式——李瑛研究之一》,《诗探索》1984年第2期(总第11期)。它无疑借鉴了古典诗的“意境”理论,又如前文探讨过的那样,加进了“升华”因素。这既是一种发展,也是一种规约,决定了上面所说的凝视与谛听的单一化正方向。再加上在李瑛们所营造的诗歌意境中,人物形象的影子较古典诗要更为浓重,这些都成为我们称之为“新意境”的原因。
总之,正是诗人李瑛,将“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发展到一种极致状态,从而使他不仅成为“新意境生活抒情诗”集大成者,更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当代新诗屈指可数的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但我们同时也不能不加以注意,当我们将李瑛视为坚持最久也最具恒定性的“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诗人时,实际上已无意间暴露了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在这样一种极致状态下,日趋衰微与停滞的倾向。
四
这一早在1960年代中期便已初露端倪的趋向自有其深刻的内外在因由。
就外部原因而言,其一是,随着时间推移,生活渐渐呈露其严峻与不尽如人意的面目。人们无法像十年前那样,以轻松的姿态作出这般乐观判断:“祖国的面貌一日万变,幸福的远景越来越近,诗人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高,歌唱的声音也更加响亮。”1臧克家:《序言》,《诗选(1957)》,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臧克家这段话与本文此前第三章节首段所引顾工那段话如出一辙,虽事后看来满是盲目的乐观与浮夸气息,但毕竟与共和国建国之初时代与人心的自信有关,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一大底气与支点。时过境迁,底气不足,支点崩塌,新意境生活抒情诗那种柔和明快的特有抒情体式与因景“升华”的造境方式顿时陷入空中楼阁式的尴尬。
既然共和国从童年的天真、青年的稚狂,开始走入壮年的颠沛和创业的曲折,那么诗作为人内心世界与时代情绪的诗意过滤与呈现自亦应随之而改变,否则便会无趣地折射出自身的浅薄与局限。譬如,诗人雁翼1960年出版的配画诗集《雪山红日》2诗画集《雪山红日》以雁翼诗配牛文、李唤民画,由重庆人民出版社1960年出版。单纯地看,形式创新,诗画互衬,造境极为优美,予人印象深刻,但却典型地暴露了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较之其他诗歌品类更单弱、某些时候甚至不免有害无益的地方来——它以对大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的盲目赞叹,以及对人的乐观精神的无限夸大,掩盖了彼时中华大地的物质匮乏与精神困窘。
其二是,从1950年代后期开始,在一系列“左”的错误支配下,中华大地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日益浓烈的火药味不可避免地遮蔽了新意境生活抒情诗那一份独有的生活实感与清灵气息。诗人严阵便在现实政治导向下,写出了与此前格调迥异、强调阶级斗争的《竹矛》3严阵:《竹矛》,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1964年版。,在其全部15首诗里,以《……颂》为体式的诗就占了九首,堪称一本不折不扣的颂诗集——像如下这首《北京站颂》,渲染的就是由“喷涌”“翻卷”“喧嚣”“沸腾”等一系列干柴烈火般浓烈的形容词所叠加出来的热火朝天的生活表征与气势:
在你的轨道上,车辆永远向前,
哪怕万里途程,千道江河,万重关山!
北京站啊,北京站,你的出口,
是多少伟大事业的起点!
……
这里空气里的汽油味,烟草味,
比所有的玫瑰花,更加香甜,
这是伟大生活的气息,伟大斗争的气息,
谁?谁能不受到它强烈的感染!
(严阵《竹矛·北京站颂》节选)1严阵:《北京站颂》,《竹矛》,第21页。
李瑛则不仅在其《红花满山·生日》2李瑛:《红花满山》,第111~112页。之类的诗里礼赞所谓“忆苦思甜”,而且还在《枣林村集》中向写实化倾向靠拢,并着意涂抹阶级斗争色彩。总之,在当时极“左”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琴韵越来越转化为对极“左”错误的诗化粉饰。
随着被纷纷划为“右派”,公刘、白桦、高平等不少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诗人连同其他群体中追求本真的诗人一道,在1950年代末不得不中辍写作。而他们被迫销声匿迹,应该说是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走向衰颓的又一外因。
必须指出的是,上面缕析的那些外在因素并不仅仅只对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这一个品类或诗群发生作用。同时,文学有其自身发生与寂灭的内在规律。因而,导致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走向式微的本质力量只应是那些内在因由。
其内在因由首先在于,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本质上与浪漫主义有着极深刻的关联,随其变化而变化。准确地说,它是政治抒情诗所秉承的中国式革命集体浪漫主义与一般的自我浪漫主义杂合的产儿。这种杂合本质上不可能,因而我们面对的至多只是一个畸形儿,难免导致一种看似“完美”的虚假:本来比集体浪漫主义更具活力,但随即因这种活力的不能完全生成与释放,而转向一种尴尬状。写《雾中汉水》1蔡其矫:《汉水四首·雾中汉水》,《长江文艺》1958年2月号。、《川江号子》2蔡其矫:《丹江口·南津关》(包括《川江号子》一诗),《收获》1958年第3期。的蔡其矫后来终于摆脱了这一尴尬,冒着不断被批判的风险,顽强地强化了“自我”在诗中的地位。发展到朦胧诗诗群的舒婷们,则把浪漫主义这种强调自我的一翼涵养丰满,从而令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阶段最终导向止息。而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存在的意义在于:在艰难时势下,其“艰难”地成为这一过程的桥梁。
其内在因由其次在于,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不仅在本质与风格上是一种杂合(浪漫主义的两翼),而且在艺术构成、表现方式与文化渊源诸方面也是一种杂合。或者说,是带有某种“改良”意味的“杂交”。这一“杂交”在本文第二节里曾详加讨论。“杂交”与“嫁接”模式几乎可说是中国文化独有现象。因而,文论界有关“两个结合”的提法,虽很难说是一条道路,但不失为一种总结。这一模式本来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但当人们将这一模式诉诸实践时,常常会令发生联系的诸因素超出质与类的必要限制,从而使结局呈现为分崩离析的迹灭。而新意境生活抒情诗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这样一种情境下的产物,其式微或衰颓的结局也便可想而知。
新意境生活抒情诗趋向停滞或衰微的内在因由还在于,因了上述诸内外在规定性或限制,它越发展到后来,便越严重地陷入了从风格到内涵、从造语到意境的全面雷同与单调,既自我雷同又彼此雷同。互相之间赖以区别的往往不是各自特异的创作个性与抒情风格等内在因素,而更多只是诸如地域与表现内容等外在因素的差异——譬如,你写“大海”,我则写“高山”。把不同诗人的诗作放在一处,你若说是出自同一个人,或来个张冠李戴准有人相信。甚至,一个作者不同时期的作品也很难给人以明晰的发展线索。这样一来,个别地看,都各有千秋,较显丰富;但若整体予以俯观,则难免会令人大失所望——各个相似的面孔叠归于一,反而尽显整体上的孱弱与单调。譬如,李瑛的诗歌整体上看,既集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之大成,这方面的表现便尤为突出。这当然很可悲。
这其实是当时整个共和国文学的一个普遍现象。不妨回顾和考察一下曾一度蜚声文坛的作家杨朔及其散文创作,当会有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事实上,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与茹志鹃《百合花》1茹志娟等:《百合花》(含茹志娟《百合花》、愿坚《七根火柴》和勤耕《进山》三篇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14页。等一类小说创作,以及杨朔《茶花赋》2杨朔等:《茶花赋》(含杨朔《茶花赋》、李广田《花潮》和季羡林《石林颂》等15篇散文),云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页。式散文,在当时不约而同地参与创制了对中国一度深有影响的一种类美文式写作文体。这其实是复杂、神秘和独特的中国文化于特定时期生成的某种内在契合性的显现、物化或所谓的结晶、升华。
耐人寻味的是,创制并依循这一文体的创作主体多半出自军旅阶层,很特殊:既是高尚的,又是普通的;既是单纯的,又是半知识分子、半“有闲”(中性)的;既是出世的,又是入世的。它决定了这一文体在格调上甚至多少有些过分了的单纯与轻灵、松快与透明——因为恰恰是他们,最能适应于一种独特中国式的半入半出的观世态度。历史的经验教训是,这一态度发展到极端,就会导致文学创作流于浮表与虚假。
这一文体的另外一个特色是行文节奏的“散”化。不过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自由体式除受现代新诗自由体的部分熏染而外,更多是从民歌与古典文学上化来的。至于这一文体对于物象的取舍,则是一种见微知著式的微观聚焦与细部折射。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造境方式自不待言,杨朔与茹志鹃等的创作所关注的,也都是平凡的物境与小人物事迹,以及凌驾其上的精神升华。
总之,这一类美文式写作文体的影子在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中随处可寻。它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在并不适宜纯文学的氛围里,却实际起到了一定的纯文学作用。因而它当时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水准相对较高,对人的心灵也起过良好的陶冶与慰藉作用。
然而,也诚如我们以上对新意境生活抒情诗的全部分析所显示的那样,这一文体本质上是一种体现为理想主义(不是感伤主义,但有浓重的个人情氛)的浪漫主义杂合的产物,它所涵蕴并欣赏的境界越来越变得既非真实的现实,又非个人的切身体验,而只是一种“群”心态的外化,是一种于1960—1970年代得到强化的“集体意识扩张”。
事实上,结合性与升华性的立意造境方式作为这一文体的源“代码”,原本出自当时整个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普遍的美学风尚。譬如,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一场关于古代山水诗阶级性的讨论中,一种观点就认为,像唐代山水诗人王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这类直观反映大自然的诗,“严格来说不能算作艺术,至少只能说是艺术的低级阶段”;“只有自然形象和社会思想感情结合起来的作品,才是真正的艺术作品”。这类认知指向并崇尚的其实正是立意造境的所谓结合性(无论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还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还是浪漫主义的两翼——革命的集体浪漫主义与一般的个人浪漫主义结合,还是民歌与古典诗歌结合,还是自然形象和社会思想感情结合——所谓情景交融……)与升华性。1参见叶秀山《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文学评论》1961年第2期。
这也就难怪,诗评家易征等人当时会责难李瑛《红柳集·静悄悄的海上》2李瑛:《红柳集》,第78页。(1956年)一类诗歌是即兴式作品,意义不大,仅仅表现“海大帆轻”:“全诗写来写去,无非是‘海大帆轻’,我们看到的不会比它提供的东西更多些。”3易征:《诗的艺术》,广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63页。换言之,无非是说结合得不够、升华得不够。平心而论,李瑛这首小诗寓静于动、动静相生,充满画面感和美感——而以南方淡水堤边静静歇晌的蝴蝶,比喻咸腥大海里一叶看似不动的轻帆,最是巧妙、贴切、有生活实感之至。看似纯为以画静物画的细腻和悠缓画海画帆、状物写景,其实反映的是对美好人间烟火发自内心的挚爱和自豪感——由“在那遥远的水天尽头,/仍然有我们的岛、我们的城”一句便可约略看出,远非玩物丧志、粉饰太平可比。
在这种强求一律、狭隘枯索的理论与批评趣味导引下,新意境生活抒情诗最终身不由己地向“政治抒情诗”靠拢,被一并纳入由“天安门”习惯性想起“枣园”,又想起“井岗山”一类极尽铺排之能事的言说模式,渐渐走入死胡同,也就毫不足怪。譬如,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代表诗人李瑛就曾身不由己地信笔由之,一头扎向政治抒情诗怀抱:
秋收起义的烈火,
南昌城头的红旗,
井岗山上的云水,
一齐激荡在我们的热血里。
(李瑛《红花满山·生日》倒数第二段)1李瑛:《生日》,《红花满山》,第112页。
综上所述,新意境生活抒情诗作为特定文学史阶段的产物,其生成、发展与式微或衰颓,或者说,它所象征的琴师的复活与隐遁,都有其内在必然性。虽作为一个诗歌群落、一场诗歌运动,或简言之一种诗歌现象,它存在过不少失误,有些甚至牵连得颇为深远,但它毕竟作为与写实倾向相对的不可多得的抒情倾向、与政治抒情诗的豪情意向相对的不可或缺的柔情意向,为中国当代新诗的向前发展,铺垫了宝贵的基石与有意味的预期。
因此,不管新诗的观念已或将有怎样的深化,不管抒情诗的抒情意向已或将出现怎样不同的变延或扩展,以公刘和李瑛等为代表的新意境生活抒情诗那独特而柔美的琴韵,都将作为中国新诗史的保留曲目长久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