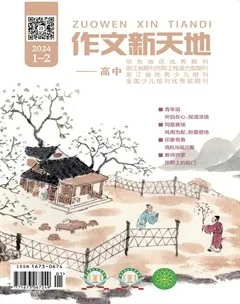风雨为配,粉墨登场
2024-05-13董泓博
董泓博
深夜的京城人声俱寂,一天的喧闹退去,这座城露出了倦容。一座并不恢宏的小院里,还发出依稀的光,似乎在与明星相望。
三喜咧着嘴嘶嘶呼着冷气,小心翼翼地扭过手去给腰背上抹红花油,身边是一支折断的花枪。一想到明天还要让他那令人“闻风丧胆”的父亲验收基本功,三喜怅惘地抬头,望着昏黄的夜灯与萦绕其间的蚊子,叹了口气。
董三喜生来便在戏班,其父董德祥年轻时是名震京城的武生,一手花枪耍得神出鬼没,台下的观众不见枪身,只见一抹红缨不停跳脱,一进一出,一往一返,便取得敌将首级。后来年纪大了,董德祥便经营起一个戏班,用平生的积蓄置办了一个院子,用来平日的练艺。台上,他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台下,在三喜眼中,他却是“活阎王”。三喜,即得名于京剧中的“人生三喜”——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等人生快意之事,大抵是出于此种对孩子的期望,三喜自满周岁开始便被董德祥像小鸡一样拎着,被拉去打磨筋骨,舞刀弄枪。整日是汗流浃背、精疲力竭,回到房间一沾枕头就睡,醒来又得拖着“病躯”,捂着酸痛处,一瘸一拐地走去后院练武。
三喜心里满是怨气,脑海中父亲成了一个恶魔模样:发立眉竖,面目狰狞,其黝黑的脸总使人毛骨悚然。此时,后院旁一间房子的门“吱嘎”一声响了,三喜回头看去,却是柳娘。柳娘是戏班里的旦角,人瘦,脸白净,唱起戏来像三月春的柳条,挠得人心痒,便被观众们称为“柳娘”。柳娘从小身子便弱,年纪日长,患了不少慢性病,终年脸色苍白。她在戏班却成了三喜唯一的慰藉,他自小失去母亲,每逢什么跌打损伤、大小病痛,都是柳娘来关心、照顾,给他上药。兴许是听见了声响,柳娘走到了三喜身边,轻车熟路地为他抹红花油,语气温柔:“咋了?这愁眉苦脸的,又受伤了?”
三喜默默听着,也不说话,眼泪裹挟着委屈一同泄了出来。内心里,他想,或许只有柳娘才知道,他并不喜欢唱戏。他渴望像平常人家的孩子一样,早晨起来吃焦圈、喝豆汁,去上学,回家写写作业,再吃一顿热气腾腾的饭后去朋友家闲逛;而不是整日舞刀弄枪,精疲力竭。
是夜,一个少年澎湃的心被浪击打着,逐渐要失去了跳动的力量。
一日清晨,三喜独坐在早餐店里,叫了一碗滚烫的豆汁、一碟焦圈,默默吃着。其略带酸味的气味触动着三喜的味蕾,他鼻子翕动着,揉了揉带着黑眼圈的双眼,感受到了一丝烟火气。
周围的人们在闲聊,三喜聽到一位老大爷粗着嗓门讲话:“现在的京戏是真不行了,前天我去看了台戏,那唱得,哎哟,没法听!”另一位老大爷喷吐着旱烟应道:“是啊,从前有个耍花枪的,叫董什么来着,那才叫京戏!”“唉,现在也不行喽……”
三喜听着很不是滋味。蘸着豆汁的焦圈也没吃完,钱一扔就走了。
日子没有什么变化,三喜的心也似乎失去了方向,练不好的花枪仍然经不住父亲的检验,红花油总也抹不完。
直到那日,柳娘病倒了。
三喜冲进院子,撞开房门,一眼就望见躺在榻上气若游丝的柳娘,戏班大家伙们都聚在一起,皆是满目愁容,忧心忡忡。
三喜推开旁人,抓紧柳娘的手,连声叫道:“柳娘,柳娘,你怎么了?你怎么就病倒了?”三喜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滚了出来,打湿了被褥。柳娘伸出无力的手,为三喜拭去眼泪,说:“三喜,别哭,你要帮你父亲支起戏班。”
后来,三月的柳枝折了,一声雏凤的清啼传遍了京城。那日,宾朋满座,一武生自后台跃出,舞起花枪,神出鬼没,站定,一瞪眼,粉墨登场。
指导教师:王德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