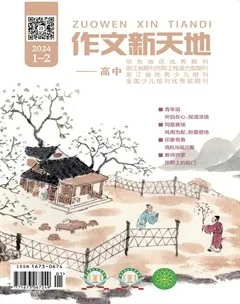田野上的柜门
2024-05-13斤小米
冬日黄昏,湖区水杉柔软的针状叶全变成深浅不一的枯黄,像中年男人的头顶,日渐稀少的头发使人生出几分“临风听暮蝉”的意味,参天的身影,壮实的树干,在冷风中彰显出一种桀骜不驯的高冷感。成群的麻雀编织成一块在天空变幻着形状的黑布,一忽儿东,一忽儿西,高天里流传着鸟的絮语,如同大地上冬眠的虫声。
我背着相机往一望无垠的稻田里去,稻茬有点硌脚,田里的水已经干了,土壤还有一点点柔软。这里是洞庭湖的腹部,无论围湖造田有多么成功,无论时间过去多久,芦苇这种植物还是会时不时地在田埂上展示一下它们蓬勃洁净的身姿,以体现它们作为湖区主人的强势地位。从一丛孤独的芦苇里望去,血红的落日,圆润饱满,光焰平静,像是谁画上去挂在西边大堤上的,这真是绝美的构图。这会儿,垸子里分布零落的几户人家,沉落在一片即将暗下去的静默里,似乎亘古以来都是这样,又似乎在不久的未來,这里终将真的沉入无人的死寂。
只剩一线天光了。我返回已经亮起了灯的房子,如同一位侠盗返回自己的深山老林里遗世独立的窝点。为了让这个临时“窝点”住上去舒服一点、看上去美观一点,我们对老房子进行了改头换面的整修。不仅做了一个水泥浇筑的顶,内部全部采用现代化装饰,换掉了所有的旧家具,而且在东面的竹林中间做了一个木亭子。于亭子内放置了石桌石凳,又修了蔷薇花围篱、石子路,修整了两个小池塘,在池塘边堆了大石,种了鸢尾。
作为老家的“匆匆过客”,我们把它改造成了喜欢的样子,于当代都市人而言,有一处如此安静恬淡的“世外桃源”,自然是一种奢侈。而我们想,如此雅致舒适的环境,对于父母来说,亦是最大的欣慰吧,尽管我们这么安排时,只跟婆婆商量了,完全没有问过公公的意见。他能有什么意见呢?对于婆婆的决定,他这一辈子都没有过意见,他总是默默地做事,黄昏时就开始打盹,凌晨四点准时起床,大声说着一天的打算。把碎布条一根接一根地做成绳,挂在所有他认为能够挂得了的地方。在儿女们这里,他是必要而又透明的存在,没有一个人想过要问他的意见,即使他偶尔会为了什么事大声地表达不满,但谁都装作听不见。
通往房子的水泥路边,码着一大堆干柴。对于摄影者而言,夜中的干柴是绝好的意象。我再次举起相机,对准造型独特的柴堆。这时,竖在路边挡住干柴的一块深黄色木板闯入了我的镜头。木板上写着许多小楷,一排一排,歪歪扭扭,但笔画之间,又显得极为严肃认真。调焦,仔细看下去,是一些农历日期:
一九六九年六月初六卯时三刻,女儿,红。生时哭声微弱,瘦小不足四斤,只怕养不活。补充:养活了,长大,像个霸王。欣慰。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寅时一刻,儿子,军。眼睛很大,很漂亮。我的第一个儿子,以后有劳动力了。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初五子时,女儿,珍。哭声响亮,不停歇。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八辰时,儿子,海。出生一百天,哭一百天,会看着灯,就停止。
每一排字的墨色深深浅浅,看得出即使是同一个人的内容,都是不同时间写上去的,那里面凝聚着一位父亲所有的欣喜、期待、惊奇、担忧和责任。木板的反面是掉漆的衣柜表面,上面的铜制门环还没有敲下来。
时间在此刻停驻了,然后又迅速地如同一个漩涡一般,往前,往后,奔腾不息。
这里并不是我的出生之地,尽管我已经来到这里二十年。它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到目前为止,我生命里有超过一半的光阴,是与这片土地对视而行的,但我从未真正了解过这片土地,正如我从未在意过我丈夫的父亲,他曾有过的年轻过往,和往日时光里作为一家之主的他,对未来岁月的所有预算。
那一辈人,大概认为,把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以及孩子成长最重要的细节,写在装衣服和储蓄以及所有的秘密的大柜子的内侧,就是永恒的吧?在贫穷而缺乏想象力的过去,他是绝没有展望过有一天这个大柜子将失去它的作用的,毛笔小楷的印记将被书本、电脑、居民身份证打上真正恒久的印章,这也不是他的认知能够接受的事。
大柜子敲掉,放置于露天,一位父亲的所有与爱相关的秘密在这个黄昏被无限放大。在无数次经过这个被遗弃、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大柜子时,在码起干柴,并终将在烧掉这些干柴之后,也将这块木门烧成灰烬的未来某刻,作为父亲的他,是否能够习惯这种巨大的失去?
房子里亮起了灯,但他没有坐进屋子,他在西边的小棚里烤火,双手拢进袖口,默默地看着火光,目光迷离,似要睡去。太阳完全落下去了,鸟已经宿入竹林,水杉倔强的暗影,笔直地指向天空。
那块写着生日的木板,是保留在相机里,还是锯下来留给他做个古物,或许我们应该问问他的意思。
斤小米,原名王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湖南省作家协会教师分会副主席,《教师博览》签约作者。已出版《此路遥迢》《失散的欢年》《故纸素心》《彼岸风吹》《聆听遥远的呼吸》等散文集,主编高中教辅书三本;获第五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三周文艺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