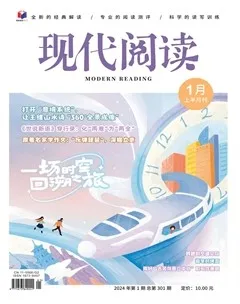生命旅途上的中年责任
2024-04-29梁开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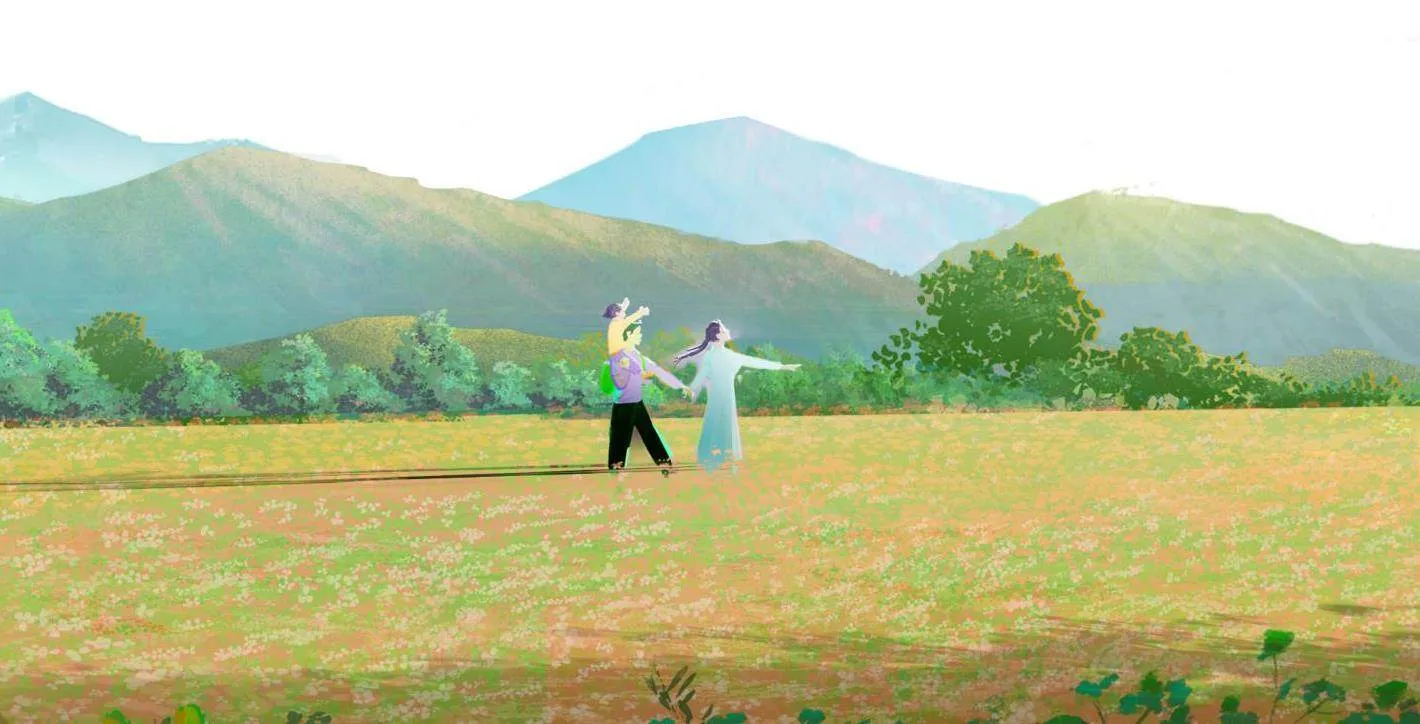
莫怀戚的《散步》弥散着浓郁的亲情,同时也包含了对生命的感慨,这是我们通过阅读文章能够感受到的。在教学中,大都会重点解读亲情主题,而对文中蕴含的生命主题简略带过。本文分别从亲情、生命、中年三个层面对文章进行解读。
感人的亲情与对生命的感喟
四人三辈,平畴垄上,一次平淡而真实的散步,我们从故事中感受到的“亲情”,是确凿无疑的,也是不言而喻的。
“母亲本不愿出来的;她老了,身体不好,走远一点儿就觉得累。我说,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母亲信服地点点头,便去拿外套。她现在很听我的话,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这一段言辞冲淡而又情致深婉的叙写,将母亲的依赖与顺从、“我”的体贴与孝顺展露无遗,如话家常,又耐人寻味,有一种静水流深的表现力。时光流转中的角色转换,使得一切都变得柔软与平和。
“到了一处,我蹲下来,背起了我的母亲,妻子也蹲下来,背起了我们的儿子。”这更是一幅融融泄泄的天伦之乐图。血脉绵延,生命轮回,从“我的”到“我们的”,那奇妙的缘分,还有甜蜜的责任,无不让我们沉醉在谐和、温馨、心意相通的亲情之中。
尤其难得的是,在精思巧构之中、叙事和抒情之外,文章始终闪耀着理性的光泽,对生命的深长感喟贯穿其中。“今年的春天来得太迟,太迟了,有一些老人挺不住,在清明将到的时候去世了。但是春天总算来了。我的母亲又熬过了一个严冬。”这段话不仅起到了为下文写景张本的作用,而且非常自然和恰切地道出了万物轮转、人事代谢的自然规律。一个“熬”字,有生命的坚韧,也有人类在时间和病痛面前的身不由己和无能为力。“这一切都使人想着一样东西——生命”,更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文章其实是别有怀抱的:亲情被安放在生命的流动之中,生命又因为亲情的存在被赋予了真真切切和无可置疑的意义。
这一点在作者莫怀戚写于2005年的一篇回忆性文章《二十年后说〈散步〉》中有所体现。“有人问我:你那个《散步》,是写尊老呢,还是爱幼?或者既尊老又爱幼?我认真回答:看起来当然是既尊老又爱幼,其实我骨子里是想写生命。”这种生命循环往复的立意,集中体现在两处景物描写之中。初春新生的田野,随意铺展的新绿,日渐浓密的嫩芽,还有汩汩流淌的冬水,是那样的清新可喜,生意盎然;而“金色的菜花”“整齐的桑树”,还有“水波粼粼的鱼塘”,又是那样的平凡而亲切,洋溢着生命的活力。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体味到人间值得,让人没有任何理由为生命的流逝而忧伤、沉沦和绝望。物换星移,花开花谢,个体的生命是有终点的,人类却生生不息,延续不止。
情感平衡的中年责任
在写作手法上,这篇散文运用了作者所擅长的小说笔法,使得叙事富于曲折性和镜头感,集中表现在“我”对母亲和儿子的不同选择的决断上。“分歧”一词,大词小用,放大了祖孙想法的不同,同时也强化了“我”的一锤定音的身份定位。
“我想找一个两全的办法,找不出;我想拆散一家人,分成两路,各得其所,终不愿意。”这不正是几乎所有中年人的现实困境吗?他们总是生活在这种没有答案的纠结之中,生活在这种没有出口的情感罅隙之中。上一辈的垂垂老矣与下一辈的天真烂漫,于中年有着同样的分量,他们瞻前顾后,左冲右突,却常常找不到落脚之处。这是中年的尴尬,当然也是中年的荣耀。文中多处在“母亲”以及“妻子和儿子”前面都特意加上“我的”这样的限制词,或许就是为了强调中年人的决策者和守护者的地位,以及无时无刻需要平衡的中年责任。
近代学者谭献有言:“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散步》中许多含义隽永的对称句,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作者遣词造句的风格,另一方面,也是作者中年心绪的真实写照。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我的母亲要走大路,大路平顺;我的儿子要走小路,小路有意思”“我的母亲老了,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我的儿子还小,他还习惯听从他高大的父亲”“我的母亲虽然高大,然而很瘦,自然不算重;儿子虽然很胖,毕竟幼小,自然也很轻”,如此密集的对举的句子,让人感觉作者在努力避免情感天平的失衡,一方面增强了文章思想内涵的张力,另一方面也凸显了中年人的生存处境和家庭责任。
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年本是承上启下的,但就当下的社会现实而言,中年的情感重心多是向下的,抚养之于赡养,似乎要更加尽心尽力和无怨无悔。父母对子女的爱和子女对父母的爱从来就是不对等的,正因为如此,《散步》里所隐含的中年立场也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我决定委屈儿子了,因为我伴同他的时日还长,我伴同母亲的时日已短。”这是非常坚硬的现实,也是非常朴素的道理,然而,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懂得呢?又有多少人能够把智性的认知变成主动的行为呢?“好像我背上的同她背上的加起来,就是整个世界”,这是文末的画龙点睛之笔,也是对中年使命的最好诠释。不错,这是三代人所组成的完整的世界,而中年人无疑是这个世界中无可推卸的责任担当者。
课堂指引
《散步》这篇课文安排在统编版语文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这一单元的人文主题是“至爱亲情”。在单元导语中有这样的表述:“在整体感知全文内容的基础上,体会作者的思想感情。有的文章情感显豁直露,易于直接把握;有的则深沉含蓄,要从字里行间细细品味。”笔者在教学中发现,不论是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还是泰戈尔、冰心的散文诗,都较难区分作品属于“显豁直露”还是“深沉含蓄”,实际上,包括《散步》在内的本单元文章,既是“显豁直露”的,同时也是“深沉含蓄”的。
故此,笔者认为,若将单元导语中“有的文章”改为“有的(部分)”,本单元的教学落点自然就变各篇文章“分门别类”的解读为每篇文章内部“多角度、多层次”的探讨,而这一调整与改变,恰恰是比较符合本单元文章的文本特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