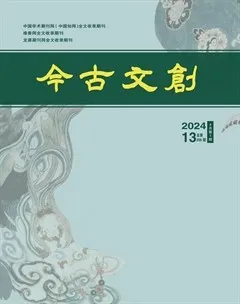南方情结与逃逸线
2024-04-27李林
【摘要】威廉·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的代表人,以独特多样的艺术形式、对美国南方事实的深刻剖析著称。多年间,国内学者对《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研究热度不减,涵盖叙事技巧、人物塑造、精神分析等多个角度。本文试图在德勒兹的理论视域下分析小说中艾米丽悲剧背后蕴藏的颠覆性以及作者想表达的深刻内涵,认为小说演绎了交织的克分子线、分子线和逃逸线。福克纳借南方贵族艾米丽的悲剧经历来实现人物与自身的解辖域化,在尝试颠覆南北方新旧文化的二元对立时,打破个人悲剧的局限去思考自身、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作为一个清醒的审视者,他呼吁旧南方人正确面对新旧文化交迭,摆脱社会变革带来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危机。
【关键词】《献给艾米丽的玫瑰》;逃逸;克分子线;分子线;逃逸线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13-0013-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13.004
一、引言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是20世纪美国文坛最杰出的南方作家之一,他在创作中大胆尝试现代文学中的各种新旧表现手法,追求深奥写作内涵,为当代美国小说做出巨大贡献。他笔下“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作品均以美国南方社会为背景,借助小镇村民的经历,深刻洞悉社会变革的强烈冲击给人造成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危机。[1]作为福克纳的经典小说,《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依旧反映了美国内战后南方社会的衰落。故事聚焦一位旧南方贵族小姐艾米丽,以她在清教思想和旧南方传统观念的双重摧残下的悲剧,再现南北战争后南方社会的变迁及其对人的物质和精神的强烈冲击。时至今日,“福克纳研究热”仍在持续,这部短篇小说更是以它独特的写作技巧和怪诞的情节吸引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内研究者大多从叙事艺术、象征与隐喻、矛盾冲突等角度切入研究。相较之下,国外学者不仅关注小说的叙事技巧、文本形式与语言风格,另有部分学者将心理学与空间研究引入福克纳作品批评,进一步挖掘小说背后的深厚意蕴。然而,少有学者从精神分裂分析出发关注小说中各种“线”交织出的人物命运和时代变迁——优雅的贵族小姐逐渐变得癫狂,新进的北方文明逐渐侵袭南方。为了揭示悲剧背后蕴藏的颠覆性以及作者想表达的深刻内涵,本文从德勒兹哲学的精神分裂分析出发,借助“克分子线”“分子线”和“逃逸线”,探讨艾米丽的悲惨命运,试图揭示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人应对社会变革的强烈冲击的正确途径。
二、克分子线:封困于木屋
德勒兹和伽塔利宣称“精神分裂分只着眼于线,既贯穿着群体,也贯穿着个体。”[2]第一种线为克分子线( molar line),是“对意识进行辖域化或者殖民的力量”,[3]它对人的一生进行准确的分割与规划,进行界定与编码,以二元对立的机制来构建循规蹈矩的发展轨迹,隐含着权力的运作,制约人生的重要抉择。[4]小说中最先出现的封闭空间是木屋——艾米丽小姐的房子,那幢保持70年代风格的木房子挤在棉花车与油泵之间显得格格不入,异常碍眼。作者着重描写木屋与周边环境互相分隔、各自封闭,而与外界连接的前门也被多次提及“紧闭”。木屋承载的是南方的传统文化,而外界已经处处受工业文明的侵袭。不仅如此,关于艾米丽一家的客观形象,小镇村民的描述更为具体——村民一直将艾米丽一家看成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艾米丽小姐立在背后,她父亲叉开双腿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着艾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门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5]如此看来,艾米丽居住于封闭的木屋,实则受控于克分子线,她的意识在南北方文化之间被强行分割,与外界隔绝。屋内的这幅画将束缚艾米丽的克分子线“具象化”。首先,手执马鞭的父亲恰好挡住前门出口,表明南方传统“父权制”及其价值观念迫使艾米丽只能循规蹈矩,不可跨出前门,即不能挣脱克分子线的控制。父亲是家中无可争辩的主宰者,以马鞭维持家庭地位。艾米丽出生于这样的贵族家庭,意味着享受贵族特权与荣耀的同时,她只能顺从父亲的控制,恪守旧南方的传统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其次,那时基督教新教在美国南部占据主导地位,以加尔文主义为中心的新教思想在美国南方民众的思想中扎根。在这种情形之下,艾米丽的行为和思想深受腐朽传统的束缚和影响。再者,在小镇人们的观念中,艾米丽是传统的代表,是南方旧社会体制的象征,更是南方传统文化的纪念碑。因此她的一言一行必须始终恪守传统,一旦有所相悖就是打破传统。她无法追求自己的幸福,因喜欢一个身份为北方佬的工头荷默·巴隆而受村民指责。在克分子线的控制下,她只能被动地成为一位真正的高贵淑女,是理想的南方女性,是满足全镇乡民的传统道德需求的替身,更是南北方新旧文化冲击下社会变革的受害者。
三、分子线:游荡于小镇
分子线(molecular line),這一概念与克分子线相互对应、影响,“两条线不停地相互干扰、相互作用”。[2]德勒兹与伽塔利曾将分子线定义为一种同时具备柔韧性与切分性的线,这条线的主体具备打破二元对立的系统的能力,可以链接被克分子线切分的片段,即存在变异的潜在可能性,分子线在固守和逃逸间摇摆不定,既不愿受控于克分子线,又未决定完全逃离。于是,分子线的这种动态运动又被德勒兹与伽塔利定义为解辖域化运动。[6]
木屋与外界环境的鲜明对比贯穿故事始终,反映了艾米丽固守旧南方传统,与北方新文化的对立局面。与外界隔绝的木屋好似南方传统思想及阶级制度对抗北方工业文明的最后防线。从屋内与社会脱轨的老旧装饰,长期关闭的前门,拒绝接受新事物的举动到新镇长的亲自到访,村民偷偷撒石灰以及最后强行打开阁楼房门等种种细节不难发现,克分子线作用于身受南北新旧思想冲击的艾米丽身上。即便父亲去世,在克分子线的限制下,艾米丽也始终相信父亲没有死。部分学者认为她的这一举动是逃避现实,而从精神分析视角来看她依旧未冲破克分子线的规划,即南方的父权制、贵族传统等老旧思想观念在她心中根深蒂固。然而矛盾的是,建筑公司来后艾米丽开始走出前门,在公众视野中与一个名为荷默·伯隆北方佬交往。即便面对小镇村民的指责和议论,每逢周日下午,她依旧会和荷默先生乘着漂亮的轻便马车高调出行,成双入对。身为圣公会成员,她拒绝众人请来的牧师,甚至继续策划着与荷默结婚。堂姐妹劝告也无济于事。艾米丽的一系列反常行为可以解释为分子线开始发挥解辖域化作用,她开始试图挣脱克分子线的控制,反抗长期束缚她的旧南方传统观念和行为准则。她无视小镇居民的诽议和一而再地干涉,为两人的婚礼订购刻有荷默名字的银质盥洗器具,购买一整套的男式服装。此外,荷默的身份——来自北方的铺路工头,代表着先进和新兴的北方文化,艾米丽对他的喜欢则意味着她对新北方文化的逐步接受,这与分子线作用下艾米丽试图冲破辖域的运动相呼应。
然而,艾米丽这些举动并不意味着她彻底挣脱了南方传统思想的禁锢,即她在分子线作用下试图冲破辖域的运动是相对性的。进一步解释为,艾米丽仍旧身处“传统与新生的断裂地带,既可能进一步生成逃逸线,也随时可能退回到克分子线的等级之中”。[7]在喜欢荷默的同时,艾米丽饱受南北方新旧文化冲突的折磨,她在分子线与克分子线之间游荡。因此,当荷默以同性恋推脱结婚时,克分子线与分子线间的微妙平衡被彻底打破。艾米丽无法接受荷默离开让她有损颜面,同时荷默的欺骗也让她失去对北方新兴文化的信任和再度反抗南方传统的勇气。最终,她选择毒杀荷默,继续坚守在代表旧南方文化的木屋中,即艾米丽再次退守南方传统,退回克分子线的规划之内,形成一种再辖域化运动。在克分子线的辖域化作用下艾米丽再次生活于南方父权制和传统价值伦理的压迫下,一如无法清除的毒素再度侵袭艾米丽。不仅如此,福克纳采用的错乱的叙事顺序与艾米丽错乱混杂与疯狂精神状况再次遥相映照。[1]这些种种都是艾米丽进行解辖域化和再辖域化的具象体现。
此外,克分子线与分子线的相互作用不仅作用于个人——艾米丽,还作用于集体——小镇居民。他们会十分积极地把孩子送到艾米丽家学习瓷绘画,一如去教堂礼拜一样频繁与虔诚。这表示即便他们在逐渐接受北方文化,内心深处依旧认可南方传统文化,希望后代能够将其传承下去。关于艾米丽喜欢北方佬这件事,原本与小镇村民并无关系,他们却从旁指责,认为即使她的父亲去世,她也不能放下南方贵族的传统,在街上抛头露面甚至与北方工头高调交往。在村民心中,艾米丽是南方传统的代表,是他们坚守南方文化的寄托。然而正是这样的他们也在积极接受北方工业文明,以文中镇议员会议的人员分配为例,由三个老头和一个年轻的后辈组成的议员团体代表着新兴文化思想的加入,即南方封建社会正在逐渐向资本主义转变。另外,因为无法忍受臭味在艾米丽房外撒石灰时,村民从肩上的口袋里掏出什么到处播撒,这一熟练的播种动作表明白人也开始干农活,暗示旧南方的奴隶制正在逐步瓦解。由此可见,小镇居民种种前后矛盾的行为实则是他们一直在分子线上反复游荡的又一写照。
四、逃逸线:运行于关系之间
依据德勒兹的观点,文学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作者寻求逃逸线的过程。他曾明确地指出文学创作的最高目标——离开,出走,划出逃逸线。[8]逃逸线是颠覆性的,它类似于挣脱束缚、打破既定规则。在逃逸线上人或事物可以朝着不同方向发展,进一步让人或事物逃脱原有的压制或束缚。[6]德勒兹提出的克分子线、分子線及逃逸线则为创作者和读者创造了不同的逃逸路径,即在创作或者阅读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逃逸,追寻新的事物,从而创造更多可能性。
具体而言,逃逸线具备变革的动力,可以使内在欲望从外部禁锢中获得解放。[4]旧南方社会受清教主义的影响,注重阶级出身、性别,在日常生活中以“妇道”“女性美德”约束女性。艾米丽从小受南方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压抑欲望——三十依旧单身,约束言行举止。即便她出身没落的贵族,她的头也总是高昂着,摆出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傲姿态。然而,在美国南北战争后,随着北方新兴资本主义的兴起,南北矛盾愈演愈烈。作为南方没落贵族,她既依附又抵抗南方传统,既想接受北方文化又碍于身份与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抵制变革。她将精神错乱的自己困于木屋,看似逃避现实,实则在这段自我营造的高贵宁静、不为所动的时光里,她实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逃逸,逐渐成为“神龛里塑像”,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抛开南北方文化的冲突,直至去世她在精神上实现了自己的解辖域化。
此外,一份未经删减的福克纳的亲笔手稿和碳墨打印稿于2000年出版。其中有一段在正式版本中被删掉的对话,艾米丽对托比说:“在我死之前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听懂了吗?”“那时他们会来的,就让他们到上面去吧,去看看那屋子里到底有什么。一群傻子。就满足他们的心愿吧,让他们觉得我疯了。你认为我疯了吗?”[8] 这段对话表明她始终是清醒的,她清楚小镇村民对她的异样看法,但实际上她看透了新旧变革冲击之下的社会事实,种种疯癫行为只是无力消极的反抗罢了,只是她作为力量薄弱的个体进行的消极的逃逸,也是她在逃逸线上摆脱束缚的又一映照。
五、结语
借助德勒兹的理论分析,这部短篇小说蕴含的深刻内涵远超于艾米丽的个人悲剧。实际上,艾米丽小姐的遭遇不是绝对的悲剧,她在困境中实现了另类的解辖域化。此外,小说中的逃逸线不局限于艾米丽,作者福克纳通过创作同样实现了自身的逃逸。他从小生活在美国南部,对这片土地有深厚的情感。然而,美国南北战争后的巨大变革使他为南方传统的衰落而悲痛惋惜,与此同时他也逐渐意识到北方新兴文化的先进之处。即便还有很多人像他一样,无法放下南方情结,南方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确存在缺陷。在战后社会变革过程中,美国南方需要在固守传统与接受新兴文化之间做出选择。尽管福克纳对南方传统的消逝感到留恋与悲伤,但他最终实现自我解辖域化,冲破南北方文化的局限,超越个人悲剧的局限去思考自身、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9],正确面对新旧文化交迭,试图摆脱社会变革带来的精神困境和生存危机。
参考文献:
[1]李纾淇.时序倒错中的幽暗玫瑰 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叙事时间特征[J].四川戏剧,2007,(03):110-111.
[2]德勒兹,伽塔利.千高原[A]//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286,276.
[3]Deleuze G.Encyclopedia nomadica.[EB/OL].[2016-08-10]http://www.encyclopediaomadica.org/English/gilles_deleuze.php#Publications_by_Gilles_Deleuze.
[4]董树宝.西方文论关键词逃逸线[J].外国文学,
2020,(04):116-127.
[5]威廉·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45.
[6]曾静.论吉尔·德勒兹的逃逸线[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04):98-101.
[7]李震,钟芝红.无器官身体:论德勒兹身体美学的生成[J].文艺争鸣,2019,(04):98-109.
[8]康有金,侯雯.《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逃逸法解读[J].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05):180-184.
[9]刘西锋,彭静.《献给艾米莉的玫瑰》的叙事学解读[J].社会科学辑刊,2008,(03):236-238.
作者简介:
李林,女,汉族,河北衡水人,河海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文学及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