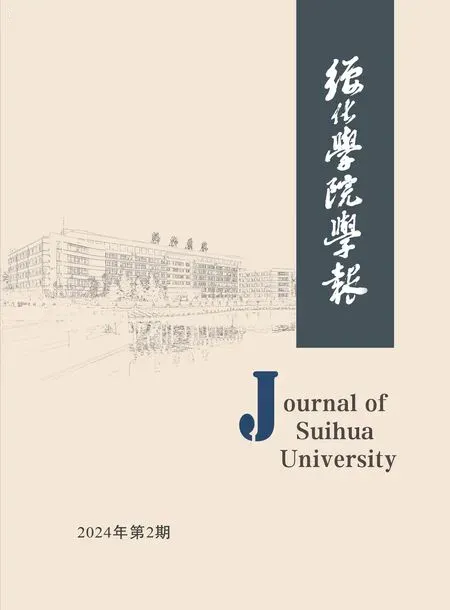生态翻译学:《英韵三字经》译本的生态诗性分析
2024-04-09吴静
吴 静
(重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1331)
近年来,国学经典的翻译已经成为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面对国学经典《三字经》的翻译,我们究竟如何体验与回归其中的诗性智慧与生态美学?面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视野,我们又如何想像与超越以往英译《三字经》的语义化表征而达到《三字经》翻译作为诗性之思的真实形态?简而言之,《三字经》翻译是关于翻译之路如何朝向理想之境“形美、音美与意美”统一的生态诗性?在此背景下,本文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以赵彦春所译《英韵三字经》[1]为诠释对象,揭示《英韵三字经》“以诗译诗”的本源与本质,探究国学经典《三字经》翻译所内蕴的诗性思维,考查“以诗译诗”背后蕴藏的生态智慧与生态美学,以回应与解决以上《三字经》翻译所涉及的根本性问题。
一、《三字经》翻译的诗性思维
生态翻译学致力于追求译者与翻译生态的和谐统一,所追求的就是翻译生态系统中诸项元素的统一和谐。因此,国学经典《三字经》的翻译需要源于“天地合一”的诗性智慧之思,强调繁中求简、散中求和、异中求同、殊中求共,展开对翻译的生态思考与诗性探寻,促使《三字经》翻译通向“天人和一”的诗学境界。
《三字经》开篇之诗节“人之初,性本善”中的“性”如何翻译以及“人”如何出场,成为了《三字经》翻译首要考虑与探究的诗性问题。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过程是译者对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和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对译文的“选择”[2](P232)。因此,译者主体需要梳理汉语的《说文解字》与西方的《圣经》的“性本善”思想,才能复原“性本善”所追问的本性的原本形态。“性”乃是由“存其心”而“养其性”,是与生俱来的“天命”所赋予的“性”。“性”由“心”和“生”构成,可理解为与生俱来的心性,即本性(nature)[3]。本性(nature)的出场,这是译者以“入侵”方式对原文进行的一种势在必行的“进攻”。基于“入侵”的思想,译者以本性为“登录点”,挖掘出“生”(birth)源于“人之始生,得之于天”;而“天”又内在于“人”(man),外在于“地”(earth)。于是,译者由“本性”(nature)对源文进行接近、亲近与阐释,才能破解“天、地、人”之间互融互渗的密码。可见,《三字经》译者的翻译之道贯通了天道、地道、人道的整体智慧,蕴含着“天地和一”的诗性智慧。且看如下译文:
人之初,Man on earth,
性本善。Good at birth.
上述对“人之初,性本善”的翻译背后蕴藏着诗性思维。从生态翻译学的视域来看,《三字经》翻译之诗学智慧是不断地追求译者主体与翻译生态的和乐、和融与和谐,让翻译在nature的存在之中前行,继续将不在场的存在或词语牵引出来,赋予《三字经》其他诗节的“言说”与“述说”。词语“性”(nature)的出场,就或隐或现地“言说”与“述说”了词语“伪”nurture,其原因在于“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荀子·礼论》)。正是追问nature与nurture之间的关系,展开为翻译的形美与意美之间的张力,乃是翻译的诗学智慧之光与生态思辨之光,闪烁着翻译之本质与本质之翻译。因此,虽然人的最初本性状态是一样的(same),但是由于“伪”(nurture)的作用,人的习性开始发生了变异(varied)。正是通过“性”与“伪”之间的辩证性思考与探询,找到了nature 与nurture 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其外在韵律,巧妙地表征了翻译所隐藏的诗学智慧。且看如下译文:
性相近,The same nature,
习相远。Varies on nurture.
Nature与nurture成为翻译《三字经》的一对核心范畴,开启了《三字经》翻译的辩证统一之路,展现出《三字经》在《英韵三字经》的翻译过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生生不息。可以说,Nature 与nurture 之间的辩证统一,抑扬之韵气势磅礴,其翻译策略是“中庸”平衡之道,其审美意境在于形意神似,真正做到“形即是神,神即是形,神倚形而出,形依神而构”[4]。Nature 与nurture 用自身固有的形式来表征整个诗节,巧妙地“复活”与“平衡”了《三字经》源语系统的生态结构,创建一个与源语生态相适应的生态环境[5]。Nature 与nurture 的选择与适应、调变与取舍,展示了生态翻译学的生态理性思想——“注重整体/关联、讲求动态/平衡、体现生态美学、倡导多样/统一”[2](P101),展示了译文在异域中的诞生、再生与成长。
二、《三字经》翻译的生态诗性
生态翻译学主张翻译是一个和谐统一的系统,强调“牵一发,动全身”的特征,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及其内部结构的整体性[2](P80-81)。《三字经》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本生态,其翻译需要生态地和整体地看待翻译生态环境与翻译的存在、看待译者的存在和作者的存在、看待源文的存在与译文的存在,并整体地和生态地去做适应性选择与选择性适应,将其纳入生态诗学的轨道,促使其通向源初的生态诗性。诗歌以其简洁含蓄而又和谐的语言,鲜明的节奏,整齐的句式,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特质,超越了仅仅语言意义的层面。这些元素共同构建了诗歌的整体意境。因此,如何将建构与再现《三字经》翻译的生态诗性,成为译者研究并付诸于翻译实践的驱动力。
(一)《三字经》翻译的生态智慧。在生态翻译学的框架下,翻译的生态智慧就是“将原语的文本‘原汁原味’地移植到译语中去,就是在译语生态里建构、修复和调适能够使译文存活、生长、乃至长存的生态环境”[2](P243-244)。这意味着《三字经》翻译需要消解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之间的相互对立,通向共生共存、动态平衡与完美和谐。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不断进行语言对比,作出更合适的选择以实现翻译系统的和谐统一。在此和谐思想的观照下,获得一种整体性的平等感、平衡感与协调感。因此,《三字经》翻译所追求的生态智慧就是一种整体和谐与生态平衡。
在生态智慧的观照下,译者主体在《三字经》开篇之作的翻译就以nature 为认知机制,以nurture 为调变机制,关注原文生态与译文生态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在译语生态里协调和平衡,奠定《三字经》的生态翻译生成、运行、变化、发展与存在的生态基础。Nurture的出场不仅会牵引出译者主体的生态智慧,而且也体现了nature对译者的审美要求。《英韵三字经》第二诗节的词语出场,正是展开于nature与nurture之间的辩证统一与和谐平衡,此乃是《三字经》翻译的生态智慧要求。且看《英韵三字经》的第二节译文:
With no education,苟不教,
There’d be aberration.性乃迁。
译者在翻译此节诗文时,正是以nature与nurture的统摄性功能来界定education 与aberration 之间的音韵美感与意义潜势,aberration 中词素(ab-)与no education 中否定词(no)的意义相对应,蕴含着nurture所牵引的主体作用对nature产生了消极效果。此时,education 在否定词(no)的作用下,与aberration 获得了音韵与意韵上的内在关联,不但融合了译者的翻译思想与教育思想,而且体现了译者对于当今没有灵魂的知识教育的忧虑与对于偏离轨道的适应教育的思索。这是译者主体通过aberration中词素(ab-)与no education中否定词(no)基本语义结构进行巧妙处理,挖掘出彼此之间的意义潜势。这正是译者的生态智慧以及对翻译生态的追求,才能保持原诗的思想与意韵,让读者获得整体性的教育意义及其内涵。Nature与nurture之间的辩证统一、education 与aberration 之间的对立统一,教育与受教育者之间的互动,都以不同的方式显现了翻译背后所内蕴的生态智慧。
如前所述,no education表征着nurture对教育主体产生的反面作用,那么nurture的正面作用是如何与反面作用交互呢?译者主体高瞻远瞩,以《英韵三字经》开篇之诗节good at birth来牵引出nurture的调变机制,强调以“教之道”的方式对教育主体引发积极作用。此时,与good 遥相呼应的well 自然而然地出场了,与education紧密相关的teach也跃然而至。那么,如何表征教之道的“专”性呢?正是在译者主体性与诗学创造性的作用下,以deeply的音韵效果拉近与teach的音韵距离,进一步凸显了原作的意向性,创造了教育主体与“教之道”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召唤与well具有诗学象似性与音韵象似性的词语(dwell)的出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文进行“改写”,任何形式的改写都是译者诗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反映[6]。正是基于译者对此节诗文的创造性“改写”,well与dwell,teach与deeply之间的音韵获得了诗学意义上的象似性,从而象似性地创造了一种逼真的美学效果。
To teach well,教之道,
You deeply dwell.贵以专。
在翻译此节诗时,译者主体通过教育之道、自我翻译意识和翻译创作的融合,既使well 与good 相互对应,又使well 与no education 和aberration 的意义潜势(badly)相互对立,表征着nurture可以通过对立面的调变合乎nature的认知机制,凝聚了此节诗的内在逻辑关系,突显了教育整体性的生态智慧。译者的翻译策略使此节诗文与第一节诗文“有一种遥相呼应、首尾相援的节奏,而原作者正是以这种节奏为骨骼,附辞会义,晓义切理,使文章意味深长,富有叛党寓意”[7]。可见,译诗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要找到翻译的生态诗性,而且在于发现翻译的生态智慧。由此,此节诗译文的生态智慧既展现为形美、音美与意美的统一结构,又映射了翻译的整体之美。
(二)《三字经》翻译的生态美学。生态翻译学强调,在生态翻译过程中要体现生态美学,兼顾意美、形美、音美,追求真、善、美,促使翻译通向生态平衡与完美和谐。综观《英韵三字经》,译者始终以生态美学为内在要求对《三字经》进行整体性功能综观,从《英韵三字经》第一诗节nature与nurture的出场到第二诗节education 与aberration 的出场,牵引出“教”与“不教”之间表征出相反相成的二元对立,进而牵引出《英韵三字经》第三节诗中日常生活“人”“教育者”的出场。至此,我们仿佛活生生地看到中西方所融贯与塑造的“启蒙教育”的思想,似乎感受到了长辈对晚辈的终极关怀与人文回归精神的召唤,从而感悟到启蒙教育所注入的恢宏于未来理想的生态美学追求。且看《英韵三字经》的第三节译文:
At Mencius sloth,子不学,
She cut th'cloth.断机杼。
译者遵循生态美学的思想,将“断机杼”译为cut th'cloth是与At Mencius sloth 的意义潜势相对应的,cut th'cloth 犹如断了孟子的sloth,也创造性地取得了cloth 与sloth 之间的音韵像似性,从而彰显译文的意美、形美与音美。词语cut 的出场,一语双关,使语言与意境、韵律与节奏之间产生巨大的生态效应,让sloth 断得彻彻底底,让孟子的学习中断得以延续,生态美学的意蕴达到了新的高度。可见,此译文的音律韵律与孟母的一言一动,让我们仿佛听到了孟母割断织机之布“一刀两断,便斩绝了,更不复萌”的决心,仿佛感受到孟母“诲尔谆谆,听我藐藐”的殷切之情,此乃是译者翻译《三字经》的惊人之笔,表现出一种令人震撼的温良之美。如此,译入语读者就会满怀兴趣去阅读这样充满生态诗性的译作,而原作也就内在地拥有了自身固有的翻译价值,实现有效传播。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三字经》过程中运用生态诗学的理念力图充分保留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异质性”,力求原汁原味地传播中国文化,用中国的经典说好中国的故事。
结语
综观《英韵三字经》,无论是本文所论述的诗节还是整个诗节的翻译,都是在英韵三字格的框架内进行生态翻译思考的结果,俱以形美、音美、意美为主,展现了《三字经》翻译所蕴藏的“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的生态诗性。可以说,《英韵三字经》是对以前《三字经》英译版本的一种超越,亦是翻译规范之内的一种超越。那么,如何在规范之内,还能“匠心独运,不落恒蹊”,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戴着脚镣跳舞”吧[8]。译者主体正是戴着脚镣跳舞,“随心所欲不逾矩,制衡调和臻如如”,舞出《英韵三字经》“形—音—意”三美合一的洒脱与飘逸,舞出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珠联璧合”的生态韵味,闪烁着中华民族古典文化的生态诗性与生态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