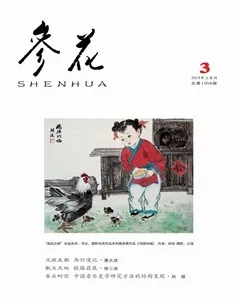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呈现
2024-04-07孙璐
一、引言
中国音乐史于自觉的历史记录中萌发,在理性的研究中逐步建立,随着具体研究对象的发掘与丰富,学术成果的积累与研究范式的建立,关于中国音乐史学的理论建设也逐渐兴起,通过对众多成果进行梳理与归纳,中国音乐史学的理论体系也逐步形成,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一方面在研究实践中应用,同时它也是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实践是理论构建的基础,理论反过来又会影响实践的过程,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过程也是如此,在一定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分类、提炼、加工、总结等过程,对研究方法这一理论问题进行归纳整理,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进一步指导研究实践的进行。通过实践到理论的构建过程,以及对部分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理论成果的研读,笔者观察到其独特的发展路径,这是研究中所呈现的客观现象,也是中国音乐史学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同时还体现了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特殊性与独特性。因此,本文立足于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对其在研究实践中呈现出的现象进行理论的归纳与探讨。
二、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根基所在
研究对象是展开研究的基础,研究方法是为研究对象服务的,同样也是因为研究对象的存在才会有与之相匹配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可以说是研究方法得以使用的前提,有研究对象的存在,才有研究方法的用武之地,研究对象应当是与研究方法密不可分的。
在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研究对象有容量巨大、种类繁多、内涵丰富等特点,同时随着研究观念的发展、新生事物的不断涌现、新材料的不断发掘等因素,研究对象又进行了扩容。例如,系统的文字记录,一方面对远古时期的音乐传说进行记录,另一方面通过历时的书写,对历朝历代的音乐活动进行记录,由此使文字史料产生。此外,由于古代器物的不断发掘及其史料价值获得重视,并被纳入研究范围之内,纵向上使研究的历时性得以延伸,推动了远古时期音乐史的研究,同时也在横向上扩展了音乐史的研究范围,使不同形式的史料进行互补与参照。另外,随着时代的变化、研究观念的更新以及科学技术的创新等,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充了容量,如古代文人的书信、笔记,现代音乐会的节目单、学校教材、期刊、报纸等都纳入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因此,研究对象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与之匹配的研究方法也要依照研究对象的变化进行不断的自我完善。
在远古时期发生的重要事件大都通过口耳相传进行记录并因此流传与保存,如《世本》中记录一些有关乐器制作的传说,《山海经》记载了远古时代有关音乐活动的神话传说,《吕氏春秋》中“古乐篇”对远古的部落音乐及帝王制乐进行了记录。这是后人对上古传说音乐活动的追溯,是将口头流传的事件进行记录,虽然其内容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后人在修著之时也会做添改,但其中符合客观事实的因素也是存在的,其实质是“史料”。当运用系统的文字进行记录,这些史料也就有了物质性载体,文字的记录从龟甲上的甲骨文到青铜器上的金文逐步形成体系,在造纸术产生后书写更加便利,印刷术发明后文字得以广泛地应用与流传。如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三件商代编磬分别刻有“永启”“夭余”“永余”铭文,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在钟体共有铭文2828 字,在官方著述的二十五史当中,有十六部史书都设立了“乐志”类目,《吕氏春秋》更是在先秦时期完成的私人著书,其后还有各种类书、会典会要、“十通”以及不同的专题音乐著述等。此类事物在物质形态上为“文献”,当其纳入音乐史学研究对象范围内,与之对应的音乐文献学研究方法也就随之产生了。我国古代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因而保存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不论是官方的史书,抑或是民间的私家著书,从数量上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不论是专门论述音乐的文献,还是兼及谈论音乐的文献都是车载斗量的。因此,从研究对象的角度看,音乐文献法是早期音乐研究最为基本也是最不可缺少的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是研究方法产生的基础,而研究对象的增加又促使研究方法的应用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
自20 世纪以来,由于众多新形式的成果产生,近现代音乐史料的形式与数量相较于古代音乐史进一步丰富与增加,如档案资料、书信、回忆录、报纸、期刊以及结集成册的丛书、文集等。音乐学领域独有的新史料也数量众多,如歌曲集、乐谱、唱片、录音录像资料等。这些新的研究对象促进了音乐文献学方法的发展,其应用范围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如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创作,由于距研究时间较近、文献保存较为完整等原因,作曲家在音乐创作时的大量手稿得以保存,在创作过程中的多次修改、不同版本的改编等都留下了可供参考的材料,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借助音乐文献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研究。例如,嚴镝的《< 黄河大合唱> 各版本的产生和流传》[1] 对《黄河大合唱》流传的六个版本及其相关背景进行了梳理。杨和平、李岩的《< 黄河大合唱> 四版本考》[2]对《黄河大合唱》不同版本的音乐信息与音乐技术做出对比,并指出:“截至目前,《黄河》的最好版本,依然是“中央乐团”在严良堃主持下修订的《黄河》。”[3]
中国音乐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于20世纪初兴起,在20 年代已有叶伯和、郑觐文等学者以不同史观书写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积累了数量可观的音乐史书写成果。此外,有关音乐的杂志也数量丰富。1906 年李叔同编印了《音乐小杂志》,虽然此刊只出版了一期,但它是中国音乐期刊出版的基石,对后世音乐期刊的出版及发行有着重要影响。[4]自新中国成立后,学术性音乐期刊也如春笋般生长,焕发生机与活力,更不必说专业人才队伍的培养,这些都为中国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增添助力,也为中国音乐史学积累了众多学术成果。到目前为止,中国音乐史学发展已历经百年,百年来学术成果丰硕,通过专著、期刊、丛书集成等形式展现。此类成果可以进一步被看作新时期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开展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因此音乐文献法的使用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展。
因此,基于上述文献或类文献形式的研究对象,是音乐文献学方法形成的基础,同时也对此方法的发展与应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与文献相对的则是实体器物,一些学者认为我国古代的金石学可以看作是现代考古学学科的前身。金石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为传世的器物,从金石学著述看,有对乐器的临摹,对乐器尺寸的记录,对乐器铭文的收录等。由此可见,由于时代、研究观念的不同,对乐器所含的音乐信息及文化信息并未完全发掘出来,同时,此部分的研究对象并未脱离金石器物这一大类,往往与其他青铜器如礼器、兵器等共同记录,此时还未能形成独立的音乐考古学科。
20 世纪初,中国考古学学科诞生,学科的建立及研究方法的逐步成熟使器物信息的发掘更为充分。另外,相较于传世器物,这一时期出土器物的数量也开始逐步增多。科学的发掘流程,使器物的原始信息也得以保存,大量音乐考古实物的发现,使得此类器物作为研究对象进入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横向看,出土的乐器种类十分丰富,有笛、鼓、钟、筝、琴等,其材质也不一而同,有骨质、石质、陶质、木质、金属材质等;纵向看,时间跨度颇为久远,具有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两个部分。如此丰富且复杂的物质属性,会在研究中拓展人们对音乐历史的认识。一方面,通过对这些音乐材料的研究,可以使人们了解到在上古时期还未形成文字记录的年代,古人是如何进行音乐活动的;另一方面,文献的记录并非历史的全貌,而对器物的研究有时会突破文献的记录,使人们了解到更多文字之外未被记录的音乐历史。如黄翔鹏对青铜乐钟上一钟双音现象的发现,文献当中并无记载,甚至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之前,一些学者对黄翔鹏的观点也不甚赞同,但正是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反而印证了黄翔鹏的观点。由此可见,新材料的面世也是产生新方法、新观点、新结论的重要途径之一。在金石学的研究传统之上,依托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现代科学技术以及跨学科研究观念,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实践后,音乐考古学方法也逐渐形成。从器物本身的音乐信息看有材质、音响、数量、组合等,从器物之外的信息看有对使用者、演奏者、演奏场合、器物象征等方面的研究,从相同的研究对象中通过研究方法的转变挖掘研究对象的更多信息与内涵。
由此可知,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不可分割的一对组合,研究对象决定着研究方法的选用,合适的方法才能对研究对象展开有效的研究;而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又能够体现出具体研究所采用的不同视角,从而体现出对某一对象研究的深度或广度,因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是联系紧密又相辅相成的。
三、研究方法——以目的为导向的合作之法
在音乐史学研究中,研究对象本身往往具备多重属性,如出土的竹简从形制看属于器物,是考古出土的文物材料,但其记录的内容经整合又可用作文献材料。而文献材料的记载,同样也会包含众多不同类别的音乐事项。因此,在研究实践当中,研究者会根据研究的目的选取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有时在不同的研究中会使用相同的研究对象,抑或是对同一研究对象使用多种研究方法,这从侧面反映出研究对象内涵的丰富性,同时也体现出研究方法之间并非是完全独立的。
从音乐文献学的方法看,一般所研究的对象大部分是文字,包括出土的竹简、乐器上的铭文、纸质的文字记载等。中国音乐文献学基本脱胎于古典文献学,运用古典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史源学等方法,并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作为基本研究理念。[5] 在文献研究之外,还有其他诸多领域的研究,会在借助音乐文献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同时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进行共同研究。
(一)乐律学研究法
乐律学是中国古代音乐史学中的重要研究领域,它是有关中国古代音乐技术理论的概称,乐律学实际包含“乐学”和“律学”
两个部分。[6] 自先秦之时便有相关论述,如《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律》中最早记载了关于十二律相生的过程,《管子·地员篇》中通过“三分损益”求得“五声”的方法,其后历代官方史籍中的“乐志”“律志”等类目都有记录,也有个人著述如宋代蔡元定的《律吕新书》、明代朱载堉的《乐律全书》等,记录了他们对乐学或律学的研究成果。这类史料以文献作为载体,依托文字而保存与流传,但其中蕴含的学理知识则并非文献载体能够囊括的,在研究过程中要依靠对文字的理解、辨析,如对“乐调”的考辨、对“宫调理论”的探究;或对其中乐律学的知识进行逻辑推理或数理计算,如对“生律法”的推算,对“纯律”“琴律”的考证等。除去历史史料外,学者通过对种种乐律学问题的研究而产生了诸多成果,进一步形成乐律学的相关文献记载,同时形成一定的研究范式,相应的方法论也就随之产生了。乐律学史料依靠文字载体进行保存与流传,其形式是文献形式,同时乐律学作为思想成果,使用乐律学研究方法对其进行逻辑的推理或数理的运算,与音乐文献学方法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对乐律学的研究。
(二)器物史料研究法与传世的文献史料相对的另一大类是考古出土的器物史料,李純一将出土器物划分为四类,即乐器、乐谱、形象和文字。
音乐文字遗存主要有刻辞甲骨、器物铭文、简牍、碑刻和各种题记,等等。[7] 文字遗存与传世文献在研究中是相互补足的,因为传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会经历传抄、刊印等过程,其中不免会有错漏、讹误甚至是篡改,但出土文献往往保留其下葬前的原貌,更为贴合文献的原始面貌。方建军指出,出土文献里专门记载音乐内容的书籍或篇章目前发现较少,而关于音乐的记载通常都较为分散,往往穿插于其他出土文献之中,需要做专门的梳理和分析。[8] 即便如此,出土文献在研究领域也依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李玫在她的文章《放马滩秦简< 律书>——为第七届国际音乐考古学学术研讨会而作》[9] 中指出,放马滩秦简的出土为《吕氏春秋》到《淮南子》中的乐律学理论提供了发展的中间点,《吕氏春秋》与放马滩秦简成书年代相同,表明当时的乐律学知识已不仅限于《吕氏春秋》当中的内容,而是更加丰富。同样,一百年后的《淮南子》也并非照搬前人观点,而是对前人成果有所扬弃与创新。这使人们对乐律学发展的认识更为连贯,同时也体现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作用。出土文献的这一作用也体现出多重研究方法的使用,就这一对象而言,它运用了考古学或音乐考古学的方法加以研究,而对其中有关音乐信息的文字记载则使用了音乐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文字所记录的思想内容则又运用了乐律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体现了研究方法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
乐器是出土器物的一大类别,也是音乐考古学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乐器作为音乐实践的材料也蕴含了丰富的史料信息,现代有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气鸣乐器分类法,我国古代依据乐器材质进行的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的八音分类法,一方面可以看出乐器种类繁多,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乐器的数目总量之多。在众多乐器中,编钟与编磬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礼乐文化的物质化代表,在中国上古音乐史与音乐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众多新器物的出土,以及对传世器物信息的收集,使学者对青铜乐钟的研究也更进一步。文献中对编钟的记载有《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凫氏》,[10] 记录了钟各部位的名称,及铣、钲、鼓等不同部位之间的比例关系,并对钟的声响和调音方法做出描述與指导。《磬氏》篇则对编磬的制作标准、调音方法有所记录。但这些记载仅是从理论方面对乐器制造做出的规范,而在实践当中这些规范是否应用则需另行研究,同时这些信息仅展现出乐器制造这一方面,编钟、编磬本身丰富的音乐与文化内涵并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其所承载的信息更多的是通过对实物研究所得到的。如陈荃有的《中国青铜乐钟研究》[11] 对乐钟的历史与新生进行了分别的探讨,对新石器时代到战国中期的乐钟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从乐钟起源、形态特征、演进关系、编列组合、测音结果及其构成的音列结构进行研究,并对乐钟在当代的研制与开发做出探讨。王清雷的《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12]从器物种类的使用、摆列的组织结构和音列的设置三个部分,对乐悬制度从滥觞、发展到成熟、稳定做了细致的梳理与分析。焉瑾的《河南所见东周钮钟的音乐考古学研究》,[13] 借助《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与《先秦乐钟之研究》两部著作中所运用的类型学方法和部分钮钟的测音数据进行研究,得出东周时期河南地区钮钟盛行的形制与音列组合。
其他种种,不胜枚举,一方面以音乐考古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同时辅以音乐文献学的方法,共同作用于同一研究对象,得出合理可信的研究成果。
从古谱的研究过程看,也是多种研究方法并用的,如对古谱记录与传承的探究,对乐谱记录内容的释读,考释其使用符号的含义等,往往会使用文献学的方法。陈应时的《中国的古谱及其分类法》对众多乐谱进行了收录并加以分类,并借助文献记载对乐谱进行简要说明。[14] 另外,陈应时在他的《敦煌乐谱新解》[15] 中借助沈括的《梦溪笔谈》和张炎的《词源》,对敦煌乐谱中的乐谱符号进行了解读;而古谱解译之后进行实践,关于乐器定弦、演奏等问题又与乐律学方法和乐器学方法进行了关联,同样是在《敦煌乐谱新解》中,陈应时对林谦三、叶栋等学者所翻译的琵琶定弦有所提及。这也是多种研究方法共同作用、共同研究的体现。
由此可知,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也并非完全独立,而是以研究目的为导向,选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使其在实践研究中互联互通、环环相扣的,只有这样才能够对一个事物、一个问题研究得透彻与全面。
四、跨学科思维——研究方法的养分汲取之处
一个学科能够长足发展必然不可能自我设限,现今的学术研究发展趋势也表明,不同学科之间的壁垒正在被打破,不同学科之间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被应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中。
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借鉴上大致也可分为三类,首先是在研究过程中借鉴音乐学内部不同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其次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内研究方法的利用;最后则是对自然科学领域内研究方法的借鉴。
关于音乐学内部不同分支学科的借鉴,在黄翔鹏的《逝者如斯夫——古曲钩沉和曲调考证问题》一文中,[16] 使用现存的五台山寺庙音乐与文献中记载的曲牌与宫调进行对比,以时间逆向的形式,对现存的活态音乐做出历史的考察,而五台山寺庙音乐属于晋北笙管乐,在译谱过程中要考虑其调名、定律、宫调等问题,此部分借助音乐形态学与民族音乐学的方法进行判断,同时与不同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中的同曲牌进行调名、定律、宫调等进行比对,为现存乐曲探明了历史来源。黄翔鹏的《明末清乐歌曲八首》中,[17] 根据东传日本并集合成册的《魏氏乐谱》工尺、点板,同时进行宫调、句式的判断,翻译出明末可能存在的清乐歌曲,这一译谱过程同样也借鉴了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和云峰的《纳西族音乐史》[18] 部分内容涉及纳西族古代音乐史的研究,这是将纵向的音乐史学观念纳入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以历时的观念来考察少数民族的古代音乐生活,为少数民族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做出有益探索。此外,明言在《< 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 研究导言》中指出,[19] 对中国古代音乐批评史的研究是立足于音乐批评学学科之上,融入了历史的维度,并辅以音乐文献学的方法对中国古代音乐史中不同文体的音乐批评文献加以分类,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专门史研究。
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也是当前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不断尝试与探索的一个方面。从传统的研究方法看,像音乐史学中使用频率较高的音乐文献学方法脱胎于古典文献学,继承了其传统的校勘学、史源学、版本学等方法同时结合音乐史学的自身特点发展而成。音乐考古学方法脱胎于现代考古学,在继承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结合音乐学的方法,对器物的音乐性能及其呈现的音乐文化加以挖掘与探讨,综合起来便成了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如李纯一的《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将考古学中的类型学方法在音乐考古中应用,[20] 通过对击乐器、管乐器、弦乐器三大类,包括鼓、磬、摇响器、哨、笛、埙、琴等二十多种乐器及部分乐器配件进行研究,在搜集大量样本的基础上,对众多乐器作了类型学的分类与研究。
此后,有众多研究借助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对某一特定地域或文化分区的乐器进行类型学研究,也有基于特定时间段的类型学研究,从而得出特定地域或特定时期的乐器发展特征与规律。王子初的《论音乐考古学研究中类型学方法的应用》[21] 对音乐考古学中类型学方法的使用做出了理论性的总结,他在文章中指出:“在考古类型学中,将为数众多的古代遗物和遗迹进行分类和归纳,是类型学研究的必要前提……考古类型学研究的根本目的——解决器物发展先后序列关系的问题。”[22] 文中还提到,对乐钟音列的研究也是类型学方法在音乐考古领域内的进一步发展,它的使用从有形器物拓展到了音响特质的研究,体现出此方法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特殊作用。
音乐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具有多重性质,有时也会同其他社会现象相结合,如韩启超的《中国音乐经济史(远古至南北朝卷)》。[23]其在摘要中写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原理,经济是基础,政治、艺术等上层建筑都受到这一基础的制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其基本要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24] 由此受到启发,将这一观点引入音乐生产领域,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经济环境相结合,梳理出经济与音乐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促进还是阻碍,抑或是情随事迁,这一研究将音乐史学与经济学进行了结合,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于音乐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并非单纯被视为一种艺术形式,往往会被附加众多文化功能,如“乐与政通”“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等,因此也有借助政治学视角对中国古代音乐进行的研究。例如,张瑜的《汉代“元会仪”与古代音乐政治论思想的问题》,[25] 以仪式用乐为切入点,探索“元会仪”这一政治功能的仪会因何用乐,以音乐政治论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与阐释。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研究中,田可文、留生的《音乐政治学、音乐传记学与我国的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26]对“音乐政治学”做出狭义与广义的定义区分,并对海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此外,还有余梦奇的《荀子乐政观之初探》[27]、管艺的《宋乐六改中的音乐话语与政治博弈》等。[28] 探讨是否形成音乐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也许还为时尚早,但此类将音乐与政治相关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对拓展中国音乐史学的研究方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随着研究目的与实践需求的变化,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增加。中国古代已有关于音乐声学的讨论,而随着西方声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传入中国后,音乐声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古代乐官对乐器调音都是“以耳齐其声”,借助个人的音乐修养与能力来对音进行调整,抑或是发明律准、律管作为标准器,依照特定的标准进行乐器的调音。而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对出土乐器进行测音,可以通过数理的方式对音做出直接的描述,借助声波、音分等即可对音的高低、关系等做出精确的判断与比较。韩宝强在其《音的历程:现代音乐声学导论》[29] 中,对我国从古代到近现代的音乐声学测量历史做了大致的梳理,并指出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音乐声学工作始于20 世纪初,是由刘复先生进行的。[30] 而音乐声学测音这一方法,目前已大量运用于出土乐器的研究中。此外,陈通、郑大瑞的《古编钟的声学特性》[31] 和《椭圆截锥的弯曲振动和编钟》,[32] 两篇文章通过对乐钟进行测试,对乐钟能够实现“一钟双音”以及钟内调音和“枚”的作用,认识不同部位对音响效果产生的影响,对乐钟做出物理声学角度的认识与判断。
通常而言,能够进行测音并得到相对准确结果的乐器大多是保存相对完好的,但也有许多出土即为残缺的乐器,破损的乐钟、折断的石磬……金属、石材都如此,更不必说竹、木类等乐器的出土状况了。有鉴于此,如何对乐器复原,也是研究者十分关切的议题。如对曾侯乙编钟的复原工作中,[33] 曾侯乙编钟复原工作组对编钟原件铸造工艺、合金成分、声学特性、音响效果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尝试了四种不同类型的编钟铸造方法,借助现代科技对乐钟进行物理层面的剖析,也为复原乐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由高兴等编著的《中国音乐科技史纲》一书中,[34] 将音乐科技问题大致分为六类:音乐自然科学思维、音乐声学、音乐数学、音乐力学、乐器工艺学和音乐传媒技术。在此基础上通过历时的角度进行探讨,并对历史文献中有关音乐科技的信息进行梳理,对音乐科技问题的古今状态做出观照,使读者能够更为全面地了解音乐科技发展史的古今面貌。虽说有些乐器出土时较为完整,但出于对文物保护的目的,应当减少出土乐器原件的演奏频率,使其能够更好地保存。目前除了使用复制的乐器进行测音或演奏外,还有借助现代科技,对乐器进行数字化的制作,通过演奏人员在现实中的动作来演奏数字化虚拟的乐器。如胡文娟的《手势驱动编钟演奏技术的研究与系统实现》[35] 运用计算机与个人的交互模式,预先设计相应的计算机程序,以此来识别个人的手势,从而通过非接触的形式对乐器进行演奏。这种方法既满足了文物保护的需要,又满足了音乐文化传播与普及的实践需求,赋予了古代乐器重要的现实意义。由此也可看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众多跨学科方法的实践,借助新兴科学技术对音乐问题进行探索,以及相关成果的累积,音乐科技这一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此,音乐学家于润洋曾说过:“扩大学科的学术视野,实现学术上的互补与互相渗透,意识到学科之间的‘普遍联系,这对我国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和深化,具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音乐学相关的一系列人文学科迅速发展、音乐学子学科相继形成的今天,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36] 于润洋具有前瞻性的话语在今天看来仍有指导意义,而中国音乐史学作为音乐学的子学科之一,也正以开放的态度借鉴不同音乐学子学科、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五、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方法是针对不同研究对象有选择地使用的,也会随着研究对象的发展而产生不同的变化;其次,研究不同的对象、解决不同的问题也是选择研究方法的另一原则,在研究过程中有时会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有时会运用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不论是“单兵作战”还是“集合作战”,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再次,当研究过程中有了新的需求,既有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能够解决的时候,不应被学科的边界所限制,而应当为了解决问题,勇于突破学科的边界向外探索,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解决现有研究方法难以处理的问题,从而构建新的研究方法,对学科研究进行完善;最后,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这并非意味着原有研究方法就此过时,也并非是对旧有研究方法的替代,原有研究方法与新兴研究方法并非是彼此对立的,在研究实践中应对研究方法按需索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因此,研究方法是一把钥匙、一个通道,只有用好这把钥匙,才能开启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新面貌,只有走過这条通道,才能使中国音乐史学获得长足发展,使中国音乐史学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作者简介:孙璐,女,硕士研究生在读,中央音乐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音乐史)
(责任编辑 王英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