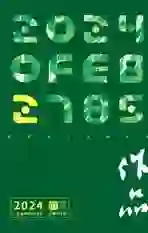新世纪青年写作的症候性表达(评论)
2024-03-19郭艳
郭艳
王幸逸作为一个青年写作者,他的创作有着鲜明的21世纪以来新文学叙事特征:文体多样性的自觉,语言表达穿越古典与现代的追求,兼具有多血质和抑郁质的情绪表达,现实和幻想维度的自然转换,等等,这些使得他的写作一开始发生就充满着多种路径生长的可能性。从本次小辑的文本写作来看,他的写作在现实、历史和审美等维度上几乎同时展开,才华在新旧文体和语辞风格中任情恣肆,写作技术的代际叠加在题材、技巧和语言层面上生成,独具面目抑或多张面孔的青年写作者从文学景深中走来,又在角色扮演的时代透过重置的现实透视人生的真相与本质。
作者現实层面的文本叙述带着浓厚的个人生存经验痕迹,一如前代的青年写作一样,清浅、诚挚、动人,驻足处皆景语情语,人物却自顾茫然,才华熠熠中折射着年轻时代曼妙的灵肉悸动,也沾染着青春期悲秋伤春的庸常。《忽闻歌古调》是对于年轻女孩日常校园生活流行的记述,开篇描述了当下流行的青春身体的安放方式,似乎无所顾忌的身体释放,蒙太奇式的放大的器物和感官的印象派摹写,现代年轻人疗愈身心的方式——简单、直接,几乎近于简陋。然而一次目的明确的幽会却在貌似无心却各自心思颇深的试探和猜疑中变得面目模糊,无法顺利进行的身体运动却意外导致了两人在精神层面某种难言的契合。《罗马玫瑰》用男孩的个人经验讲述了一个老套的故事:在闭塞而耽于幻想的小地方,年轻的心智和身体都无处安放,心仪女孩的物质主义选择无疑是最后一根稻草,在现实无言的刺激下,男孩终于开始了自己面向功利主义或美其名曰“理想”的出走。文字的诗意表达和现实的冷硬荒凉彼此映照,通过不知所终的刻着罗马玫瑰字样的戒指、维纳斯与阿芙洛狄忒以及哥哥和女孩对于不同信念的纯粹追求,等等,文本呈现了21世纪青年对于性、女人、记忆、历史乃至命运更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登仙》通过儿子的视角,讲述了未见过面的父亲和被父亲遗弃的孤儿、寡母、外祖母相依为命的故事。在儿童视角的观察中,偏远的小地方和随着时代不断变动的生活凸显着儿时记忆的伤痛和扭曲。蒙着面纱的成人世界影影绰绰,父亲缺位的不安全感衍生出眼泪、病痛和梦魇。破碎的残缺的生活被两个女性勉强地维持着外表的体面,敏感的男孩在琐屑而模糊的镜像中已然发现了生存的残酷真相。
与此同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在对于历史文本的重构中阐释和表达了青年一代对于历史的认知与解读。《胧月夜》虚构了二战前后身份复杂的日本战犯尾崎的故事,小说通过不同时空、场景和人物的倒叙和插叙,试图对尾崎的诡异人生进行复原,重述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尾崎作为一个日本人面对战争、道义、人性等的复杂体认。小说试图以在场身份进入历史情境,重新叙述历史镜像中的人、细节和心态,赋予历史叙述以当下时代的精神烙印和生命情感体验。文本游走在间谍身份、不同信念、理想与现实的狼奔豕突中,想象空间叠加在物是人非的回溯性叙事中,往事如烟的背后是无法厘清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负荷与重压。
中国文学创新时常在复古的基调下进行,古典资源一直是影响的焦虑,更是赓续创新的源头。作者的文本叙事在审美维度上也有着自己独到的发现和表达。《异闻》改编自《聊斋志异·长清僧》,作者将短短几百字改写成一个颇为繁复的故事。深宅大院里的痴傻少爷,胆怯而隐秘的少夫人,虔诚愚拙的老夫人,古板守旧的老爷……遭遇飞来横祸的少爷与老僧飞散的魂魄交合,少夫人深闺寂寞与花妖狐媚的幻化,大宅仆役的八卦与附会……文本充斥着神异故事、话本和心理分析小说的混合气味,人物也在传统古典的意境中走向现代人格分裂与精神情感的扭曲与变异。被重新改写的故事在几千年悠悠岁月的时间机器中生长,带着回望的纠结与窥视的贪婪,当下的生命体验复活了神异思维的灵动与荒诞,同时也在对于历史、人性与宗教信仰的游移与纠结中,凸显了碎片化的审美与感知。僧非僧,俗非俗,人非人,妖非妖,仙非仙……在物质主义的功利化生存中,难得有片刻的闲暇追溯古典时代的悠长、缥缈与荒诞不经。
青年写作经历了20世纪的70后、80后、90后到横跨新千年的00后,青年写作者的分化与多元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这种碎片化的多维写作又有着鲜明的新世纪文学特质。王幸逸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青年写作新世纪症候的当下表达。其一,文本叙述现代个体深陷现实生活逻辑,呈现独异个人内在精神情感世界的自闭性与自足性。《忽闻歌古调》讲述了中文系女生从本科到研究生的颇为孤独的情感生活。渴望被理解、被温暖、被呵护的女孩,才会期待生命中有男性走来。然而无论是网络和现实的恋情,都充斥着这个时代特有的个人化难题:个体间的隔膜、生存的压力以及无法倾诉个人感受的“宅性”。或许过于早熟和世故的生存体验让年轻人认识了现实,同时又远离了对于世界和人的真正认知。现代个体面对未来生计和职业的现实考虑,早熟的身心,熟谙物欲享乐的趣味。这些让这代年轻人在青涩的年华多思多虑,在身体和精神奔赴的过程中踯躅不定。当现代个体面对他者和世界的时候,既没有双向奔赴的勇气,也缺乏直面现实人生的行动。即便是遇到了良人,邂逅了相知的情感,触摸到人与人之间情爱的暖意……然而都会在冷静、理智的认知中回到个人化生存的原点——生活莫过于此,任何彼此间的理解与温情都将转瞬即逝。孤独的自我才是那个坚不可摧的堡垒和城池。我是自我的,更是安全而私密的个人王国——我轻如草芥,然而却是自己的王。其二,写作者热衷历史维度的探究与重述,同时在深度还原的叙事中走入价值碎片化的迷惘。《胧月夜》是溢出作者生活经验的创作,因而也更具写作的创意性和挑战性。作者尽管用了第一人称“我”,然而文本更多是在全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中展开。在类似于历史档案和纪录片的解说式讲述中,文本叙述谍战、多面孔人生镜像、人性的复杂与诡异,呈现出了颇有意味的战争参与者、多重身份的间谍、历史中的幻象叠加与穿越中的恍惚等等,这些不同时空的记忆在不断被梳理和厘清的过程又被赋予更多的疑问和歧义。与此同时,小说也明显有着类型写作影响的痕迹。其三,青年写作以复古的姿态走向新的先锋叙事,审美表达从古典到现代、后现代的穿越很丝滑,然而现代人的主体性建构依然阙如。《异闻》在古典意蕴和现代精神之间寻找契合点,儒释道、神魔鬼怪、仙狐幻化等,这些元素被作者在文本中铺排推陈,营造起意蕴独特的文本叙事。然而在对古雅文字的追忆中,整个故事的结构和人物都陷入某种癫狂和迷乱之中,由此重构的古典场景、人物以及人性很难抵达敏锐而独特的现代和后现代审美。古典时代的神异思维是对儒释道的反动,神佛与人间、鬼怪与人类重构起一个充满幻想和活力的人世间。因此,当新世纪文学重温神异思维的时候,祛魅之后的文本重构大抵应该让仙佛神魔、花妖鬼怪带着独特的解构色彩,给当下功利化的物质主义世界带来一缕清凉解毒的惠风。
王幸逸的古文功底无疑是非常好的。《忽闻歌古调》随手拈来的诗词歌赋、儒释道经文,《异闻》古韵盎然的词句,颇具氛围感的禅房与机锋,深宅大院书房与闺房的迷幻,仆役们阴雨天闲话主人的活泼俚俗,等等,这些锦心绣口的表达让人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作者博览百家、兼收并蓄的修养,当然也难免在此类新式文艺腔中时时莞尔。作者的语汇表达又是多变的,《胧月夜》更多社会用语的功能性词语,显出克制、内敛的陈述性特征。《登仙》则是主观性非常强的印象式的摹写,带着心理分析和意识流动的呈现。《罗马玫瑰》更多新写实小说的叙述方式,人物在生活流变和场景切换中完成各自的角色扮演,最终抵达对于生存本质真实的探讨。现代汉语白话文学到了一个需要用新语体、新句式、新词汇来表达新经验的时代,然而写作者的语言表达却常常捉襟见肘,茫然四顾,不知道用何种语辞才能做到词达意,歌咏言。王幸逸写作语辞风格的多样性表达是难能可贵的,是对于当下现代汉语白话文写作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他对写作题材和写作技术的多样性驾驭也引人注目,显示出作者拓展自身写作边界的勇气和能力。与此同时,对于青年写作者来说,多种路径的写作固然充满着蛊惑文心的强大魅力,然而在写作的初始阶段,专注于自己最富才情、最优写作资源和最深刻生命情感体验的创作依然是非常必要,甚至于是成为真正作家的必要训练。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