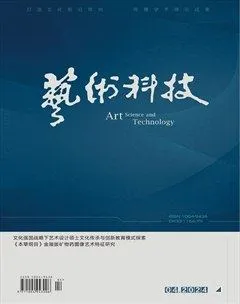《新中国未来记》叙事模式分析
2024-03-18陶宇佳

摘要:目的:晚清之际,在梁启超等人的呼吁下,小说地位逐步提高,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小说创作。李欧梵曾提到,在(现代性)兴起之前有一个想象的过程,这个想象的过程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小说和报纸是非常重要的两种载体,晚清报刊的兴盛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平台,文人通过报刊针砭时弊、辛辣讽刺,企图在面向大众的报刊中寻求认同感,营造一种“虚空的共时性”,而当读者阅读时,会拥有共同的日常生活、共同的日常时间之感,从而达到共同想象的目的。方法: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第一份以登载小说为主的杂志《新小说》的第一号第一篇连载《新中国未来记》,展示了其政治抱负和学术理念。他在小说叙事中构建了层层嵌套的叙述主体,并且在每一层级中对叙述主体进行一定的创新,引入“演讲呼告”与“一问一驳”的独特文体形式,借助大段政论文字,体现其“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写作目的。结果:文章对小说中各叙述层级进行分析,通过文本细读,分析梁启超在小说写作中的新实践与新探索。结论:《新中国未来记》继承与创新了传统叙事模式,梁启超用文学外衣包裹先进的政治理念,在新旧交杂的叙事模式下,打造虚实相间的阅读效果,传递出对未来社会的独特构想与无限期待。
关键词: 《新中国未来记》;叙事模式;叙事结构;叙述主体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4-00-03
《新中国未来记》是梁启超在晚清之际基于现实对未来社会的幻想之作,原文刊登于其创办的《新小说》,连载五回便止。在小说中,梁启超展现了一个较晚清更为先进的崭新社会,这一未来幻想将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政治理念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进行有效组合。在西方思潮影響下,他率先使用西历纪事,以当时的先进理念——共和、立宪作为叙事内容,辅以独特的文体形式,引起了极大反响。
梁启超试图以小说的形式包裹其政治思想,借小说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这导致许多读者在阅读时感到困惑。无论是小说,还是政论文,梁启超都是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新中国未来记》的叙事是小说和政治并举的一次尝试,作者在新纪元的基础上开拓了一个新未来。同时,晚清时期大量外国小说传入中国,中国文人在受到震撼的同时,将各种叙事方法融入本土小说创作,如在《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独特的叙述模式构建了层层嵌套的叙述层级,这复杂的叙述结构蕴藏着作者的慧心巧思,使得小说叙事在真实与想象之间徘徊。
1 层层嵌套的叙述结构
梁启超在传统全知视角的基础上,择取了一层套一层的叙述者,这使《新中国未来记》的叙述主体与叙述视角较为复杂。小说五回接连出现了多个人物角色,梁启超借人物之口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其中孔老先生、黄毅伯、李去病等人作为主要人物一一登场,在讲述中心故事的同时,又旁逸斜出地映射了当时的一些小人物、小故事。
第一回中孔老先生与速记员率先出场,引出了故事的讲述环境,即维新五十年后的万国太平会议。以速记员的口吻记述当时举国同庆、国泰民安、百业待兴的社会情况,从而引出第二回中孔老先生的高谈阔论。第三回从孔老先生的讲述谈到黄毅伯和李去病两人关于中国未来出路的论争。第四、五回则从黄、李二人的视角,呈现游历旅顺、山海关等地的见闻。这五回叙述结构一层套着一层、一环嵌套着一环。“当被叙述者转述出来的人物语言讲出一个故事,从而自成一个叙述文本时,就出现了叙述中的叙述,叙述就出现了分层”[1]117,如速记员讲到孔老先生,孔老先生又成为叙述者宣讲新中国的政治主张,“提供叙述者的层次可以认为比被提供叙述者的层次高了一层”,故“小说的超叙述层次是第一人称叙述(书记的口吻),主叙述层次也是第一人称(孔博士的口吻)”[1]40,那么黄、李二人的谈话及其在旅途上的见闻就自然而然为次叙述的层面。并且在超叙述层面和主叙述层面、主叙述层面与次叙述层面之间,小说中都有专门的句子连接,如“孔老先生登坛开讲,便有史学会干事员派定速记生从旁执笔,将这《中国近六十年史讲义》从头至尾录出,一字不遗。一面速记,一面逐字打电报交与横滨新小说报社登刊”[1]7,这便建立起了速记员与主叙述层孔老先生的关系;“但讲到创始的功劳,老夫便不说,诸君也该知道,就是这讲堂对面高台上新塑着那雄姿飒爽、道貌庄严一个铜像,讳克强,字毅伯的黄先生便是了”[2]20,则是由孔老先生顺接到黄、李二人。在第三回的结尾亦提及“那日孔老先生演说,就拿着这部笔记朗读,不过将他的文言变成俗话,这是我执笔人亲眼看见的”[2]54,这便把三个叙述层面全部连接起来,整部小说在叙述主体上也有了一定的完整性。
在这一层层的记录中,总是由叙述主体回溯往事,“高层次时间在后,低层次时间在先”[1]118。如表1所示,超叙述速记员记载着孔老先生的宣讲,主叙述层面的孔老先生追溯了黄、李二人的欧洲旅行,次叙述层面黄毅伯与李去病讲述过往亲身经历,这一层层嵌套赋予了小说更高的权威。由他人之口讲出的话语,加上时不时出现的《乘风纪行》《长兴学记》《仁学》的佐证,在虚虚实实之间提高了文本的可信度,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读者身边。
梁启超层层嵌套的叙述实践脱胎于古代传统白话小说中说书人的讲述格局。传统白话小说大多由说书人讲述,听众在底下仔细聆听、大声喝彩,说书人娓娓道来各种新鲜、古怪的故事,引得听众如痴如醉。传统白话小说的叙事层级仅限于说书人与故事中的人物两层,若层级过多,就会使结构过于复杂,亦会影响台上说书人的讲述,破坏下面听众的感受。直至晚清,《红楼梦》成为传统白话小说中“唯一具有成功的超叙述结构的作品”,赵毅衡甚至评价其为“现代之前世界文学中可能绝无仅有的复杂分层小说”,并将其分成四个层次[1]119,之后晚清“新小说”进一步实践。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拟书场写作”对晚清小说叙事有极大的影响。但因西方小说的译介、报刊业的盛行、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小说从小道、街谈巷议之作逐渐开始向案头文学转变,叙述者从直接面对面的讲述转向书面文字中的传播。文字的转译、解码与编码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的延宕,如何吸引读者的兴趣,如何让读者相信自己作品的真实性,如何实现对读者确定意义的传递,都是晚清小说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层层嵌套的叙述层级仅仅是他们最初的不算成熟的一次实践。
2 “演讲呼告”的叙述主体
在小说前四回中,梁启超采用一个章回一个层级的叙述主体。第一回以《新小说》报刊编辑与速记员为全知全能的叙述主体,第二回“孔觉民演说近代史,黄毅伯组织宪政党”则以孔老先生为叙述主体,第三回虽然对话主体为黄、李二人,但仍以孔老先生的视角谈及“求新学三大洲环游,论时局两名士舌战”,第四回则将叙述主体转向黄、李二人,涉及二人所见所闻。这种架构使得各章之间有所联系,又存在一定的独立性,适应了报刊连载中存在的时间中断的情况,也在某种程度上规避了读者因连载间隔过长而无法回忆起前因后果的情况。并且,《新中国未来记》采用传统章回体小说创作形式,传统的章节分割方式需要设置悬疑点吸引读者,同时满足了报刊连载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需求。因此,梁启超专门对每一层级的叙事主体即主人公讲述故事的方式进行了创新探索。
第二回中,梁啟超采用了以孔老先生为叙事主体的演讲叙述模式,孔老先生成了第二回唯一的讲演者,梁启超借助这一人物的话语来传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在小说中,他将孔老先生的讲述内容设定为演讲讲义,而这讲义算是国史,包罗万象,既有“零零碎碎琐闻逸事”,又有“紧要的章程”,更有“壮快的演说”[2]10,并且要“演成小说体裁”,以便和《新中国未来记》这一小说体裁相吻合。因此,孔老先生一开始讲述了宪政党、保皇党、国权党、爱国自治党、自由党等党派之间的纠葛,这时的叙述还有说书人的气氛,其中穿插“诸君啊,你道我们新中国的基础在哪一件事呢”“诸君啊,这怎么会算得新中国的基础呢”[2]10等与读者进行探讨的语句。然后是大段篇幅“背诵”宪政党的党中纲领、办事条略(总纲),虽然讲述者也知道“恐怕诸君讨厌,也不必全文背诵出来”,但章程九章二十五节、总纲子目八条在书中仍有较长篇幅的详细记录,宣扬宪政党的所作所为,如此长篇累牍式的罗列很难不让读者在阅读中认识、了解梁启超所倡导的政党活动和政治理论,有如“几百年后社论的起草”[3]。这应该也是梁启超设置孔老先生讲述出来的目的,“令人知道维新事业有这样许多的波折,志气自然奋发”[2]10,作者渴望借他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借助小说让更多国人关注社会与世界的变化。大段的演讲呼告进入文本,使得小说异于传统的说书氛围,即使有叙事主体想要与听众对话,其追求的也不是听众的回应,而是使读者在阅读时更加关注孔老先生传达的宪政党理念。
3 “一问一驳”的谈话主体
在小说第三回,梁启超从孔老先生谈及黄毅伯和李去病二人,黄、李二人的争论是其心中情感与思想的抒发。相较于古代赋体文学中极为常见的“一问一答”,梁启超更多化用策论文《盐铁论》的“一问一驳”。在双方四十四回的争论辩驳中,黄毅伯站在“立宪”一边,以拿破仑为例,谈及革命最后是“把那皇帝的宝冠往拿破仑第一的头上奉送”,革命最终仍要走到“立宪”这一阶段。李去病则高举“革命”大旗,其观点大段篇幅涉及对“以暴制暴”的批判、对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痛恨,他大声疾呼“我一定不想跟着他们学那无廉耻的事”[2]50,坚持“以仁易暴”的看法。二人“句句都是洞切当日的时势,原本最确的学理,旗鼓相当,没有一字是强词夺理”[2]54。
虽然谈话主体对“革命”与“立宪”各执一词,但都是梁启超心中不同政治理论的两相博弈,是其对未来社会幻想摇摆不定的体现。在第三回末尾的总批中,梁启超又极力讲明《新中国未来记》在《盐铁论》上的创新,即“此篇却是始终跟定一个主脑,绝无枝蔓之词”“无一句陈言,无一字强词,笔墨精严,笔墨酣舞”[2]55。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这本酝酿了五年的小说有着极其严谨的创作态度。“一问一驳”的叙述方式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几乎没有,大多为古代策论文中使用,其将《盐铁论》的辩论形式引入小说创作,进一步迎合了当时小说转为书面阅读的倾向,同时也破坏了中国传统小说以情节为中心的叙述结构。在梁启超看来,“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1]50,小说的功利作用大于审美效果,新小说的作用在于“新民”,长篇大论的“一问一驳”恰恰可以在带动读者阅读思考的同时,进一步反映现实、传输观念、记录历史。“一问一驳”亦是一辩一难,在二人的你来我往中,两种政治理念自然而然展现,大量政治理念文字也再次佐证了梁启超对小说真实性的潜在追求。但不可否认,这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小说的可读性,使得《新中国未来记》的趣味性大大减弱。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梁启超对传统叙述技巧进行创新,以中国传统创作技巧加之西方政治思想来创作中国新政治历史小说。他还在此基础上,拓展了“演讲体”“游记体”多种文体样式在晚清“新小说”中的使用。如此看来,《新中国未来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早已大于其在文学文本上的意义。
4 余论
《新中国未来记》的残章断尾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黄、李二人辩驳结果的难以为继,更让人们去思考仅在文学世界中构建“新世界”的意义何在。梁启超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曾写道,原计划有三部政治小说的写作,即《新中国未来记》《旧中国未来记》《桃花源》,但三者都无疾而终,唯一面世的《新中国未来记》只有五回便戛然而止。晚清孙宝瑄曾在其《忘山庐日记》中断言《新中国未来记》必不能完成,因其“演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以今日为过渡时代。盖今日时势为未来时势之母也。然是母之断不能生是子,梁任公知之矣,而何能强其生乎?其生则出乎情理之外矣。……梁任公,天资踔绝者也,岂肯为无情无理之著作乎?故吾料是书之必不能成也”[4]572。未来本就是开阔、没有边界的,“新中国”的建构也大多只能存在于想象之中,而中国未来的出路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找到。因此,“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的《新中国未来记》本身就带有梁启超“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创作目的。王德威曾批判晚清文人“对历史及未来的‘总结,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其结果只能是把现在的文化、道德观、目标和幻想投射进未来”[5],梁启超也不例外。未完结的《新中国未来记》在某种程度上昭示了旧中国的难以为继、没有出路,梁启超用一个个开放的、未完成的文本向读者表达他的迷茫,暗含新中国在未来实践中的多种可能。
5 结语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对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进行了一定创新,使小说创作拥有更多可能。同时,他也向读者展示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惶恐与设想、对当下社会极为强烈的责任感。他以笔展现了迫切想要寻找新中国出路的努力,虽然在叙事中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梁启超对政治的看法、对小说的探索永不停止、永远在路上,正如其本人所言,“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参考文献:
[1] 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117,40,118-119.
[2]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20,10,50,54-55.
[3] 许子东. 1902年: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幕礼: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J].名作欣赏,2020(28):5-12,2.
[4]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 1897-1916[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50,572.
[5] 王德威,王吉,陈逢玥.小说作为“革命”:重读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31(4):1-10,61.
作者简介:陶宇佳(2000—),女,河南南阳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晚清报刊小说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