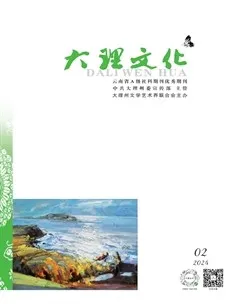博南古道上的三个身影(下)
2024-03-02张继强
张继强
云南,是个什么地方呢?简单的说,云南是个真正意义上山高水长的地方。云南有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有东北西南走向的乌蒙山脉,全省山区半山区面积占94%。高黎贡山、怒山、云岭由北肩并着肩蜿蜒南下,越往南,山峰间的距离越大。云南有六大水系,长江水系注入东海,珠江水系、澜沧江水系注入南海,元江水系注入南海西北部的北部湾,怒江水系、伊洛瓦底江水系注入印度洋东北部的安达曼海。
在山凸水凹之间,一直隐藏着许多外界也包括我们自己难以了解的自然和人文密码。秦汉开始,虽然云南形式上已经被纳入中原王土,但由于王朝看似宏大的机器动力毕竟有着时代的局限,实在是难以把整个云南运作得彻底开化,有很多地方一直都是王权难以抵达的死角或是外來文化浸润的空白区。这些地区的存在,使云南常被皇权朝廷当作戍边流放的去处。由于被流放者曾经都是士大夫阶层,也是中原文化的载体,他们的到来,一方面似乎是要接受改造惩处,同时为了活命也要接受云南本土习俗的同化。但事实上这些人却成了汉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生存活动,让云南的文化在远古的地方底色之上,增加了各种方向、各个朝代的元素,显得越来越绚丽多彩。特殊地理环境也使道路方向性随之确定,于是远远早于先秦的“蜀·身毒道”在云南400个新石器人类的脚下自然就有了雏形。最终,“蜀·身毒道”发展成秦汉博南古道,博南古道发展成抗日战争时期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发展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320国道,320国道发展成现代的杭瑞高速公路、铁路、资源输送管道等。
不追溯道路的历史,云南的故事很难讲;没有道路的云南历史,割裂的山水就会割裂远古的历史。道路不仅让云南的山水互通互联、来脉清晰,还让云南的人文经络凸显。
第一个专题考察博南道的人
乔治·沃尼斯特·莫里循是近代来到中国的人物中,与中国关系比较密切、在中国取得较大名声和影响的记者、旅行家、藏书家。他亲身经历并向西方世界报道了中国的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俄战争、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等重大事件,所以早期是一位著名的记者。1912年~1920年期间历任北洋政府四任政治顾问,以至于袁世凯一度把莫里循府邸所在的北京王府井大街命名为莫里循大街。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收集了主要关于中国的书籍、报刊和地图等资料两万四千余册,被称为东方学“莫里循文库”。
1894年2月,莫里循从上海出发,到达重庆之后,离水上岸,从四川宜宾进入云南,通过昭通、东川、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后抵达缅甸八莫、曼德勒、仰光,最后再转水陆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记载了张骞发现中国与印度之间的道路,被称作“蜀·身毒道”。这条道路把四川的物资通过印度中转,输送到了大夏(现在的阿富汗一带),再从大夏往更远的欧洲非洲输送,所以“蜀·身毒道”被概定为一条远古的民间国际商道。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又出现了汉武帝寻找“蜀·身毒道”、开凿博南山道的记载后,博南道的概念便据此出现,“蜀·身毒道”的总体称呼逐渐淡出。在历史典籍和现实生活中,人们常用“朱提道”“盐津道”“灵关道”“五尺道”“永昌道”“博南道”等地域地段名称的分段称呼代替最早“蜀·身毒道”整体叫法,也等于用逐渐明晰的行政辖区分解了整条原始道路的整体意向。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最早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他的《中国》一书,把“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道路”称作“丝绸之路”,这一名词被广泛认可并使用。到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家郝尔曼出版了《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把李希霍芬提出的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在此基础上,有人又把丝绸之路作了南北之分,张骞踏空开辟的河西走廊称作“北方丝绸之路”,他分析发现的“蜀·身毒道”也就成为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最早存在形式。关于“南方丝绸之路”,有很多有记载有名气的路段,这些路段因为客观上相连相通,所以逐步被打包固定下来,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固定特指。目前,认可度最高也最常见的“南方丝绸之路”有两个起点,一个是成都,一个是宜宾,当然成都和宜宾之间在古代也是相通相连的。以成都为起点的统称“灵关道”,经过邛崃、芦山、雅安、荥经、汉源、石棉、甘洛、越西、喜德、西昌、德昌、会理、永仁、元谋、大姚、祥云;以宜宾为起点的“朱提道”通过盐津、大关、昭通、威宁、会泽、宣威、曲靖、昆明、禄丰、楚雄、南华、祥云。东西两线进入云南,在大理祥云县汇聚成“博南道”。“博南道”经过祥云县、弥渡县、巍山县、大理市、漾濞县、永平县后,跨过澜沧江,进入永昌道后,至少又分为三条线路出境出国。故大理境内的“博南道”成为“南方丝绸之路”上唯一没有岔道的枢纽地段。由于“博南”原始词根有“博达南方”或“博览南方”的意思,与“南方丝绸之路”的内涵相近重叠,所以有时出现二者在称呼上有互代互替的现象,有的专家在画“南方丝绸之路”线路图时,直接以“博南道”作为名称加以标注。
莫里循陆路出发地、行程、目的地,与南方丝绸之路“朱提道”在线路上和意义都高度重合。所以莫里循到云南的这次考察成就了书作《1894——中国纪行》,书中突出了两个考查察主题,一个是关于长江上的航运,另一个便是南方丝绸之路。全书二十三章,后二十章都是有关南方丝绸之路的记述。由此可以说莫里循是专题考察南方丝绸之路的第一个人,他的《1894——中国纪行》是一部隐形的南方丝绸之路游记,因为单看书名,似乎很难看出与云南及南方丝绸之路有多大关系。
真正的“雪糕”
1894年4月,乔治·沃尼斯特·莫里循来到了大理,在他的著作《中国纪行》中,用了三个章节的文字记述呈现出一个我们想象不到的大理和美丽的洱海。
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三小时后我们到了大理。沿着一条被无数脚步打磨得光光滑滑的宽阔石板路进城。一条条溪流从山脉上穿越多石的溪床流入湖泊,溪上架着数不清的石桥,都是用雕琢的石头砌筑的,许多厚石板都是长达十八英尺的刻凿整齐的花岗岩。一个路边小摊在卖上乘的雪糕,那可是真正的雪糕,把雪在碗里压紧,再加上蜜糖,一文钱一块,相当于一便士可以买三打。”读到关于“雪糕”的这段文字,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享用过大理“雪糕”的味道,或者多少人听到过它的故事,而我从中感觉到的是那时苍山洱海的纯粹和美好不但可以及目所望,还可以用一文钱品尝到。早在明朝,就有诗人留下《卖雪词》:“双龙关里百花香,银海逶迤抱点苍。六月街头教卖雪,行人错认是琼浆”。清朝张泓编纂的《滇南新语》中有一则《卖六月雪》的描述:“点苍山距大理西,长百里,有峰十九,涧三十六。最高曰‘太和’,顶有池,广数十亩,龙窟其中,祷雨辄应。池旁生交河菜,类菜味辛,采者须屏息,稍有声,冰雹立至。山亦不甚高峻。至菊节后,两峰已积雪,迄夏始消。土人及时取雪藏阴岩间,届六月,卖于驿亭。雪每碗一文,微加蔗糖于其上。余偶过,必买数碗。虽未及齿,已寒沁心脾矣。”张泓解释了大理晚秋时节飘落的雪在来年六月成为雪糕售卖的过程,从中可以窥见“苍山雪”因为成为了一种博南古道驿亭上的商品,便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延展,早已声名远播。所以它成为现在大理“风花雪月”四景品牌之一,应该还是和道路强大持久的传播功能分不开。顺延“苍山雪”品牌陈酿的故事,同样可以找到“洱海月、上关花、下关风”等诸多历史典故的精底板素材。大理,无疑是整条南方丝绸之路文化的时空聚落,就如著名人文学家费孝通所说的“北有敦煌,南有大理”。古今中外的过客们关注或是记载下来的街头小吃“六月雪糕”,今天看来恐怕就是我们的一种乡愁追寻。现在的大理街头,依然有雪糕,但传统意义上的雪糕里的“雪”已经被苍山逐年升高的雪线没收了。在这种时候,苍山雪线的话题会自然而然地让我们想到洱海的水线。陈鼎《滇游记》有一则叙述:“云南县古名洱海,县南二十五里有水目山,梵刹容众千余”。沧海桑田,往往不是我们想象着的那么久远,我们自己见证几十年的人文或是自然况景,都会有面目全非的感觉,更何况在几百年、几千年的时间力量面前,一切皆有可能。数千年前,现在的祥云所代表的应该是它及其周边广阔的一片碧海,那时汉武帝派出寻找“蜀·身毒道”的使者到达后,就有“汉习楼船”的故事发生了。而现在祥云坝子干旱的现状下,很可能掩盖或是误导了他本真的许多水域故事。所以,古代到现在无论清晰还是一些模糊的演变史,给我们的不应该仅仅是故事,还应该是启示:苍山的雪线与洱海的水线是一对孪生姊妹,无论什么时候她们都有着无比细微和紧密的感应,她们在升高沉降之间,呈示着大理主人的姿态,只不过这种姿态高雅得不声不息而已。洱海永远望着苍山在长高,欣赏洱海的碧波万顷时,关注苍山的雪期和雪线更是一种深邃可持续的真爱。
“繁荣的村落装点着平川,土地肥沃,阡陌纵横,路边围着篱笆。左边是城墙围着的赵州城,右边远处是大理的巨大湖泊,湖对岸衬着折叠起伏的山峰,山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山高出湖面七千英尺,湖面本身的海拔也是七千英尺。”这样的文字意境,与当时那一个没落的时代背景有极大的反差。而这样的意境,在莫里循笔下的大理随处可见:“两个关口之间相距一天路程,共有三百六十个村庄,各自处于自身的林地中,村中央都有一个飞檐峭壁的漂亮的白色寺庙。洒满阳光的湖面上漂浮着一只只忙碌的打渔船”,“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大的几个商队旅馆就在大理。”
乔治·沃尼斯特·莫里循到中国后,取得了显赫的身份,被称作“鞠躬尽粹,死而后已”的中国总统顾问和中国的北京人,这与他参与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动荡沉浮有着密切关系。但他笔下的洱海是恬适的,是那种没有任何历史事件可以打乱的自然秩序。在一直坚持寻找大理的时空线索的过程中,我发现,追寻洱海的线索可以把大理甚至云南带到秦汉、大唐、古罗马时代,洱海也可以把大理甚至云南带到亘古甚至未来。所以我在乐此不疲地欣赏着曝巫求雨时代的洱海时,居然察觉到在中国被世界抄底的那个纷乱年代,洱海就已然波澜不惊地淡定,因此臆念中洱海似乎隐喻着某种神性,甚至于那段历史纷扰的心思瞬间得到慰藉。当然除了很多关于大理恬适的文字让我们感到惬意舒服外,还有关于大理过去繁华的描写,让我们对大理的未来充满憧憬。
莫里循的文字是这样赞誉大理的:“见过的最大的几个商队旅馆就在大理。其中一家属于地方,由官府管理,给穷人提供便利,所有利润也充作救济基金。旅馆里有几间杂货铺,摆满洋货和缅甸进口的商品,还有广州商人带来的西方日用品和小饰品。价格出奇地低。我买了‘挤奶妇牌’炼乳,相当于七便士一听。”大理历史上的繁华可以从“最大的几个商队旅馆”“摆满洋货和缅甸进口的商品”“广州商人带来的西方日用品和小饰品”这些其貌不扬的文字看出来。假如没有看到过类似于这些文字的叙述记载,我们的想象力一般都会停留在“现在的大理够好了,过去不可能有现在繁华”的固势思维中。一百多年前,在大理的驿道上,马帮行人络绎不绝,“有些明明白白是欧洲人,有些清清楚楚是印度人,还有云南土著、西藏人、广州商贩和四川苦力。”在莫里循的旅程中,云南的古道显然已经是一个国际化的中国后方街区,他遇到的各类事件、各色人种、用的钱也有各种币种、各类东西方的信仰表现等,看似有界线区别的事物杂糅在一起在古道沿线已经是一种常态。他们明显不同,却又自然而然的在大理摆放在一起,没有发生过实质上的冲突。
也许这些就是云南开放、接纳、融合、和谐的民族文化蕴制秘笈:一条路走出来,一条路开挖出来,一条路延续下来,本身依靠的就是汇聚人流、输送一切的功能,不可能排斥拒绝路上来往的任何东西。无论东来西去的行者,还是等待行者到来的人们,他们的希望都寄托给了道路,反之道路上的一切都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云南成为全国民族成分最多、跨境居住民族最多省份,究其原因,可能最本质的就是云南人接纳、开放对待外来者这种非常现实的生存之道。
事实上南方丝绸之路博南道在历史上给大理带来过巨大的实惠,人流、物流、财流通过博南古道在这里聚散,就意味着政治、商贸、经济的繁盛,一个地方哪怕是一时的繁华也会留下永久的记忆,何况洱海流域所代表的大理,几千年的道路文化沉淀下来的自然就是一种思想上开放接纳、生活上麻辣酸咸兼具的特质。研究或借鉴这种文化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它本身的方向性,比如东西南北来来去去汇合在一起就容易造成方向迷失,但大理文化在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的构架下,从来都是心向中原,门对东南亚南亚。就是本书《中国纪行》的翻译者李磊,也应该是被莫里循的这些关于大理的文字意境和附着信息所动念,才翻译了莫里循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位大理人。130多年前记录下来的大理洱海,无论如何都会让大理的现实显得更加值得珍惜。当然出于对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目的,莫里循在《中国纪行》一书中有大量的文字是有关道路、马帮、脚夫以及邮政制度和票号的内容。特别是关于马帮的大量信息,一定是值得归类、存档、分析、利用的。大理是“亚洲文化十字路口”,“十字”是个地理上交叉汇合的概念,放到任何一个历史洪流的现实中,则是一个多元选项的概念。历史的方便之处在于可以定论,但历史之下的地域可以借鉴历史来驱动现实。一旦历史的驱动力被漠视,那现实的奋斗无论何时都会显得无奈和软弱。一旦历史的驱动力被重视,最起码现实的努力方向就会准确无误。马帮文化及其所附着的信息是云南道路文化的根本,它可以回答甚至解决那些一直纠缠不休的现实问题,比如云南26个民族多元交融的动力、诸多考古发现中的域外现象、海贝经济圈形成原因等等。
美妙的锣声
“接着又向上攀爬了一段路。我们现在置身于‘云之南 ’的云南(在四川则总是处于阴云之下),阳光和煦,空气干燥而凉爽。一串串矮种马从我们身边擦过,通常每一串有八十匹马。所有的马都驮着沉重的铜和铅,都被套上嚼子以阻止它们吃草,马匹迈着像山羊一样敏捷踏实的步子,走在满是台阶的岩石路上。美妙的锣声为马队打着节拍,回声响彻四面群山。许多马匹身上装饰着红布和羽毛,还有白腹锦鸡的尾羽。这些是官方的货运马帮,可以无须检查,免费通过厘金哨卡。”这段文字是莫里循《中国纪行》第七章《叙府到昭通,云南省概观——中国的脚夫、邮政制度和票号》的内容。我们撇开盛夏天气里的云南“阳光和煦,空气干燥而凉爽”中客观无意地表达云南“四季如春”的可爱气候外,那一队满载货物的八十匹马的阵势就值得大胆地放开思维去想象:八十个活物运输队伍,矫健有序地行走在古道上。不妨用八十辆的车队做一下对比,单是秩序维持、速度统一都是一个繁杂的流程。但是云南的马帮千百年运行下来,已有一个成熟安全的运作体系规程,围绕其中提到的嚼子、锣声、红布、羽毛等展开,这些都是古代运输业一些十分专业知识,也是一些极具云南特色的故事。其中的锣声指的是赶马人敲击铓锣的声音。铓锣是马帮的喇叭,一般一队马帮有一位赶马人负责提带并敲击,其声音在山谷间穿透力强并传得远,用来通知对头马帮让路和驱赶虎豹豺狼。装饰有红布羽毛的马匹,是头骡、二骡、尾骡。云南的马帮概念,其实包括了马、骡、驴、牛等驮力,提到运输队伍时都以“马帮”概全。真正意义上的马帮少不了骡子。最小的马帮要有五匹骡马,赶马人称“一手”,其中走在最前面称“头骡”的一定是骡子。因为骡子生性温和聪慧、能与人交流沟通、意会能力强,头骡有包括红布、羽毛、镜子、缨须、大铃等一整套配饰。二骡、尾骡也有一些配饰,但不如头骡的气派。头骡脖子下挂两个硕大的响铃,二骡尾骡都挂着一串铃铛,叫“二叉”。莫里循所说的“美妙的锣声”应该包含着头骡的大铃声、二骡尾骡的“二叉”声,因为只要马帮在行进,哐啷哐啷的大小和聲一定有节奏地一直响着,而铓锣声则是间歇性地敲响。这声音不仅仅好听,还是马帮行走停歇的指令信号。当两队马帮的骡听到对面有马帮过来时,都会各自判断所处位置是否能够让路,如果道路宽敞,头骡会自觉停下,二骡也就跟着停下,尾骡听不到头骡二骡的铃响也就会停止前进,如此整队马帮就会停下来了,迎面而来的马帮听到对面停下来了,便会继续前行。这个如同“错车”的过程,几乎依靠头骡二骡尾骡的反应进行,规模越大的马帮越是如此,因为每五匹骡马才有一个赶马人,行进中无法每匹马都进行招呼照顾。
“数以百计的驮马运载着普洱茶在路上与我们相遇,同时一整天都有负担着沉重的瓷器蹒珊跋涉的一串串苦力经过我们身边。他们的方向跟我们相同,都是向着大清国的边境而去,把茶杯、碟子、杯盖、调羹和饭碗带到各处,在中国的每一个客栈里都可以见到这些东西。大多数瓷器都是从江西运到全国,江西的自然资源似乎使它在瓷器业中几乎处于垄断地位。贸易量非常巨大。在江西景德镇的邻近地区,爆发太平军叛乱的地方,有超过一百万的工匠受雇于瓷器制造业。茶杯、碟子之类,由苦力背负好几百英里,运到如此遥远的中国边陲,售价比原始成本高出三四倍。”(莫里循《中国纪行》第十章从昭通到东川之旅)
在很多人眼中,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是个虚构的概念。因为北方丝绸之路的驼队在茫茫黄沙背景地衬托下,已经越来越光辉耀眼。而南方丝绸之路的马帮在沿途茫茫森林背景地湮没下、在现代文明的节奏挤压下,快速隐退,已经快要无影无踪。
我自己曾经在“南方丝绸之路高峰论坛”上,好多次被质问“南方丝绸之路运输的货物是什么”之类的问题,质问者始终不信南方丝绸之路曾经的繁华喧嚣。在他们看来,一直封闭、蛮荒的云南,不可能一直存在着一条与世界沟通往来的国际通道。在他们的思维中,只有西安一样的古都、玉门关一样的古关才代表着昔日的兴盛和重要。好在对这样的问题我已作了很多思考,查阅的史籍实证很多,对于回答与不回答、如何回答都有选择的余地。比如我可以回答:“只要是货物,只要我们能想到的东西都可能在南方丝绸之路上运输,甚至我们想像不到的东西也可能在这条古道上流通过。”比如信息文化、流言传说、国家建制、边防安全、战争需要等等,这些递送的方式和线路根本没有其他的方式选择,唯一依托的是道路。数千年来,云南的道路体系,主干道有且仅有南方丝绸之路一条,所以路上的承载已经不仅仅是货物了。《中国纪行》一书中,把作者观察关注到的道路繁忙与丰富记录下来,成为了故事性的史料。以上引用的文字甚至还提到了货源、利润等,就更深层地说明这条道路存在的理由了。莫里循上路是在1894年,是清王朝没落时期,南方丝绸之路依然如此热闹繁华,要是在盛世朝代或是某个太平时期,这条道路的运载能力和作用,一定会更加超乎我们的认知和想象。
莫里循一路遇到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让他目不暇接。旅程中的一路风物已经随着时代的步伐成为过眼烟云。幸运的是,在书中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作者要想向他那时的西方朋友打卡晒圈的心情,尤其是一路陪伴依托的马和遇到的马帮。
“这是一匹大骨架、毛茸茸的牲口,非常聪明,我被授权卖掉它,连同马鞍和笼头,卖四英镑。像大多数中国骡子一样,它的前腿上有两个鸡眼,据说它因此能在夜间视物。每个华人都认为,骡子具有如此不可思议的能力,是由鸡眼这对后天眼睛赋予的。”“我在云南城卖掉了骡子,又买了一匹白色的矮种小马,连同马鞍、警头和铃铛,一共花了三英镑六先令。做这笔买卖时,我逆转了一个华人就要做成的交易。骡子是比马更温文尔雅的动物,它在旅途中更精神,脚步更稳健。中国人说,如果马的一只脚打滑,另外三只也跟着打滑,而骡子呢,即使三只脚打滑,也会用第四只脚站稳。”
莫里循在云南旅途中捕捉到的只言片语,看似零碎难以理解,实质上却使云南系统的马帮文化显得真实而生动。我们小时候,总觉得能够在夜里行动的动物很神奇,其中家里的骡马就是一类,大人们给我们解释说它们有“夜眼”,所以在夜里能够看得见。关于马和骡子,很多人分不清楚。云南人总把驮队说成是马帮,这就误导了很多人,认为古道上的驮力都是马匹。事实上马与驴交配生产的后代称“骡子”,而且一定要是“驴父马母”才是骡子,反过来就叫做驴骡,骡在近亲马、驴、驴骡中表现是最优秀的。俗语说“上坡的驴儿下坡的马”,骡子兼具了马的灵性、驴的韧性、驴骡的灵活性,再加上自身的温和,才让人们选取骡子作为马帮的领队、押队。莫里循说“骡子是比马更温文尔雅的动物”,是从他的角度叙述了我们小时候听到的故事,也是云南赶马人的生活。至于说马匹的交易,本身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上的一种常态。不仅如此,在古道沿途还形成了一些有名的骡马交易市场。大理的“三月街”市景之一就是赛马选马易马。
“当晚睡觉前,我去看看我的骡子被喂养得如何。它站在地下楼梯脚的畜圈里,面前有一个大马槽,尺寸和形状如同中国棺材。它安安静静像在沉思。发现我时,它责怪地看看料槽里切得乱糟糟的稻草,再看看我,好像明白地在问,对于它这样一匹昂扬的骡子,驮着我这样一个高贵的人,翻山越岭,跨溪过涧,走过陡峭的山崖和崎岖的小道,在温热的阳光下奔走了漫长的一天,这样的饲料是不是合理。哎,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它,除非把缝在草褥里的没切碎的干草给它。它面前的草就是中国人的饲料,切成三英寸长,切草的工具是枢轴安在木板上的长刀,就像文明国家的烟草刀。它不得不满足于这种草料,否则什么也得不到。”“晚上,老黄说,骡子病了,必须请一个兽医。兽医蹊跷地迅速赶来。他拉开架势,那架势我曾见过,有几个在澳大利亚的中医,给同属人类大家庭的患者诊病时,就是这副做派,只见他摆出揭开未来秘密的深奥莫测的样子,给骡子做检查,然后收下小费走了。后来一篮子药送来了,里面装着杂七杂八的草药,至少其丰富程度可以让人期望能产生效用。”
莫里循对骡子的关切,从骡子眼神中看到的表达内容,以及流露出来的哀怨情感是会存在的。用中国人的话说,马是最有灵性的动物,也是最能吃苦耐劳的动物,故有“龙马精神”一说,“龙”为高维境界在天上,“马”代表实干在地上,龙马精神实为精进完美形象。云南有一句谚语:“驮死的马儿吃稻草,闲死的猫儿吃白米”,道出了人们对骡马的同情。赶马人喂马是有讲究的,晚上喂的叫夜料,一般是草料,稻草作夜料已经不差了。豆料、面麸、红糖等一般只有在上路前或者是路途中喂,也称作“加料”。另外,莫里循看懂了中国的骡子,却不一定看懂中国的中医,所以文中他把中医的一套看病方法说成是“架势”,把马药称作是“杂七杂八的草药”,显然就是不懂“望闻问切”的流程和配藥的本事,但毕竟他记录了人们对待骡子的一种态度。赶马人是马帮时代的信息群体,他们赶着马帮前行的同时也赶着社会文明在前进。他们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团队,领导者是“马锅头”,还有“马二锅头”,他们不仅有着严密的组织方式,也有许多规矩。在组成的人员中,有许多各有所长的马脚子,有的以力大著称、有的善于使用马掌刀、有的善于赶马调、有的善于看马病配马药。莫里循的马队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马帮,但马帮走的路和经历的过程他都体验了。
“快到黄连铺的时候,我的马掉了一只马掌,我们发现时已经掉了一些时间了。幸好我带着半打备用马掌,而且很快就有一个赶骡子的人走了过来,他把马掌钉得如同出自铁匠之手一样精巧,然后高兴地接过半便士的报酬。他钉马掌的时候,把马蹄后面的毛和马尾绑在一起,以保持马腿的稳定。”黄连铺是自古以来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铺”的概念代表着官方管理路道的机构。古代道路“五里一亭,十里一铺,三十里一驿”是官道格局,这些亭铺驿所都是道路养护保通机构,相当于现代交通的服务区加油站。黄连铺是博南古道过了顺濞河就要登上娘娘叫狗山的一个补给点,现在是永平北斗乡的一个行政村,因这里生长有古老巨大的黄连树(学名楷木)而得名,历史上非常有名,在博南古道上行走的大家名士在这里大部分都留下诗词文字。如今博南古道虽然沉寂,但像黄连铺一样的古道设施和名称,基本还保留完整。博南古道在永平县东段的黄连铺、北斗铺、新北斗铺、天井铺、梅花铺大多发展成村落或是文化遗迹。这一段博南古道也是许多逸闻趣事、典故史籍比较丰富的道路。黄连铺有杨慎“老羊(杨)茴香(回乡)”的故事,北斗铺有诸葛亮迷途、观音娘娘叫狗引路的传说,天井铺有林则徐在万松庵作出“风吹罗汉摇(姚)和尚,雨打金刚淋(林)大人”的绝对后施财建庵的记载,梅花铺则有文人骚客的题壁诗存留。莫里循到了黄连铺,遇到并记载了一个马帮行进中的细节——钉马掌。马帮团队具备的组织性,必然使得成员间有很细的分工,任何一个工种环节上都会有许多绝顶高手,他们身怀绝技,独当一面。比如说钉马掌的活路,看似简单,但却是马帮能否顺利行进的重要一环。马掌就像现在人们在山路上行走时的鞋子,跑步运动员的跑鞋,离开它基本不能行进。马掌在驮畜的蹄子上起到保护和防滑两个作用。驮畜负重,每一步都在用力蹬行,如果不依靠铁质马掌着地,那么马蹄在很短的时间就会被坚硬的路石磨伤磨坏。马幫在上坡下坎过程中,马蹄与石头之间必须扣得紧、扣得牢,才不致于发生马仰驮翻的事故,这也只有靠马掌把马蹄与路石之间吃紧吃牢。马掌作用的发挥全靠马掌钉的好坏。钉得好既牢固又不伤马蹄,钉不好既会伤到马蹄,又会很快脱落,致命的是一匹马的马掌问题会影响整个马帮的行程速度。所以一个马帮的马掌师傅,手艺要好、工具要齐。工具分为“公母割刀”、既能起钉又能敲钉的两用铁锤,少一样都无法操作。手艺包括割蹄技术、钉掌技术。割蹄关键是要稳准狠,要割得平,钉掌时不能深也不能浅,钉深了驮畜直接落帮,钉浅了马掌很快脱落。钉得好的马掌一定是被磨烂都不会掉。好的马掌师傅随时会观察整个马帮马掌的情况,他会根据马匹走路的姿态看出马掌是否需要除旧换新。
“一整天我们都遇见从缅甸过来的运棉花的马帮。还隔着几英里,马帮的锣声就在沉寂的山间回响,很长时间之后,才听到马铃的叮当声,不久就出现了驮着大包棉花的马匹和骡子,最前面的一匹,扎着红缨和雉鸡的尾羽,最后一匹驮着马帮头子的鞍麟和被褥,以及魁梧的、高高在上的马帮头子本人。总有一个手持铜锣的人在前面开道。每五匹牲口有一个人负责赶。在河床沙地上,有一个马帮在休息。他们的包裹一排排堆放着,马在山坡上吃草。我数了数,单是这个马帮就有一百零七匹马。”“每天有五十到一百匹驮运物资的骡马渡过浅滩进入中国,大多运的是棉花。每匹骡马要征收六安那(Anna,旧时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辅币单位,十六安那等于一卢比)的通行费,这笔钱由政府分发给各个克钦诏法(即土司),那些人享有征收这项贡金的世袭权力。收钱由两名缅甸税吏负责,每天上交给军营指挥官。进入缅甸不收税。”
后 记
第一次读到莫里循的《中国纪行》是在2018年初,书是大理摄影博物馆馆长赵渝老师送给我的。他是在大理长大的重庆人。由于我们都对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感兴趣,所以很长时间以来相互影响,共享资源,他也是我一直坚持研究南方丝绸之路的鼓励者引导者之一。在《中国纪行》之后,赵老师又找到几本类似的书送给我,我也找到了一些。这其中有些书还没有翻译成中文,甚至还是手稿。在阅览到这些书籍时,对于我来说一直处于兴奋状态。因为在外籍作者的笔下,云南这条古老的道路不再是传说中和未发掘文物状态下的道路,那些刚刚涉足云南的作者们自己所持的好奇心、新鲜感是书中最有趣最有活力的内容,到现在则成为了难得可贵的文史资料。阅读经典大部分是启示人生,阅读史料大部分是启示社会。我个人喜欢阅读南方丝绸之路的相关书籍,是因为我从小生长生活在南方丝绸之路博南古道的氛围中,所以思维一直重复沿着南方丝绸之路的过去未来穿梭,得到的启示也就有些空泛。比如对最后引用的这几段文字,我总是会因为作者把缅甸与云南的往来叙述得很平常而感到着急,甚至是愤愤不平,因为这一类信息背后有着很多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对现实有着许多提示。应该说历史上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间往来和贸易往来就是现实中期望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一条国际通道在云南横亘几千年的结果,这种状态也是现实发展方向的一个引题、启示。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古老云南的开放之门早已面向南亚东南亚,早已形成常态、具备规模、具有秩序。古道上的马帮是常态、规模、秩序的具体表现。马帮的自由来往是常态化的体现,马帮的数量代表着货物运送的规模,马帮自身的管理和被管理体现着秩序。针对马帮收取通行费,说明道路通畅是需要管理的,而马帮的自我管理,从马帮的行头上可以看出来,比如文字里的铜锣、马铃、红缨、尾羽等看起来是些无关痛痒的物件,其实是马帮自我管理的工具。比如前面已经赘述过的铜锣,赶马人称作铓锣,是一队马帮的开道、警示器,马铃则是马匹自己交流的传声感应器,红缨尾羽等则是马匹身份地位的象征。把这些有关马帮行头的常识展开来研究分析,马帮团队其实就是一个组织严密、行头精细、层级分明、团结协作的商企单位。
莫里循旅程中也并非全是美好,包括他自己难以克制的殖民思想,以及对沿途落后人物事件的藐视和嘲讽。但作为我仅仅只把他的这本《中国纪行》当做南方丝绸之路相关信息读本,那他数落弱者毛病的世俗就被忽略了。阅读中我自然专注与我相关的内容,比如他结束长江的旅程从重庆开始步行,横穿云南直达缅甸,最终进入了印度。南方丝绸之路的史前形式就是张骞臆想的一个名称“蜀·身毒道”, “蜀”指四川,“身毒”是印度古称,这两个起始点之间隐匿着云南和缅甸,因此莫里循的这次行程就是完整而古老的“蜀·身毒道”。并且书里的章节布排、重点突出、风物凸显也都与古道自身的客观线索基本上重叠一致:历史最早的盐津古道、灵关道和朱提道交汇的祥云古道、博南古道上世界最古老的霁虹桥、高黎贡山上的路段等等,这些在书中都给了重点描述。当然可以反过来看,作为初次在古道上行走的莫里循,是这些重要的古道遗存让他有了自然而然的文字记述,而一直行走在古道上的我,依然如此。